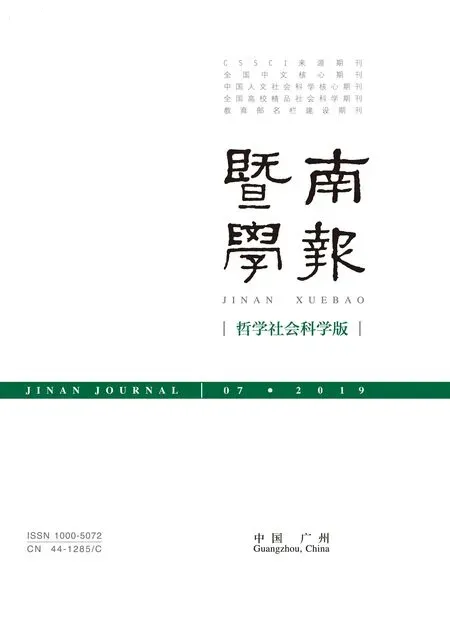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立法问题探讨
——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七百七十九条为对象
柳经纬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二审稿)第七百七十九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条规定是否意味着我国法律将一改过去不承认违约精神损害(非财产损害)赔偿的态度,承认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法典应如何规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等问题,值得探讨。
一、态度暧昧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七百七十九条
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实质是将精神损害纳入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合同当事人可以直接通过违约之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因此,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不能等同于违约造成精神损害的赔偿。后者可以通过违约之诉实现,也可以通过侵权之诉实现,通过侵权之诉实现的精神损害赔偿不属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而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
尽管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在比较法上已经得到许多国家(地区)法律不同程度的确认,我国理论界也不乏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积极主张者,司法实践中更是多有支持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案例;但是,我国现行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性司法解释并不支持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最能体现这种态度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发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和2010年发布的《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前者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言下之意,如果物品所有人提起违约之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则不予支持。后者的规定就更加明确:“旅游者提起违约之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变更为侵权之诉;旅游者仍坚持提起违约之诉的,对于其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不难发现,《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七百七十九条从其行文来看,其针对性十分明显。该条中的“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针对的是上述两项司法解释所强调的人民法院不支持原告在违约之诉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态度。而且,从该条使用“违约责任”一语来看,似乎也表明受损害方在提起违约之诉时,不影响其将精神损害赔偿作为违约责任来主张。由此看来,这似乎表明《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是承认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
然而,情况似乎并不十分明朗。首先,《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七百七十九条所处的位置是“人格权”编(第三编),而不是“合同”编(第二编)。《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二编“合同”关于违约赔偿责任的规定(第三百七十四条第1款)延续的是《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1款的规定。虽然《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1款规定的“损失”在文义上并没有排除精神损害,但从精神损害赔偿通常由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看,其所谓“损失”应解释为财产损失,而不含精神损害。我国民法学界也大多作此解释。这也是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强调当事人需另行提起侵权之诉的原因所在。如果认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1款、《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三百七十四条第1款之“损失”已经包含精神损害,那么《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七百七十九条就变得多余了。因此,如果以为《民法典分编(草案)》第七百七十九条表明我国民法将承认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那么这种结论为时尚早。其次,《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七百七十九条被安排在“人格权”编第一章“一般规定”。该章共12个条文(第773条至第782条之一),7个条文是关于人格权保护和人格权侵权责任的规定。第779条之前后6个条文规定的均是人格权侵权责任。从法条之间的逻辑联系来看,如认为第七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是违约责任,理由似乎不够充分;如对第七百七十九条作侵权责任的解释,似乎更为合理。再次,《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七百七十九条中的“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也可以理解为,受损害方在提起违约之诉因受第三百七十四条第1款之限制无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这不影响其另行提起侵权之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如果作这样的理解,那么第七百七十九条与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态度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七百七十九条的态度是不够明朗的。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七百七十九条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所持的暧昧态度固然可以通过法律的解释使之明确,但这将徒增法律适用的麻烦。法律贵在明确。法律如果能够对所涉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将有利于法律的遵守和司法的运作。除非不得已,法律应对所涉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因违约造成精神损害的赔偿问题上,《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七百七十九条既然已经明确了“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即肯定了受损害人有权就相对人的违约行为侵害其人格权造成的精神损害请求赔偿,那么就应当在民法典合同编之“违约责任”中作出明确规定,而不应安排在人格权编中,更不宜采取“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样态度暧昧的文字。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前述司法解释表明,在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该不该赔的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的基本态度还是明确的,应该赔。只是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如果原告人提起违约之诉,将精神损害赔偿作为违约责任来主张,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如果原告提起侵权之诉,将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侵权责任来主张,人民法院则应予以支持。因此,这里所涉及的只是程序性问题,而不是实体性问题。笔者认为,在《合同法》未明确规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通过程序性的安排解决违约导致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是为了保持与《合同法》的一致,这一程序性安排具有合理性。但在编纂民法典的背景下,仍然坚持这种程序性的安排就不具有合理性。在民法典编纂的背景下,应当在合同编作出明确的规定,从实体上解决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问题。
法典是有序的立法整体。在民法典合同编规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较之在人格权编规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更符合民法典内在体系的要求。
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不应以侵害人格权为必要条件
依据《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七百七十九条之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的条件之一是“损害对方人格权”。依《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以及《民法典分编(草案)》第三编“人格权”的规定,人格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以及一般人格权(人格尊严)。因此,依据《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七百七十九条的规定,在确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时,首先必须确定上述人格权中何种权利受到违约行为的损害,如不能确定当事人的何种人格权受到违约行为的损害,那么即便发生精神损害,也不在违约赔偿责任范围之内。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精神损害是否只存在于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场合?是否存在人格权未受损害但存在精神损害的情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七百七十九条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限定在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场合,就是不妥当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民法典分编(草案)》第七百七十九条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所作的限定也就无可厚非。
所谓精神损害,即精神痛苦,泛指人在心理上感到难过或不愉快而表现出的一种复杂的情感,包括悲伤、失望、压抑、焦虑、不安、恐惧、愤怒等。这种不愉快的情感状态,如因他人的不法行为所致,受损害人依法有权请求行为人以金钱赔偿其精神损害。这就是精神损害赔偿。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因他人的不法行为导致的精神痛苦,并不限于人格权受侵害的场合;使不法行为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也不以原告的人格权受侵害为条件。许多得到法院支持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并不都属于人格权受到侵害的情形。例如,在“戴西琴、戴爱国、戴爱民、戴西民诉延安市殡仪馆殡葬服务合同纠纷案”中,被告延安市殡仪馆未尽遗体保管义务,致使原告父亲遗体腐烂,法院支持了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该案显然不存在原告人格权受侵害的情形,但法院认为被告未履行合同义务“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商丘市殡仪馆与轩慈真、张久和、张武杰等赔偿纠纷案”中,张文魁(原告轩慈真之夫,张久和、张武杰、张俊杰之父)死后骨灰盒存放在被告之处,后因骨灰盒丢失引起纠纷。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将其家属骨灰盒交与被告保管,并交纳了一定的保管费用,双方已形成保管合同关系,因被告保管不善,致使张文魁骨灰盒丢失,给原告造成巨大精神痛苦,被告依法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保管合同的标的物被盗,同样不存在侵害人格权的情形。又如,在“程鹏诉紫薇婚庆服务社婚庆服务不到位应退还部分服务费和赔偿精神损失案”中,被告紫薇婚庆服务社因摄像机故障未能拍摄到婚礼重要场景的影像,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害也得到法院的支持。在本案中,被告未完全履行婚庆服务合同约定的义务,因摄像机故障漏拍了一些婚礼镜头,谈不上侵害原告的人格权。因此,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不取决于原告的人格权是否受到侵害,而取决于原告是否因被告的违约行为而发生精神损害。在人格权因违约行为而受到侵害时,原告人可以就其精神损害请求赔偿。在不涉及侵害人格权时,如违约行为也导致原告的精神损害,原告也应有权请求赔偿。《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七百七十九条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限定在人格权受侵害的场合,显然不妥。
这一点也可以从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得到印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是侵害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第二条规定的是侵害亲子关系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第三条规定的是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第四条规定的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述4条中,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均不涉及人格权侵害。尤其是第4条规定的“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如果从侵权的对象来看,侵害的只是物之所有权而不是人格权。例如,在“杜如辉、李红艳、马恒、刘冬梅与安康市中心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李红艳与刘冬梅2001年5月3日凌晨3时许在安康市中心医院产房相隔数分钟各产下一女婴,由于该院护士的过失,造成两家孩子抱错。再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由于被申请人安康市中心医院的过错行为,致使四申请人的两个孩子相互抱错,客观上给两个家庭的亲子关系均造成严重损害,给四申请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对此依法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本案中,原告受到侵害的只是亲子关系而非人格权,属于非人格权受侵害的情形。又如,在“郭秋实、张秀君诉辽宁世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旅游合同纠纷案”中,被告丢失了原告的护照,法院认为:“所丢失护照上的旅游签证及出入境记录,确如郭秋实、张秀君所述,是郭秋实、张秀君夫妻的情感经历的见证和宝贵的纪念物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故世纪公司应赔偿郭秋实、张秀君精神损害抚慰金。”在本案中,被告丢失了原告具有纪念意义的护照,所侵害的也不是原告的人格权。由此可见,即便是在侵权责任中,精神损害赔偿也不以人格权受到侵害为必要条件。因此,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也不应限定在人格权受侵害的场合。
之所以不应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限定在人格权受侵害的场合,原因在于许多合同本身就包含精神利益,合同中的精神利益应属于合同法保护的对象。与财产利益(物质利益)不同,精神利益是“以精神需求对象为实际内容的利益”。在法律上,基于一定法律关系而产生的精神利益,属于法律保护的法益的范畴。当事人基于合同关系而产生的精神利益,通过合同的履行得到满足,如合同得不到履行,当事人的精神利益就无法得到满足。合同中的精神利益应受法律保护。例如,在旅游服务合同中,经营者提供的旅游服务具有休闲属性,表现为消费者在旅游过程中处在一种自然、随兴、轻松、愉悦的状态,通过旅游可以达到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目的。消费者订立旅游合同的目的不在于获得财产利益,而在于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即精神利益。如果经营者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旅游服务,势必直接损害旅游消费者的精神利益,造成精神损害。又如,在美容服务合同、婚庆服务合同中,经营者提供的服务同样具有满足消费者精神利益的特点,消费者订立这些合同同样不是为了获得财产利益,而是为了获得精神利益,经营者违反合同同样会给消费者造成直接的精神利益损失。再如,在对特定当事人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的保管合同(如骨灰盒保管)或租借合同(如祖传物品的出借)中,标的物本身就承载着寄托人、出借人的精神托付,如保管人、借用人违反合同致使标的物毁损灭失,不仅仅造成财产损害(物的所有权丧失),也会直接给物品之权利人造成无法弥补的精神利益损失。上述这些具有精神利益的合同之违反给特定方当事人造成的精神利益损失,虽然不存在人格权受侵害的情况,也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将其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显然不合理。
三、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精神损害具有“不可逆性”,一旦发生,无论采取何种救济方式,都无法使受害人已经遭受的精神痛苦回复到如同没有遭受侵害之前的状态。法律所能做的只是在损害发生后通过采取一定的方式使受害人得到一定的精神抚慰。抚慰的方式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等其他法律形式。在刑事法律上依法惩治罪犯,对受害人同样具有精神抚慰的作用。在民法上,金钱赔偿无疑是一种较好的精神抚慰方式,它对受害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的安慰,还可以使其收到“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实际效果。
然而,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无论是在侵权法领域还是在合同法领域,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都采取谨慎、克制的态度,并非任何因他人的不法行为导致的痛苦或不愉快,都能够获得金钱的补偿。从有关法律规定看,对精神损害赔偿持谨慎、克制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适用范围的限制,强调精神损害赔偿以法律特别规定为限。如《德国民法典》第253条第1款规定:“仅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因非财产损害而请求金钱赔偿。”二是损害程度的限制,强调精神损害需达到“严重”程度始得请求赔偿。如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353条规定:“对违约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将不予支持,除非违约的同时还造成当事人身体受到伤害,或者违约行为极易对当事人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进而指出,“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也应采取谨慎、克制的态度,从适用范围和损害程度两个方面予以限制。有关损害程度的判断,因人、因事而异,应由法官根据具体的案情进行认定,在此不作讨论;需要重点讨论的是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关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应从合同利益和侵权法的实践两个层面来考虑。
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合同利益。合同利益基于合同而产生,通过合同的履行而实现,因合同的违反而受损害。合同法的宗旨在于保障合同利益的实现,于合同利益因违约受损时,使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给予救济。因此,如果合同本身存在精神利益,那么就有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如果合同本身不存在精神利益,原则上无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例如,在普通的商业合同(商事合同)中,当事人追求的是财产利益而不是精神利益,法律上自无给予精神利益保护之必要,因而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在判断合同是否存在精神利益的问题上,可以从合同的目的、合同的标的、合同履行带来的利益(或所避免的不利益)三个方面加以考虑。如果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某种精神利益,那么违反合同势必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此时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旨在维护合同的目的利益。旅游服务合同、观赏表演合同、宾馆服务合同、美容服务合同、婚庆服务合同、殡葬服务合同,属于此类合同。如果合同的标的物(如遗体、骨灰盒、祖传文物、珍贵照片)承载着特定方当事人的精神利益,那么标的物因违约行为而毁损灭失,势必使得特定方当事人的情感无以寄托而造成精神损失,此时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旨在保护特定方当事人存在于合同标的物之上的精神利益。对当事人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之保管合同、租借合同、加工承揽合同等,属于此类合同。在某些情况下,合同的目的不是为了精神利益,合同的标的也不承载当事人的精神利益,但合同的履行将给当事人一方带来精神上的利益或可以避免精神上的不利益,如不履行合同则会给当事人带来精神上的不利益,此时也应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以保护合同履行带来的精神利益。例如,加拿大法院曾经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律师未告知委托人其所代理的案件已经办结,致使委托人焦急地等待了六年,法院以原告的精神损害系被告可预见为由,判决成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在本案中,从合同的目的和标的来判断,均难以认定精神利益,但律师如履行合同义务,及时告知委托人案件办理结果,势必可以避免委托人长时期等待案件结果的焦虑,合同履行带来的精神利益显而易见。在客运合同中,承运人延误导致旅客在长时间的等待中引发的焦虑心情,也属于这种情形。2004年,我国国家民航总局发布的《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对国内航空公司因自身原因造成航班延误给予旅客经济补偿的指导意见(试行)》强调指出:“本指导意见所指‘补偿’措施,属在发生航班较长时间延误的情况下,航空公司主动安抚旅客、加强服务的措施。”航班延误补偿不等于也不能代替财产损失赔偿。此所谓“安抚旅客”,也表明航空公司给予旅客的航班延误补偿是对旅客因航班延误导致焦虑的抚慰。
其次,在确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时,应考虑侵权法在保护精神利益方面已有的经验。如果违约造成精神损害已经被纳入侵权法保护的范围,那么也应纳入合同法保护的范围。在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四种情形,包括:(1)人格权遭受侵害(第1条);(2)亲属权(亲属关系)遭受侵害(第2条);(3)死者人格利益遭受侵害(第3条);(4)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遭受毁损灭失(第4条)。在实践中,上述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四种情形既可以存在于单纯的侵权之中,也可能存在于违约之中。例如,酒店违反合同提供不卫生的食品导致消费者的健康权遭受损害;医院违反医疗合同致使新生儿被抱错导致亲权(亲子关系)受损害;殡仪馆违反殡葬服务合同致使死者遗体损毁;保管人或租借人违反合同致使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标的物毁损灭失。在违约情况下上述四种权利被侵害导致精神损害,应当纳入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
在上述两个层面上,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虽有交织,但不尽相同。交织的情形,例如在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物品的保管合同中,因保管人的违约行为致使物品毁损灭失造成保管合同的寄托人(也是物品的所有权人)的精神损害,既属于合同中精神利益损失的情形,也属于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的情形;又如在美容服务合同中,美容手术失败造成消费者容貌的毁损,既属于合同中精神利益损失的情形,也属于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1条规定的健康权或身体权受侵害的情形。然而,在某些情形下,违约造成合同精神利益的损失,并不属于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例如,在婚庆服务合同中,婚礼现场播放哀乐;在殡葬服务合同中,葬礼现场播放喜庆歌曲;在观看演出合同中,演出机构撤换演员或演出节目,均不属于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合同履行带来的精神利益也不在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之内。
综合上述两个层面的因素,笔者认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应确定在以下四种场合:一是如果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一定的精神利益,那么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导致他方的精神利益无法获得满足,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精神损害责任;二是如果合同的标的物承载着当事人一方的精神利益,标的物因违约行为导致毁损灭失,违约方应承担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三是如果合同的履行将给当事人带来一定的精神利益,其势必造成当事人精神利益的损失,违约方应承担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四是如果违约行为致相对人的人格权、亲属权(亲属关系)遭受侵害,违约方应承担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四、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建议
在法律制度构建上,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实质是将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从财产损失扩大到精神损害,而不是在违约损害赔偿制度之外另行构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因此,在立法上,应当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违约损害赔偿制度。关于违约损害赔偿,《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这一规定确立了违约损害赔偿的两项原则:一是损失与违约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二是损失的可预见性。上述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四种情形中,前三种情形的精神损害均为合同利益的损失,具有可预见性,将其纳入违约赔偿的范围,符合可预见性原则。例如,在旅游服务合同中,消费者参加旅游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享受,旅游经营者理应清楚,旅游经营者违反合同导致消费者精神利益的损失,属于订立合同时可预见的损失,将此精神利益的损失纳入赔偿的范围,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可预见性原则。在第四种情形,对违约造成人格权、亲属权受侵害而产生的精神损害给予赔偿,是否符合可预见性标准?答案也是肯定的。例如,上述“杜如辉、李红艳、马恒、刘冬梅与安康市中心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中,医院与产妇之间形成的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中,医院的义务既包括为产妇和新生儿提供医疗服务,也包括将新生儿确定无误地交付给孕妇夫妇的义务。由于医院的过错致使新生儿被抱错,侵害了孕妇夫妇的亲子关系,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属于“人所共有”的情感,这种情感的痛苦也是“人所共知”的,完全可以认定为医院于合同订立之时能够预见的损害。使医院对此承担赔偿责任,符合违约赔偿责任的可预见性原则。
理论上,可预见性原则的构成包含预见的主体、预见的时间、预见的内容和判断可预见性的标准。关于预见的内容,比较法上有类型说和程度说之分。类型说认为,只要损害的类型是可预见的即可,损害的程度或数额不属于应当预见的范围。程度说认为,损害的类型和损害的程度均应是可预见的。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精神损害属于情感的范畴,损害的程度常常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损害的程度不具有可预见性。因此,应以精神损害为合同当事人一方订立合同之时可预见为满足,而不应要求损害程度的可预见。
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违约损害赔偿制度,为确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固有的法律依据,同时也使得有关违约损害赔偿的规则,如因果关系、可预见性规则(《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1款)、过失相抵规则、减轻损失规则(《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损益相抵规则以及预定赔偿额(违约金)及其酌减规则(《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等,可适用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从而构建包括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的统一的违约损害赔偿制度。
虽然《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1款之所谓“损失”在文义上并没有排除精神损害,在法律解释上也有将该条项下的“损失”作包括精神损害的解释的情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需对《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1款作出解释即可满足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需要,而无须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作出特别规定。鉴于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并不支持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也考虑到理论界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还存在不同的认识,有必要在违约赔偿制度内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专门规定。
当前,我国民法典编纂正在进行中,在合同编中规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合同当事人的精神利益提供法律依据,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在具体方案上,可以考虑在《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三百七十四条中增加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致使对方依据合同享有的精神利益遭受损害的,或者侵害对方人格权、亲属关系,造成对方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增加一款后,为行文的统一,《民法典分编(草案)》第三百七十四条应进行适当调整。调整后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三百七十四条如下: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三百七十四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致使对方依据合同享有的精神利益遭受损害的,或者侵害对方人格权、亲属关系,造成对方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民法典总则编即《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六条已经对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作出规定的情况下,在合同编中规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并非多余。因为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的意义在于在违约责任之外,为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提供多一种可供选择的法律途径,当事人可以根据案件争议事实和具体情况,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途径(违约之诉或侵权之诉)保护自己的权益。如合同当事人的权益既没有被纳入合同法的保护范围,也没有被纳入侵权法的保护范围,那么责任竞合制度也就无能为力。如前所述,合同精神利益难以全部纳入侵权法保护的范围,因此责任竞合的规定不足以保护合同当事人的精神利益,在合同编中规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仍属必要。
最后,在《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同编增设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同时,建议删去位于人格权编的第七百七十九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