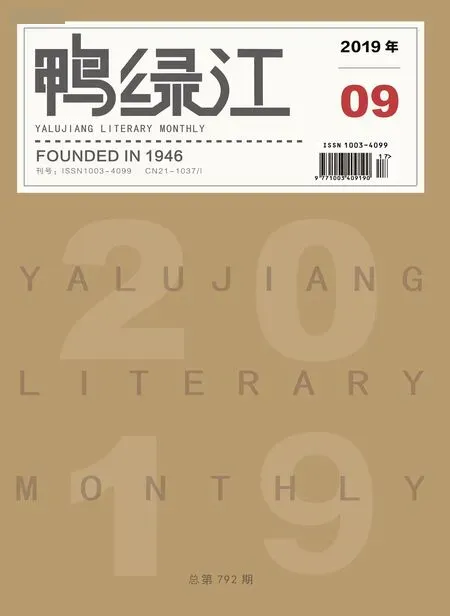死亡阴影下的日常叙事(评论)
——王海雪小说论
徐 威
一
王海雪是近年颇受瞩目的青年作家。她的写作在绵密的叙事背后往往隐藏着更大的思想表达和精神诉求。新作《白日月光》延续着她一直以来的书写特点:将故事的发生地设置在一个小镇中,用日常化、生活化的叙事语调勾勒那些隐秘的情爱,在碎片化的故事中掀开人物命运的一角,在平淡中编织出独特的感染力与冲击力。更具体地说,《白日月光》中关于刘加与钟晓回到家乡小镇这一事的寥寥数笔,就让我们想到了《失败者之歌》中屏风在远赴他乡后又跟随琼剧团再次回到塘镇定居,《归离》中“我”回到塘镇工作以照顾病重的父亲,《夜色袭人》中刘圆年迈之后重返塘镇旧地,等等。在这些小说中,“还乡”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原初动力。想得再久远一些,我们还可以想到鲁迅《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故乡》等小说中的还乡叙事。还乡叙事总与时间相关,此刻与昔日往事时常交融于一体。《白日月光》中父亲与刘朝颜的故事、杜眠琼与钟晓父亲的故事,均在刘加与钟晓的爱情中缓慢展开——但只是轻轻地掀开了一角,更多的“你侬我侬”“刻骨铭心”“歇斯底里”都在岁月的长河中任由我们去猜测、想象。在这一点上,《白日月光》延续着王海雪对爱情故事的叙事特征。
我试图详细论说的是《日白月光》中另一个异常吸引人的元素:死亡。情爱与死亡相交织,这是王海雪小说叙事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死亡,这是谁都无法逃脱的终极命运,它意味着肉体生命的结束、情感伦理的戛然而止、此在世界的失去与因未知而带来的神秘与恐惧。因恐惧而忌讳,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死亡话题,甚至对“死亡”这一字眼都充满了排斥与逃避。然而,死亡又是每一个人——不管他学富五车还是目不识丁,不管他家财万贯还是身无分文,不管他亲友满堂还是孑然一身——都曾暗暗思索的问题。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人们对死亡的思索重心亦有不同:青少年时对死亡的疑惑与不解,人到中年对死亡的无奈与恐惧,乃至于耄耋之年见惯死生之后对死亡的平静、安然与豁达,等等。因而,“生死问题体现人生最根本的困惑,和人的本质、美的本质问题一样,处于同等的逻辑地位,是一个终极性的哲学命题”。尽管如此,当我看到王海雪——一个生于1987年的青年小说家——在小说中如此频繁地书写死亡时,我依然感到一丝惊讶。
死亡在小说叙事中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死亡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中最为常见的元素之一。这源于死亡元素在小说叙事中的独特功能。在小说文本中,死亡能够激发矛盾与冲突,有效地聚合小说文本力量,从而使得小说情节走向高潮;同时,死亡又时常扮演“重要转折点”的角色,能起到发散的作用,引发诸如探秘、复仇等重要情节;此外,死亡是悲剧之一种,它还能够最大限度地激荡起人物与读者的情感波动。在小说叙事中,死亡除了作为一种小说情节,也时常作为一种叙事视角与基调而存在,它直接地影响到小说整体结构与叙事风格的生成。正因如此,许多写作者在小说创作中,往往借助人物的死亡来更有效地促成小说情节的转变,凸显小说的人物形象,渲染、传递或升华其创作意图,生成独特的美学风格。
在《白日月光》中,三对有着千丝万缕隐秘情愫的男女都与死亡相关。刘加与钟晓在回乡之后相遇并相爱,然而其中又夹杂着钟晓前女友之死带来的影响:钟晓因死亡刺激而患上精神疾病。刘加找来的护工刘朝颜——她长期在医院服侍濒死病人,见惯生死——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杜眠琼。但是,刘朝颜又与死去的父亲有过恋爱关系,且刘朝颜至今仍对父亲持有深刻的情感,仍收藏着父亲被遗弃的一切物品。杜眠琼反对刘加与钟晓的婚事,一方面因为钟晓的精神疾病,更重要的是钟晓的父亲是她曾经求而不得的旧爱。刘加的渴望、担忧与反抗,刘朝颜的平静、怀念与满足,杜棉琼的麻木、暴躁与隐于深处的希冀,如此多难以言清的情感在死亡的阴影中若隐若现,在冷静而克制的字词之中若有若无。小说因而显得张力十足:愈是克制的,愈是有力的。小说的最后,刘朝颜将自己与小镇的所有男女比喻成一只只“蜗牛”,“一辈子爬不出小镇四周遮天蔽日的绿”。这是点睛之笔:爬不出的不是小镇,而是男女之间的情爱。
二
在王海雪的小说中,死亡事件及死亡意象随处可见——需要注意的是,王海雪对死亡书写的偏爱具有专一性与持久性。
2016年出版的小说集《失败者之歌》收录了十篇2010年以来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拿来,酒瓶》中庙婆的祝词、被妹妹捂死的父亲及其葬礼;《躁动》中,“我”租金便宜的小床上有斑斑血迹,那是谌桥叛逆的姐姐死去时所留;《归离》中奶奶的葬礼、因癌症将死的父亲、为父亲准备的生墓及其仪式、阿宝丈夫的尸体被盗、阿宝之死、父亲之死等情节共同构成了小说中浓郁的忧郁气息;《道具灯》和《新街》对有着种种死亡禁忌与习俗的鬼节的书写充满地域色彩;《在光亮的房间点燃蜡烛》里,芝麻之死充满现实疼痛,令人怜惜,吴旺的自杀使得他一改往日卑微、窝囊的活法,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讨论的焦点……在这部小说集中,病痛、尸体、自杀、鲜血、墓地、葬礼、法事、祭祀等死亡意象层出不穷,与生死相关的庙婆、神棍、牧师、神父等特殊人群也轮番上场。这构成了我对王海雪小说的初次印象:死亡是她讲述小镇故事的关键词之一。
这种印象在阅读近两年她的小说新作之时不断得到加深。《烟火荡漾的告别》(《十月》2017年第6期)中,妹妹的死亡改变了一个家庭中每一个人的生活;《暮年》(《长江文艺·好小说》2017年第7期)中,“我”在父母的将死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到死亡带来的蜕变;《暹粒》(《广西文学》2018年第8期)中,那塔与召恩在一场葬礼中触发各自对死亡的个体记忆,在死亡教育中生发对存在的思考:“人终究都要一死,那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漂流鱼》(《芙蓉》2018年第5期)中,父母的死亡如同无法躲避的乌云时刻笼罩着周故,死亡带来的恐惧与阴郁虽无形却深入骨髓;《夜色袭人》(《花城》2019年第1期)中,人到中年的刘圆在一场葬礼中与李恩慈相识,在教堂的熊熊火焰中摆脱肉欲之欢而真正爱上他——在这重新唤醒她的不道德的爱恋中,刘圆重新思考生死爱欲,重新发现了个体的存在意义与生存姿态;《夏多布里昂对话》(《青年作家》2019年第3期)中,“我”总结出一个死亡公式:“晕倒小于睡眠,睡眠小于死亡”,而宋镇则认为“烂醉如泥人事不省才最像死亡”。
可以说,王海雪在小说中毫不遮掩她对于死亡的迷恋。她写下各式各样的死亡事件,而其中最常见的是父母之死;她又时常借助小说人物之口,单刀直入般地阐述自己对于死亡的思索与体悟。在阅读的过程中,这种感觉不断地透过那些反复出现的、与死亡息息相关的字眼显现出来。以至于我认为,死亡是王海雪小说叙事中最为重要的主题。然而,当我从这持续的阅读中抽身出来,跳出王海雪在小说中建构的世界,并在时间的缓冲与隔离中摆脱那些葬礼、死亡、祭祀、招魂,再回头思索,发现这只是一个错觉。在王海雪的小说中,并未生成诸如亡灵叙事、鬼魂书写、零度叙事、死亡狂欢等较为常见的死亡叙事模式。死亡仅仅作为一种情节存在。更关键的是,众多的死亡只是表象,生命的不断逝去只是小说的幕布——死亡留下的阴影才是核心;在这死亡阴影下各式各样的活法,才是王海雪的叙事主体。换而言之,在见证、遭遇他者的死亡之后,在死亡的阴影中,“我们”如何活着、何以活着以及活着之种种艰难,才是小说的重点书写对象。
维克多·布朗伯特在论述托尔斯泰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时谈到,“比重病更可怕的是活着这个疾病”。活着之不易,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我们早已深有感触。“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余华在《活着·中文版自序》中的这句话语,成为当下我们对“活着”最好的注解之一。小说中,福贵的忍耐、许三观的黑色幽默,亦是“活着”或者说“抵抗活着之难”的姿态之一种。在此之外,“活着”的姿态还有许多种,譬如积极进取、为爱而生、消极麻木、得过且过、逃避遗忘,等等。在帕斯卡尔看来,通过娱乐或者分散注意力来忘却,从而进行逃避,这是人类的悲剧之一:“人类既然不能治疗死亡、悲惨与无知,他们就认定为了使自己幸福而根本不要想念这些。”逃避或许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然而,王海雪小说中的塘镇众生恰恰与此相反:死亡不断地激发起他们对于逝去时光与亲朋的记忆,死亡阴影持续地笼罩着他们,改变着他们的活法与命运,也给予了他们不同寻常的日常。
在《烟火荡漾的告别》中,两年前妹妹在浴室触电身亡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影响是深远且难以磨灭的。在母亲看来,父亲摔断手臂、哥哥爱情破灭与断指之伤、姐姐为爱私奔却又惨遭抛弃等等一系列不幸都源于妹妹的亡魂在作祟。因而,母亲整日在家中办法事,最后甚至通过结阴婚的方式将妹妹迁出这个家庭。妹妹的双胞胎哥哥,在空荡的房间里还能听见妹妹的声音,闻到妹妹的味道。他一直想搜寻死亡的秘密,又不得不同妹妹的亡魂进行告别。同母异父的姐姐情路坎坷,甚至想到过死去,让自己的房间也和隔壁一样凋零。在低落与无望中,她思索“我们应该怎么活着”,但却无法解决这个深奥的问题。作为一个孤儿,父亲在年轻时同样有过自杀的念头。然而,在岁月的打磨中,他已经成为一个看破生死、不动声色之人。在小说中,生者不断试图遗忘,试图磨灭生的痕迹。只是,死亡阴影依旧顽强地以香火、法事、梦境、幻觉与寂静等多种方式显现于生者的生活之中。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妹妹的死亡是这个家庭普通而又不寻常生活的背景,它是整个小说叙事的开始,亦是小说叙事得以延伸的最大推动力。小说以四个生者的命运为叙事单元不断循环,其中回忆与现实交错接替,着重呈现出死亡阴影中的“活着”的多样与艰难。小说以“结阴婚”为节点,让这一家人告别了亡魂,与死亡握手言和。但是,这充满仪式感的告别是否真正有效?我们谁也无法得知。
“死亡不是一了百了的事情,死亡的影响仍然在活着的人之间延续。”小说中的这句话,可以用于概括《烟火荡漾的告别》这篇小说,也可以用来概括王海雪相当一部分的小说作品。王海雪时常借死亡阴影叙述情爱之艰难——这同样是“活着”之一种。我不知道这是王海雪的有意为之,还是长期迷恋死亡书写而带来的写作惯习。但无论如何,在叙事上,情爱与死亡联系在一起,总会增添其悲凉之感,亦能凸显出情爱之深之苦。另一方面,王海雪笔下的死亡又绝不是疯狂的、波涛汹涌的、歇斯底里的。相反,它显得安静,显得再平常不过,这正如同王海雪笔下的情爱纠缠与日常叙事一般。
与《白日月光》相似,在小说《归离》中,死亡阴影下王海雪试图呈现的是父亲与寡妇的陈年旧爱;《在光亮的房间点燃蜡烛》试图刻画的是“无后”焦虑,死亡恐惧中吴旺与芝麻这一对贫贱夫妻艰难而又温暖的爱情;《暹粒》中,那塔与召恩两个心中都藏有深刻的死亡体悟的孤独者,因同病相怜而在一起,又因在一起而生发出新的死亡事件。死亡,抑或说死亡带给生者的影响,在王海雪小说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王海雪的小说始终披着一层“死亡风衣”——一眼望去,阴郁弥漫,又冷酷冰凉,充满腐朽的味道,令人印象深刻;而细细探究,则会发现在这死亡笼罩之下,其实另有一番天地。
三
王海雪小说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字眼是:塘镇。早期的长篇小说名为《塘镇叙事》,小说集《失败者之歌》中,故事都发生在塘镇这一片小天地。在《白日月光》中,塘镇已然升级为了塘县。显然,王海雪与福克纳、莫言、苏童、贾平凹一样,试图在文字中建构属于自己的“专属领地”。王海雪在海口龙塘镇成长,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她最为熟悉的。如同王海雪在《夜色袭人》的创作谈中所说:“我的作品,包括《夜色袭人》的故事背景地,都发生在一个小镇上,那是我生活之地在纸张之下的变形。”然而,无论如何变形,龙塘镇的点点滴滴总会影响到其在文字中对塘镇的虚构。也就是说,这必然影响到了王海雪的小说叙事。譬如,龙塘镇的陶瓷泥塑、石雕和木雕驰名已久(龙塘雕刻艺术入选第二批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实中的龙塘陶瓷厂就被移植到塘镇叙事中,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故事都与此相关。又如,海南种种热带植物,也反复出现在王海雪的小说中:印度紫檀、椰树、波罗蜜等。
以上所言是显而易见的影响。更深层次的影响,来自于地方特有的风情、民俗、文化心理等。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反复提及:“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同样以死亡叙事为例,在荆楚大地,巫鬼文化盛行,精怪、鬼魂、天眼、轮回等在民间文化中广泛流传。于是,我们看到,在陈应松《还魂记》,王十月《米岛》《收脚印的人》等作品中,植物化灵、人鬼共存、魂魄夜行等匪夷所思的情节如同现实事件一般常见。迟子建笔下的“万物有灵”、莫言笔下的“生死轮回”等,同样受到当地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在王海雪的死亡叙事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许多海洋文明、海南地域文化等特征,譬如随处可见的印度紫檀被称为招魂之树、细致的葬礼文化(包括生前为人挖生墓)、灵魂离了身迷了路招魂幡也招不回、结阴婚、充满禁忌的七月十四鬼节、用椰子祭祀祖先、寺庙中具有神性的庙祝、颇有能力的算命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王海雪笔下的塘镇,还具有鲜明的文化融合气息:她多次写到塘镇中本土寺庙与基督教堂共存,寺庙执事与基督教徒混在一起。显然,这是近现代中西文化碰撞、并存、交融的一种缩影。
回到王海雪对塘镇的写实与虚构,我们看到,她的书写大多是一种现实的日常叙事。这与莫言《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等小说对高密东北乡进行的传奇化叙事策略显然是不一样的。塘镇的家长里短,时代变迁中的塘镇风貌,不同家庭各自的“幸”与“不幸”,男男女女之间的爱欲情仇,等等,成为王海雪的重点书写对象。当然,书写一地风貌,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国度”,在当代小说中并不显得独树一帜。令人眼前一亮的,是王海雪总是善于用那阴郁、冷酷又充满腐朽气息的“死亡风衣”,包裹那些温暖的、悲伤的、坚韧的、独立的、卑微的、反抗的个体生命,在冷静而克制的叙事中,传递出多层次的、个性化的生活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