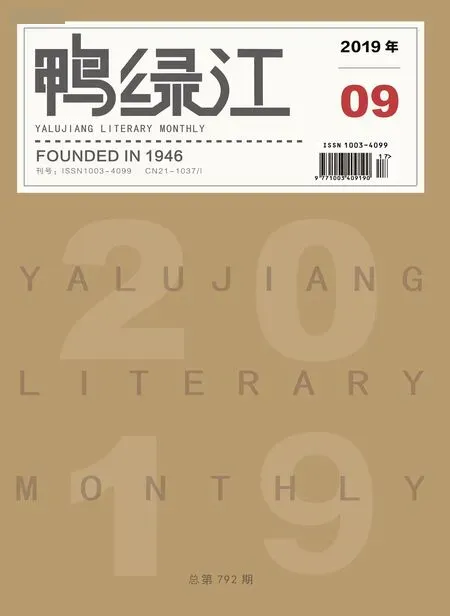梦的转弯
——评姚伟新著《楞严变》
李成师
时隔将近十年,在201年凭借长篇处女作《尼禄王》被冠以天才之名的青年小说家姚伟带来了他的第二部长篇《楞严变》。十年过去了,这些年姚伟一直在广东的一个古典书院工作,几乎不从事文学创作,这部新书是他特地请了一年的创作假奋力写成的。如今的姚伟,已经不再是写《尼禄王》时的青年大学生了,对于人生、世界的看法也与从前的自己判若两人,于是才有了我们面前的这部《楞严变》。这样一位天赋异禀的作家,十年之后再度归来,我想这对于中国文坛来说无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喜事。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姚伟小说一贯的可读性则会再次带给他们少有的阅读快感与严肃思考的奇妙结合。而我,作为一个专业的文学从业者,又是一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无疑同时享有了这双份的乐趣。
书归正题,就一般看法而言,姚伟同小说前沿文库丛书的其他作者一道,被纳入“先锋文学”的范畴之中,这当然是一种粗陋懒惰的做法。对80年代末那场形式主义纯文学浪潮的定义,从一开始就是特定历史局限下的错误,对其拨乱反正的翻案是中文学界亟待完成的任务,而不是任由它继续这样在歧路上越走越远。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取巧却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众所周知,在先锋作家群中,两位代表性的作家余华、格非都上演过十年沉默、重磅归来的戏码,甚至最近文坛的焦点《应物兄》,也同样是李洱十年磨一剑的大作,而这些人,除了90年代成名的李洱,都是姚伟在创作谈中公开承认的儿时偶像,尽管他对十年之作们的评价甚是低下,乃至直言其为堕落:“当然,庸俗(或犬儒)现实主义的大兴,余华也一度是主要推手之一,但是现在,在良心和野心的共同刺激下,余华开始了艰难的转型。对余华来说,从犬儒现实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的转身尽管华丽,但智性的贫乏,最终导致艺术表现力的虚弱粗糙,使批判力度和精准度都大打折扣。当一位牙医操起手术刀在你腹腔内东剜西砍,你很难认可那是一场庄严的手术。在我看来,余华首先需要摆脱由巨大名声编织的空壳,才有望真正完成一场精神上的蜕变。”
先锋作家群的转型,这是一个学术界至今还在争论的未解之题,对其的评价也褒贬不一。在这里,我们不必深究姚伟对余华等人转型的看法是否正确,而是应该首先注意到,姚伟与他曾经的偶像们一样,在经历了时间漫长的洗礼之后,他文学的品质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楞严变》的情节并不复杂,可以简单概括为几则发生在唐宋之际的彼此相关的传奇。全书共分六章,前三章分别写了古龟兹国取《楞严经》的故事、仞利天界取《兰亭集序》的故事以及在第一章中出现的做梦人的故事;后三章则讲述了前三个故事中的一些人物投胎转世之后的命运。这些故事环环相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构成了《一千零一夜》式的套盒结构,这是作者对前者的有意学习与应用。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故事明显的具有唐代佛教话本的特征,因此又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变文”这一体裁在当代文学中的一种再生,故而黄德海先生为这部原名《尘镜录》的小说改名为《楞严变》。不论是《尘镜录》还是《楞严变》,如果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有一些基本的了解,那么读到这里他就已经能够大体感到姚伟文学风格之变化所说为何。是的,我们甚至不用翻开这本小说,仅仅从小说的名字就能强烈地体验到,今天的姚伟,与十年之前非常不同。
《尼禄王》——《楞严变》,你很难想象一个曾经从思维到语言都如此西化,写的小说也完完全全是西方故事的作家,是怎样一跃回到东方的叙事传统中来的。当我从书架的角落里取下姚伟的那本成名作时,时至今日我依然震惊于他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稔熟掌握、对真本与伪书的巧妙穿插、对注释体结构的娴熟应用以及那节奏优雅宛如诗歌的繁复长句。这绝不仅仅是姚伟出于对尼禄这样一个西方暴君题材的考虑而刻意采用的叙事策略,恰恰相反,正是西方文明对他的深入灵魂的影响让他选择了这样一个题材去表现他对于人性恶与现实政治的思考。这点从他更早的短篇小说《琴殇》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我是荆轲的亡灵。多少年来,我一直在黑暗中沉默和游走,诉说的渴望总是被往事和悲伤打断”。在选择荆轲刺秦这样的中国历史题材的时候,姚伟依然使用了西化的语言与现代的技巧,这充分代表了他转型前的文学风格。而到了现今的《楞严变》,我们看到,姚伟明显开始刻意“加入一些中国古典小说的语言方式”,不止重新聚焦于中国故事,也将语言向传统白话靠拢:“古时,龟兹有位国君,在八十岁上喜得一子。国中虽已立下太子,但老国王对新生幼子爱若至宝,寻思将来由他继承王位”。语句更加精简,也抛弃了从前一贯擅长的西式从句,从而令语言与题材达成一致。
姚伟为什么会在而立之年回归中国的传统叙事?这就要从他文学的内部寻找答案。在《楞严变》之前的创作中,姚伟的小说始终被一种暗黑的气质所笼罩,噩梦、巫妖、杀戮、性饥渴反复出现在故事的各处,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对立也处于一触即断的状态。而这些最终无法得到缓和与解决,只能在末日狂欢式的戏剧化高潮中蓦然收场,最后得出“世界的存在是造物主的错误或玩笑”这样一个绝望的答案。姚伟曾经自述《尼禄王》的创作动机:“它首先源于一个年轻人内心的黑暗……向世界发出刺耳的叫喊、质问、怀疑与希冀。《尼禄王》吸纳了我青年时期所有躁动和战栗的情愫,企图在黑洞中挤压出一丝光亮……可以说,是存在的焦灼、死亡的阴影,构成了当初书写的第一推动力。”显然,当他在今天批评“流行作家,过度沉浸于这个时代,因长久凝视深渊,最后被深渊吞噬,失去所有判断力和逃脱能力,自身也成了深渊的一部分”时,十年前的自己也包含在内。但是,就像张承志在1984年的大雪中发现了伊斯兰一样,在《尼禄王》出版两年后,姚伟遇到了一位佛门中人的启示,虽没有遁入空门,但在对佛法的参悟中他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答案,其中禅宗经典《楞严经》尤其对他产生了顿悟式的影响,最终导致他的“写作质地也随之发生了根本转变”。
如何面对现代化带来的虚无主义,一直是姚伟文学的核心命题。在第一部长篇中选择了尼禄,是因为“尼禄皇帝作为一名艺术家,其虚无主义性格也与今日的时代氛围暗合”,而由于当时姚伟全部的“精神资源,被牢牢限定在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范畴内”,本身并没有足以面对虚无的武器,最终导致“《尼禄王》既是对上述危机的回应,继而又成了危机的一部分”。《楞严变》的出现,则更像是作者对虚无主义以及年轻时的自己的一次反击。善恶有报、因果轮回的观念贯穿全书始终,慈悲而又淡雅的气质完全取代了过往的绝望情绪,成为支撑全书复杂结构的一股有力能量。
《楞严变》的回归传统,是姚伟“精神返乡”后的必然转变。我们无法评论《楞严经》到底是不是这个世界的普世圣经,也无法预测它对每个个体的有效性,但显然,在姚伟那里,他打开了自己的真理之门。从这个角度看,似乎姚伟也进入了曾经的偶像格非所经历过的从《敌人》到《人面桃花》的先锋转型的命运轮回。这的确是一个很容易导出的结论,但它未必准确。
姚伟一贯不认同将自己的创作同80年代的先锋小说画上等号,他“自认为从价值立场和叙事方式上都很传统,但我的出发点和写作方式区别于流行作家,才被划归到先锋派或异质性写作的阵营”,这点被很多人忽视了。当姚伟两年前向我说起正在写一部佛教题材的小说并正在重温《一千零一夜》与冯梦龙时,我丝毫没有画风突变的错愕感,这不只是因为我知道他近些年潜心于传统文化的修习并曾经给我排过八字,也因为早在五年前第一次知道他这位作家并细读《尼禄王》时,我就在小说的正文与后记中同时看到了他对古代语言典雅隽永风格的向往以及古代笔记小说的推崇。在《尼禄王》中,姚伟曾描写过一份罗马开国时期流传下来的文书,他这样形容它:“这份文书只有十数页,而且字迹疏落,寥寥数言就将监狱的建造及与之相关的奇闻轶事描绘得令人神往,其文辞之典雅,用语之精确,意向之简练,在今人文章中已经罕有。一份过去的普通文书,也能让人感觉到今天的文风已经败坏到多么深刻的程度。”而在后记中,他则表示:“古代汉语是贵族语言,现代汉语则是平民和贱民的语言……把现代作家们的白话小说放在庄周、司马迁、李公佐、罗贯中、冯梦龙、蒲松龄、李渔等古代叙事艺术的大师们面前,我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寒碜。”事实上,在《尼禄王》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法与西方叙事中,我们很容易忽略姚伟语言的优美节奏并不仅仅是欧化的汉语,其中更包含着中国古代文言典雅的余韵;我们也会忽略,尽管他的故事是纯粹西方的,但他的精神指向并不是现代性,而是轴心时代的哲学起源。正是为此,我们不能说姚伟是走在格非等人的老路上,他从始至终不是一个全盘现代化的实践者,更何况他组织文本的方式一如既往地保持了探索的精神,一些核心的修辞手法也丝毫未变。
《楞严变》的故事起源于一场持续百年的睡梦:西域雪山下孤竹国的小王子机缘巧合得到了树神帮助,能够前往地狱看到人死后的悲惨业报。起初,凭着神通的他满足了尘世的愿望,但凝视深渊日久,他也越发痛苦,终于被黑暗笼罩了双眼,直到顿悟之后方才重新看清世界,但也因为找不到解脱之法而在一处废园之中陷入无穷无尽的梦境无法苏醒。他的梦汹涌泛滥,如瘟疫一般扩散,最终导致两个邻国龟兹与乌苌的人民深受其害,这才引出了小说开头龟兹国派人取《楞严经》以唤醒造梦者的情节。显然,这样的剧情设定是姚伟对自身经历的一种隐喻,但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他的自我解剖,而是他对于梦这个主题的矢志不渝的迷恋。在《尼禄王》的开篇,少年尼禄就讲述了自己受到的梦的困扰,甚至表示“这场始于十二岁的怪梦,是我一生全部灾难的开端”。而在被丛书主编霍香结编辑删去的《楔子》中,我们看到其实整个《尼禄王》的故事都是一位自称尼禄转世的二战军医的噩梦。显然,不论是东方叙事还是西方叙事,“梦的套盒”都是姚式迷宫的标准入口,在这一点上,他从未改变。当然,从做梦的方式来看,《楞严变》相对于《尼禄王》来说更加东方了,后者是弗洛伊德式的时空错乱,而前者则充满了佛家亦真亦幻的意味。不过造梦者在晚年的教诲:“只要通晓了睡梦生起的原因,生命和世界的真相也就昭然若揭了”,又让人觉得姚伟似乎无法完全把这两者界限分明地区分开来。
以上种种,让我觉得《楞严变》在姚伟的文学道路上,并非是大破大立的回炉重造,而是生命走向成熟后的一种调整。他依然在既定的方向上前进,也许稍有转弯,但绝对没有掉头。当然,如同所有的作家一样,改变现状必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在姚伟这里,则出现了如下的问题。
首先,他未能完全调和自己原来习惯使用的西式语言与着意借鉴的传统白话之间的矛盾之处,这最终导致小说语言出现了前后不一的情况,尤其在相对较弱的后面三章,让人愈发产生一种不伦不类的杂乱感,这也让姚伟自己感到遗憾:“我的叙事风格成了一种东西方的杂糅:一部分是朴实的《一千零一夜》语体,另一部分是古白话的变体。这其中自然有一些抵牾之处,也是我所体会到的缺憾。”其次,随着小说语言在后三章的愈发失控与变形,小说的结构也出现了严重的倾斜失衡。《楞严变》全书十三万字,分为六章,每一章都有单独的词牌名,看似是彼此平等的分量,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只是前三章就占据了全书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这不仅给人一种虎头蛇尾之感,也让这部小说显得很单薄,更像是一部中篇小说的加长版。更让我错愕的是,一直给我一种厚重之感《尼禄王》,也才只有十四万字!是什么支撑起了《尼禄王》的体量,给人大书之感,而《楞严变》没有做到,这也是姚伟亟须总结的问题。最后,对于《一千零一夜》与佛家思想的引入,我想在有些地方可能太过生硬刻意了。像小说第六章最后一节“女王与书生”,本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叙述,并且这种视角也一直保持到了全书的倒数第三个自然段,但结尾两段视角却突然发生了转变,变成了第二人称主观视角:“你可能已经猜到,我便是故事中的黄衣罗汉”,这并没有任何内部逻辑可言,明显只是为了收尾的那一句“只要你愿意,我的故事可以每晚为你无穷无尽地讲述下去”做出的硬着陆。我认为,像姚伟这种级别的作家不应该出现叙述视角层面的低级失误,更不应该为了学《一千零一夜》而学《一千零一夜》。对佛家思想的引入也是如此,让一些人物生硬地进行佛经式的对话,打破原有的叙述语言与叙述节奏,这是非常得不偿失的。小说毕竟不是教科书,要做到教化于无形,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希望姚伟能向现代文学中真正的大师许地山学习。
总体来说,《楞严变》是姚伟继续向前探索的一部作品,格局之大,格调之高,都足以令同辈作家汗颜。但由于姚伟选择的这条路在之前并没有人走过,因此借鉴的缺乏导致他不可避免地犯下了一些错误。不过,要想成为真正伟大的作家,就不能害怕犯错与失败,希望能很快见到姚伟的下一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