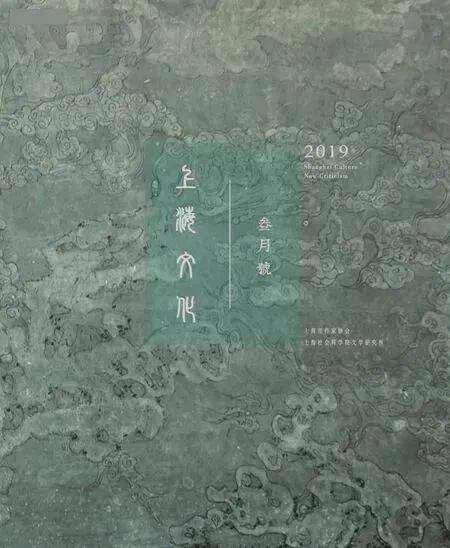纯然督造着生物钟
木 朵
我用整个身体品尝这些桃子,
我摸它们嗅它们。谁在说话?
我吸收它们如金雀花王朝
吸收安茹王朝。我看它们,如恋人看着,
如年轻的恋人看着初生的蓓蕾,
如黑种西班牙人弹奏他的吉他。
谁在说话?但它必定是教堂的钟
为我,那个野兽,那个俄国人,那个流亡者
滋生在心里的声音。
桃子又大又圆又红,
哦,它们有桃红的绒毛,
哦,它们满含汁液,皮是软的。
满含我的村庄的颜色,
美好的天气,夏天,露水,和平。
房间是安静的,它们在那里。
窗子敞开。阳光洒满窗帘。
甚至窗帘的拂动,如此细微,
也惊扰我。我不知道
这样的残暴能否将一个自我
从另一个撕开,如这些桃子为之的。
(华莱士·史蒂文斯《一盘俄罗斯桃子》,李景冰译)
在众生平等的观念弥漫整个空间之际,人率先跨出一步,走进那盘平等以待的桃子、尚未濡染人迹的桃子:这一步预示着一种建立更为亲密的友谊的尝试已经发生。人吃桃子-桃子被吃,这种看似不可更替的事实将由人品的自我塑造得以改观:桃子极有可能打破沉默的惯例,开口说话,在吃-被吃这种单一关系——也关乎二者命运的关系——中,掺入其他的命运因子,从而一改人吃桃子这个单调的场景/趋势。
总有一个更为凑巧的饱满时刻启发了人,桃子不只是奉献一个被吃前夕的凝思场面,作为一件等待被咀嚼的消费品而孤零零存在,它焕发了一个时刻的光焰,并把自己和人平等地置入一个改观各自命运轨迹的新境界,不仅是一位静物画家将以人的名义来重温这盘桃子的宜人性,而且包括后续赶来的诗人,他也将审视二手桃子的怡人性。画家最初把握到的桃子,已经脱离了桃子的一般性命运套路,而进入了一个对视之际可能自我异化的永恒时刻,于是,画家以创作的名义许诺,盘子里的桃子不再是盘中餐,而是完全能够仪式化的艺术品组成部分。
于是,“品尝”这个行为变得文雅起来,不再是用嘴牙去做物理意义上的接触,而是扩展了这个词应有的伶牙俐齿色彩,人“用整个身体”去品尝,就已经涵盖了吃的生理环节,而强化了一个对视的永恒时刻:人不得不约束自己的嘴,而用整个身体来接待一个他者。这里当然有对嘴或咽喉的功利主义主张的否认,看起来为了争取到一个全身心蓄势以待的良缘,人谦卑地把自身弱化为一个单纯的整体,一个一,坦诚相对桃子所蕴含的一。纾尊降贵的态度看来就是品尝桃子内蕴的前提。整个身体的表态,已经把嗅觉、味觉、听觉、视觉、触觉等各种身体反应机制都交付给了对视的一幕:桃子将在这些反应机制中难以隐身,而被榨取出更多的形象,这也正是当事人之所以孤注一掷的信心之源。
然而,桃子到底能够提供什么信息?在这个初涉人世的片刻,它们并不承诺有多少付出或报答,两厢情愿的可能性大小,也不予置评。人感觉到了这是一个丰沛的意义暴增的时刻,值得用整个身体去应对。桃子此刻真的不同以往,仅仅是人的倾力之故。当这人在初遇意义迸发的场面时,他还只是一个画家,或者是一个果农的儿子/邻居,而记述他与桃子邂逅一刻的诗人出现得更迟,乃至于缺乏足够的条件直接以“我”的口吻也参与到品尝的场合中去。诗人所要做的就是假定邂逅已然发生,桃子的宁静世界已经与画家的世界合二为一,于是,凭借想象力的光辉,重返那快要寂灭的最初至少一厢情愿的时刻。
诗人随后看到的场景很可能只剩下画布上/印刷品上的一盘桃子,一张画,桃子在画面上已完成了对早先一个创作者的召唤,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位俄罗斯画家,于是,桃子的无名无实被俄罗斯一人改变了,进而在后来人的眼里,改了称谓,成之为“俄罗斯桃子”。画家不见得是这样命名的,也许他有过私密的昵称,只是现在他本人整个地消失在画面以外,任由那看不见原生桃子的人士通过这张画来重构人与桃子最初相互作揖的场面。
桃子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开端的时间状况,而是一个半途的机缘,人并不是第一次进入这样一种新颖的对峙关系之中,但对于一位打算把桃子画进画框之中的画家来说,这时候的桃子从常态中摆脱出来,专供画家这个访客的端详、侍弄。这个时候,画家面临两个方面的选择:其一,“摸它们嗅它们”,极尽人的感觉体系之能事,建立起人与桃子之间的双向联系,也即,桃子即标的所在,把桃子画活就是当前的使命;其二,桃子仅仅是一个相对完善的中介,通过它们,画家想聆听的是“谁在说话”,显然不是摆在眼前的桃子在议论纷纷,对人评头论足,而是在透过桃子的色香之后又一个“谁”很值得研究。诗人乐意在这两个选择中徘徊,既要奉献出桃子作为一个物体的内秀,比如面临这样的自问:“桃子”有什么东西可写?又要,不受桃子物理空间的限制,而力图造成一个说话者的形象,一个位于初见桃子时的待舒展的关联中已萌生的声音,声音也可能成为这首诗开发的主题。
桃子的外在性逐渐被认知而转变为内在性,人对桃子的理解力在增强,画布上已经多出了一些桃子的形象,它们是盘子里的桃子的模仿者,然而,一旦着魔/着墨于画布上的桃子,在画家眼里,盘子里外在的桃子反而是意义迟钝的反应者,或可说,现实中的桃子在模仿画布上的桃子说话。摸、嗅、看,这些人为进度,既是人所谓的“品尝”进程,也是一个关于“吸收”桃子精华的步骤,显然,诗人认定画家已然完成了一次汲取:他为“吸收”打了一个比方。吸收的意思不只是把桃子的形象绘制在画布的空白之中,让画面吸收了桃子的光泽与风味,还把关于桃子的品尝史也吸收在内,画面上的桃子包含着对自身轶事的反观,富含必要的历史意识。就如同诗人设计的比喻从句中的那个“吸收”,与主句中作为谓词维持基本秩序的“吸收”存有不小的差异,但是,细察差异并不是诗的后续步骤,在这里,无非是为“吸收”这种来自人力一方的做法打个圆场,并预留了遁词:即便是吸收得不够味,却也可以史为鉴,没必要在意“吸收”的成色几何。当然,这个比喻也是对吸收的效果予以解释。但诗人并不建议在此逗留过久,他继续营造其他的比喻来扰乱独一比喻的象征意义。第二个比喻仿写了头一个比喻,使得比喻的差异性研究被悬置,而不得不顺应诗的脚步去看个究竟。
“我看它们”中的“看”不同于此前程序的摸与嗅,看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也即当事人看到的东西比盘子里的桃子许诺的视线更充分,不仅是盘子里的现实桃子还可以反复看,而且,经过“吸收”之后,画布上的桃子也能繁复于看,于是,“它们”这个复数形式已略不同于此前的阵容而加入了一个新生儿:桃子拥有了孪生姊妹。这时的看,已经是意趣溅射,不是一眨眼功夫,而是一段时光的端详,看的不再是看本身,而索要比喻的转轴来输送看的勃勃生机。被要求赋予看一点看法、一定的意义,自问:这是怎样的看?看与被看的关系是否从咫尺千里的人与物难以心灵相通的原始关系递进到恋人一般的亲密关系?看的诠释造成了诗人对作为画家的当事人的痴心妄想:那人当时会怎么看自己的作为/作品?
的确,人的创作是一个看的进度中新来的变量,桃子被挪动了位置,而已有一往情深于精神世界追根溯源的憧憬,这是一个新变化、新时刻。首先,看,透露出一股子甜蜜、喜悦,从“恋人”的视角汲取玄妙,但这又会是怎样的恋人呢?诗人在此做出了双重的蹀躞/叠写努力,犹如前述两次“吸收”的关系塑造。第一次蹀躞于本体之看与喻体之看的关联,第二次则用一个扩充句来流转恋人之看的情趣,“如恋人看着”这个短句被扩展为“如(年轻的)恋人看着(初生的蓓蕾)”,倒也似两个“王朝”相互吸引对方的魅力。倾向于看画布上初生的蓓蕾,然而,这个几乎要完成画作的人伫立于看的气氛之中,又是一个值得一看的物理空间现象,甚至,有经验的诗人,这个后来的看客,也可轻巧地从一幅画作的表层光辉中设想、遥望到曾经一位画家踌躇满志于那时恋人般的看。
要知道“初生的蓓蕾”这个被唤醒的词组,随即可能会要求更多利益(修辞伸展的更大空间),要求给予更多诗句的关照,这个比喻从句快要反客为主,成为弥漫观看与被观看组合的对峙情境空间的主角,说时迟那时快,诗人从容地再度出手了一个比喻,逆转了恋人-初生的香氛,而重返一个听觉激荡的世界,重返“谁在说话”这个疑问氛围之中。年轻的恋人太过匿名而随机,而黑种西班牙人则是另一幅画作捎带的信息,那熟悉的蓝色吉他想必具备完胜初生蓓蕾光耀的音质,能施予一种平等的比喻连带关系,同时,又动静结合地把声音元素再度取出。然而,值得读者留意的是,还有一个坎/可能,那就是:画家看到画布上的桃子,看到画作已完成,喜悦之情使得他洋溢在一个初为人父般的神奇氛围之中,但他接下来,要么继续从初生的蓓蕾上遐思更辽远的事物,为萍踪侠影/旁逸斜出做更深邃的尝试,要么,他趁此交出看的主动权,而任由诗人接替他的位置去调查初生之后还有怎样的成长动静有待摸索。如此说来,第三小节的两个“如”并非平等关系,后者以平等之名义替岗似地请走了蓓蕾,而是,递进关系,即后一个“如”深化了前者的亏欠,开启了更幅员辽阔的意义之旅,它不再是对“我看它们”的精致应付,而是对被看之物无尽的意蕴的慷慨赠予。
吉他这个意象并不是对蓓蕾的超越,虽然一开始有这么一点私心杂念,但是,更强烈的冲动在于让“弹奏”接替“看着”,而重返“谁在说话”的复沓式疑问之内侧,似乎在申明:端看之余,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有一静一动的转换。的确,无言的桃子已经是声音的前兆,为一个声音随之奏响的世界奉献了悦目的底色,是时候把这个声音从画面深处找出来了!这一次不再是停滞在一个质问的犹疑之中,而是明确地给出了这个发声者所在;声源来自教堂的钟,供人忏悔的钟声带来了必然色彩,并婉拒声音中的其他响动而纯然督造着这唯一的钟。
钟太像一个看热闹却又克制的他者,直逼着“我”这个类似的创作者现形,于是“我”谦卑地一分为三:野兽、俄国人和流亡者。其实到这一步,仍未说破这是一个画家的自谓,却点明了诗人的人称所系,这个幕后英雄此刻并没有参与“我”那个人称的分红。“我”的三重身份为心灵之音带来了繁复的动静,这正是外在教堂之钟需要予以启迪/对应的人之生物钟。既是宗教之钟在响动,从画面上悠扬传出清音,也是被这先在之音所激发的本在之内心滴答滴答的应付。于是,从逻辑上看,内心之钟是被宗教之钟所滋养的,就好像内心的声音仅仅是外在纯音的孳息。于是,谁在说话?答案很可能最终落脚于当事人本身,在桃子-画面-由内而外的教堂之钟三者陆续作为中介启迪之后的内心之应答,正是这个说话者。“我”终于听得见自己的声音,听得见自己的心跳。诗如此迅猛地找到了答案,几乎把诗的空间打探得一干二净。接下来,声音继续交待自己丰富的内在属性以奔赴应然世界更好,还是再度洄游桃子的已然世界更妙,仍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或许,已揭示过心灵状况的桃子还不满足于此,还要带领当事人寻觅更多的意趣,留下这已触探到的心灵港湾,继而再以桃子的宜人性为主题,去寻觅野兽般的俄国流浪者的命运抛物线。
此刻,桃子利用了自己的可修饰性,展示出足以对应人的三个特征的自身属性:又大-又圆-又红。这是思绪驻留在声音的边缘再无进展之际,桃子给出的救济性福利,此前的诗节并未给出关于桃子的这些属性,而此刻,不得不为之,不得不以此为过门,把声音上的追查责任转移到桃子的未了情上。桃子开始逾越本分,为流浪者营造必要的乡愁,也即,它们完全可以扮演故乡/祖国的桃子,为吟哦的当事人提供鲜嫩可口的异地色彩,这就是桃子的通用功能,仿佛它们的品性因咀嚼人的籍贯不同而具备不同的国籍。它们愉快地承担了身份上转变的义务,变成了俄罗斯桃子的复制品。“满含我的村庄的颜色”正是桃子的俄罗斯化趋势,这是不可避免的从内心翻山越岭回到故乡的必由之路。
画布上的桃子出现了些许异样,不同于创作一幅画作所处的房间里摆放的物理意义上的桃子,桃子的外在特性的通用禀赋许可这一跨国流转,然而,桃子所处的空间感仍在产生摩擦力,既有创作之际的异国房间,也有故乡曾经出现过类似一盘桃子的房间,这种画面上所不能呈现的较大的物理空间,正是自由想象的阻力,故乡的房间再怎么舒适宜人,都会逊色于当前房间的宽宏大量,可见,在桃子形象的想象不受限制之后,房间的想象开始构成了反作用力,反制着当事人过分地把桃子外地化,桃子作为一个中介的职能达成之际,它们作为诗的主题的使命太过耀眼而难以泯灭本地的抽象。安静的房间可以指故乡,窗子一并在故乡敞开也行,窗帘配合着故乡的阳光起舞也好,但是,桃子所提供的乡愁半径到此为止,已难以再涉足一个窗外的世界,更何况,本地的窗帘已经更为迫在眉睫地拂动起来了。
房间的安静看来矛盾于教堂的钟声,作为心灵之音的港湾也很容易成为大而无当的空间所在,毕竟关于房间,所能捕获的形象要么是“安静的”,要么是房间-窗子-窗帘这种倍缩的趋势,更何况,营造记忆中的一个房间本身作为任务已经达成,而回归本地的空间既是一种礼尚往来的风俗,也是对桃子往返演化功劳的酬谢,于是,得有什么打破房间安静属性的东西提供一个反推力,这自然就把担子交给了爱运动的窗帘身上。即便是故乡轻微拂动的窗帘也足以为迷失者提供一份注意力,为其情系故土不知所措提供一次惊悸,叫醒那人,使得想象的故乡不复存在,而退回想象伊始的原型,或许,可以责怪窗帘坏了好事,但迟早会发生这一幕,同时,也可以这么看,本地的窗帘恰好拂动了一下,这轻微的动作足以把情陷故乡的当事人从愣怔中摆脱出来,并为此背负了惊扰的罪名。
桃子这时倒是撇得干干净净,不会承揽/分担这个惊扰罪名,但来龙去脉都跟它们有关,却又洗脱不了干系。有它们好看的。本地的桃子、画布上的桃子、故乡房间里的桃子来来回回、推推搡搡,把当事人折腾得够呛,那个在想象中回过神来的画家突然意识到故乡回不去了,这个残酷的现实构成了令人不适的惊扰。但他还得感激桃子所做的一切,正是它们巧言令色,合力建设出时空隧道,将一个人一分为二,将一个自我与另一个分开,使得想象中的、灵魂中的自我得以穿越千里回归故乡,这是桃子的功绩,然而,这种裂变/撕开的能事很可能为其他事物所具有,从而造成某种杀伤力较大的残暴性,当事人在惊扰之际,想必阵阵后怕,乃至于认识到其中的残暴之力,更何况,对于这种残暴他还感到无知(“我不知道”),这跟此前碰到的“它必定是教堂的钟”那种肯定无误的意识明显不同,他担心什么呢?事实上,诗人此刻苦思冥想的也正是两个问题:其一,为突如其来的“惊扰”升格为一个更富震撼力的结果,使之吻合诗的尾声需要;其二,怎么让桃子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很可能是半个句子的位置上再现魔力?桃子经过抽象处理之后已经变得足够永恒了,它们将浓缩为单数形式的它,一股寄寓在人的感官之中的复述/复苏之力量,必要时施以援手,既让人赖以出神入化,至少拥有两个自我,又让人完好无损地复原为整全之人。但是,使之倍感余悸的是,有一种既是窗帘又不是窗帘所造成的破坏力,具备一种能力,足以残暴地单向度地把人撕裂却不能(双向地、一来二去地)使之复合为一。字里行间更令人恐惧的是,这种无名之惊扰、这样的残暴很可能连撕裂一个人的可能性都没有,不应许一个人身心两用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幸好有这些桃子,至少赐予过一次确凿无疑的回乡之旅,画家在这样一次折返跑中增进了人与桃子之间的感情,它们/它日后将既是抗拒残暴的可能性之善力/惯例,也是对不知道之景况的预览/预告。确实,如我们所知道的,桃子在诗的最后半句这个位置上,以似是而非的比喻口吻告诉我们:人对桃子所做的越多,桃子对人的回馈也越多,倒也暗合投桃报李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