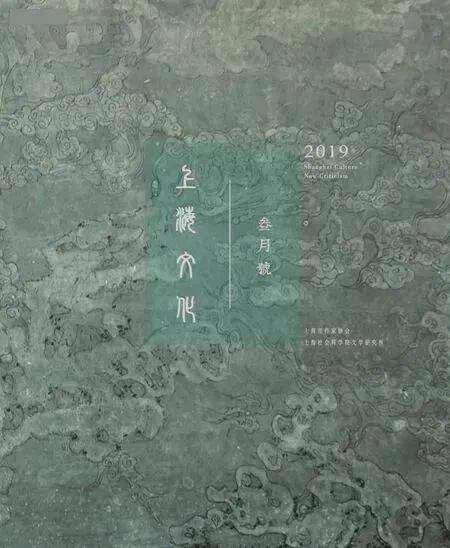易卜生主义百年祭
万 之
有时我的生命在黑暗中睁开眼睛。
感觉是好像有大批群众涌过街道
正在盲目和不安中迈向一个奇迹
同时我依然站立着没有被人看到。
……
——特朗斯特罗默《垂怜经》
呜呼哀哉,易卜生主义!
哀其不幸,生于动荡不安之世!
哀其早夭,殁于民族危亡之时!
* * *
近代的世界舞台上,各种主义像幽灵一样连续不断粉墨登场让人目不暇给。有些主义风靡全球,大行其道,而有些主义默默无闻,不为人注意,甚至已经销声匿迹。易卜生主义无疑属于后者,也可能是其中最鲜为人知者。
我在题头引用了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诗作《垂怜经》中的一段,因为在我看来,盛行于世界的各种主义就如“正在盲目和不安中走向一个奇迹”的那群人,而易卜生主义就是“没有被人看到”的那个人。其人已逝,不可悲乎?
诗名 《垂怜经》,就说明这是一首哀歌。
我酝酿这篇祭文其实已经数年,每思及此,悲从心生,就有如独自步入一个墓园的凄清角落,而故人的墓碑前花叶凋零,荒草萋萋,已经很多年无人祭奠了。
* * *
回顾易卜生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常让我唏嘘不已。
谁还记得,整整一百年前,在1918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易卜生号”上,胡适曾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大力推荐这种主义?《新青年》在当时的所谓新文化运动中是一份领军刊物,旨在传播新思想新文学新主义,刊行全中国,所以这期“易卜生号”也广为传播,胡适这篇文章在读者中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时之间,易卜生主义成了很多年轻人的人生指南,尤其受到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女性的青睐。茅盾在1925年发表的《谭谭》一文中曾写道:“易卜生和我国近年来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有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号’曾把这位北欧的大文豪作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的象征。那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的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司和列宁”。
由此可见那时的易卜生,曾经是多么风光!那时的易卜生主义,曾经是多么让人追捧!
易卜生成了当时在中国知名度超越很多其他西方文学家的作家,一度几乎是独占鳌头,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或托尔斯泰,例如《新青年》就没有出过什么“莎士比亚号”或“托尔斯泰号”。再如和易卜生齐名、并称为现代戏剧之父的瑞典戏剧家斯特林堡,相比之下当时在中国就默默无闻。
但时过境迁,之后的数十年里,内乱外患民族危亡之时,集体主义压倒个人主义,易卜生主义就风光不再,没人提起了。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有过所谓的思想解放,易卜生一度重新得到关注。1984年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79级学生毕业演出易卜生的《培尔·金特》,这部剧作描写主人公培尔·金特一生追求自我确认的努力,打动了很多年轻观众,尤其是北京的大学生,演出轰动一时,连演几十场。
从1918年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整整一百年过去了,现在还有谁会谈论易卜生主义?易卜生的剧作已经很少有人读。虽然他的剧作偶尔还在大城市的剧场上演,也有个别研究生会拿易卜生戏剧做篇学位论文,但易卜生已经不再是人们熟悉甚至崇敬的伟人,易卜生主义也已经不再是人们指导自己人生实践的指南,早已被埋葬到历史坟墓中去了!
去年秋天我曾应邀到上海戏剧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讲课,就以“易卜生主义百年祭”为题。我问在座听课的研究生有谁读过易卜生的书,看过易卜生的戏剧,举手者寥寥无几。当然,知道什么是易卜生主义的学生就几乎没有了。
当人们“正在盲目和不安中迈向一个奇迹”、只顾狂热追求与时俱进的时候,一百年前胡适推崇的易卜生主义不合时宜了。谁还能“看到”那个落后于时代的人?
也许,就如人间万物,本来就都有兴盛衰亡。易卜生主义就算在五四时期是艳丽盛开的鲜花,最终也会衰败凋零。
难道我不该悲叹:呜呼哀哉,易卜生主义?!
* * *
其实,无可奈何花落去,易卜生主义已经过时,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我想起一件往事:1986年我出国留学之前,当时美国好莱坞电影巨头之一环球电影公司到北京拍摄《末代皇帝》,总裁也到了北京。我的老朋友陈凯歌也在电影中客串了一个角色。这个总裁想结识一下中国文艺界年轻一代的后起之秀,就请陈凯歌约几个这方面的朋友到四川饭店吃饭,好像还有提携这些中国年轻艺术家的意思。陈凯歌把我也叫去了,还安排我坐在这个总裁旁边。其实我理解陈凯歌的用意,并不是因为我也算什么后起之秀,而是在座的后起之秀们大多英语不秀,而我英语还可以凑合,可以帮着做些翻译。席间环球总裁问我将来想做什么,有什么计划,或许也是想提携我一把吧。我如实告诉总裁,我即将去挪威奥斯陆大学戏剧学院攻读有关易卜生戏剧的学位。哪知这位总裁听了仰天大笑,然后带着嘲讽的口气,用英语对同来的美国人说:“瞧这个家伙(Look at this guy),他要到挪威去学习易卜生啦,哈哈哈哈哈……!”
从他轻蔑的口气和嘲讽的笑声里我可以听出,易卜生对他显然是早已过时的人物。现在谁还要学习易卜生戏剧?而我这个被他称为“家伙”的中国人,居然不识时务,没有巴结他这个总裁,到美国好莱坞去留学,却不远万里要到世界的一个偏僻角落挪威去学习易卜生,这难道不是一件让他忍不住哈哈大笑的愚蠢行为吗?
我当众受到羞辱,被称为“家伙”,但那时却没有用英语回击的能力,只能哑口无言,只能在心里默默用中文说,你好莱坞全部电影加起来,也抵不过一个易卜生啊!
这顿晚餐让我很不愉快,早早就告辞了。
多少年后,我已经不记得这顿晚餐时还有哪些人,还发生过什么事情,只有好莱坞环球总裁讥笑我的笑声仍响在我耳边,让我难以忘怀。
* * *
那么,何谓易卜生主义?
其实,不同的易卜生主义倡导者对此也有过不同解释。
最早提出易卜生主义的应该是长居英国的爱尔兰文学家戏剧家萧伯纳。萧伯纳也是主张渐进式社会改革的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的重要成员。在他眼里,易卜生不仅是戏剧家,也是社会改革者,是旧制度的颠覆者革新者。费边社在1890年春季发起过以“当代文学中的社会主义”为题的系列演讲活动,因此那年7月18日萧伯纳在伦敦圣詹姆斯酒店做了题为《易卜生主义的精华》的著名演讲,后来还成书出版,对当时震动欧洲的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一些剧作做了精彩的分析和概括。萧伯纳认为,易卜生这些剧作打破了陈规陋习,运用了全新的戏剧创作方法,这就如春风给欧洲剧坛带来新的生命力,也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人生观,萧伯纳把易卜生的这种方法和观念称之为易卜生主义,把这种主义的精华总结为一句话,即“没有公式”(There is no formula)。
“没有公式”,就是否定一切已有的公式,不论这是什么公式。如此的易卜生主义,是一种革命的、造反的、推倒旧世界、颠覆历史的主义。
萧伯纳后来继承这种易卜生主义从事戏剧创作,标新立异,成绩斐然,还获得过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这种易卜生主义“没有公式”,却有着丰富意蕴。在戏剧创作和戏剧观方面,这是指不落窠臼,不拘泥于陈规陋矩,能别具一格,艺术创新。而在人生观社会观方面,则是敢于挑战传统道德教条、宗教戒律和家庭规范。
在戏剧专业这方面,我只想简单地说,易卜生既承继了古典主义戏剧的传统,比如三一律,又确实不墨守陈规。他的主要贡献是改变了欧洲戏剧的传统要素,也就是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总结的古希腊悲剧的动作要素、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戏剧中突出的性格要素,更突破了他那个时代的欧洲戏剧流行的情节剧以情节为要素的俗套(萧伯纳把这类戏剧讽刺为“糖果店”)。易卜生是把社会问题,即个人和传统社会之间发生的冲突提升为戏剧要素,并在舞台上对这些社会问题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手法推动戏剧情节的发展,得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结论。“讨论”这些社会问题的剧作后来就被称为社会问题剧,也给世界戏剧带来了一个新起点。现代中国的话剧基本上是在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这个新起点上发展起来的。胡适根据易卜生《玩偶之家》的模式写出的话剧《终身大事》,曹禺根据易卜生《群鬼》的模式创作出的话剧 《雷雨》,都是现代中国话剧奠基之作。
我后来在中央戏剧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给我开列的必读书目中有一本美国戏剧家埃里克·本特利的《作为思想家的剧作家》(The Playwright As Thinker)。作者在这部著作指出,从易卜生开始,现代戏剧开始强调思想。一个优秀的剧作家同时也必须是思想家,他要思考社会的问题,指出社会的病症,追求个人生存的意义。这是现代性进入戏剧创作的标志,所以易卜生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
我在巴黎罗丹雕塑博物馆看到过那个著名雕塑“思想者”。那个沉思形象,不一定是剧作家,但在我眼中,他也就是一个易卜生主义者。一个易卜生主义者必然是思想者。
戏剧要素的转变其实也是戏剧观的创新。一方面是对戏剧功能的看法有了转变。戏剧的功能不再是亚里士多德总结的古希腊戏剧的“净化”或“宣泄”(cathasis),不是后世美学强调的移情或娱乐,而是为了揭示社会问题,批判社会现实,这就把戏剧纳入了当时欧美文学的主流批判现实主义,所以易卜生主义其实还包含了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另一方面是戏剧塑造的人物形象的转变,占据舞台的已经不是以往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和才子佳人,而是被传统社会压迫和摧残的个人,这样的社会因此才需要揭露和批判。
萧伯纳推崇的易卜生主义,当然不仅是戏剧创作手法和戏剧观的创新,也是社会观人生观的颠覆,“没有公式”的含义不仅是在戏剧创作层面,更是在社会革新的层面否定旧有的社会公式,提出新的人生观。所以,它不光指导你如何创作剧本,也告诉你做一个怎么样的人。
在萧伯纳的演讲中,他根据对理想和真实关系的看法,把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菲力士主义者,占人类大多数,一千个人里有七百,是那种浑浑噩噩的人,根本不在乎什么理想和真实;第二类是理想主义者,正如这个类型的名称所指明的,这类人都带着“理想”的面具,这种“理想”其实就是传统道德规范,是道貌岸然的面具,他们用这个面具掩盖住真实的面容,这类人也比较多,一千个人里有二百九十九个;第三类是真实主义者,是那种要把一切面具揭除,让人看到真相的人,这种人稀少,一千个人里才有一个。易卜生名作《国民公敌》里的坚持说真话的斯多克曼医生就是这样的人,因为说真话而成了全体人民的公敌,孤独但强大;而《玩偶之家》里摘下了自己作为丈夫玩偶面具而离家出走的娜拉,也是这样追求真实的人。
所以,在人生观和社会意义上,萧伯纳的易卜生主义又是做一个“真实主义者”(英文原文为realist,有人翻译为“现实主义者”或“写实主义者”,因为这种译法多用于文学流派和创作手法,所以我认为翻译为“真实主义者”更为准确),就是说,不仅限于文学的观念,做人也要追求真实、追求事物的真相。
所谓“没有公式”,就是抛弃传统规范,不循规蹈矩,不墨守成规,不佩戴传统“理想”的面具,坚持说真话,同时又不怕成为社会中的少数。这是独立的个人,独立不羁,独立独行。
在萧伯纳看来,传统社会(如当时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充满陈规陋习和虚伪的道德教条。这种教条压制了个人的发展,是导致个人悲剧的根本原因,而这正是社会主义者需要揭示、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萧伯纳这种“没有公式”的易卜生主义,听起来甚至有点目空一切、妄自尊大、舍我其谁也的味道,只有优秀的千里挑一的个人才配称得上易卜生主义者。其中不免看出达尔文《物种起源》中提出的优胜劣败的进化论的影响,以及与尼采超人哲学的呼应。所以萧伯纳后来还写出了一部剧作《人和超人》。
* * *
易卜生的名声是在上世纪初传入中国的。首先是通过一批到日本留学而在日本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学生如鲁迅等介绍给了中国人。鲁迅于1908年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摩罗诗力说》就提到了易卜生(鲁迅翻译为伊勃生),称赞伊氏的“处世之道”就是做“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又称赞伊勃生继承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先驱人物基尔凯廓尔(鲁迅翻译为契开迦尔)的思想,视“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鲁迅还在散文集《热风》中也提到了伊勃生,号召中国青年向他学习,做“有几分狂气”的“个人自大”的国民。这种反抗传统、带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易卜生主义,也正是萧伯纳总结的“没有公式”,鲁迅还借用了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说法,称为“轨道破坏者”。
正如我前面写到的,在中国,最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倡导易卜生主义的当属胡适,不仅策划了《新青年》“易卜生号”,组织人翻译出版了几部易卜生代表作,比如社会问题剧代表作《娜拉》(又名《玩偶之家》),还亲自撰写了《易卜生主义》一文。这篇文章,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另一重要人物、创办了《新潮》杂志的傅斯年先生称为“文化革命的宣言书”。
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胡适先生首先是把易卜生主义解释为“写实主义”。他开篇就这样写道:“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如前文所说,这个词我愿意翻译为“真实主义”,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描写手段,也是人生观。
之所以首先强调“真实主义”,因为易卜生和胡适这代人,都认为传统社会展示的、在人们言语中描述的表象是不真实的。正如胡适在文中所写的:“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要说一点病都没有!”
一个易卜生主义者就要揭示社会的真实,要说实话,这首先是因为他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也是因为他对社会有一份责任感。胡适引用易卜生的话说:“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的。”但这种责任感,并不是说人要把社会放在第一位,把个人放在第二位。恰恰相反,就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而言,易卜生主义是把个人放在第一位的。易卜生和胡适都认为,他们那个时代的传统社会,包括其法律、宗教、道德和家庭观念,都是压制个人束缚个性的。其实鲁迅也是这个看法,所以在他被称为中国首篇白话小说的《狂人日记》中,把当时的传统社会影射为“吃人”的社会。这个被吃掉的“人”就是个人。
易卜生主义认为,只有把个人解放出来,使人具有独立自由的个性,才可以达到社会的解放。正如《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当她发现自己成了丈夫的玩偶,没有了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只承担家庭的责任以及对丈夫和孩子的责任,而没有承担对自己个人的责任,她才需要离家出走。
所以,易卜生主义其实和欧洲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社会时个人主义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自我意识的增长,个性的自由发展,使人把自我放在高于国家、社会和家庭的位置。这种个人主义,甚至用易卜生自己的话来说,是“为我主义”。当我们每个人都发展出了独立自由、富有个性的自我,社会自然就会变得美好。
胡适后来把这种人生观,定义为“健全的个人主义”。这个定义里包括了几个关键词,最首要的当然是“个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独立自在的个体,都应该“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这个“个人”应该高于一切,高于民族,高于国家,高于社会,高于家庭。如果说,有人认为只有社会先解放才有个人的解放,只有民族先独立才有个人的独立,只有国家先强大才有个人的强大,那么“健全的个人主义”恰恰相反,认为个人先解放才有社会的解放,只有个人先独立才有民族的独立,只有个人的强大才有国家的强大。要拯救世界必须先拯救自己。胡适在《易卜生主义》就引用了易卜生自己的话,“有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另一个关键词是“健全的”,因为这种个人主义不是病态的,不是自私自利、自怨自艾,不能和为我主义利己主义混为一谈。“健全的个人主义”追求真实,就要求个人有理性,有思想,有是非观念,有批判精神。
对于旧世界是破坏者,对于新世界是建设者,这就是易卜生主义。
这种易卜生主义,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清末民初的中国从传统社会往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实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座标,是一代人的追求。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我看来也是为易卜生主义对这代人的影响做了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