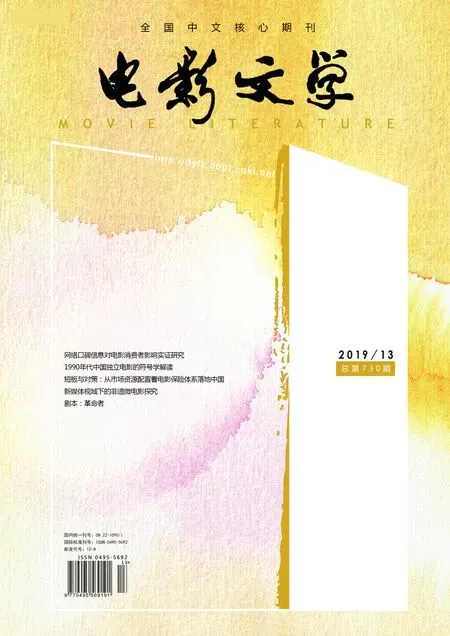民间故事在厦语电影中的异化与归化
黄 宁(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人文与传播学院,福建 漳州 363105)
厦门语电影(或称之为“厦语电影”“厦语片”)是华语电影发展历史中极为特殊的一种方言电影。它是20世纪中叶前后,在香港制作生产,面向东南亚地区观众,以闽南语为语言载体制作的电影类型。[1]厦语电影作为独特的方言电影,直接面对的就是东南亚华人群体(以操持闽南语方言的华人群体为主,下同)。1947年,由菲律宾侨商创办的新光影业公司筹拍了首部港产厦语电影《相逢恨晚》。新光影业公司前往厦门甄选女主演鹭红,后至香港拍摄制作,传播至东南亚地区,华人观众反响强烈。
东南亚华人对于厦语电影的喜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主要有三个因素:其一,是移民社会所形成的天然观影市场。在过去的四个世纪中经历过四次移民大潮,东南亚华人总数约3348.6万,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6%,约占全球4543 万华人华侨的73.5%。[2]而这其中,福建及广东先民“下南洋”,所形成的事实上的华人社会则为厦语电影的勃兴提供了必要条件。其二,是方言所形成的强有力的联结纽带。语言是仅次于宗教的、使一种文化的人民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民的要素。[3]“流寓的福建人”等地域性身份认同,在语言使用上也存在分歧,不同地域的人通过保持并使用自己家乡的语言与其他族群分开。[4]操持闽南方言的华人群体,这一表现特征更为深刻。闽南方言成了他们交流沟通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语言。也因此,当厦语电影中的人物讲闽南方言,以南音等具有强烈闽南地域特色的歌曲为配乐时,旋即拉近了与东南亚华人群体的距离。最后,是特殊政治环境下所衍生的对故土的想念。1949年后囿于意识形态对立与隔绝,众多群聚而居的东南亚华侨无法回到中国,对母国故土的想念形成了浓厚的乡愁。厦语电影完全使用闽南语对白,通过乡音的重现,缓解或是慰藉了他们往往难以言喻的乡愁。
要缓解东南亚华人因种种原因无法回到中国的强烈乡愁,最大限度地满足这部分群体对于母国的想念,甚至是满足一些从未涉足中国的华人后代对中国的想象,厦语电影就必须在影片内容上有精准的选择。早期厦语电影就从对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的改编入手,从内容和价值观上营造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电影故事世界。
一、改编民间故事的背景
华语电影诞生以来,不少作品是来自对古代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文学名著的改编,这类改编使得观众拥有了新的与神话、故事和名著进行对话的端口。[5]促成此类改编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以及文学名著本身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故事原型内容。例如针对《西游记》的改编,早期者有《大闹天宫》(1961)、《哪吒闹海》(1985),晚近者如《大话西游》(1995)、《大圣归来》(2015)等。《西游记》庞大的内容体量,以及丰富的文学元素,为电影改编提供了非常理想的故事原型。其二,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以及文学名著所营造的价值观念往往符合改编需求。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的民间故事,除了为电影营造戏剧冲突提供了故事原型,其故事本身所体现的对于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较为深刻地反映了普通民众的需求,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其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以及文学名著历经数代,普通民众之间口耳相传,故事为大家所熟悉,改编电影省略了许多原本需要前置的背景介绍等环节,令观众在观看电影时不会有陌生感,较易得到认同。
厦语电影对民间故事进行改编,自然也是受了上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歌仔戏传统四大出(《陈三五娘》《山伯英台》《什细记》《吕蒙正》)都曾被改编翻拍过厦语电影,此外,《孔雀东南飞》(1955)、《泉州姑嫂塔》(1956)、《花魁女情钟卖油郎》(1956)、《百里奚忘恩负义》(1957)等具有代表性的厦语电影都是对民间故事的改编。由于厦语电影使用闽南语为对白,以及观众为操持闽南方言的东南亚华人,所以不少电影又是由闽南民间戏剧故事改编而来。下表是部分改编闽南民间故事的厦语电影情况[1]:
由民间故事改编的厦语电影,受到了东南亚华人的广泛欢迎,除了故事的丰富性、吸引人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蕴含了很深的怀乡情怀,传递的价值观念往往能较容易引起共鸣。此类影片的故事原型,都非常接近世俗生活,价值取向善恶分明,有着较为强烈的道德训诫的意味。
二、民间故事改编的“异化与归化”
厦语电影对于民间故事的改编,与中国本土电影对民间故事的改编相比较,在迎合观众需求层面上,存在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的放映环境是在东南亚地区,是与中国相对的、事实上的“异国他乡”,观众群体虽自中国移民而来,但毕竟是处在异种的文化环境中。这一点,在移民的后裔身上体现得更为显著。20世纪50年代起,东南亚华侨在当地国的入籍归化成为潮流,作为移民及其后裔的东南亚华人,逐渐成为当地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此外,东南亚各国政府通过各种限制方法,强制华人转变身份认同,接受当地文化,部分华人不得不选择了融入归化[4]。一方面,东南亚华人身上保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拥有对于母国家乡的向往与想念;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已经身处迥异于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并深受其影响。
由此看出,厦语电影的观众群体,其所处地理环境为东南亚国家,并受所在国文化环境的影响,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厦语电影对于民间故事的改编,必须与中国本土类似改编电影做区别,要能够适应东南亚的异国文化语境。为此,厦语电影对民间故事的改编,就采用了“异化与归化”的方法。
归化与异化的理论内涵最初是由西方翻译理论家提出来的。1813年,德国的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Schleiermacher 在其《论翻译的方法》一文中提到:“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译者尽量不打扰作者,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1995年,美国翻译学家Venuti 受Schleiermacher 的影响,明确地将Schleiermacher 的第一种方法称为“异化法”(Foreignization),将其第二种方法称为“归化法”(Domestication),即前者是“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最大限度保存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而后者则是“遵守目标语语言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译文迎合本土的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需要”。[6]如同对原文翻译存在异化与同化两种倾向,厦语电影对源自中国的传统民间故事改编,也存在这种现象。对于前者,厦语电影的改编,几乎是照搬民间故事,除了将人物对话、影片配乐转换成闽南语,其他举凡内容、情节、人物、结局等,都没有改变;而对于后者,则充分考虑到了观众所在国的文化氛围和价值观念,对原文故事进行了艺术性的加工与改变,电影受观众所在国的影响较大。
(一)异化:思乡之情催生的强烈“国族想象”
经过国共内战,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并形成了事实上彼时大陆与海外较为隔绝的态势。随着政治情势改变,以张善琨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原本活跃在上海的电影人纷纷涌入香港。他们的到来一方面为香港电影业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另一方面随着1950年新中国政府颁布《外地电影输入暂行办法》,香港电影的引进变得极为困难,这批南下电影人迎合东南亚的闽南华人族群观影的需要,转而加大投入并促进了厦语电影的发展。这批南下电影人通过改编中国传统民间故事,拍摄出的厦语电影既满足了慰藉东南亚华人因为无法回到母国,而产生的思乡之情;同时,这批电影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在电影中寄托了他们对于母国的“国族想象”[1]。而厦语电影正是通过对中国民间故事的改编,建构了一个遥远的家国历史、传统的中国伦理道德,充分满足了观众对母国的怀念与想念。
以厦语电影《圣母妈祖传》(1955年上映,导演:周诗禄,编剧:凌汉,主要演员:江帆、黄英、凌波)为例,在这部电影里,改编的是流传于福建沿海地区的林默娘的民间故事。在这则故事里,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孝”,以及仁善的思想,得到了强烈的体现。导演和编剧对这则故事进行改编时,基本沿用了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情节故事,并与民间故事中所体现的价值观念高度吻合[1]。下表体现了这两者之间的对比:
在民间故事基础上改编而来的《圣母妈祖传》,对于身处东南亚国家的华人观众而言,是一种坚决的“异化”,是忽略了观众身处国家的文化因素的影响。电影人与观众一起,通过《圣母妈祖传》完成了对那个已经逝去的家园的“国族想象”[1]。
(二)归化: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厦语电影对于民间故事改编的“异化”,使得影片充满了浓郁的思乡情怀,满足了东南亚华人中的闽南族群对传统文化的精神需求,寄托了他们对囿于政治因素限制而无法回归的家乡故国的美好想象。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而言,此类厦语电影也在无形当中,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发展、再延伸。
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东南亚华人群体除了思念故土,渴求充满传统文化特性的厦语电影,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时空环境有了更深切的切实体会,自觉或被动或被迫地受到所在国的文化环境影响。他们对于厦语电影产生了新的要求,迫切希望能有反映当下生存状态的电影作品出现,以寄托情感、满足情绪宣泄。由此而起,在厦语电影发展中后期,对于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的“归化”改编逐渐兴起。
民间故事改编的“归化”,使得厦语电影最大限度地适应观众所处环境的特点。以厦语电影《弃妇沧桑记》为例,它虽改编自元高明创作的南戏《琵琶记》(脱胎于民间戏文故事《赵贞女蔡二郎》[7]),以该戏为原型进行故事设计,但在改编中充分考虑到了观众所处时代的特征,将影片故事的发生地搬到了现代的香港,男主角、女主角都成为现代的人。影片与原故事相比较,不单是时空环境、人物设定有了改变和调整,而且对于结局以及所体现价值观念等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改编,以期能用这种“归化”的方式,获得更多东南亚华人群体的认同。下表是对电影与原作戏文之间的比较。
从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弃妇沧桑记》这部影片实现了“归化”的目的,尽量地贴近现实生活、实际情况,以适应观众所处环境的特点。和近代飘零海外的华人由于社会网络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导致道德的冲突以致家庭变乱的现实处境遥相呼应,表现了华侨妇女对自己婚姻关系不稳定状态的潜藏恐惧。《弃妇沧桑记》通过对《琵琶记》故事的“归化”改编,迎合了当时观影群体的内心需求,可以说,厦语电影对民间故事的“归化”改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当时电影人的必然选择。
三、“异化与归化”的现实意义
厦语电影的出现,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厦语电影在东南亚的兴盛,可从马来西亚历史最为悠久的华文报纸——《南洋商报》登载的厦语电影消息中以见一斑。每逢厦语电影新片上映,《南洋商报》均做映前报道和广告。遍查《南洋商报》(1953—1959)七年间的资料,大致可以统计出,新马(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地区首映的厦语电影共计242部[8]。这一时期涌现的厦语电影,借鉴改编了众多的民间故事。民间故事在厦语电影中的表现,不论是异化还是归化,都是时代特征的反映。
时代永远处在改变之中。20世纪中期以后,“作为移民及其后裔的东南亚华人,逐渐成为当地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2],这一身份变化对华人的政治、文化身份认同产生了巨大冲击,文化消费也相应有了深刻的变化。到20世纪末期,东南亚华人在身份认同上已经明显“去中国化”,华人文化逐渐呈现脱离中华母体的趋势[4]。老一辈华人故去,到了“华二代”“华三代”等后裔,连华语都不再操持,更遑论接受那些深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消费——不论是文化产品,还是文化服务。但民间故事在厦语电影中的异化与归化,其所体现的特点和经验做法,对于当下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实,中国在东南亚以及全世界影响力凸显,华语价值空前提升,传统文化得以被再次重视和加强,东南亚华人也有了重新认识来自中国的文化消费的渴望。从民间故事的归化与异化来看,一方面要能保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正面向的价值观念的优势,另一方面又能融入所在国文化环境中,并进行相应改造,最终掀起东南亚华人的文化消费风潮。如前述厦语电影《弃妇沧桑记》为例,它在电影宣传时就打出口号,“演变成最现实的故事”[9]。这类故事进行“归化”改造后,符合当时的社会文化特征,因此影片受到了当地华人的欢迎。
四、结 语
《梁山伯祝英台》这部厦语电影,当时上映时的宣传口号是“轰传闽南脍炙人口,十足地道厦语对白,妇孺听得懂”。[10]在这句宣传口号中,所谓“听得懂”,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用的是“厦语对白”,也就是闽南语方言,对于那些来自闽南的华人群体而言,那是他们的方言母语,自然听得懂影片的对白语言;二是指对于故事情节的理解,以及由故事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念,观众能够看得明白,领悟得到。对于后者而言,一批改编自民间故事的厦语电影,对原型故事进行了“异化”或是“归化”的处理,目的就在于为东南亚华人群体的观众服务,真正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异化与归化”,不论是哪种形式,最终都是由电影这个文化产品所决定的;“异化与归化”所体现的作用,对于实现推动文化“走出去”的目标,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