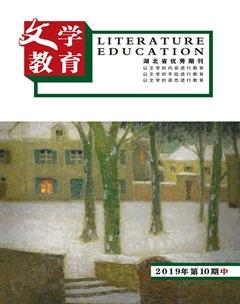《秦腔》中引生形象的精神分析学解读

内容摘要:《秦腔》是贾平凹代表作之一,其中的叙述者“引生”这一“疯子”也是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形象之一,本文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切入,以作品中与其形象的“自我”、“本我”、“超我”相关的叙述,从引生的疯子身份、不顾危险的本能追求、生存的理性约束要求、疯子的超我抑制方式等四个方面对其形象加以分析和解读。
关键词:精神分析学 《秦腔》 “引生”形象 本我 自我 超我
贾平凹作为当代重要的主流作家之一,其小说创作成就突出。有研究者将他的小说创作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这三个研究时期是一九七八——一九八四年,二是一九八五——一九八九年,三是九十年代以来至今”。[1]在其创作的第三阶段,即上世纪90年代至今,“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索”。[2]小说《秦腔》中引生的成功塑造就是这种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索的范例。因作品中引生与他人的对话、大段的心里描写以及作者给他设定的“疯子”身份,都透露出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对精神分析学地运用,因此,以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切入来研究这一典型形象,不仅是有效方法之一,而且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作家的创作方式与作品内涵。
一.引生的疯子身份
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佛洛伊德认为,人的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是本能和欲望。“自我”出于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是理性控制。“超我”由道德和良心组成。“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更是人格系统内部3个部分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结果。当自我能很好地平衡这三者关系时,三者和谐同一,人格便处于正常状态,人的精神就健全;当自我失去对本我和超我的控制时,三者之间的关系无法平衡,系统便陷于紊乱状态,人格就不正常,发展到极端,人的精神就失常。”[3]这一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引生的“疯癫”。“疯癫”就是精神失常,人的行为不受理性控制。表现在引生身上,就是他不受社会规范的约束,行事荒唐,想法怪诞,经常出现幻觉。比如,把一颗牙齿种在墙角并认为它会长成一棵树;能感觉到风驾着自己在飞;看到白雪走路是有一溜儿、一溜儿的莲花等等。
作者塑造“疯子”引生这一形象,给予他的是一个悲剧的定位。引生生活在清风街,而清风街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如对土地的认知上,夏天义就说过,土地是农民的根,离了土地农民就不是农民了,就什么也不是了。而夏天智则极力地维护着家族的礼节和秩序。在这样的环境里,人被要求为人处事都要合规矩。像引生只配和要饭的在一起,他不能爱白雪,连想也不能想,想了就是不道德。他只能“安分守己”,才能被清风街认可并接受。但实际上他的行为却因爱恋白雪而荒唐怪诞。白雪结婚前,他爬到树上去偷看,听到她结婚的消息时哭晕过去,白雪结婚后他依然不死心,甚至去偷胸衣,结果直接导致阉割自己的悲剧。促使他完成这些行为的是他人格结构中的“本我”本分,是他自己与生俱来的本能冲动。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类具有本能的性欲冲动,但在性欲这场灵与肉的战争中,“灵”被置于道德高度,而“肉欲”则让人觉得羞耻,被认为龌龊而加以隐藏。这种羞耻感和隐藏行为则是人格的“自我”和“超我”的抑制结果。但引生却将这种本能冲动不加隐藏的暴露出来,这时候他人格中的“自我”部分,明显强于“本我”和“超我”部分,这种不协调让他的行为变得疯癫。
引生的悲剧人生除了有关他人格结构上的“本我”、“自我”、“超我”三个部分的失调所导致的他的疯癫外,还有来自他所处社会环境的因素,清风街弱者的地位,使他只能任由夏天智,夏风这样的强者侮辱与损害。作者塑造这个人物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不仅从心理角度透析了人物在灰暗的环境里,“自我”、“本我”和“超我”的失调所导致的悲剧性命运,而且也从客观社会环境出发,控诉了传统思想固化对人物悲剧性的加深。
二.不顾危险的本能追求
引生的疯癫最直接地暴露了他人格中不受理性和逻辑制约的一面,即不具有道德因素的“本我”本分。“本我”即原我,是指原始的自己,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是人格结构里面不讲道理的一部分,‘它迫使个人去作为”。[4]“本我”的目标是求得个体的舒适、生存及繁殖,它是无意识的,不被个体所察觉。引生是一个本能意识很强的人。他对欲望直白地表达,不够理性的行为,对不惜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快乐的追求,幻想、幻觉、梦等等,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本能需求。在作品中,大家都认为他是个疯子,并且会时不时“疯圆”。但其作为一个男性未婚青年,有着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本能冲动。他瘋狂地爱恋着清风街最漂亮的女子——白雪。他只因为别人在背后议论了白雪而用刀子割去人家柿树的一圈皮,让树慢慢枯死;为了能见到白雪,每天黄昏时偷爬上桑树,甚至失足从树上掉下来跌破嘴;听到白雪和夏风要结婚的消息而哭晕;一见到白雪,行为就不受控制,就发痴等等。正是这一系列的荒唐事,坐实了大家对他“疯子”的判断。而引生之所以愿意这样做的深层原因便是对白雪的爱以及性爱臆想,这种性欲要求,正是源自他潜意识里面不能抑制的本能冲动,是个体生命的性本能体现。所以说“爱不过是性本能以性满足为目的的对象投注”。[5]只不过因为他的疯癫举动与其他人的隐秘相比,他的“本我”冲动表现得更为直接。
除了对白雪的爱恋体现了他的性欲本能之外,他作为一个社会人,对团体的群居本能也是先天就具有的。群居本能又叫群聚性,“这种群聚性,从生物学上说,类似于多细胞结构,并且仿佛是后者的延续(按照性力理论,它是源自性力的倾向的进一步表现;透过所有同类生物,以愈益复杂的单位结合起来而得以体现)。如果一个人独处,他会感到不安全。”[6]引生是个孤独者,尤其表现在精神上。他在他爹死后便孤身一人,爱恋白雪却得不到回应,在别人眼中“疯子”的身份又让人们不愿亲近。夏天义在他生活中的出现或者说是他主动地靠近夏天义,都是他另外一种求得个体生存本能的体现。孤独是痛苦的,为此,在情感上受到伤害的他,主动去寻求能够消解孤独与痛苦的人或物。夏天义就是其情感寄托的人物,这使得他潜意识里将其定义成父亲的形象。基于此,当夏天义要他跟自己走时,他毫不犹豫就去了,并“鞍前马后,给他支桌子,关后门,端吃端喝,还说趣话,一直跟到了他去世。”引生潜意识里的这位“父亲”的存在弥补了他亲情的缺失,淡化了白雪带给他的痛苦,弱化了他的孤独感。同时他看到了夏天义具有的号召力和,他觉得只要紧靠夏天义就能融进集体当中。这表明他不想被敌对,被孤立,他积极主动地向团体靠拢,这是他群居本能的体现。
然而“本我”唯一要求是获得快乐。这表现在,引生作为弱者在经常遭受伤害的同时,他又在伤害着其他的弱者同伴。他这样做不是想要报复,发泄或蓄意伤害,而只是出于无聊或者潜意识想寻求快乐的目的,如煽动武林和陈亮打架。这两人与他一样,都是清风街的弱者,引生与他们没有对立的必要,这样做是因为他不能在其他地方获得快乐,而只能在这个过程享受到获得快乐的满足。因此,他的行为不具有价值、伦理和道德因素,只是一种追求快乐的愿望的支配。
三.生存的理性约束要求
引生作为一个弱者,他的“本我”的实现是有限度的,时而疯癫的行为是他本能冲动的实现,但是,他对团体的需要与对认可、接受的渴望也是强烈的。所以在实际生活中“自我”的存在对他也显得很重要。“人要生存就不得不考虑外界的现实(环境),不是靠适应它就是靠支配它来从中获取所需的东西,这种人与外界之间的交往要求,形成一个新的心里系统,这就是自我。”[7]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秦腔》透过引生的眼睛看到的是一些生活碎片,清风街的故事都是一群平凡人的生老病死。故事的叙述人引生,他是个时好时疯的人,他深爱着白雪,却也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他忠心地追随着夏天义,却并不是事事都认同他的做法。清风街的人从来都不重视他,他也欺负那些与他一样的弱小者。他的疯癫不能作为他为追求快乐而恣意妄为的保证,所以为求得生存,他必须获得人们的认可。
疯子引生爱着白雪,白雪却嫁给了夏风。俊奇对他说“不该你吃的饭,人家就是白倒了,也不会给你吃的。”为此引生生气了,并从此不再搭理俊奇。但他心底却认同俊奇所说的“门当户对”,所以他也尽力压制着对白雪的爱。虽然引生的行为有时会给白雪造成困扰,却并没有实质性地妨碍到她的生活。在这种关系中,白雪所代表的“受伤害者”周围聚集了一群保护者,他们作为正义的一方,谴责与声讨着以引生为代表的作出流氓行为的“伤害者”。在现实社会中,“伤害者”是孤独的,因为处在道德的对立面而被大众所排斥。当他们的行为一旦让人受到伤害,就会遭到大家的一致谴责,甚至被放逐,被迫离开团体。引生他害怕与群体对立,害怕孤独,因而为了不被放逐,不被排斥,正是因为考虑到了自己的生存处境以及他内心深处有对孤独的害怕与对被放逐的担忧,他只能让自我的理性发挥最大的克制。
引生生命中重要的人除了白雪还有夏天义,在引生心里,他把夏天义当父亲对待,这里既有他“本我”的个体本能的体现,还有更具现实意义的自我生存需求。引生在清风街没有一个亲人,他精神上的孤独和物质的贫穷,加之“疯子”的身份以及平日里所作所为,使他成为被大家看不起并排斥的人,以君亭为代表的热衷于市场经济的新一代农民,对他的作践表现的尤为明显。而具有曾经的老主任和夏家家长双重身份的夏天义,在清风街具有一定的威信。这使引生选择跟随夏天义。他与夏天义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为了满足自我的现实需求,而互相利用的关系。夏天义要淤沟,不仅需要人在精神上支持他,还需要人力来帮助他。引生追随他,不仅可以获得父亲般的关怀与庇护,还可以通过劳动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获得大家的认同。同时,还可以通过劳动来“忘记白雪带给我的痛苦和村人对我的作践。”虽然环境对他不公,但为了生存他就不得不适应现实。
由此可见,引生虽被他人定位为“疯子”,但更多的时候他是有理智的,他用直接的、质朴的眼光看待事物。他自身虽然有比较强烈的本能冲动,但不会无所顾忌地只去追求本能的满足,作为一个社会人,在当他有足够理智时,他人格结构中的“超我”就会极力发挥作用,评判和限制其思想及行为。
四.疯子的超我抑制方式
引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疯子,他十分清楚他对白雪的爱不仅不会被社会所理解支持,相反还会让自己陷入极其糟糕的处境之中,他在意自己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形象。虽然爱白雪,但只要在足够理智的情况下,他不希望其他人知道他的心思。所以在偷白雪胸衣被抓住后他说:“我的心思,它给暴露了,一世的名声,它给毁了。”也就是说引生这个大家眼中的疯子,在他不疯不痴时,他完全有着一个正常人对尊严、名声的需要。除了对个人尊严,名声的维护之外,来自清风街其他人的对他的威胁,与被伤害被驱逐的担心也使他感到害怕,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他在偷了胸衣后又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阉割自己。爱恋白雪是引生作为一个青年男性的本能冲动,偷胸衣是这种本能冲动的“本我”体现,而在被抓被打之后阉割自己则属于“超我”抑制。精神分析学认为,“‘超我它监督自我的行为、思想及意图。自我的活动受到超我严格的禁止所限制”。[8]“超我”遵循的是“道德原则”。引生在冲动之下偷了白雪的胸衣,暴露了对白雪的性欲,他所受的文化传统暗示他这是不道德的。这样的行为让他感到羞愧。所以,在痴狂中他阉割了自己。但即便如此,并没有阉割掉对白雪的欲望,他只是阉割了这种欲望能够最直接表达的生理载体。所以,引生的这一举动多半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自我惩罚,是对自己本能冲动所酿成的错误的一种惩罚,也是对“受伤人群”的一个交代。通过这一动作,他在表达他认同大家的看法,自己做错了事情就应该受到处罚,并且以后不能再犯!“超我”的功能就在于控制和引導本能,以及对个人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加以约束。引生的自我阉割,虽然是在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发生之后,而且阉割也不是“超我”抑制的正确方式,但这种残忍的方法,却正是属于他自己的赎罪方式。
引生的这种“超我”抑制不仅表现在这一阉割动作上,还扩展到对待白雪家人的态度上。夏天智家的所有人,四婶,夏天智,夏风,夏雨都曾践踏过他的尊严,但在进行内心的自我判断时,他得出的结论是,报复他们是不道德的,而这种想法在对待武林陈亮之流时则是没有的。
总之,引生作为《秦腔》的叙述人,他是一个时疯时痴的青年,在清风街是个遭受侮辱与损害的弱者。他有着正常人一样的人格结构中“本我”的对性欲的需求,对团体的归属意识,“自我”的作为一个社会人,而对自己的本能冲动进行克制的需要,还有“超我”的对自己思想及行为的判断。但是,在他的身上有时候失调,即当“本我”部分过强,“自我”和“超我”部分较弱时,他就会做出疯癫的行为。这种失调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内部原因,而他所处客观环境则是外面原因。作者选择了一个疯子作为故事的叙述人,疯子质朴的、纯粹的、不带任何情感偏好的视角,客观公正地再现了故事发展的始末。透过叙述人的悲剧命运,作者暗示了作品故事的悲剧性结局。对引生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作者创作方法的独特之处及其作品内涵的丰富性。
参考文献
[1][2]符杰祥,郝怀杰.贾平凹小说二十年研究评述[A]//雷达.贾平凹研究资料[C].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490、495.
[3]张传开,章忠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评述[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134.
[4]马起华.精神分析与政治行为[M].台湾.华冈出版部,1973:44.
[5][6][8]弗洛伊德 著,杨绍刚 译.弗洛伊德之性爱与文明[M].台湾.旭升图书公司,261、152、75.
[7]张传开,章忠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评述[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139.
(作者介绍:陶君艳,信阳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助教,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