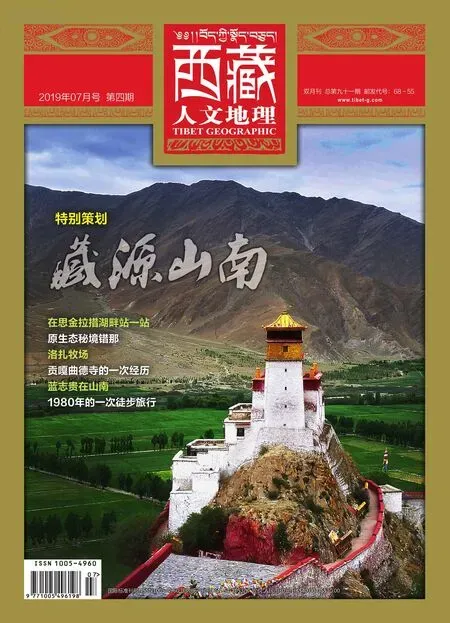理想和希望的彼岸
——西藏油画《渡》
撰文于小冬
这张画1997年已有较成熟的构思,是几次在桑耶寺渡口乘船过江的经历激起的创作冲动。一船人渡江是为了去对岸朝拜桑耶寺,桑耶寺是莲花生大师创建的,是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
从1997年起我便开始了资料搜集的准备工作,从小构思稿到最后的草图,不知道画了多少次。1999年完成了素描稿的第一稿,经一段时间的沉淀,越发感到这张草图问题很多,最主要的是它缺少人物情绪上浑然天成的统一,没有我所希望达到的看似幽静又深藏激动的丰富性。
2000年底我专为此画在冬天朝圣者最多的季节重返西藏,在雅鲁藏布江渡船上过了十几天。那些在江边的日子,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反复的乘渡船去北岸再返南岸。和一批批的朝圣者挤在船上,亲身体验了朝圣者们对信仰的虔诚。
渡船过江要两个多小时,这一段时间朝圣家族的长幼们总是最寂静的。他们看着远方,目光中有迷惘和苍茫,那是远不可及的,连孩子也都是一脸的庄严和坚定。
在一个傍晚的时刻,太阳落到山边的云层后面,唯对岸的远山,在太阳的余晖里闪着如赤金炽铁般奇异的光辉,金灿灿的,那是对岸最后的一片阳光。那也是我要的时刻!
在渡口小屋中的烛光下,我在日记本上勾画了无数次小草图,推敲构图的整体气氛,画面在脑海里逐渐显现出来。
也许是白天想的太多,以致一次梦里清晰地看到了这张画完成时的效果。这次梦中所见对后来色彩稿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那个梦境至今难忘。
2001年初经多次修改,一张整开纸的第二幅素描稿终于完成。我还记得面对一张空白的大画布,耳边伴着西藏古老民歌的吟唱,内心涌起的激情和冲动。我一直担心这股激情能凝聚多久,是否能一直保持这种良好的状态到制作的最后,在两年的创作时间里,也多次反问自己,这似乎是一百年以前苏里柯夫时代激情的延续。在今天它是否还有意义?我的信念是对古典精神的坚守,我认定自己走的就是一条正途。
这张画是目前我所作尺寸最大,也是用时最长,花心血最多的作品。两米高,三米七长的尺寸暗含纪念,二十岁是我刚到西藏的年龄,三十七岁是我开始画这张画的年龄。
两年来,《渡》,在时而艰难、时而快乐的工作过程中一点点地呈现出来。由于家里画室空间的局限,我看到的总是一张张的脸,几乎不知道这张画的具体面貌到底什么样。有时感到这张画像是永远也画不完了。直到我停止了一段时间的工作,把画拆下内框,卷到楼下重新绷起拍照的时候,才得以远观这张画,发现它终于完成了,这正是我想要实现的最终效果。
我想,西藏给我最重要的东西是:西藏的高山大川与和谐于自然的宗教文化,为我建立了宏大与深厚的审美参照。我选择画西藏的原因是,在西藏人身上还保持有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人类品质,善良、虔诚、简单,和谐于自然也和谐于心志是西藏对我的启示。
在西藏的十三年,我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代。艰苦环境的历练能使人变得坚强,与信仰佛教的藏族朋友交往,能使人变得善良。对西藏人、西藏文化与西藏自然的热爱,自己青春时代记忆的感情,对佛教世界观的认同,使得西藏人的肖像和群像成为我作品的主要题材。
但是西藏特色是不应被刻意强调的。我注重人的本性和生命的尊严。
我多是用照片和速写资料作画,照片提示我对那个生命存在的强烈记忆,最终的画面必能远远超越照片,一个个生命在我的眼前活起来,我几乎能感觉到他的呼吸、听到他的声音。这样的幻觉时时产生,这是一些无比幸福的时刻。肖像的魂在笔下总是漂浮不定时现时隐,一旦出现必牢牢抓住,他是容易跑掉的!
肖像画是属于善良画家的题材,没有关怀就没有感人的肖像画。被画的对象必须先成为我的朋友,要成为朋友就要通过一起生活,做到相互了解和信任。
我只画那些接纳我、配合我工作、允许我画的西藏人。在画中挖掘自己本性里的佛性和古典精神。我崇尚平实、敦厚的画风,认定最直接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相信“返璞归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这个道理。
《渡》,是最近十几年来我最重要的创作之一,也是我献给西藏亲人的礼物。

《渡》(于小冬/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