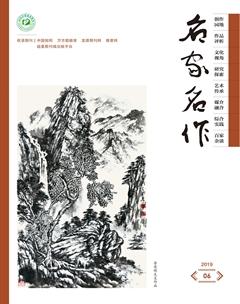贯云石散曲诗歌中的永州情结
赵凌峰
[关 键 词]贯云石;散曲诗歌;永州情结
在元代屈指可数的几位文学大家中,有一位与永州有着“剪不断、理还乱”联系的文学名家,叫作贯云石。贯云石(1286—1324),全称为贯小云石海涯,表字浮岑,以酸斋号闻名于世。他是元代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能够熟练地运用汉语进行创作并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少数民族作家之一,明王世贞在《曲藻序》里曾将之誉为元曲的首席代表作家,后人推崇其为“元曲泰斗”,其在散曲、诗词、古文、书法、声乐等多种文艺创作中均有建树,才华横溢。据《元史》的记载和《贯公神道碑》的描述,有人曾依古代礼仪常识推测,贯云石“承袭父爵”,“镇永州”长达五年之久。在其可考的散曲、诗歌作品中以永州的风土人情、民俗故事和自然风光为创作对象的计有散曲九首、诗歌二首,多为男女情爱之作、情怀之吟,整理其“署理永州”期间作品,有几个重要的特点。
一、永州的明媚山水点缀了其清新旖旎的创作风格
贯云石“镇永州”五年间恰是其青春成长的五年,从弱冠到青年,坐镇一方,意气风发,官宦之余,长期沉浸、徘徊于永州的山水之间,得柳宗元《八记》之韵味,感元结碑刻之工整,上感舜德之神化,中有帝妃之婘属,其间作品多呈清丽的风采,对其归隐后淡泊疏志多有影响。
例如[双调 ·水仙子 ]《田家》: 绿荫茅屋两三间,院后溪流门外山,山桃野杏开无限。怕春光虚过眼,得浮生半日清闲,邀邻翁为伴,使家僮过盏,直吃的老瓦盆干。(其一 )
茅屋青青、溪水潺潺,竹林茂盛、野杏浪漫,所居山野情趣,主人好客热情,有“春光懒困依微风”的慵懒、清闲和自足,这样的生活恰恰是作家向往的田家风味。唐代柳宗元曾在永州创作了一首《渔翁》,相比都有超然物外、逍遥恬淡之悟,都是永州山水给予作家的创作灵感。贯云石辞官,归隐杭州,以洒脱旷达之意抒写飘逸俊放之愿,展现了天人合一的心态。永州“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山水给予了创作者无限的创作感悟,赋予他们清新自然的风格。
二、 永州神奇的历史典故构建了其意境深远、形象生动的写作特色
舜帝与娥皇、女英的历史典故事传诵千古,其凄美的爱情故事、浓烈的别离情怀、隽永的生死相依成就了许多名家的经典吟唱,“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在名家的吟唱中总是神采奕奕。宦居永州多年的贯云石对舜帝的爱情故事也应神往之,在作品中就难免不会随手拈来。
如其撰写的《别离情》:吁别离之苦兮,苍梧之野春草青,黄陵庙前春水生。日暮湘裙动轻翠,修竹亭亭染红泪。又闻垓下虞姬泣,斗帐初惊楚歌毕。佳人阁泪弃英雄,剑血不销原草碧。何物谓之别离情,肝肠剥剥如铜声。不如斫其竹,剪其草,免使人生谓情老。
贯云石将娥皇女英千里寻夫的典故和霸王别姬的历史典故自然而然地引入诗歌中,营造了生离死别的悲愤和无奈,渲染出别离的凄凉和忧伤,将人世间那种离别情思之苦状描绘得淋漓尽致。其中的“肝肠剥剥如铜声”,极尽人生悲苦之描绘,再加上“斫其竹,剪其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来反衬相思的难断,更增加了全诗情感上的凄风苦雨。“日暮湘裙动轻翠,修竹亭亭染红泪”,将娥皇、女英寻夫不得、天人相隔的悲痛和不舍描写得感天动地,令人不由为这段爱情典故而揪心。贯云石在诗歌中善于借助典故来深化诗歌的内涵、简化诗歌的语言,强化了诗歌人物形象刻画的生动性。
三、永州瑰丽风土人情铸就了其奔放豪爽、壮怀激烈的诗歌风貌
自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了“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就给这片土地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在永州谪居10年,写出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和《捕蛇者说》等,历代文豪如司马迁、蔡邕、李白、杜甫、李商隐、元结、颜真卿、欧阳修、苏东坡、寇准、朱熹、陆游等都曾仰慕前贤而游永州,或咏诗称颂,或撰文述志,或提笔摩崖,留下大量“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诗文、胜迹。元代的贯云石虽然在此“镇守”,但骨子里豪放洒脱、不拘一格的文人气节还是让他去领略前人的风采,并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贯云石的永州情结是其宦居永州多年的结果,也是永州绮丽的风光、神奇的风情、绚烂的风情对其的熏陶和感染。永州的五年是贯云石成长的五年,后来虽然挂冠而去,但其创作的风格都馔刻了永州的风骨。
参考文献:
[1]张维民.论贯云石对汉文化传统的接受[J].新疆大学学报,2006(6):23-24 .
[2]蒋书红.贯云石的湖湘印迹与湖湘情结:以其诗歌散曲为中心[J].中国韵文学刊, 2016(3):86-91.
作者单位:永州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