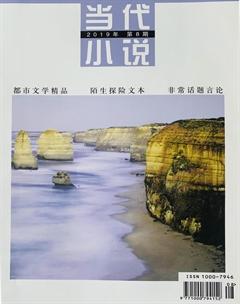海鸥飘飘
王守军
斜倚着拦潮坝,我恣意地朝坝体撒尿,一股股酒腥臊味逆着海风蹿上来,偶尔有风头折下去窜入裤筒,舒服得让人想飞。
我笃信海鸥不是鸟,是一群化成飞鸟的巫师,连着蓝天和大海的巫师,它们嘎嘎的叫声里充满了心事。海鸥们扇动羽翼,把大海撩拨得浪起浪涌,深醉了般七荤八素地晃荡,海浪被它们蛊惑着,愚蠢地拿着脑袋往拦潮坝上乱撞,就像昨天五里香饭店里那场打斗。
肥皂喝了酒,不服输,一次又一次向我扑过来,被我顺手牵羊连摔四个仰八叉。人群中一声喊,方才把双方喝退。这喊声音量不高,内容却让大家忌惮:蓝海鸥来了!
蓝海鸥是油田公司派给我们的工长。说实在的,蓝海鸥有啥可怕?!可是,我打心眼儿里怵她。她管理我们土方队,知道我姓牛,不叫我名字,见面喊我公牛。工友们打趣我,说,蓝海鸥这是把自己当成母牛了。我们是由施工队从各地招来的农民工。蓝海鸥头一次来我们队上时,口头语出乎我意料:操!还能这样。说着,不管对面是谁,飞起一脚踢到对方小腿迎面骨上,钻心地疼,这已经有好几个工友领教过。一个操字,我们这些民工有她在场时都不好意思往外出溜,她张口就来。偏偏,人长得柳眉大眼,脸面白皙,周身匀称,和她的粗鲁口头语一点儿都不搭。与小母牛绰号相比,我们更愿意偷偷叫她小辣椒。大家说,油田的女人都这样,骨子里是个男人,只是生错了模样,所以不懂得柔情似水。
肥皂看上了五里香的服务员小翠,昨天晚上喝酒拿钱让小翠陪桌,喝醉了就抓住人家姑娘的手不撒。小翠偏偏爱凑到我们桌上,从我左右靠过来靠过去上菜上酒。同伴犬子偷偷和我说,小翠暗暗打听我的婚姻和家庭。肥皂吃醋,扬言要给我点颜色看看。
肥皂是另一个工程队的,也归蓝海鸥管。肥皂有一回喝醉酒耍赖早晨不起床,蓝海鸥一个大姑娘家家的,愣把他从梦里被窝中光着腚拖出来,浇上一舀子凉水。昨天晚上,可能就是那舀子凉水的余威还在,肥皂一伙儿也立刻撤回。
我还没有撒完这酝酿了一宿的尿,后面犬子跑过来,喊:快点哥,蓝海鸥来了!
我抓紧收兵回营,胡乱扎上腰。远远看见蓝海鸥一身蓝色工服,脖领扎了一条红色围巾,围巾在海风中跳舞似的飘来飘去。她脸盘像一朵芙蓉,美得人心里直 蛹。看看,辣椒美起来根本不是蔬菜,是一朵生动撩人的花儿。
一见面,她却捂着脸说:操,咋能这样?
我晕,又怎么了?我不知所措,时刻提防着她的三寸金莲发怒。她今天穿的可是皮鞋,这很少见。眼睛盯着她的脚,我问:咋了?青工长。
操!重新扎扎腰。她的笑带着调侃。
我低头一看,脸顿时臊红,刚才匆忙间,腰没扎好,红绒衣一角从开气儿里探出来,十分扎眼。人家姑娘家,这多不好意思!
故意的吧?她皱皱眉,并没有生气,笑着,语气倒还平静。
她一说话,我就紧张,一个没抓牢裤腰,裤子反而掉下去一截。
操!我说故意的吧?!你这晾武器呢?高声刚落,抬腿就是一脚。该来的还是来了!
我的天,这一脚冷不防疼得我咧嘴哎呀一声,双手抱住小腿迎面骨原地转了三圈儿。这娘们儿属驴的啊!我的裤子徹底落到脚踝上。
一旁的人都哈哈笑。
我手忙脚乱提上腰带扎紧,说:不敢!
有啥不敢?昨天晚上打架够英雄啊。
是他挑衅的,我还手。
影响太坏。为一个酒店服务员,争风吃醋,败坏社会风气,认罚吧!
我等着下文。
打包,今天滚蛋!敢在我手下耍横。
我一下了,爹娘等着我挣钱盖屋呢,一身热汗腾地起来。我抹一下脸,求道:工长,别开我,咋罚都行。
蓝海鸥并不回答我,煞有介事地背起手,瞅着我问:多大了?
二十一。
什么学历?
初中。我不解,有按学历和岁数惩罚人的吗?
体重?
一百六十五。
身高?
一米七八,净高儿。
她点点头儿,又问:昨天推了多少方土?
犬子赶紧帮腔:牛哥推得最多,四十五方,顶一辆十二的拖拉机。
比肥皂还多七方,真是一头公牛。今天,你给我干到五十方,我到大队给你说情去,要不然滚蛋回家!
还有,大家往近处凑凑。蓝海鸥招呼大家,我们齐刷刷凑过去像聚在一起的花瓣,把她围在里面,她花蕊似的仰着脸说:气象局又预报今晚有海啸,公司命令你们上午推土方,下午搬家,所有的窝棚都搬到六号公路西面。搬迁时,来来回回注意交通安全。夜里一有风吹草动,立马攀到六号公路上等待救援。
一旁人说:什么海笑海哭的,我们不怕!
操!不懂就听从命令。谁敢违抗命令,弄死你!干活去吧!
大家散开。
蓝海鸥回头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看我,眼睛里好像有很多内容。我意会到她叫我过去,便看着她的脚凑过去。
今天小翠可能来找你!我目光游到她的脸上时,她已经扭过脸去,话没说完就走了。
她正对着六号公路往前,一溜足迹就像一条带箭头的垂线正画过去,风从背后吹着她的头发,撩来撩去。箭头越来越小,一直没回头。
六号公路是条高六米,宽双向四车道的公路,在距离我们的窝棚一里半地的西边。脚下这片土地上在未来几年内将隆起一座现代化的港口。
蓝海鸥一走,大家都轻松了。犬子揪揪我衣服,严肃地说:你那一呱哒,全被蓝海鸥看去了,看她表情好像没啥不高兴。
我不这么认为,这是多么丢人的事情!
上午歇工时候,远远见小翠走过来。她果然来了!姑娘身材苗条,眉眼周正,个子比蓝海鸥高出半头,看上去算是个朴实的北方女孩。她径直走近我,看着我的脸低声说:你能娶我吗?
工友们嬉笑着看我。我一阵懵懂,觉得小翠话里有话,不能应她,就摇摇头。
我是个干净女孩,最起码现在是。
我说:我不知道你啥意思。
我初中毕业,本可以上高中,怎奈家庭不济,母亲常年卧病,我得挣钱给她看病。你要是看中我,我给你留着身子,要是没那意思,有人六十块钱一宿等着我。我就不要爱情了,光要钱。
她的话就是海啸时的大浪,砸得我蒙头转向。我没想到她这么大胆泼辣,活生生又一个蓝海鸥。不过,悟得出来,她是故意这么说给我听的,目的是让我重视她。我不知道咋回答,我压根儿没想过娶她做女人,但是也不想让她这么把自己卖了,她的初夜不仅仅值一天多的土方钱。我说:你等等,我不可能这么快答应你什么。
她说:等不了,我妈等钱做手术。
她说完扭头走了。
我觉得她留给我的问题十分沉重。要是我答应她,她就要爱情不要老妈的命?要是我不应她,她就要老妈的命不要爱情?这个逻辑有些不合理,但她的表达好像就是这么个意思。内心深处,我确实不愿意娶她做老婆,她理性得有些冷,好像什么事情都有预料和设计,不像蓝海鸥整天就像一团燃烧的明亮的火。她把问题抛给我,弄得我和有罪似的。如果哪一天她堕落了,好像是我推了她最后一把一样。可是,我有责任拯救她?没有。对,我们没有责任拯救她,卖身是她自己的事儿。一定是那个肥皂作孽,操他娘的肥皂!
拿她跟蓝海鸥比较,完全是我一厢情愿,这事和人家蓝海鸥没啥关系。
犬子推推我,问:看样子她想以身相许?
我说:我没应她。
犬子又推推我:蓝海鸥也喜欢你。
我哂笑一声,心里有些满足地走开。说实话,我很希望蓝海鸥喜欢我,尽管她爱踢人。不过,一个农民工身份想人家蓝海鸥似乎有些过分。
时已近午,远处,肥皂晃里晃荡走过来。
他是朝我来的。打架?我不怕他。
肥皂肚子滚圆黑亮,走路架着胳膊,像一头黑熊。初秋的风有些凉,他还穿着半袖。他横眉立目地说:小翠找你了?
我偏偏刺激他,说:她要跟着我。
不等我说完,他截住话呵斥道:你,敢应?
我有啥不敢应!
他眉头一皱,猛地扑上来,趁我不备一下把我撂倒,挥拳就打。
犬子见我吃亏,急忙抓住他的胳膊,说:哥,哥,这么打,不仁义。你们比腕力,掰腕。
肥皂果然同意,从地上爬起来,说:吃了午饭,北边一里地拦潮坝那里一决高低。说完,倔驴似的走了。
午饭毕,我如约去指定地点。这里没有工程队,安静,没人打扰。
犬子跟在后头,边走边说:谁胜谁败得有个见证。再说,他要是带了帮手,你不吃亏?
我没理他。
渤海湾的海风带着潮腥味翻过拦海坝,吹在我身上,像一个无赖反反复复地纠缠,但是它的凉意却让我浑身充满力量。远处有一艘大船劈波斩浪航行,显示出一种勇敢和无畏。海鸥箭似的穿来穿去,叫声合唱在一起,和大海的涛声交响。一只调皮的海鸥从点点群鸟中分离出来,落在拦潮坝上,朝着我嘎嘎嘎叫几声,然后翩然飞走。它是示威,还是向我点化什么?
肥皂一人应约前来。他一声不吭,站好,伸出一只钳子似的大手,另一只手攥拳摆在身后,立在那里像一只伸着两只巨钳的大个儿蟹子,张牙舞爪。我也没话可说,脚头和他对齐了,右手迅速抓住他的铁硬的大手。
犬子说:听我喊,一,二,三!
他进攻,我防守。他用尽蛮力,推着我的胳膊往我侧面拽,我则力托千金,用上腰腿臂三合一的力量,稳稳地托住,抵销他推过来的力量。两个人的脚陷入湿土中,两只大手颤抖着在身体侧面角力。几分钟后,汗珠渗出来点缀在脸上。
犬子大喊:诓他!
我听得真切,左脚往后一退的同时,右手随之往身后一带,果然借到肥皂的推力,把他诓倒趴在地上。第一回合我赢了。肥皂看看犬子,没说话,又伸出手来。我示意犬子别说话,伸手相迎。这一次,甫一交手,我先发力,推着他的胳膊尽最大力气往侧面带,以防他诓我。渐渐地,我能感觉出我的力气要大于他,他在我的摆带中,后脚不稳定了,左左右右地点着几个小幅度来回后,身体变形倾斜,前脚再也支撑不住,挪了位置。前脚挪了位置就算输。他眼里渐生怯意,不过还是伸过手来,想再过一个回合。我越来越有信心,马上伸手相抵。这一次,我势如破竹,直接一鼓作气把他摆倒在地上。他躺在地上呼呼喘气,不起来,朝着天说:小翠归你了!
我回道:小翠归谁,你说了算?她愿跟谁跟谁。
那不行!小翠不归你,就归我,别人都是骗她的。
他的话令我大出意外。
肥皂坐起来,看着我,若有所思,一会儿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走了。
我朝他背后说:今晚有人想六十块钱睡小翠!
我和犬子快步回到窝棚,继续推土方。城里人一定都怕死,海笑海笑,都预报了好几次了,也没见大海笑。城里人听风就是雨。搬家是他们的事,我们不搬。大家意见很一致。
六号公路上车辆往来如梭,比平时忙碌很多,真的好像有啥事情。海面,海鸥一改平日云里浪上地潇洒穿行,幽灵般疯狂地舞蹈,叫声急促而凄婉,搅得海水煮沸一般翻滚。它们也害怕海啸的到来,才这般张皇?风中,海腥味加大了浓度。
下午又完成二十五方土,一天共六十方,蓝海鸥说啥也不会开我了吧?带着这种想法,晚饭后我钻进冰凉的被窝,一个窝棚十几个人很快进入梦乡。我有心事,一开始心里反复交替出现小翠和蓝海鸥的影子。狗皮褥子孝顺人,我很快全身温暖,汇入鼾声合唱。
梦里,我在海边追赶小翠不让她跳海,怕她淹死。追着追着却碰到了蓝海鸥,她拿着一只水桶,不言语,提起来把水浇入我的脖领,我感觉凉水从脖子一直流到脚跟,顿时一股冷凉从我的头顶窜到脚心。这是一股要命的寒流贯穿了我的身体,我忽然惊醒,觉得自己好像泡在水中,伸手一划拉,果然身边全是水。我一个激灵:真的来海啸了!立刻坐起来大喊:快起来,海啸来了!其他人多在半睡状态,一听喊,都稀里糊涂站起来,嚷嚷着找衣服袜子鞋子。只是一瞬间,海水没过脚踝,鞋子早不知漂到哪里,再过一会儿,海水快到膝盖了。海風在外面魔鬼似的吼叫,吹得窝棚晃动着呜呜直响,吓得人心里直哆嗦。不能犹豫了,快逃!我喊着往窝棚外钻:别找衣服,活命要紧,快跑!我站在窝棚门口方才感觉出海水海风的巨大力量,就像一群人站在身后不停歇地推搡。大家都一丝不挂往外挤,一个,两个,我一边数着人数,一边告诉他们逃生的方向。有个伙伴儿吓晕了,出门就朝大海的方向跑,我拉他不住,追上去啪啪给他两记耳光,他方才调转头朝六号公路的方向去。始终没看到犬子,我想,他那么机灵,或许早就跑了。海水快到臀部,我不能再等了,抓紧逃生。就在离开窝棚门口的当儿,脚腕儿被深深地劐了一下,然后一阵疼痛钻心而来。坏了!脚腕儿被海水漂过来的铁锨割伤了,海水一泡,伤口立时疼痛难忍,直钻心尖子。顾不了疼痛,我拼命朝六号公路方向奔逃。
六号公路上有一排路灯,路灯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大家跑着跑着,一长溜儿路灯却渐次闭上眼睛,路灯忽然熄灭了,我们彻底被光明抛弃。周遭一片漆黑,狂风裹着怒涛在身后肆虐、吟啸,天地难以分辨。海水已经升到臀部以上,好在海水还有一定的推力,但是越靠近六号公路越有较高的坡度,坡度的反作用力使得涌上来的海水形成返流,一波又一波海水冲到六号公路被阻挡,力量潜流回来,对冲着我们求生的挣扎。我的行动也愈发困难,右腿用不上力气,全身寒冷入骨,上下牙齿不停地叩响。往前看,六号公路上隐约有人慌乱走动,高声哆里哆嗦地问询,一定是同伴们有到达的。我忍住疼痛,双手扒着海水,艰难地向前挪。
忽然,一个黑影冲下六号公路,向海水里面扑过来,是犬子?渐近了,听到声音:公牛,你在哪里?傻牛,你在哪里呀?蓝海鸥声嘶力竭的声音。我明白,她冲进海水里,一定是找我,刚才我就有这种预感。我高声应道:辣椒,我在这里!她个头矮,海水已经齐了她的腰腹,这在她是冒着生命危险。她伸手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拽着往前。蓝海鸥的到来,无疑给了我莫大的力量。她猛一拽,拉疼我的右腿,我不由自主哎哟一声。我凑她耳朵上说:我受伤了,小腿被劙了个豁口,一走就疼。她二话不说,一低头钻到我腋下,把我的胳膊架到自己的肩上,拖着我和我齐头并进往六号公路趟。
好不容易挪到水边,海浪在海风的怂恿下一波又一波舔舐着六号公路的路基,涌上来的海水一推一拉,不让我们利利索索地攀登。蓝海鸥拉着我胳膊往上爬,走斜坡,我的右腿疼痛,用不上力,不仅如此,我全身一用力,伤口处也一阵阵撕裂。我想用双手加左腿爬,一个海浪扑过来把我压倒,我顺着斜坡下滑了几步。情急之下,蓝海鸥快速挤到我的身前,下蹲,弯腰搂住我的两腿,把我背起来,巴扎几步走不动,便双手着地,手脚并用趴着向上,这一会儿,她不是海鸥,倒像一只企鹅。往上走了几步,我才感觉到自己还是赤身裸体呢。终于,我们挪蹭到公路之上。她放下我,把上衣脱下来扎到我的小腿上,站起身来数人数,一数发现少一个人,急了,大声问:谁不在?说!人们相互打着招呼,最后确定,少犬子。
犬子!我哭着朝大海的方向喊。其他人也喊。喊声淹没在狂风和海浪中。
一辆车过来,车灯像巨兽的眼睛,贼亮,老远照出一个胡同,就像在漆黑中掏了一个白洞。灯光里,大家都没有穿衣服,除去蓝海鸥都是光屁股。我们疯狂地叫喊停车。车子眨眼呼一声过去,没停。蓝海鸥说:一群裸体猴子,谁敢停车?又过来一辆车,蓝海鸥招手试图截住,车子还是没停。其实,蓝海鸥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全身湿透,没有外衣,内衣紧裹在身上,头发凌乱,光着脚板,像个风尘女子,一般车子怕是也不敢停留。蓝海鸥嗷嗷骂:操他娘,停车——哦!蓝海鸥冷得说话结巴。她在我们一群裸体中转一圈,说:这些车辆昂,不是不乌管我们,都是有呕任务的。没没有好法——啊。大大家手挽手——呕摆成人墙——昂,强行拦车。妈的,再不走,咱们全都冻僵在这里。公牛,过来!蓝海鸥抓着我的手,我又抓住其他人的手。
漆黑夜里,我们十几个人光溜溜地排成人墙,雕塑般悲壮地横截在公路上,视死如归地等着下一辆车来到。
远处行来一辆车,到跟前吱地刹住,老天有眼,是带篷子的解放。司机不敢下来,可能是被我们一群裸体吓住了。蓝海鸥马上跑过去,拉开车门,喊:救命!这群人再不转移就冻死了。司机招呼上车。蓝海鸥把我拉进驾驶室,说:这这是个伤伤员。司机叹口气,说:吓坏我了,我以为一群水鬼呢。去哪里?蓝海鸥上牙磕下牙:最最近近的宾馆——唵!
拉到一家宾馆前,蓝海鸥进去交涉,专门腾出一间屋,扔一堆被褥进去,服务员回避,我们鱼贯而入。已是过夜三点,蓝海鸥让我出来一下。
我回去联系工服。蓝海鸥说着话,两胳膊抱在胸前,她有点冷的样子。
犬子找不到了!我披着被子哭。
她说:先别说这茬儿。你看护好这些人,不要出门走动。你的伤,我看看。
她蹲下扯开捆在我腿上的衣服,呀了一声。我低头看,见伤口一指宽五指长,豁口翻着,被海水泡得发白,就像一个贫血的大嘴唇不高兴地噘着。她说:这得缝合!
她说完转身就走,我立刻把身上的被子抡下来披到她身上,转身快速跑回房间。我想象着,她在狂风中奔跑被吹得摇来晃去的样子。
次日医院来人给我缝合伤口,打了针,留了口服药,让我静养。
一周里关在宾馆中,再没见到蓝海鸥和犬子,我把蓝海鸥的衣服洗一遍又一遍,干了叠起来放好。倒是听到肥皂一些口传消息,开始说民工中没见到肥皂,人们怀疑他让海啸卷走了,后来听说在公安局里。大家说起蓝海鸥,夸她真够泼辣,领着我们一群裸体走出险境;有个说,蓝海鸥本来是穿雨衣去的,冲下六号公路下水前,她一声声叫着公牛,把雨衣扔了。我心急如焚,油田公司早早就给我们送来工服。我得去找犬子,死见尸活见人。这几日,天天有从大海上打捞回来的尸体,一共十几人,没有犬子。走在六号公路上,阳光很好,海滩光溜溜的,一望无际不见人影,拦潮坝像被斩成无数段的蛇身泡在海水里。我们的窝棚呢,早就漂到大海里不知去向。海面上,偶尔有一两只海鸥掠过,形影孤单。
我想蓝海鸥,这些天我每日做梦梦见她,夜里眼睛一合,她就来到我跟前。那一夜伏在她身上,总觉得是完成了一种交割,交割什么呢?說不清。无论如何,这一夜把我和她的关系拉近了,彼此间有了一种不能向第三人诉说的感受。直到现在,还能感觉到她的身子的温度和柔软,这么近距离和一个姑娘肌肤摩擦,想起来足以让我融化让我疯狂。她在黑暗中的模样,她的湿漉漉地贴在脸上的头发,焦急闪烁的大眼睛,湿透贴在身上的内衣,浑圆的身体,在我的脑海里蒙太奇般闪现,一遍又一遍。
我买了几个苹果,腋下夹着她的衣服,一路打问找到蓝海鸥家。
这是一溜工人宿舍。敲门进去,蓝海鸥正在收拾屋子。她一脸病态,身后跟个男孩,见到我她十分惊喜,大眼闪烁着问:伤好了?咋找来的?
你好吗?
嗯!我刚刚回家来,一直重感冒在医院。她的声音多少带点鼻音,病还没利索。
我升起一阵心疼的感觉,我看她的眼神一定有无限的爱怜。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就这么傻愣愣地看着她将近半分钟。两人的眼光都很沉稳,谁也没有打破寂静。
我把衣服递到她手里,她闻闻,笑一下说:香!那天我惩罚你,怕你累得不行,逃不出来呢。
我说没大事儿。只是受伤影响了我,想想后怕,多亏你大胆救援。
蓝海鸥招呼我坐下,去烧开水,说起犬子的消息。犬子在海啸当晚并没有留在窝棚,而是悄悄去五里香饭店找小翠。他喜欢小翠,想和她谈谈。和小翠的对话还没进入正题,肥皂闯进去。彼此以为对方就是那个买小翠初夜权的人,两人二话不说直接开打,犬子咬了肥皂的耳朵,肥皂折断了犬子的一根手指头,两个人都被公安局拘留。这一拘留反倒让他们二人躲过了海啸。
听完这些,我心里轻松许多,没话找话说:那天我推了六十方土,全被海水冲走了,冲走的还有窝棚,衣服,被子,裹在被子里、放在枕头里的工钱。
蓝海鸥眼光柔柔地看着我不说话。
我从来没有遇到这么近、这么亮、这么温柔的眼神,浑身有些不自在,看看她身边的小孩,随口问:你弟弟?
操!啥子眼神儿?我儿子哩!
我听完,脑袋一陣血往上涌,心里顿时乱得像海啸。我明白我为啥来,我来的目的不仅是一般礼节性地想看看她表达谢意,我确实很想她很想她,是男人想女人的那种感觉,想得睡不好觉。我本来想和她说我喜欢她,没想到她是个有孩子有家庭的人。我只是演练过被她拒绝后的心理体验,而这一情况,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心里登时迷乱,像偷东西被逮个正着,我的脸一下子红到脖根儿。我哼哼唧唧说去找犬子,努力压住羞怯不失态。
她看着我走出很远才关门。她一定在笑话我的唐突和狼狈,我能感觉到。
我稀里糊涂走出她家,一直跑,跑上六号公路,迎着侧面来的海风往北边狂奔,我想扯片白云挡在脸上,我想跳进大海洗洗脸目。我觉得每一阵风,每一缕阳光,每一株小草都在笑话我的冒失,海鸥嘎嘎的叫声也在揶揄我。幸亏蓝海鸥这人皮实,不然,无缘无故跑进一个家庭和女主人没话找话,定我个骚扰的罪名也能成立。好了,到此为止,不自作多情了!
我一直跑到海啸前我们的工地附近。
海滩里有个人影,正深一脚浅一脚垂直朝六号公路走来。我以为是犬子,冲下公路,跑近了看清,是肥皂。真是冤家路窄!
你敢欺负犬子!我心里为刚才在蓝海鸥那里的洋相而感到懊恼,眼下有打一架的冲动。
肥皂看看我不说话。他眼睛里有一层雾雾的东西,是泪水,想不到这个死彪子还有柔软心肠。他膝盖上沾了一层泥巴,有跪过的痕迹。
管他为什么,我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挥拳就打,重重抡在他的后背上,感觉砰的一声,像捶在一面鼓上。他的心空了?
他只是拿眼瞪瞪我,不说话,不还手。
我喊道:你让海啸吓傻了吗?我要给我兄弟出头,你害怕了吗?
肥皂头也不回,晃荡着身形一直往六号公路上走,视我为无物。
我正想进一步挑衅。
犬子忽然出现在六号公路上,看到我们,喊着快步跑过来。
我问:犬子,这家伙傻了?
犬子眼角泛起泪花,抓住我的胳膊,说:哥,你不知道。彪子的叔伯兄弟被海水卷走了,那一夜因为看不到他,就找他,耽搁了逃生机会。他正伤心哩!小翠不让他打架,他自己发了毒誓。哥你不知道,肥皂不是六十块钱买小翠初夜权的人。那夜,公安局逮他时,他告诉小翠,他娶她,让小翠无论如何等着他。肥皂很仗义,吐个唾沫就是钉,是条好汉。
看着肥皂的背影,我后悔刚才的冲动。
我们民工按要求都回到油田公司集合,公司宣布,我们这伙民工全部转成港口工人。
大家欢欣鼓舞,喜极而泣。
犬子和我说:哥,我不要这港口工人身份,我要回家。
傻瓜!这是正式工。说实在的,这个身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足以光宗耀祖。再说,海啸这事,是百年一遇的,不可能天天发生。以后,我们都是安全的。
犬子还是摇头,说:刚才小翠找我了,她说她选择肥皂,肥皂已经给她凑够了手术钱。她告诉我,说我不属于这里,让我回校复读,说我这么聪明能吃苦,明年一定能考上大学。我听她的!
我忽然觉得小翠是个好姑娘!
你咋办?犬子忽然问我。
啥怎么办?
你和蓝海鸥啊!我看得很准,蓝海鸥喜欢你,你也喜欢蓝海鸥。
哎呀呀,你不知道哩,人家孩子都两三岁了。
犬子:我问过了,她今年二十四,男人一年前车祸没啦。别磨蹭,开完会就找蓝海鸥,打开天窗说亮话。咱也是这里的工人了,应该有信心!
我醍醐灌顶,信心陡增。
此刻是下午四点,我在院里水管上使劲洗几遍脸,把脖子搓得麻沙沙地疼,觉得足够干净,一口气跑到蓝海鸥家门口。遥看六号公路上空,有一群海鸥在夕照中盘旋。海鸥在陆地上面舞蹈,这是天下奇观,闻所未闻。很显然,这群精灵也满腹心事。
我整整衣服,抬手敲门。
这回我要郑重其事地告诉蓝海鸥三件事:一是,我愿意给她身边那个孩子做爸爸;他要是不愿意,做哥们儿也成;二是拜托她继续管着我;三是,把操字交给我说,以后她就免了吧。
责任编辑:李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