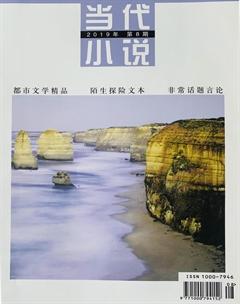方生未死
羽瞳
我从小就想当尧小智的妈,他比我小两岁,长得像个洋娃娃。出生时脐带缠脖,早产,差点儿给憋死在娘胎里,打出生起尧小智就像个一掐脖儿就能断气的小鸡崽儿,比人家矮,比人家瘦,比人家多灾多病,也比人家的脑壳来得憨。
比如那个烂大街的问题,“树上有十只鸟,一枪崩死一只,还剩几只呀?”
尧小智会瞪着他那双大葡萄似的眼睛,盯着我家院儿里的臭椿树,认认真真地回答,“乌鸦。”
真是个好孩子。
堯小智他妈在他三岁大时跟一个磨剪子戗菜刀的跑了,这事儿在他妈跑之前就已经是胡同里心照不宣的秘密,男人扛着扁担来,一声吆喝八条胡同外都听得见,那吆喝总得在尧小智家门前销声匿迹一阵儿。尧小智在门口蹲着,跟三四窝蚂蚁玩儿,那时候我刚从幼儿园光荣毕业,因为岁数不够被小学拒之门外,一整年赋闲在家,我们两家门对门,我提溜着裤子从公共厕所出来,问他,“你家到底有多少菜刀要磨?”
尧小智抬起白白净净的脸,一手的蚂蚁,“我妈说,我家的刀,没人家的好使。”
我是在很多年后才明白这句话的,那时候我和尧小智都还没屁大,他因为脑子有问题三岁了还穿着开裆裤,晃荡着他家院儿里唯一一只鸟儿。我们都处在一个性别模糊的年纪和年代,分不清男和女究竟有什么区别,后来,在我意识到这一生都有可能择不清的时候,我莫名地想起并明白了尧小智他妈说的话。
他妈跑的那天,尧小智也在门口和即将钻入地底过冬的蚂蚁玩儿,他被咬了一手的红点儿,我从我妈的医药箱里偷药膏给他抹上,模仿我妈的手法把他的手缠成了个粽子,看着像电视里的僵尸,他用这只全是药膏味儿的爪子蹭了蹭我的脸,对我说,“谢谢,小北哥。”
那些蚂蚁密密麻麻地往我心尖里钻,我觉着有什么东西从血管里活过来,很热,满足感冲昏了一个五岁孩子的头脑,我拉住他的手放在嘴边亲了一下,“以后我给你当妈吧。”
他手舞足蹈咯咯直笑,我以为他同意了,他挥舞着胳膊冲我后头脆生生地喊,“天使!”
我吓得一哆嗦,猛回头瞧见我妈正站在我身后,她又把尧小智的奶奶领回来了,佝偻成一只蚂蚁的老太太对我妈大声喊,“小智他妈走了。”老太太好几年前就聋了,在尧小智他爸去包头找建筑工地之前,她就聋了,她成天起得比鸡都早,拎着把折叠板凳去胡同口晒太阳,一晒一天,看见一个人出去就在脚边放一枚石子,回来一个人便拿走一个,石子每天每天只多不少。
我妈冲老太太笑笑,伸手摸了摸尧小智的脸,我妈原本是个妇产科护士,尧小智就是我妈接生的。医院倒闭之后,我妈骑着婆家唯一的彩礼、一辆乳白色永久自行车,把药箱放在车筐里上门打针。这片日本人遗留下来的棚户区里基本没有人没挨过我妈的针。棚户区像一块破竹席,我和尧小智住的胡同像一根烂藤条穿插其中。老人传说这条胡同叫“卡蜡思”,不明白什么意思,日本人跑了几十年,鸟羽一样排列的房子中间塞满了虱子似的违章建筑。
我妈瞄了一眼尧小智的手,推了一把我的脑袋,“你干的?”
我怕她听见了我刚才对尧小智说的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怕,我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汗,“啊。”
“还行,有天赋,”我妈说,“回去我教教你。”
我松了口气,尧小智还在叫我妈天使,他脑子有问题,两岁多才会说话,那天他在我家看电视,电视上在播医疗题材的电视剧,我妈在厨房做饭,尧小智突然跑出去,冲我妈喊,“天使!”
我妈把尧小智抱起来,尧小智的口水蹭在我妈的白棉服上,我妈总是一身白,自行车也是白的,在以脏乱差为主要特征的胡同里分外扎眼。她亲了一下尧小智的大脑门儿,尧小智晃荡着他的小细脖儿上的大脑袋,细胳膊细腿地在我妈怀里扑腾,我妈侧腰也被他踹脏了一块。
我妈说,“你跟你小北哥玩儿一会儿,等姨把饭做好了给你们端一份。”
我妈把他放下来,他没站稳,往前扑了一下,先天不足加上后天缺陷令他的大脑袋和小身子极不成比例,像挂在小卖部墙上的洋娃娃,我扶了他一把,他抬起脸看着我笑,尧小智长得好看,比洋娃娃好看,像他刚刚离家出走的妈,我看着我妈推着自行车进院门的背影,突然意识到,在街坊四邻眼里,尧小智早就是个没娘的孩子了。
我说,“拿上你的枪,我要上厕所。”
尧小智欢呼一声跑进院儿里拿枪,一把黑色的玩具枪,比他还高,枪口拖在地上早就磨起了毛茬,这把枪是我妈给他买的,能打塑料子弹,我妈经常要用镊子把这花花绿绿的小塑料球从小孩儿鼻孔里取出来,所以她只给尧小智买了枪,没有买子弹,并且再三叮嘱我也不许买。
我还是给他买了,一整包都倒进枪里,并且命令他在我去公共厕所的时候站在外面站岗放哨,如果有人要进来就开枪,反正他是个傻子,不会有人和他一般见识。尧小智很喜欢这个游戏,除了为我站岗,他平时从不碰这把枪,整片日本房只有两个男孩不喜欢玩儿枪,一个是我,一个是尧小智,我不好意思说我更喜欢喝洋娃娃玩儿喂奶打针的游戏,尧小智只对蚂蚁、麻雀、乌鸦一类活着的东西感兴趣。
胡同的公共厕所在我家旁边,旱厕,两个帘子两扇水泥门简易地区分了男女,在我五岁那年春天,不知是谁在女厕里生了个孩子,生在茅坑里,孩子直接淹死了。
我妈念叨了一晚上造孽,她趴在床上,边往废旧的演算本背面记账,边讲起她护士长的女儿,她说那女孩十七八岁和男人有了孩子,找赤脚医生打胎,结果人死了,男人和医生把她和死胎装进冰柜扔进了大凌河。
我妈说,“你长大了可不能当玩弄女孩的畜生。”我心不在焉,把脸埋进她的腰窝,嘴贴上去,吹出一连串“噗噗”的响声,她身上酒精和药水混合的气味钻进了我的鼻孔。
我是在这种气味里长大的,母亲的气味。关于父亲,我没有任何概念,我妈不说,街坊不提,我也不问,至少在我五岁之前,我不觉得我的生命里需要这样一个角色。我妈能给我所有我需要的,我很崇拜她,有时候我跟她去别人家打针,羡慕无论男女老幼都乖乖听她的话,也羡慕所有人都很信任她,我看到过高烧不退不停抽泣的小女孩在她怀里破涕为笑,也看到过她握着七八十岁老人的手低声细语,老人脸上对她的依赖甚至比我对她更加厚重,这时我心里便会涌起崇拜和骄傲。
幼儿园总会组织小孩玩一种游戏,女孩发洋娃娃、小厨具、医护玩具,男孩子发没有水的水枪、类似于大檐帽的儿童帽,全班一起过家家,我在第一次做游戏时就发现了自己的异样,我对水枪毫无兴趣,我盯着女孩怀里的洋娃娃,想起我妈,想起尧小智他妈敞开衣襟给尧小智喂奶的样子,在那个幼儿园里其乐融融的下午,我被突如其来的恐惧击溃,毫无理由地哭了起来。
从那天起,我便不能站着撒尿了。
这件事只有尧小智知道,只有他知道就等于没人知道。他把遵守约定当成比吃喝拉撒更重要的事,我曾经听到过他和乌鸦约定明年再来,生我养我的小城每年冬天都会迎接成千上万的乌鸦,在日本房这一带,乌鸦只会停歇在“卡蜡思”胡同,每家每户的树梢电线上全都黑压压地坠满乌鸦,是桩怪事,见怪不怪。
我的卫兵提着枪站在门口,“小北哥,我妈也是蹲着撒尿的。”
“你见过啊,”我一边绑裤绳一边骂他,“小流氓。”
尧小智没回答我,他开枪了,连发扫射踏着正步高喊顺口溜的毛豆和二饼,这俩小瘪三是隔壁胡同的,比我大一岁,已经上一年级了,昂首挺胸声音嘹亮,生出了我和尧小智这种无业游民难以理解的光荣和骄傲。
“一九九一年,我学会开车,上坡下坡,压死二百多。警察来抓我,我跑进女厕所。女厕所没开灯,我掉进粑粑坑。我和粑粑作斗争,差点没牺牲!”
好死不死,当年在街头巷尾操场教室流传的顺口溜里我最膈应这首,每次听都有种被现场抓包的惊心动魄,这种头皮发麻的感觉时至今日也不得消散,只要想起就能回忆起童年棚户区旱厕的恶臭和尧小智开枪的声音,塑料子弹迸溅在石子地面,弹起来崩到了毛豆的脸,毛豆和二饼尖叫着“小疯子”扑过来把尧小智按在身下,我从厕所冲出来,抄起我妈忘在门口的炉钩子,瞄准二饼背着书包的后背抡了下去。
我们迅速扭打成一团,也迅速被我妈分开,二饼和毛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我妈打针,我妈一瞪眼他俩立刻噤若寒蝉,他俩恶人先告状,控诉小疯子无缘无故用枪打他们,我妈把尧小智一直死死抱在怀里的枪接过来,晃了晃听了听子弹碰撞的哗啦声,她狠狠剜了我一眼,对他们说,“小智是弟弟,还不懂事,你们俩过几天就戴红领巾了,是大孩子了,让让他,好不好?”
二饼抽了抽鼻子,不等他说话,我妈按住我的后脑一使劲儿,“道歉!晚上不许吃饭!”
我乖乖道了歉,抬头看见他俩偷偷冲我做鬼脸,一股火“腾”地烧起来,我妈又说,“还有,以后谁再叫小智疯子,阿姨就给谁多扎几针。”
二饼脸色一白,毛豆捂住了屁股,连跑带颠地穿小道回家去了,我心里的火立刻又降了下来,冲他们跑远的方向呸了一口,我妈给了我一脚,我怕她追问我尧小智开枪的原因,连忙说,“妈你看,小智的脸划破了。”
我媽蹲下身,把又开始玩儿蚂蚁的尧小智抱起来,看了看他脸上的擦伤,又看了看他手上蹭掉的纱布,尧小智的奶奶在院儿里大声放收音机,她听不见,却每天晚上都要听收音机,我妈冲尧小智家望了一眼,叹了口气,抱着他进院儿去了。
进了十月,晚上冷了,棚户区没有暖气,我妈怕我冻着,早早生了炉子,屋里一股煤灰和苞米糊子混合的烟味儿,棚户区的天黑得也早,没有路灯,月亮的光晕被远处的火车站和大马路吞噬,只有些许的余温落在沙土路、沥青屋顶和红砖墙头,薄薄的一层,像炉盖上的灰。
我钻进被窝,紧挨着我妈看电视。晚上我还是吃到饭了,尧小智吃剩下的鸡蛋糕,他吃了我家的鸡蛋糕,还拿走了我妈前些天收拾东西翻出来的牡丹相机,我和我妈都不喜欢照相,传说两三岁时我只要被镜头对着就会嚎啕大哭,尧小智看见柜子上的相机,抓起来就不撒手,我妈从抽屉里找出一卷胶卷装进去,教他给正蹲着捅炉子的我拍了两张。
尧小智欢呼,死死抱着对他而言又重又大的黑盒子,我妈说,“喜欢就送给你。”我吓了一跳,“啊?你不是说这相机是我姥爷送你的吗?”我妈说,“我也用不上了,再说了,这东西给小智比给你保险。”
那天的尧小智失去了令他生的人,得到了令他死的宝贝。我妈在很多年后仍因这件事追悔莫及,可那时的我们谁也不会预测未来,我妈沉浸在对尧小智的怜爱和同情里,而我从那时起就在被困扰我一生的问题纠缠,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电视开始播广告,我把下巴搁在枕头上,听我妈叹了口气,“小智他奶有一天没一天的,他爸也不回来看看。”
我说,“小智他奶要是没了,小智怎么办?”
“跟他爸走吧,他爸在外边儿打工肯定有……”我妈顿了一下,“落脚的地方。”
我妈时常接触生死,她无处可讲,就讲给我听,我也就比其他孩子更早地对生与死有了认知。我妈八成是怕我问下去,话头一转说,“我今天上午给老李头儿打针,下午人就没了,岁数大了真没办法,生老病死人之常情。”
我问她,“妈你怕死吗?”
她侧卧过来,摸了摸我的脸,“怕,没你的时候我不怕。”
我愣住了,我觉得我不怕死,这使我很羡慕母亲,有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甚至想把隐瞒的一切都和我妈坦白,我又想起了尧小智,想起他比洋娃娃还好看的脸,想起他在我妈怀里的样子。我说,“妈,我也想怕死,我想当妈妈。”
我妈没有回应,她太累,已经睡着了。我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冷汗从头出到了脚,我躺在床上暗自庆幸她没听到我的话,屋外传来几声乌鸦叫,又到了闹乌鸦灾的季节,我这么想着,第一次彻夜未眠。
从那天起,尧小智不管去哪儿都抱着我妈的牡丹相机,吃饭抱着睡觉抱着。我妈找了根绳儿把照相机挂在他脖子上,像在他的小细脖儿上坠了个枷,随时都能把脑袋下来。一卷胶卷十块钱,三十六张,他不和那些活物玩儿了,改成了拍,让它们都活在他的小盒子里。入了冬,除了人以外能找见的活物越来越少,于是他开始每天坐在门口等乌鸦过路。
我比他闲,见天揣着张乘法口诀,往砖头上一坐死盯着尧小智,他等乌鸦,我守着他和相机。那时候,治安也远不及现在稳定。我家离火车站近,遍地小偷儿,小偷儿在公交车上用镊子掏包,被抓包了敢拎着水果刀跟到家里报复。我家被偷过一次,贼是从木条窗框爬进去的,我妈回来冷静地检查了一遍,发现家里丢了半桶豆油,一袋没拆封的钢丝球,还有她刚收的没来得及存的药费。她检查了一下堆在卧室的纸壳箱,药一瓶没丢,我妈开火做饭,跟我说,“这贼真不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