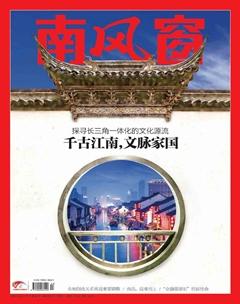乡村“混混”,家门口的陌生人
刘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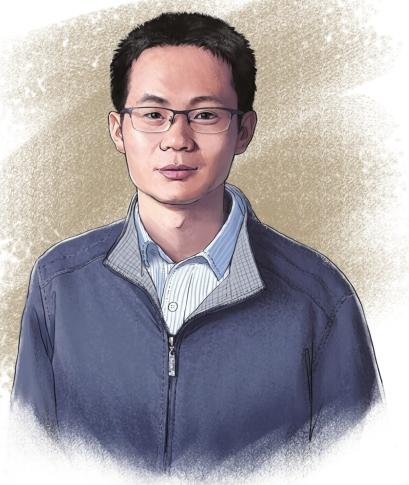
人们印象中“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中国乡村,实际上多有“混混”群体的身影。在种种涉及巨大利益的灰色领域,乡村“混混”以暴力和暴力威胁的手段,通过滋扰和压制来参与利益分配。
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持续开展的背景下,乡村“混混”无疑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之一。
乡村“混混”现象为何出现?出现在哪里?如何解决与应对?就这一相关问题,《南风窗》记者专访了陈柏峰教授。基于十余年间的社会调研,他认为,乡村“混混”介入基层治理,主要源于行政体制内上下级之间责、权、利分配不对称的结构。这一涉及多方主体的问题,同样需要多方力量实现协同治理。
找出背后的社会原因更重要
南风窗:在你看来,什么是乡村“混混”?这一群体和刑法当中所指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的“涉黑组织”,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陈柏峰:在中国,有利益的村庄基本上就会有乡村“混混”的身影,他们积极介入各种灰色领域,“插手”乡村治理事务,参与形塑着基层治理生态。
我在调研中发现,“混混”这个词汇的“复兴”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之前人们对类似的乡村越轨者的称呼是“流氓”。这是一个带有严重贬义色彩的词汇。
要强调的是,“混混”本身是个日常用语,定义比较含糊,不是一个规整的法律概念。采取普通农民的看法,我在研究中把乡村“混混”定义为那些在普通农民看来不务正业,以暴力或欺骗手段牟取利益,对农民构成心理强制,危害农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扰乱乡村生活正常秩序的人群。
当下,整个社会生活和社会形态已经高度复杂化。有些黑社会性质组织比较隐蔽,普通人在生活中难以察觉。不过,这些组织基本都带有“混混”色彩,但“混混”却未必都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未见得一定会违法犯罪。
乡村“混混”是村民“家门口的陌生人”,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虽然“混混”群体的主要生活和谋利场域在城镇,但在乡村区域有利益的地方,仍然在介入相关事务,对乡村治理有着很大的影响。
南风窗:你研究乡村“混混”有十余年的时间,为何会持续关注这一问题?研究过程中,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什么?
陈柏峰:一方面,对于改革开放后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来说,乡村“混混”这一现象相当熟悉以至于会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另一方面,在外人印象中,中国传统村莊是安宁祥和、“温情脉脉”的,但实际上,普遍存在的“混混”群体已经给乡村带来很多暴力冲突。
2005年7月,我跟随罗兴佐教授到湖北荆门调查农民抗旱和农村水利供给问题,我们发现,有两农户因为在抗旱中争水引发纠纷,后来双方居然都从市区或镇上找来“混混”,当着村干部和派出所民警的面在村里展开对峙。
这一场景,与我们想象中的乡村很不一样。因此,我开始观察这一群体,关注中国乡村治理。十余年间,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大量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
对于这一群体和现象,我持着中性态度,这是做学术的应有姿态。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他们在偶尔违法和灰色经营之外,也有不少人在做正当经营。比起道德指责来,冷静地找出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更加重要。
南风窗:纵向横向来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乡村“混混”是否表现出不同的群体特征?在不同的乡村地区,这个群体是否有较为显著的不同?
陈柏峰: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的乡村“混混”普遍经历从“名”到“实”的发展过程,起初在80年代,他们“混世”是为了争勇斗狠,后来逐渐发展到牟取实际利益,所使用的手段主要是暴力和暴力威胁。
目前总体来看,乡村“混混”主要在城区生活和消费,但和农村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农村出现有利益的地方,他们就跑回来插手涉足。比如,承揽黑车,垄断猪肉渠道,暴力催债,例子数不胜数。
从地理维度来看,利益较为持久、“混混”非常活跃的有三种类型的村庄。
一是村域范围内有丰富矿藏资源的村庄,这些资源可以被村民承包经营,乡村“混混”就很容易趁机介入;二是在各地城郊农村,由于征地拆迁事务乡村干部摆不平,乡村“混混”很容易在灰色地带被引入;三是传统农业型地区中有自上而下的各种项目投入的村庄,项目的实施过程其实也是利益分享过程,乡村“混混”自然不会放过这些机会。
南风窗:一般来说,乡村“混混”的经营手段和组织方法是怎样的?
陈柏峰:在基层社会,一个人要想经营涉及相当利益的业务,在借助情、理、法之外,必须还得借助“力量”。别人来“找茬”滋事干扰,就得有办法能“降得住”对方。警察不可能随叫随到,也很难真正管理好民事纠纷。这样的关系,就给了乡村“混混”们市场和空间。
他们主要是依靠“江湖关系”来维系整个群体。一个电话,一呼百应,有了事情,“兄弟们上”。相对来说,乡村“混混”并不涉及太多实体雇佣关系,没有形成严密的组织这样一种形态和策略,也就导致他们很难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虽然“混混”群体的主要生活和谋利场域在城镇,但在乡村区域有利益的地方,仍然在介入相关事务,对乡村治理有着很大的影响。
“混混”多少与现代化程度有关
南风窗:中国的乡村“混混”群体是为何形成的?他们主要分布在哪些经营领域?
陈柏峰:乡村“混混”的形成原因,涉及相当多的复杂变量,但主要与中国地域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生态相关。在调研中,我发现,无锡的社会状况就非常好,基本上没有“混混”的存在。相对而言,苏南地区整体社会治理水平就很高。这也说明,一个地方,现代化程度越高,“混混”群体往往就越少。
“东北黑社会”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流行词语呢?因为东北的国营经济最早出现经营不善的情况,留下的人没有正式职业,还有的人就大量外流,所以就在各地采用横行霸道的手段,滋生出一个又一个“混混”群体。
在经营领域中,只要有灰色利益空间的地方,基本上就会出现乡村“混混”的身影。第一,资源型村庄会有垄断利益。村域范围内有丰富矿藏资源的村庄,它的资源可以被村民承包经营,乡村“混混”就很容易趁机介入。山西煤矿区曾经是极为鲜明的例子,乡村“混混”势力从最初的打打杀杀、敲诈勒索,演变为攀附公权,向煤炭经济领域全面渗透。
第二,城郊村庄会有土地房产利益。无论是农民从违法建设获得利益,在征地拆迁中获得利益,还是村干部获得灰色利益,各方主体都处在一个博弈过程中。也因此,乡村“混混”有了介入其中参与分享利益的空间。此前在湖北咸宁郊区违法建设的控制中,因为城管控违力度不够、效果不好,政府干脆把任务“承包”给当地“混混”王某组建的公司。之后,违法建设基本得到控制,王某以及依附在他周围的“混混”从中获取了丰厚的收益。
第三,传统农业型村庄会有项目利益。项目制的实施,已经成为向中西部农村输入利益,重新激活乡村“混混”关注点的政策因素。国家涉农资源以项目的形式投入到具体村庄中,典型的如精准扶贫、“村村通”公路工程、水利设施工程等。无论是项目指标的争取,还是项目的实施落地,都存在着巨大的利益空间,这些自然就会吸引乡村“混混”的关注和介入。
南风窗:在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中,乡村“混混”群体和基层政府、当地企业和民众的关系是怎样的?
陈柏峰:在所有类型的村庄中,“混混”介入乡村治理,基层政府几乎都是容忍和利用的态度。各方主体的利益往往会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即便基层政府本身也并非“铁板一块”,各部门也会有不同的诉求和立场。
在资源型村庄,“混混”或与“混混”关联在一起的村干部、企业家等,就会占有和经营矿产资源,获得垄断利益,压制反对和异议。
在城郊村庄,为了应对征地拆迁中的“钉子户”,有的基层政府也愿意将难办事务转包给有“混混”背景的公司。
在农业型村庄,“混混”也以被村委会利用,或者以充任村干部的方式介入基层治理过程,用暴力威胁“钉子户”就范。由于可以推进项目进展,提高项目运行效率,基层政府对此有时是乐观其成的。
其实,基层政府一般不会直接雇佣“混混”为其办事,而往往保持一定的距离。政府容忍或利用“混混”,在形式上发生在市场和社会领域。
构建“防火墙”
南风窗:你曾提出,基层政府容忍或利用“混混”参与基层治理,主要源于行政体制内上下级之间责、权、利分配不对称的结构,你对这一结构的具体阐述是怎样的?
陈柏峰:“混混”群体的滋事作恶,必须依附于“权力”本身。而基層政府既要推动经济发展,又要维持社会稳定,往往需要借助“混混”群体的力量。
在市场或社会环节让“混混”介入,有助于完成治理任务,提高治理绩效,一旦出现影响社会稳定的恶性事件,政府又处于较为超然的位置,不会直接被卷进事件中,从而可以规避直接的责任。这种模式是基层政府对社会势力的一种利用,也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基层政府部门,中国的行政系统内权责不对等现象都普遍存在。正是因为行政体制内部上下级之间的责、权、利分配不对称,基层政府才被迫进行“创新”,容忍或利用“混混”在市场或社会领域参与基层治理。
南风窗:自2018年1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后,这一群体和基层治理生态发生了哪些变化?
陈柏峰:“混混”介入乡村治理秩序,最终会使国家治理目标受到冲击。我在农村调研中时,经常会听到农民反映“中央政策越来越好,基层官员仍然不好”等类似观点。这说明,治理好“混混”问题,找到适切的乡村治理机制和政治原则,颇为重要。
乡村“混混”的形成原因,涉及相当多的复杂变量,但主要与中国地域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生态相关。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指出,要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随着这一行动的展开,我在调研中明显感到,这两年来的社会治安水平和治理生态进一步向好发展。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的是,在现实中,“混混”的绝大多数活动,尚不属于黑恶,而是处于灰色地带。他们往往并不直接采取黑恶性质的暴力手段,大多只是以暴力为后盾的威胁。“扫黑除恶”很难触及“混混”们的根本。
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大力“扫黑除恶”,还要从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原因,寻找乡村“混混”的应对对策。
南风窗:你认为,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来改善治理生态,治理乡村“混混”这一问题?
陈柏峰:在我看来,乡村“混混”问题至少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对策也应该从这些方面着手。
第一,“江湖”对身在其中的“混混”提供了一条社会阶层上升的途径。很多“混混”文化水平有限,家庭情况不好,在正常社会渠道下,很难实现社会阶层的上升,在“江湖”中混世之后,可以谋取灰色利益,过上中产阶层甚至资本阶层的“幸福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基层政府要杜绝对乡村“混混”的利用,社会要拓宽健康的发展渠道,让更多人可通过健康渠道来实现社会流动和上升。
第二,学校教育对“江湖”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和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供给。基于教学秩序的考虑,学校在教育和管理中不但不尽力帮助那些不良少年,反而在主观客观上将他们尽早推向社会,促使不良少年更早成为“混混”。这就要求政府重建正确的教育观念和舆论环境,让学校恢复教育的本来面貌。
第三,市场和社会中存在诸多未能有效纳入法治范围的利益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江湖”之所以繁荣,是因为“混混”在其中可以谋取大量非法利益,而这些利益往往就是法治不及之处。因此,需要尽量将所有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纳入法治范围,完善立法,提高司法能力和执法能力,让灰色利益和非法利益无处可遁。
我认为,从以上几点出发,乡村社会才能达到善治,乡村治理才能在政治正义的高度上有效进行,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才会完整,基层治理生态才可能走入良性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