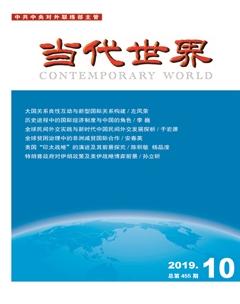2019年大选后印度政党政治的发展动向
【内容提要】2019年5月,印度第17届议会大选落下帷幕,执政的印度人民党赢得大选并巩固了优势地位,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及其他政党则陷入衰落、分散的局面。这意味着印度的政党政治正在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两大党制向印度人民党“一党独大”转型。印度人民党政府虽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形势严峻的压力,但其过去5年来出台的各种惠民政策、强力推进改革的决心和能力仍然让普通民眾对其寄予厚望。印度人民党胜选是当前印度意识形态领域印度教民族主义全面扩张,国大党、左翼政党和种姓政党在社会主义和世俗主义上不断退却的结果。
【关键词】印度人民党;意识形态;印度教民族主义
【DOI】10.19422/j.cnki.ddsj.2019.10.011
2019年5月23日,印度第17届议会大选落下帷幕。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在下议院选举产生的人民院542个席位中赢得303席,创下该党自1984年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有着134年历史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下称“国大党”)只获得了52个席位,比2014年大选时仅增加了8个席位,在法律上仍然缺乏成为官方反对党的资格。[1]在印度人民党势力扩张的背后,是形形色色的地方政党尤其是种姓政党势力的整体衰落。2019年大选标志着印度政党政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印度人民党体制”的形成
自20世纪90年代印度国大党的“一党独大体制”衰落以来,印度政党政治经历了短暂的动荡。1991—1996年间,执政的国大党少数政府勉强完成了任期。1996年大选后,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形成势均力敌局面,印度政党制度逐步过渡到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各自领导一个政党联盟(联合进步同盟和全国民主同盟)轮流执政的“两大党制”。[2]这种稳定的竞争模式一直持续到2014年。
2014年后,由于国大党的整体衰落和印度人民党的全面扩张,印度政党政治进入了新时期。由于印度人民党连续两次在大选中获得半数以上席位,并将势力范围扩大到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从而形成了绝对优势地位,印度政党政治正在朝印度人民党“一党独大”的方向发展。
第一,印度人民党不仅在联邦议会维持多数地位并组建政府,还在大多数邦建立了政府。在联邦层面,2009年大选时,印度人民党获得116个联邦议会席位;此后在2014年和2019年大选中,印度人民党连续两次都在联邦议会中获得半数以上席位,席位数量也从2014年的282个上升到2019年的303个,得票率从31%上升到37%。[3]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也是1984年以来唯一一个在联邦政府连续执政的多数党政府。印度人民党基本保持了在北方邦、比哈尔邦的地盘,并和其盟友垄断了拉贾斯坦邦、古吉拉特邦、北阿肯德邦、喜马偕尔邦、中央邦、哈里亚纳邦的人民院全部席位,同时将势力范围从印度北部地区扩大到南部和东北部,获得了东北部7个邦24个人民院席位中的12个。[4]在西孟加拉邦,印度人民党在42个席位中获得了18个,比上届增加了16个,取代左翼政党成为该邦第一大党。[5]在地方层面,截至目前,印度人民党在12个邦是执政党,其中包括北方邦、古吉拉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哈里亚纳邦等重要邦。[6]印度人民党势力范围所到之处,都有该党或党的外围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的组织建立起来。
第二,在2019年5月的大选中,国大党获得的席位不足议会规模的10%,不足以和印度人民党抗衡。在2014年和2019年的两次大选中,国大党的得票率没有明显变化,总体上维持在约19%的水平,大约相当于印度人民党的一半。[7]在16个邦和联邦直辖区(印度共有29个邦和7个联邦直辖区),国大党未能获得一个席位,甚至在6个月前赢得邦议会选举的拉贾斯坦邦、中央邦和查蒂斯加尔邦,国大党也遭遇了惨败。在上述三个邦的65个人民院席位中,国大党只获得了3个,其余席位全部由印度人民党获得。[8]国大党主席拉胡尔·甘地甚至丢掉了尼赫鲁家族在北方邦的传统地盘阿梅提选区的席位,使得该党在北方邦仅剩下索尼娅·甘地所获得的1个席位。在国大党获胜的选区中,得票率优势也在下降。国大党52个席位中的平均得票率优势为8.6%,比2014年的44个席位中平均13.6%的得票率优势要低5个百分点。[9]此外,国大党具有竞争优势的选区(国大党候选人得票率排第一或第二)的数量从2009年和2014年的350个与268个下降到了2019年的262个。[10]其中,在国大党与印度人民党直接竞争的席位中,国大党的得票率进一步下降。2014年大选时,在189个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直接对峙的选区(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分别排名第一或第二)中,印度人民党赢得166个选区,获胜比例为88%。而在2019年的大选中,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直接对峙的选区有192个,印度人民党赢得176个选区,获胜比例为92%。[11]在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两党对峙的选区,印度人民党的得票率明显上升。《今日印度》的民意调查显示,拉胡尔的支持率仅在喀拉拉邦、泰米尔纳杜邦和安得拉邦超过了莫迪。[12]
第三,左翼的共产主义政党变得无足轻重,其他小党和地方政党作为松散的第三阵营整体实力下降。在2004年大选中,共产主义政党共获得人民院62个席位,仅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就获得了43个席位,是位于国大党、印度人民党之后的第三大党。在2019年大选中,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分别只获得了2个和3个席位。共产主义政党在西孟加拉邦的地盘完全被印度人民党占领,在其执政的喀拉拉邦也只获得1个席位。[13]而在地方政党层面,2014年大选中所得席位较多的几个地方政党分别是泰米尔纳德邦的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同盟(37个席位)、西孟加拉邦的基层国大党(34个席位)、奥里萨邦的比久人民党(20个席位)。[14]在2019年大选中,席位较多的几个地方政党包括泰米尔纳德邦的德拉维达进步同盟(23个席位)、西孟加拉邦的基层国大党和安得拉邦的青年、劳工和农民大会党(22个席位)。[15]在北方邦,为对抗印度人民党,自1995年以来一直处于竞争关系的社会党和大众社会党组成同盟并达成席位分享协议。然而,社会党和大众社会党的联合只获得了15个席位。[16]或许这印证了莫迪所说的,虚假的联盟最终只会失败。[17]
按照印度宪法规定,一个政党必须在人民院中拥有10%以上的席位才能成为正式的反对党。尼赫鲁执政时期,由于国大党长期在中央和邦执政,很长时间里人民院没有真正的反对党。印度政界曾有人提出国大党应该帮助建立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他们认为,国大党从一个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组织变为印度独立后唯一的执政党,需要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以便监督议会民主制度在印度扎根,同时也需要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来保证国家权力的民主活力。[18]对此,尼赫鲁的回答是,在印度,反对党有充分机会发表意见和进行竞选,新闻媒体也有批评政府的自由。反对党虽有机会但仍未能形成力量,那么国大党恕不能为反对党的弱小而负责。[19]印度政治学家科萨里对印度政党制度特征做了一个经典的概括,他将1947年以来印度政党政治中国大党“一党独大”的体制称作“国大党体制”。[20]在“国大党体制”下,国大党处于支配地位,自身存在着宗派分裂,但对外界的压力非常敏感且能积极应对。反对党不能对执政党造成挑战,但可以压力政党的形式在体制外围起作用。在这种体制下,反对党的作用,是“通过影响权力空白处的舆论和利益,持续地给予执政党压力、批评、责难,进而影响执政党。在此背景下,如果执政党偏离有效的公共舆论平衡太远,或者它内部的派别制度不能动员起来恢复平衡,它就有可能被反对党所取代。” [21]70多年后,印度的政党制度似乎是历史的重演,只不过名称换成了“印度人民党体制”。
经济发展与政党选举绩效
2014年,印度人民党打着“发展”的旗帜赢得了大选。2019年大选时,印度人民党在竞选中却不再关注“发展”,而是转向国家安全和民族主义。印度人民党竞选策略的转变,固然是利用2019年初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冲突及由此引发的民族情绪,更多的则是与印度经济发展的形势有关。在2019年大选前,印度正面临着经济放缓的压力。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4年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为7.41%,但在2016年上升至8.17%后开始出现下降。[22]2014年大选期间,莫迪曾承诺如果印度人民党上台,政府将在未来5年创造1000万个就业岗位。[23]但到莫迪任期快结束时,失业问题却成为政府和社会最关注的焦点之一。由于经济形势欠佳,发展议题在2019年大选中被印度人民党巧妙地掩盖了。也正因为如此,国大党将失业问题和农业发展、农民收入问题作为选举中的主要动员策略。针对贫困问题,国大党还提出了一个类似于2004年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计划的旗舰政策——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即为全国5000万贫困人口(大约20%的家庭)提供每年7.2万卢比的现金补贴,到2030年消除贫困。[24]印度的媒体上也充斥着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就业形势严峻的报道,尤其是针对就业问题,媒体反复强调莫迪在2014年大选时高调做出的增加就业的承诺没有兑现。在此背景下,印度人民党的当选意味着什么?经济增长与印度的选举政治存在何种关联?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米兰(Milan Vaishnav)等人针对1980—2012年间印度18个邦、120次邦议会选举结果所做的研究显示,整体来看,印度经济发展绩效与选举结果之间几乎没有多大相关性。但是如果从前后时间段的对比来看,在21世纪头一个10年的中期,印度经济发展经历了结构性转型,许多邦一级领导人的政治生涯都说明经济增长确实能够带来选票。莫迪本人在古吉拉特邦就连续三次当选,古吉拉特邦也是印度最具经济活力的邦。印度人民党执政的中央邦首席部长希夫拉杰·辛格·乔汗(Shivraj Singh Chouha)也是如此。比哈尔邦人民党(联合派)领袖尼提什·库马尔(Nitish Kumar)因为承诺要将比哈尔邦从“丛林政府”转变成“发展政府”,[25]将此前在该邦执政的全国人民党政府赶下台并实现连续执政。[26] 2011年,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前副主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尔温德·帕纳格里亚(Arvind Panagariya)和世界银行的著名经济学家进行了一项研究,考察印度经济增长是如何与选票挂钩的,他们对2009年印度大选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执政党候选人的当选具有显著影响力;同时,他们还对几个重要邦的选举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同样表明经济形势和选举的相关度在上升。[27] 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迪正是依靠其在古吉拉特邦执政期间的发展成就,成功动员了印度选民对于发展的渴望,从而获得了2014年大选的胜利。
2019年初,印度的一些民意调查机构预测莫迪政府有可能在大选中失去多数党席位,其主要依据就是经济增长不如人意,废除旧货币的改革(下称“废钞政策”)严重损害了非正式部門的增长,商品和服务税改革虽然是重大突破但却在短期内干扰了市场。[28]尽管如此,相关民调数据却表明,印度民众对莫迪政府的绩效仍然保持了非常高的满意度。2019年1月《今日印度》的民意调查显示,仍然有高达54%的受访者对莫迪政府的总体表现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虽然莫迪政府经济层面的各项指标满意度较2017年1月的调查结果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是仍然有49%的受访者认为印度的经济形势会向好(2017年1月的结果是60%);甚至是在反对党猛烈攻击的就业问题上,也有42%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做得非常好,这一比例比2018年1月和8月时的调查结果还要高(分别是30%和37%)。与此同时,有60%的受访者认为即使印度人民党失去多数党席位,全国民主同盟仍然能稳定完成任期。[29]
此外,印度民众对莫迪治下印度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充满信心。大选前一周,位于新德里的印度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的3—4年中就业困难。尽管如此,仍然有6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再给莫迪政府一次机会。[30]这些数据表明,由于关注对象不一样,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对莫迪政府的感受存在差异,普通民众对莫迪政府充满信心。经济学家关注宏观经济数字如GDP增长水平、失业率、进出口贸易等;普通民众则更加关心日常生活是否有所改善。莫迪政府在过去5年中实行的惠民政策,如向农村推广天然气、在全国推广金融账户并将补贴直接支付到居民账户、基本实现全国通电等,都明显改善了普遍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的生活。经济学家认为“废钞政策”损害了经济增长,而普通民众则将其视为莫迪政府强力打击黑钱和腐败的证明。至于商品和服务税改革,经济学家对其在短期内的干扰效应忧心忡忡,而普通民众则从中看到了政府推行改革的决心和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发展与印度政党政治之间的联系正在增强。
印度政党政治中的意识形态竞争
此次大选结果揭晓后,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解释印度政坛当前各政党所经历的变化。英国政治家埃德蒙·柏克曾指出,政党是人们联合起来根据某些一致认同的特定原则,通过共同努力来促进国家利益的团体。[31]虽然人们对这句话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存在不同的意见,但意识形态就是政党的特定原则,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意识形态能够为政党提供价值观,从而能够为政党提供一个被公众识别和认可的标签;能够为政党吸引积极分子和追随者并将其团结在党的周围;政党意识形态的稳定同时还意味着党组织的稳定。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考察印度政党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变迁,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印度人民党何以能形成“一党独大”的地位。
印度人民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宣扬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实现以“印度教特性”为基础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32]具体表现在印度人民党对废除穆斯林属人法、建立统一民法典、重建阿约迪亚神庙、取消克什米尔特殊地位等问题的立场上。印度人民党认为,印度穆斯林必须接受印度教文化,否则他们只能成为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莫迪执政的5年中,印度教民族主义渗透到印度社会的各个领域。如果不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巩固,就无法理解约基·阿迪亚纳斯(Yogi Adityanath)为何能成为北方邦的首席部长,也无法理解印度人民党候选人、称刺杀圣雄甘地的凶手为英雄的普拉戈雅·塔库尔(Pragya Thakur)为何能击败国大党的资深领袖、前中央邦首席部长迪维杰亚·辛格(Digvijaya Singh)而当选,更无法理解印度人民党主席阿米特·沙(Amit Shah)宣称要将来自孟加拉和缅甸的穆斯林非法移民赶出印度时,印度人民党仍然能在西孟加拉邦获得18个席位。
相反,国大党在过去30年中逐步放弃了尼赫鲁式的世俗主义,只剩下在世俗主义口号下的一些空洞言论和机会主义,导致印度以公民为中心的世俗主义观念不断被侵蚀,印度政治正朝着“宗教多元主义”的方向发展。在尼赫鲁和英迪拉执政时期,印度主流政治中常常可以听到类似的言论,即穆斯林的恐惧就是我们的恐惧,穆斯林面临的不平等是印度社会的不平等。尽管那时的印度社会也存在宗教冲突,特别是在英迪拉执政时期,但国家的高层领袖公开表示在宪法上保护少数宗教群体的言论并非全是谎言,也未被反对党攻击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但是自2014年以来,类似的言论已经在印度政治话语中消失。有学者认为,印度将会为追求成为印度教国家付出代价。[33] 如果说印度人民党打的是“刚性印度教特性”(Hard Hindutva),那么国大党打的则是“柔性印度教特性”(Soft Hindutva)。如果国大党还坚持社会主义,那么它也未能准确地界定社会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正是由于缺少核心意识形态,国大党在面对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动员时,拿不出系统的应对措施。国大党既不能提出关于印度未来发展的宏观愿景,也缺少日常政治中的具体政策。在国内宗教宽容和少数族群的权利保障问题上,国大党无法组织起能够同时在穆斯林、达利特种姓以外更广泛的群体中引起共鸣的抗议运动。在经济方面,尽管拉胡尔始终把农民问题、失业问题当成批评莫迪政府的议题,但是国大党没有发动过一起像样的、形成规模的抗议运动,也没有提出一套具有可信度的替代方案。针对莫迪政府在印巴冲突后打出的民族主义牌,国大党也提不出一套有力的、有针对性的话语体系,以重建自己关于民族主义的解释。正是因为缺少核心意识形态,国大党也难以将地方小党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建立一个能够对抗印度人民党的政党联盟。此外,由于缺少作为核心凝聚力的意识形态,国大党不得不依靠尼赫鲁家族来保持党内团结。
左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在政治上已经僵化。在经济改革开始20多年后,印度的共产主义政党仍然不能提出一套新的关于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同时实现自由主义的经济增长和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的理论路线。在对外关系方面,共产主义政党批评印度的对美政策侵蚀了国家的战略自主性,使印度成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但是却无法改变印度与美国在国际政治中日渐走近的事实。对左翼政党而言,其在知识领域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其政治影响力。
最近的两次选举结果显示,在印度政党政治中,种姓的重要性相较于1989—2014年联合政府时期已经明显下降。这也是为什么在北方邦,社会党和大众社会党的联合并没有带来外界预期的结果。但这并不是说种姓不重要。事实上,印度人民党在北方邦也精心打造了一个由非亚达夫(Yadav)的其他落后种姓和非贾特夫(Jatav)的达利特种姓组成的联盟。落后种姓中的亚达夫种姓和达利特种姓中的贾特夫种姓正是社会党和大众社会党的核心选民。[34]种姓政党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低种姓追求身份和权利的社会运动。运动的主体认为种姓是印度社会不平等和压迫的根源,而执政的国大党试图隐藏这种社会分裂。种姓政党宣称要实现被压迫种姓的代表权和尊严,并通过夺取政治权力来实现种姓的解放和繁荣。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追求平等和公正的意识形态逐渐消失,社会正义的叙事日渐衰微。曾经代表全体被压迫种姓的种姓政党已经分别成为特定种姓的代言人,而他们的组织结构又与家族联系在一起,是印度家族政治的集中表现。
结 语
当前印度政党政治表现出来的右翼民族主义倾向绝不是孤立的现象。这种民族主义正出现在巴西、匈牙利、土耳其等国,某种程度上也出现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右翼政党和领导人把自己包装成民族和国家的救世主,而民族和国家又等同于多数族群的国家。他们总是强化国家内外部面临的威胁,并认为解决国家安全问题才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前途。在印度,國大党、共产主义政党和种姓政党都先后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他们批评印度人民党威胁了印度的民主和世俗主义,却又不能联合一致结成同盟,因而这种警告就变成了空洞的口号和选举中的投机。
20世纪,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哈特曾用“协合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理论来解释印度民主成功的原因。在他看来,独立后的印度一直实践一种权力共享式的民主制度。[35] 2019年大选后,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印度的民主正在走向多数主义民主的形态。[36]显然,这种多数主义民主的背后是一个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和一种带有典型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或许有助于印度形成一个多数的政府和在政治上更加统一的国家,但它会将印度带向何方,却只能拭目以待了。
【本文是2015年上海市社科規划中青班专项课题和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批准号:16PJC07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甘冲)
[1] 参见印度选举委员会网站数据,https://www.eci.gov.in。
[2] 陈金英:《两大党制:印度多党制分析》,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1期,第57-61页。
[3][4][5][6][7][8]同[1]。
[9] “Decoded: Why 2019 Was a Worse Year for Congress than 2014”, https://www.indiatoday.in/diu/story/congress-performance-elections-2014-2019-bjp-rahul-gandhi-modi-1534753-2019-05-25.
[10][11][12] 同[9]。
[13][14][15][16] 同[1]。
[17] “Fake Friendship between SP, BSP Will end on May 23: PM Modi”,https://www.indiatoday.in/elections/lok-sabha-2019/story/fake-friendship-between-sp-bsp-will-end-on-may-23-pm-modi-1506425-2019-04-20.
[18] S.S.Awathy, Indi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HAP-ANAND Publication PVTLTD, 1999, p.325.
[19] 同[18]。
[20] Kothari,“Congress System”, Asian Survey, Vol.4, No.12. Dec., 1964, pp.1161-1173.
[21] 同[20]。
[22] 参见世界银行关于印度经济增长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IN。
[23] “One Crore Jobs if BJP Comes to Power: Narendra Modi”,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politics-and-nation/one-crore-jobs-if-bjp-comes-to-power-narendra-modi/articleshow/26165012.cms.
[24] 参见国大党2019年大选竞选纲领“Congress Will Deliver: Manifesto of Lok Sabha Elections 2019,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https://manifesto.inc.in/pdf/english.pdf。
[25] “丛林政府”即“jungle raj”,用来指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人民党(RJD)执政时期比哈尔邦法律和秩序混乱、经济发展退居末位的治理状态。“发展政府”即“development raj”,指人民党(联合派)[JD(U)]上台后比哈尔邦经济发展快速增长时期。
[26] Milan Vaishnav and Reedy Swanson, “Does Good Economics Make for Good Politics? Evidence from Indian States”, India Review, Vol. 14, No. 3, 2015, pp.279-311.
[27] Gupta, Poonam Panagariya, Arvind, Growth and Election Outcome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New Delhi: National Inst. of Public Finance and Policy, 2011.
[28] “非正式部门”是印度政府经济和产业划分的一种,与正式部门相对应,通常用来指那些缺少正式就业合同和就业保障的经济部门。
[29] “Mood of the Nation January 2019: Complete Findings”, https://www.indiatoday.in/magazine/web-exclusive/story/20190204-mood-of-the-nation-january-2019-complete-findings-1439768-2019-01-26.
[30] 参见新德里印度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Lokniti-Csds-Tiranga Tv-The Hindu-Dainik Bhaskar Pre Poll Survey 2019”。
[31] 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柏克政治论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第148页。
[32] 参见印度人民党章程“Constitution & Rules of BJP”,https://www.bjp.org/en/constitution。
[33] Ashutosh Varshney, “Transfiguring India”,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narendra-modi-bjp-rahul-gandhi-lok-sabha-elections-2019-5749518/.
[34] 其他落后种姓称作Other Backward Casts,简称OBC;达利特种姓就是表列种姓。这两大类型的种姓都是法律上享有保留制度的种姓。亚达夫种姓属于其他落后种姓范畴,贾特夫种姓属于达利特种姓范畴,前者属于社会党的核心选民,后者属于大众社会党的非核心选民,正因为如此印度人民党才在这两类种姓外建立地盘。
[35] Arend Lijphart, “The Puzzle of Indian Democracy: A Consociational Interpret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0.No.2. June 1996, pp.259-260.
[36] “Christophe Jaffrelot, Election Results Invite Questions for Liberals. Worldwide, They Lack Their Rivals Discipline”,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narendra-modi-vikas-lok-sabha-elections-5745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