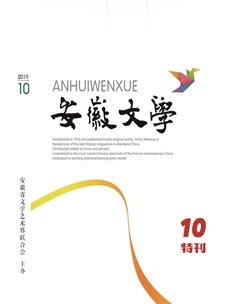金达莱
孙龙
孙秀连,战士,1951年5月牺牲在朝鲜三八线上。
——《S县志》
孙秀连奋力睁开双眼,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丛金达莱。
而后,他忍着剧痛,将盘了一地的肠子塞进开了花的腹腔,他这时像是在寻找谁似的,眼珠转动着,视野很小,只有一线天大。教我唱歌的人哪里去了?孙秀连满心迷惑着。他似乎想到了一年前刚跨过鸭绿江时的那个傍晚,那时假如有《金达莱盛开的地方》这支歌曲,凭借家族的艺术天赋,加上小学四年级的文化程度,孙秀连定会哼唱出“小时候常听姐姐唱阿里郎……哪一行脚印连着他的远方?我的家在金达莱盛开的地方,山和水都像是画中一样,每当燕归来冬雪消融,火红的花就开遍原野山岗……”
五月中旬的三八线上,除了炮火,还有一丛一丛的金达莱在石头缝间盛开。在高阳以北碧蹄里5号阵地上,孙秀连意识朦胧地想唱歌,我想这歌曲定会是《金达莱盛开的地方》。他也许想到了教他唱歌的连长,连长现在在哪里?孙秀连动了下头,用眼睛搜寻他的连长,他的战友,可进入他眼睛里的几乎全是血肉模糊的尸体,他再用力一搜,终于发现了连长,连长其实就在他身边。孙秀连看样子已经认清了身边躺着的不是连长,是他的姐姐,他用尽力气打算爬起来,但是,他只能动一下子身体,就又合上了眼皮。我猜想孙秀连这时竟觉得姐姐就在身边的那丛金达莱中间,他哭了起来,“呜呜”声果真就唤来了他姐姐。
姐姐实际上是大他一岁的未婚妻张素梅,赴朝参战前,他母亲曾找人为他订下了结婚日子,年底的腊月二十四,好日子。临参军前,姐姐张素梅来了,朦胧的月光下,两个年轻人依靠在门旁的枣树上,诉说着衷肠。张素梅说,你要记着我。肯定的!孙秀连突然拉着姐姐张素梅的手,信誓旦旦地回答。姐姐张素梅挣脱开手,说,你得喊我声姐。孙秀连上前一步,脆生生地叫了句,姐姐。这句只有两个字的话语,69年来一直就活在古汴水畔张大桥庄张素梅老人的心中,只是前不久这位老人去世了。
两个年轻人的这一幕,被我父亲从门缝间看见了,以后的许多年里,我父亲只要提起孙秀连,总爱说道这些。据说他那时已经是副连长了,要是活到现在,至少是县城里的一个什么官哩,我们家还会这么受穷吗?父亲那一年带我去唐河湾给祖先上坟,看那瘦小的祖坟,我父亲这样对我说。那是旧世界的风气,共产党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纠正着父亲的话。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烟火弥漫住了远山山尖上的那轮通红通红的太阳,这当儿,西北方向的天空压来了一块巨大的乌云,太阳不见了。
孙秀连此时头脑里出现了幻觉,他看见了姐姐正在向他跑来,他用尽全身力气想站起来拥抱他的姐姐,他好像还伸出了手去接他姐姐递过来的一支野蔷薇呢,孙秀连清楚,这是一支类似于他身边的金达莱一样的花朵。“哦,我曾听姐姐唱我的郎,时时我在想远方人的模样……”他这样哼唱起来,“唐河湾里的孙家庄是画中的画,美丽的野蔷薇开遍田野和村巷。”
但是,孙秀连这时却慢慢闭上了双眼。
一阵风吹来,头边乱石堆中的一丛金达莱盖住了他的眼睛。我想象着,孙秀连此刻也许正在和他的未婚妻张素梅姐姐乘着金达莱的花香,让灵魂舞蹈着,一起飞回唐河湾,他要给亲人们一个惊奇。不久,我们家就接到了孙秀连牺牲的消息,他的未婚妻张素梅起先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她整日哭成个泪人样,去找族长诉说,讲他孙秀连怕是升官了就将她这个乡下女人甩了。几个月后,孙秀连的遗物也由组织上送到了家中,张素梅这才一步一回头地走向了张大桥庄,几年后,她重新说了婆家,丈夫恰好是我三奶娘家那庄人。
据家藏的“革命军人证明书”中记载,孙秀连生前“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152团三营九连工作”。我读这些文字时,仿若那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三八线上的一丛一丛金达莱,正在血肉模糊的孙秀连眼前盛开着。
有关孙秀连的战斗故事,我曾在中篇小说《碑》中,通过韩石匠这个悲情人物的塑造演绎出来:“漫山的枯草已成了灰烬,连同那些坚硬的岩石都被炸成了深可没膝的沙状石粉。身为志愿军工兵的韩石匠,自己一个人又一次将磨盘大的反坦克雷布置好,正侧伏在弹坑边静候,美军的一辆坦克就‘吱扭扭地响过来了,只听‘轰隆一声,那钢乌龟眨眼间成了一堆废铁,韩石匠被冲天的气浪抛到了十几米远的山石上,昏死了过去。在他被冰凉的雨水激醒后,一看四周是坟茔一样的寂静,远处的夏虫在低鸣,身边有‘哗哗的流水声。韩石匠本能地爬着,他想找到部队,可是和他一起投入这次战斗的人,都死光了。他摸到的几乎尽是肢体不全的战友尸体,他大声痛哭了一会儿,觉着身子骨又冷又痛,就继续爬摸……”
韩石匠没有死,他当了逃兵,为保全身家性命他回到了唐河湾的孙家庄,而十八岁的孙秀连则成了烈士。
今天,在县城“烈士陵园”的东南隅,由县委縣政府于清明节期间修建的“革命烈士英名录”的碑墙上,就有孙秀连的名字。
这位在我心中像碑一样的人,他留给我父亲的是一块热乎乎的高粱面饼,留给家乡父老的是他扎着一条崭新的白色毛巾站立于敞篷军用汽车上的挥手,留给我的是自我幼小时就知道的英雄称号。
1950年秋天的一个逢集日子,长直沟街的人流中,他母亲挤来挤去,找针一样地寻着她的五儿子,一个乳名叫“小闯子”的十七岁的青年,已经离开家十天了。离开家时,他和他母亲是吵了一架的,当时,他从唐河湾里背来满满的一粪箕青草,猛一下甩在了牛槽前,顾不得其他就直奔锅屋,拿了两块刚出锅的新饼子,大口地咬着,吞咽着。当他发现草粪箕旁哭嚎的侄子时,他才知道自己的鲁莽,可是,大病初愈刚从县城医院回到家的他八岁的侄子,身体哪里经得起他的这一粗心,他侄子左眼泡被他的粗心甩出了一块青紫,还出了不少血。孙秀连母亲很心疼她的长孙,破口大骂,并手脚并用地打了她五儿子。孙秀连也很歉疚,把手中的另一块饼子塞给他的侄子,然后扬长而去……几天后,听说他去报名参了军,要去朝鲜打仗,他母亲这才心疼起来,她哭丧着脸逢人就念叨说,小闯子,这一下找枪子去了。这天,听人说她五儿子要走了(可能是政府通知的),母亲就去了汽车途经的地方——长直沟街给她五儿子送行,然而,她没有见到五儿子。还是许多天过后,邻村的一位老人对他母亲说,那一天他看见了小闯子。当时一大群头扎白色毛巾的年轻人,在秋天的太阳光下,精神抖擞地乘汽车奔向远方。孙秀连抻长脖子和手臂,他的手招着,挥着。他多想亲一下家乡,摘走一把家门口已经成熟的枣子啊,哪怕是河湾里的一缕风也好!每一个远离故土的人都会有这种情感,我想。
孙秀连战死在了三八线上。
他母亲从那以后,倒是享受起了政府给予的“烈属”好处,每日里喝着小酒,嚼着炒香的蚕豆,“嘠嘣、嘠嘣”,度着幸福的日子。我上小学时除了外婆家,最爱去的也就是她老人家那里,她很疼爱我们这些后辈,每次都弄最好的给我们吃。要是赶上她老人家亲手栽种于房前屋后的枣树和石榴树果实成熟的季节,非得让我们吃个嘴满肠饱不可,有时还让我用舌头舔她酒杯里的酒,辣得我直吸冷气,这时的老人家则在一旁眯缝着眼睛,满足地看着我,脸上的皱纹间爬满了慈祥。
很多很多年后的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了我从没有见过面的孙秀连,他握着他大哥还有他母亲的手来到我面前,说要朗诵一首诗歌。孙秀连面朝无边无际的金达莱,羞涩地朗诵起来——我静静地躺在异国的土地上,大哥送我的那块怀表,指针就永远地停留在了那一天的霞光中。我心中的姐姐死了,她的笑葬在了千年的月光里。我的爱击碎了青春的梦,三八线啊,是金达莱的馨香铸就……他大哥不解地问,金达莱是不是唐河湾河边坡上的野蔷薇?孙秀连说,不是的!他母亲又问,金达莱到底是什么?我替孙秀连回答说,金达莱也许是一艘穿越时光隧道的船。对!孙秀连点头称是。
其实,孙秀连就是我曾祖母的五儿子,我祖父的五弟,我父亲的五叔,我的五祖父。
这些日子,我总觉得有一丛盛开的金达莱在唱歌,是不是我五祖父孙秀连的英魂?若是,也该是他飞越三八线,跨过鸭绿江,跋山涉水地来到了魂牵梦绕的孙家庄啊!
姐姐,你要等等我哦!一个声音在唐河湾上空大声喊着。
我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