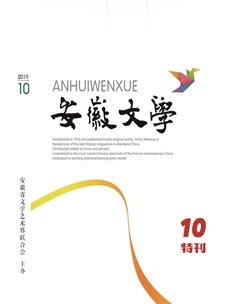一份杂志与一方文学:“十七年”《安徽文学》风雨路
陈宗俊
作为“十七年”时期安徽省文联机关刊物之一的《安徽文学》杂志,从1952年9月创刊到1964年12月休刊共出刊141期,其间刊物的更名、休刊、停刊,以及不同时期不同栏目的设置等情况,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围住文学文本,向它施加各种影响”,反映了地方文学刊物在特定年代下的某种生存图景,是“十七年”文坛的一个缩影。
一、刊物的更名与出版情况
在“十七年”,《安徽文学》办刊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安徽文艺》时期(1952.9—1956.6)、《江淮文学》时期(1956.7—1958.12)和《安徽文学》时期(1959.1—1964.12)。虽然《安徽文学》前身与1950年11月皖北文联创办的《皖北文艺》有一定渊源,但我们这里将《安徽文学》的源头从《安徽文艺》算起,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1952年8月7日,在皖北行署与皖南行署合并基础上成立的安徽省人民政府,是共和国成立后的新生地方政权,而《皖北文艺》属于皖北行署时期的文学期刊;二是1959年1月由《江淮文学》更名的《安徽文学》,其出版总期数也是从《安徽文艺》创刊号算起的。
1952年9月1日《安徽文艺》创刊于合肥,这对于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的安徽省来说,可谓是文化事业上的一件大事,如刊名是鲁迅先生的集字、时任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曾希圣为创刊号题词等。从出版周期来看,《安徽文艺》从1952年9月创刊至1956年6月停刊,共出版44期。其中从创刊号至1953年第12期,刊物均以《安徽文艺》“第×本”命名。从1953年1-2月合刊号起至1956年5-6月合刊号(终刊号)止,刊物以《安徽文艺》“×月号”或“第×期”命名。整个《安徽文艺》时期,刊物的“编辑者”署名均为“安徽文藝社”。这一时期的主编是时任安徽省文联主席戴岳。
《江淮文学》从1956年7月创刊至1958年第12期止,共出版33期。其中,从1956年7月至1958年9月为月刊,共出版27期;从1958年10月至12月止,改为半月刊,共出版6期。同《安徽文艺》时期刊物署名相似,《江淮文学》以“×月号”或“第×期”命名。在刊物“编辑者”署名上,1956年7月号至12月号,署名为“安徽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和“江淮文学编辑委员会”。从1957年1月号起至1958年第16期止,署名为“江淮文学编辑委员会”。《江淮文学》时期的主编在1957年8月前为戴岳,后为范源。
从1959年1月起,《江淮文学》更名为《安徽文学》。从更名号起至1964年第12期休刊号止,共出版64期。其中,1959年1月至6月为半月刊,共出版12期。从1959年7月至1961年1月为月刊,共出版19期。1961年第2至6月休刊。从1961年7月起至1962年12月止为双月刊,共出版9期。从1963年1月至1964年12月再次休刊止又恢复为月刊,共出版24期。这一时期,在“编辑者”署名上均为“安徽文学编辑委员会”。但从1963年第1期至1964年第12期止,刊物出现主编、副主编和编委姓名。其中,主编为那沙、副主编为江流,编委会成员包括于寄愚、陈登科、鲁彦周、严阵、苏中、祖保泉等共11人。在《安徽文学》时期,除那沙担任主编外,郭城也曾一度担任过刊物主编。
从以上《安徽文学》的历史演变来看,每一次的改刊或者更名,大都与当时国家文艺大环境有关。如1952年《安徽文艺》的创刊,既是新成立的安徽省为“努力贯彻毛主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有关,也是贯彻1951年国家“整顿文学艺术出版物,首先是整顿文学艺术的刊物”精神的产物。1956年6月《安徽文艺》停刊,创办《江淮文学》,是“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最近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产物,也与当时全国期刊集体性改名风潮有关。同样,1958年10月,《江淮文学》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也是当时文艺“大跃进”的产物。但改刊后因稿源不足、印刷与排版质量较差等因素,刊物不得不在1959年7月起又恢复为月刊,“我们对党的政策理解的不全面、不深刻,因而在某一段时期里,对‘两条腿走路的原则贯彻的不够好”。在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安徽文学》出刊也随之受到影响,刊物从1961—1962年间由此前的月刊变为双月刊,1961年间还曾一度休刊。从1963年开始,随着国家经济的逐渐好转,《安徽文学》又恢复为月刊,刊物纸张也较好,装帧也很精美。
“十七年”时期的《安徽文学》,虽然是一份地方文学期刊,但发行量也是可观的,是“立足安徽面向全国的文艺刊物”。从1953年第9本《安徽文艺》(总第13本)开始,刊物封底标有具体印数,这一期印数为2550册,随后刊物发行量都在3000册左右。从1955年11月号(总第38期)开始,刊物发行量突飞猛进,这一期印数为13900册,随后刊物都在这个数字上下波动,最高时印数达20000册。这种发行量在当时国内地方文学期刊中也是较高的,说明了《安徽文学》在当时地方文学期刊中的影响力。
二、聚焦国内外时政要点与服务地方文艺相结合
与“十七年”时期《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国字号”期刊相比,这一时期的《安徽文学》杂志同样在发表文艺作品同时,也担负着引导、宣传和阐释党的文艺方针与政策的职能。聚焦国内外重大时政要闻与服务地方文学事业就是其中两种具体体现。
在国际时政方面,一些重要的国际时政要闻,刊物大都予以高度重视。如1953年对《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刊物立即发表社论表明立场,认为“朝鲜停战的实现,是英勇的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及全体朝中人民的光荣胜利”。另外,像“悼念伟大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专辑(《安徽文艺》1953年第3本)、“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特辑(《江淮文学》1957年11月号)、“坚决抗议英美海盗侵略中东,支援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专栏(《江淮文学》1958年8月号)、“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击美帝侵略,保卫祖国的正义斗争”专栏(《安徽文学》1964年8-9合刊)等栏目的设置,也是呼应当时重要国际政治事件的反映。
在国内重大时政与文艺事件方面,刊物也大都以社论、专栏、座谈会、宣传画等多种形式鼓与呼,以表明刊物鲜明政治立场和发挥党的喉舌作用。以重要政治或文艺事件为例。“十七年”间文艺阵线上一些重要事件,如“《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事件”“反右”“大跃进”民歌、第三次文代会、降低稿酬、批判“写中间人物”、主张京剧改革等等,在《安徽文学》的不同时期都能找到相关内容。以1955年对胡风的批判为例,《安徽文艺》从1955年5月号开始,就以大量篇幅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反映。如5月号上,除了转载郭沫若的《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外,还以“记者”的名义报道了全省对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斗争的座谈会情况。6月号批胡风更是刊物的重头戏,共发文9篇,包括刊物社论、中国文联和安徽省文联批胡风的各项决议、6篇批判理论文章,另外还发布一则《本刊重要启事》:“因为投入声讨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这一严重的斗争,关于《老板和老板娘吵架》的讨论暂停。”7月号和8月号上,每期均发表9篇重头批判文章。这些对国内外重要时政与文艺事件的内容,既表明《安徽文学》紧跟时代的同步性,也显现了刊物作为政治晴雨表的功能。
在为地方社会发展与文学事业服务方面,显示出《安徽文学》的本土色彩与历史使命。在创刊之初,《安徽文学》就将“地方性”列为自己的办刊方针。以后历次的改刊或更名,这种服务地方性的方针始终未变。
一是为本省重要政策和方针服务。同以上跟踪国内外重要时政要闻相类似,“十七年”《安徽文学》对“配合全省各种中心任务”进行了不遗余力地宣传。如作为农业大省的安徽,《安徽文学》在农业生产与抗洪救灾等方面,均发挥着智力支持的角色。如1954年夏季安徽发生特大洪水,刊物也马上作出反应。在1954年8月号的《安徽文艺》上,除了在头条发表《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加强防汛及排涝补种的政治工作的指示》外,还编发了白石的《牛老三大战洪水》、杨雨润的《江堤上的战斗》与蕾子的《暴风雨中的战士》等抗洪文艺作品,以及《排涝》《抢救》等五幅防洪宣传画,多角度对抗洪自救作出声援。又如1964年第10期,《安徽文学》又对淠史杭工程予以关注,发表了黎佳和张燕风的报告文学《敢把那山山水水另安排》与贺羡泉的诗歌《淠史杭赞歌》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安徽文学》服务地方社会的意识。
二是引领与规范地方文艺活动。在“十七年”时期,《安徽文学》除了发布本省的一些重要文艺政策、文艺方针外,还常常以“本刊编辑部”“编者按”“编后记”“稿约”栏目设置、编读往来等方式对文学创作做出某种引领与规范,以发挥刊物的文艺导向作用,“《安徽文学》对于促进我省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提高,有其特殊的重大使命”。如针对一些读者对青年作者孙君健的小说《老板和老板娘吵架》(《安徽文艺》1954年6月号)的不同评价,刊物开始采取一种较包容的姿态,但当看到一些文章采取“扣帽子式”的批评时,编辑部则出面加以干涉,并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长文,认为这篇小说虽然有些不足,但还是“一篇值得发表的小说”,而“本省的一些公式主义的批评者们看到这篇小说之后,亦硬说这篇作品宣扬了资本主义思想”,是不对的,并指出“在研究和批评作品时,我们应该从生活出发,从作品的形象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内容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研究文学作品的基本观点和法则,也是文学作品本身的规律所规定了的”,现在编辑部对这篇小说的辩护,目的在于“作出公正的结论,以利本省的评论工作和创作”。这里刊物的立场,既是对作者的一种保护,也树立了一种正确的批评导向,同时也反映了双百时期文学环境的宽松。
“稿约”也是刊物引导文学创作的另一种方式。《安徽文学》在办刊的地方性、群众性与通俗性的总前提下,各个时期对稿件要求也不尽相同。如《安徽文艺》初期,强调稿件的通俗性,“要求能演、能唱、能说。不拘长短、不拘体裁,但以剧本为主”。因此这一时期的《安徽文学》上刊载的剧本比较多。以1953年为例,全年共发表剧本18部。《江淮文学》时期,由于安徽省文化局另创办了通俗性刊物《大家演唱》,这样就将原属于《江淮文学》的一部分通俗文学稿件分流出去,刊物加大了对稿件文学性的要求,尤其欢迎“关于作品的评介,创作思想创作方法以及文艺运动的论文,关于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论文”。据统计,仅1956年7月创刊号至12月这半年,《江淮文学》就发表评论17篇。这种文学评论稿件多与刊物的引导有关。1960年代,《安徽文学》对稿件要求又发生变化,在欢迎各类文学作品稿件同时,对“优秀的革命回忆录,优秀的公社史、工厂史和革命斗争历史题材”的作品用稿量增加,有时还开设相关专栏。
三是培养地方作者队伍与批评队伍。首先是刊物自身的编辑队伍。据鲁彦周回忆,在创刊初期,主编戴岳求贤若渴,“一见有安徽作者在外地较大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就立即了解这个人,并且用最快的速度把人调进来。写小说的也好,写诗的也好,写剧本的人也行,凡是他觉得有写作才能的人,他就下决心把他调来。他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最有魄力,最有决断的”。在戴岳等的努力下,陈登科、鲁彦周、缪文渭、严阵、钱锋、贾梦雷、吴晨笳、肖马、鲍加、吴文慧等人进入编辑部,为《安徽文学》提供了一批专业较过硬的编辑力量。其次,在广大作者队伍中发现与培养新人,尤其是工农兵作者,“重视文学新人的新作,不断扩大我们的文学队伍”。如通过刊物建立通讯员队伍、重点推介青年作者的创作、召开写作经验交流会、出版新人新作等方式发现与培养新人。如1954年5月号对陈志平、1958年第11期对高文华、1963年第12期对张万舒等新人的推介就属于此类。另外刊物还以专题或专辑的方式对某一作者或者作品进行大力宣传,如对殷光兰(《江淮文学》1958年7月号)、严阵(《安徽文学》1962年第1期)、姜秀珍(《安徽文学》1964年第5期)等的专题介绍。在这种大力培养下,陈登科、耿龙祥、江流、严阵、张万舒、殷光兰、姜秀珍等一批作者开始在国内文坛崭露头角。另外,注重批评队伍的建设也是此期《安徽文學》培养作者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刊物编辑队伍里的吴文慧、李冬生、缪文渭等亲自撰写评论外,刊物还邀请省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部分专家学者参与刊物的批评工作,如祖保泉、余恕成、胡叔和、沈敏特、王多治、苏中、黄季耕、严云绶等。这些批评家的加入与成长,既提出了一些创作上值得关注的问题,也增进了理论与创作的相互理解,为“十七年”时期安徽文艺的繁荣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三、“一体化”文学语境下的突围
在“十七年”间,《安徽文学》的整个办刊特色与“一体化”的时代文学特征是相一致的,但在刊物不同时期,也有“异声”旁逸斜出,而它的突围则主要体现在一些争鸣性作品和一些理论文章上。
“十七年”时期《安徽文学》所发表的引起争鸣性作品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小说如孙君健的《老板和老板娘吵架》、涂正祺的《捉纺织娘》(《江淮文学》1956年7月号)、陈登科的《“爱”》(《江淮文学》1957年1月号)与《风雷》(《安徽文学》1963年第12期至1964年第7期连载)、耿龙祥的《入党》(《江淮文学》1957年6月号)、尹江震的《老青年三上岳西》(《江淮文学》1958年第14期);诗歌如梦雷的《两只辣椒》(《江淮文学》1957年7月号)、严阵的《江南曲》(《安徽文学》1959年第16期);剧本如金渠的《搏斗》(《江淮文学》1956年7月号)、谢竟成的《白色的蔷薇花》(《江淮文学》1957年1月号)等。对这些作品的争鸣,有的属于一般性质的文学讨论与批评(如严阵的《江南曲》),而有的被看作是作家在创作上的“歧途”或“危险信号”的表现。这些“危险性”作品,它们或触及生活中的一些矛盾问题(如耿龙祥的《入党》),或涉及工农兵斗争生活以外的题材(陈登科的《“爱”》),或表现了所谓“资产阶级情调”(如孙君健的《老板和老板娘吵架》),等等。
比如对陈登科短篇小说《“爱”》的批评。《“爱”》是一部“十七年”间较敏感的爱情题材小说。作品描写了青年团干事牛玉山热衷于追求个人爱情生活、游戏于几个女人之间并最终害死妻儿沦为罪犯的故事。小说发表后,立即遭到强烈批评。这些批评大都围绕作品对题材的处理、人物形象的刻画、作家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情感等问题展开。一些批评认为,描写爱情本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题材”,但作家在这里处理的不好,“不论从什么角度上来考虑,都是一个无爱无憎因而也就是无事无非的作品”,原因在于“作者本身对这样的题材和人物,缺乏应有的爱憎和是非的激情”,而“以旁观者的态度来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倾向,是十分危险的”。另一些批评则将这篇小说与陈登科同时期发表的另一篇爱情题材小说《第一次恋爱》(《雨花》1957年1月号)进行比较,认为这两部小说“歪曲了同时代人的形象,提供了虚伪的生活图景,客观上宣扬了道德堕落和庸俗趣味”,其原因在于作家的阶级立场与政治立场没有站好,“作者本人就应该是社会正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化身,对于坏人坏事必须毫不容情地予以鞭挞和批判,而绝不能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把肉麻当有趣来欣赏”,因而作家对爱情题材的书写不仅不成功,更是一次“危险的尝试”。
同样,对谢竟成的电影文学剧本《白色的蔷薇花》,一些批评者认为作品“笼罩着一层灰色的气氛”,它“歪曲了党员领导干部形象”“否定人民政权的法治力量”“贩卖没落阶级的思想毒素”,是“一部贩卖资产阶级人生观的有毒作品”。而耿龙祥的《入党》同他的《明镜台》(《人民文学》1957年1月号)一样,是“一枝向党进攻的毒箭”,必须坚决予以铲除。这些争鸣性作品,在题材、人性书写等方面的大胆突破,成为“十七年”间“百花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与“十七年”时期主流批评话语基调同步的情况下,在一些文艺政策宽松时期,《安徽文学》也发表了一些富于建设性的理论文章。一是对人物形象问题的讨论。针对当时创作与批评中对人物的公式化与概念化,刊物就指出它们的不足:“内容往往列举很多事件,而忽略了写人,使得人物面貌苍白无力”,而“一些评介文章都像‘广告一样,着重内容介绍,缺乏对作品中人物的艺术分析”。为此,刊物发表了系列研究人物形象的专文。如吴戈的《“狂人”与“疯子”——鲁迅小说人物论之一》(《江淮文学》1956年9月号)与《“羿”与“禹”——鲁迅小说人物论之二》(《江淮文学》1956年10月号)、稚声的《科举制度下的牺牲品——“孔乙己”和“陈世诚”》(《江淮文学》1956年11月号)、高型的《学习〈红楼梦〉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江淮文学》1957年1月号)、千云的《关于薛宝钗的典型分析问题》(《江淮文学》1957年3月号)、吴钩的《周进与范进——〈儒林外史〉人物论之一》(《江淮文学》1957年3月号),等等。从这些理论文章来看,刊物不是从当时的文艺政策出发,而是从经典名家名作中汲取和借鉴人物塑造的方法,就显得比较可贵。
二是关于批评家的职责与胆识问题。如批评家不能人云亦云,应有独立思考意识(如白澜的《大胆怀疑,独立研究》,《江淮文学》1957年6月号)、敢于对现实生活中不良现象提出批评(如柯文辉的《批评家不要沉默》,《江淮文学》1957年1月号)、批评不能从教条出发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林兰的《反对文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江淮文学》1957年6月号)、批评家中的一些怪现象(如白河的《“文艺‘推理家”》,《江淮文学》1957年4月号),等等。这些理论文章,大都发表于“双百”理论提出前后,体现了刊物参与争鸣的勇气,后来其中的一些文章被视为“毒草”受到批判。
三是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如对爱情题材,张平治认为,“‘爱情,这是个永远带有魅力的字眼,它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许多世纪以来,不知道多少个伟大的诗人歌颂过它,赞美过它”,但是“我们今天有些诗人,却变得像腼腆的姑娘一样,在处理爱情的题材时,显得是那样地羞涩和胆小,既不敢全力地去表现这种美好的感情,也不敢用响亮的声音去歌唱爱情。”对于创作中的想象问题,胡茄认为,“生活是客观现实,是创作的基础;而艺术是生活的升华,是选择材料塑造形象的主观活动”,而在这两者之间,都要经过“以感性形象与理性思维”为特征的想象“这个无形的桥梁”。另外,对于文学批评的特性问题、作品的主题思想和题材关系问题等等,《安徽文学》也刊载了一些有意义的理论文章。
以上通过对“十七年”时期《安徽文学》的初步考察,让我们看到在特定年代里一份地方文學刊物走过的风雨之路,从中折射出“十七年”时期文学的一角。在这一角里,《安徽文学》所扮演的角色,无论是成功还是教训都值得我们总结,它也不愧为一份“重要的‘地方文学期刊”。
说明:因版面原因,该文有删节,同时,文中所列注释不再于该本之后一一罗列和注解,需要详细了解,可与本文作者联系,敬请读者和作者谅解。
责任编辑 赵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