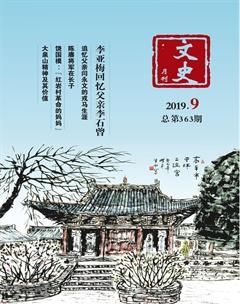追忆父亲闫永文的戎马生涯
闫广积

从小情报员成长为西北野战军战士
我的父亲闫永文生于1929年农历4月23日,由于家境贫寒,在本村只读了两年小学。1938年,日军占领了中条山区。在我的家乡绛县迴马岭,日本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所到之处怨声载道,满目疮痍,家中仅有的几孔窑洞也被烧毁。奶奶带着伯父、父亲、姑姑兄妹六人到处逃难,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第二年的秋天,日本人撤离迴马岭,一家人返回昔日的家时,只剩下断壁残垣,院落里杂草丛生,庄稼地里一片荒芜,触目皆是狼藉。当时已至立秋时节,小麦、玉米已无法下种了,一家人只能种些萝卜、白菜,在山上捡些橡籽,打点树皮,挖点野菜来充饥。大约在1943年冬天,同村的共产党员吴金山,介绍父亲前往里册峪,给驻里册峪的八路军(太岳兵团,陈赓的部队)做通讯员,那时父亲只有十四五岁,听父亲说,因为他年龄小,所以当时没有给他发统一的服装,只给他发了个大褂子。因褂子太大不合身,他就自己用针线将褂子缝割得小了一些。从此,父亲从迴马岭往各地送情报,成了一个小情报员。
有一年快过年时,部队领导让父亲前往郭家庄枣凹送一份情报。在返回的途中,遇到一队国民党士兵去郭家庄抢粮,父亲连忙躲在一棵大树后,等那些士兵走远后,他才慢慢从树后走出来,等回到驻地时,已经是半夜了。无论酷暑寒冬,还是遭遇洪水猛兽,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从没有一声抱怨,也从没一次出过差错,就这样一个人独自不分白天黑夜地急行在茫茫大山之间。
这年秋天,太岳兵团接受新的作战任务,离开了里册峪,父亲因年龄小留了下来。此时,我的大伯父已经在县公安局任职,家中境况也已有所好转,父亲就进了南樊镇高小读书。
1947年9月,全县大征兵,父亲在学校踊跃报名参军。当时,迴马岭一个小山村就有12人参军。当时村里一个爱编顺口溜的人,编了这样一段顺口溜:
歪头山,和尚帽
日本人下来就烧祖神庙
八路军,胜利啦
用了一群老百姓丈地哩
迴马岭好小伙子要走完
留下一群老人受熬煎
当年的迴马岭,满打满算不足三百人,除去老人、小孩和妇女,青壮劳力也不过七八十人,这一下就少了12个青壮劳力,确实让村里的老人受熬煎了。山区的农活主要靠肩挑背扛,但为了全中国的解放,我老区人民甘愿舍小家,顾大家,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当时绛县征兵一个团,翼城、绛县、曲沃三个县一共征了三个团。新兵在新绛县军训两个月,就跨过了黄河,赴西北野战军参战。父亲被安排到二兵团三军七师十九团三营七连(机炮连),由于他读过书,入伍就当上了文书。

在宜川战役(瓦子街战役)中机智化解危机
1948年1月29日,西北野战军在陕北米脂县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宜川战役的作战部署。宜川东依黄河,西连洛川、富县,是陕东战略要地,被胡宗南视为关中的屏障。对解放军来说,宜川是黄龙山同晋绥、太岳解放区之间联系的一个枢纽之地。解放了黄龙山,就可以进一步打通与晋西北的联系,巩固后方,造成解放大西北的有利态势。
彭德怀在会上指出,宜川是胡宗南棋盘上的一颗重要棋子,胡宗南不会轻易放弃,一定会派兵增援,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会议决定,采用围城打援的办法,先以一部分兵力围攻宜川县,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胡宗南调动的黄陵、洛川等处的敌军援军,然后再攻下宜川。这就是彭老总采取的著名的围城打援战术。
2月22日,按照战役部署,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率部向宜川方向前行。24日将宜川县包围,并发起攻击。当时父亲所属部队十九团属于许光达的部队,因父亲是名新兵,连长让他携带保护连队的一些重要文件、档案资料,同时负责转移伤员。整个上午,战斗进行得很激烈,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伤员越来越多。连长命令父亲这些新兵上去背伤员,离父亲不远处,一个昏迷的国民党士兵苏醒过来,悄无声息爬起,将手中刺刀对准了父亲。当时,父亲全身上下只有一个别在腰间的手榴弹可以防身,场面十分惊险,还好父亲及时发现了敌人,迅速做出反应,果断拿出手榴弹,拧开后盖,小指拔下导火索,手榴弹霎时就冒起浓浓的白烟,父亲瞅准时机,向对方抛出了手榴弹,机智化解了这场危机。
在转移伤员的过程中,一顆子弹从父亲的腋下穿过,鲜血直流,父亲强忍剧痛,凭着顽强的毅力把伤员转移到安全地带。这时胡宗南急调驻守在洛川的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刘戡部队增援,途经瓦子街时,遭到我军伏击,我军在瓦子街占领制高点,激战从3月1日上午一直持续到下午,我军终于将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全部歼灭,并击毙军长刘戡,大获全胜。
3月3日,我军攻克宜川,取得了宜川战役的大捷。这次战役共歼敌2.9万人,俘虏敌军的师、团级军官数十人。经过这次战役,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西北由优势变为劣势。
在洛川战役中舍命保护文件袋受到嘉奖
胡宗南自宜川会战失败后,用兵格外小心。他急电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配合他解洛川之危。他深知宜川失守后,彭德怀部马上就会攻取洛川,如果洛川失守,延安将会不保。洛川战役从3月5日打响,到4月12日结束,持续一个多月,在围攻洛川时,因为洛川易守难攻,我军发起两次总攻,攻击未克,我军围攻洛川意在使胡宗南调集别的师团来解围,但是增援的敌军十分谨慎,我军没有打援的机会。彭总机智灵活,采用调虎离山之计,他急令一纵队、二纵队、四纵队、六纵队转头去攻打敌人的战略要地宝鸡,胡宗南急调援军支援宝鸡,三纵队于3月9日完成了围城部署后,经过数日激战,艰难地拿下了洛川。
在洛川战役中,父亲所属的十九团,在阻击马步芳部支援洛川时也受到了重创。听父亲讲,先前预计这道防线上,敌方最多来两个团,结果马部从这道防线上一共来了12个团,其中10个步兵团,2个骑兵团。团部当机立断,一边阻击敌人,一边撤退,三营负责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撤退。与父亲一同从迴马岭参军的王殿武是三营八连的战士,与敌人拼刺刀时,不幸牺牲。当时营长身边只剩下司号员,他的文书和通讯员都牺牲了,这时营长叫司号员赶快把营里的文件袋交给我父亲,挥了挥手,示意他赶快撤退。营里的文件袋和连里的文件袋是三营及七连的全部资料(里面包括电台译码、每次开会的作战报告、重要的军事布防、营里的党员档案、营连里的领导机构、班子机构等),这些机密文件,对全营来说非常重要,父亲不敢犹豫,健步从那块有三米多高的土垛上跳下,紧紧追随着大部队撤离,这一跑就是两天两夜又一个早上。为了轻装前进,身上除了文件袋和水壶没扔,父亲把衣服、背包等随行物品全部扔掉。当找到自己的部队时,看看自己的脚,看看自己的脸,哪里还像个人呀。鞋也早不知道丢哪里去了,脚指甲全部出血了,脚上到处是血泡,脸上全是被树枝、荆条划出的口子,嘴上全是血泡,衣服和裤子全是口子,那真是死里逃生,惊心动魄。战友们相会,抱头大哭,都说:“我早以为你已经牺牲了!”营长在这次战役中也牺牲了,八连全部阵亡,剩下的连队幸存五分之一的就算多了。这就是十九团在洛川的首次遭遇战。
因父亲在这次战役中安全转移了营里及连里的资料,得到了营里的嘉奖,于五月份递交了党员申请书,同年秋天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自宜川和洛川战役后,父亲落下了病根。也许是当时医疗条件差,那些伤口没有处理好,年轻时还感觉不到,到60岁以后,每逢下雨天伤口总是痒得难受,两只脚上的脚指甲更是发黑,发硬,疼痛难忍,每天晚上都必须用热水泡脚来缓解疼痛。
在兰州战役中参加攻占黄河大铁桥
经洛川战役后,胡宗南的部队在延安站不住脚了,退缩到宝鸡,解放军又直逼宝鸡,宝鸡很快也解放了。之后,胡宗南残部退缩到陇东。1949年4月,太原宣告解放,毛泽东电令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赶赴西北参加解放大西北。

这时西北野战军已改番号为一野,司令员为彭德怀,一野辖四个兵团,分别为一兵团王震、二兵团许光达、十八兵团周士第、十九兵团杨德志。四个兵团直逼兰州城下。当时在西北,马步芳主要控制着甘肃和青海,马鸿逵控制着宁夏。
当解放军围困了兰州城时,马步芳和马鸿逵已经以开会的名义前往广州。兰州的实际指挥权转交给了他的儿子马继援。
马继援企图依靠兰州的有利地势、坚固的工事拦截住解放军,而彭老总身经百战,不失时机,于8月25日拂晓发起对兰州的总攻。
十九团主要作战任务是攻取黄河大铁桥。兰州桥是敌人的唯一退路,当时父亲所在的机炮连在狗娃子山上抓住一个敌方的逃兵,说马继援已被解放军打得顶不住,坐上吉普车逃向青海老巢,马继援已经下令全线撤退。这时上级下达命令,攻占黄河大铁桥的战斗打响,机炮连带六挺重机枪,三门60炮,一路横扫,迅速突进,直冲大铁桥,和先到的三营副营长邢彩江,还有八连连长许士奎,指挥突击队迅速冲向铁桥。桥头敌人负隅顽抗。八连用火力封锁桥面,引爆桥上的卡车,顿时火光冲天。父亲带领全排迅速用重机枪扫射,夺取了大桥。大桥于凌晨两点全部被我方控制。
8月26日凌晨两点,黄河大铁桥上飘起了解放军大旗。先到部队快速修筑工事,扑灭桥上的火,架起重机枪和钢炮。天快亮时,城内敌人蜂拥外逃。这时,桥头轻重机枪一起响,敌人霎时被打得落花流水,人压人,马压马,从桥上掉进河里的更是不计其数。黄河上的第一座大铁桥,经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血与火的洗礼。
26日中午,战斗结束,大西北重要城市兰州宣告解放。
在酒泉军校接受系统的理论和文化教育
兰州解放了,西北大局已定。父亲所在部队解放了张掖和酒泉后,为培养国家急需的干部,同年10月在甘肃酒泉建立了一所马列主义军事院校,父亲被选拔赴校学习。
父亲虽然上学不多,却爱学习,爱读书,爱文艺,爱唱歌,爱唱戏(秦腔,豫剧,蒲剧),家中剧本有《游龟山》《窦娥冤》《杨家将》等。父亲爱好文学,爱好历史,更爱好地理。当时军校考试是五分制,他在校学习毕业成绩各门课全是四分,达到了优秀等级。我见过他的毕业证,校长是他们的军长黄新廷。可惜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怎么也找不到这张军校毕业证了。
在两年的军校学习中,父亲白天学习文化课程,晚上参加文艺活动。听父亲说,老师经常抽他讲课、发言,晚上经常去表演节目,唱歌,唱戏。听父亲说,他的文学老师、历史老师和地理老师中,有的来自延安抗大,还有的曾是国民党的军官,地理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
1953年春,他们毕业了。抗美援朝正处于大轮番作战,父亲于当年赴朝作战。
在抗美援朝中与朝鲜人民结下血肉情谊
1953年,父亲接到上级命令赴朝作战。6月26日,由于七师一名政工干事叛变,七师布防情况被敌人掌握。美军出动了40多架飞机对十九团指挥所进行了轮番轰炸,我十九团指挥所114人全部牺牲,团干部除孙锡成一人外,全部遇难。
当晚七时,接军长黄新廷命令,重新健全十九團编制,团部、营部、连部,正职牺牲,副职补上。九时,全团战士齐声高喊着团长,政委的名字,誓死为团长、政委报仇,为十九团报仇。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攻下了主阵地。那时父亲已经是七连的指导员了,父亲说,战土们都杀红了眼,战场上那轻重机枪、机关枪的声音就像疯了一样狂吼不停,把所有的仇恨都聚集在这枪、这炮和每一颗手榴弹上了。 直到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后,又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挖掘,坑道才最终被打通,烈士们的遗体被挖出,最后被安葬于“三八线革命烈士陵园”。停战后,父亲及全团干部还亲赴陵园,追悼自己牺牲的战友。
虽然朝鲜停战了,但整个国土已被炸得千疮百孔,于是志愿军又参加建设平壤,为老百姓盖房子,盖学校,建医院,修铁路,修公路,无偿为平壤人民的生活作奉献。志愿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很多木材、钢筋都是我国无私提供的。
父亲所在的连队也积极参加建设平壤,在平壤待了一年多,书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记得家中还有一张父亲和当地一位朝鲜小学生的合影。
1955年春,志愿军要回国了,火车站前,朝鲜的老乡们一路相送,个个热泪盈眶。父亲踏上列车,看着窗外那些相送的老乡和战友,泪水模糊了自已的眼睛。列车啊,你开得慢些吧,让我在这曾经挥洒鲜血与汗水的土地上再多停留片刻。列车开始缓缓行进了,父亲摘下帽子同老乡和战友们道别,那一张张亲切的面庞,那一滴滴不舍的泪水,从此深深烙印在父亲的脑海里,成为了他一生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