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荫浏:中国音乐学一代宗师
施 艺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杨荫浏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史学家、民族音乐理论家、新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奠基人。先生饱谙经史、学贯中西,倾毕生心血在中国音乐史学、戏曲音乐、民族器乐、宗教音乐、曲艺音乐、音乐律学、音响学等众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撰写我国音乐史学里程碑式的巨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以及多部音乐论著;发表《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三律考》等百余篇文论;收集、整理、编撰《阿炳曲集》《十番锣鼓》《古琴曲谱》等大批珍贵的民乐曲集;考察和采录《二泉映月》《单弦牌子曲》等众多优秀的民间音乐作品。纵观艺术造诣、学术贡献、事业成就等诸多方面,先生被公认为是20世纪中国音乐学界的一代宗师。
学古今文化知识 习中外音乐技能
杨荫浏,1899年11月10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县城。他自幼聪慧好学,5岁入私塾专心习读十三经、《纲鉴易知录》等经史书籍和诗词歌赋,众篇章可熟背于心。自6岁起,常与兄长合奏民乐,并逐渐培养了浓厚的音乐兴趣。儿时的他双手尚小,吹奏箫时难以按住管上的全部指孔,但执着的他竭尽全力将箫的尾端抵住凳角,张大小手强按指孔练习吹奏。出于对音乐的向往与喜爱,小小年纪的他经常被周边道教仪式的音乐吸引。杨荫浏出身书礼之家,祖父辈以教书为生,在尊重文学教育的同时,也十分支持子女的音乐爱好。晚清时期社会动荡,为了让孩子能够安心在家学习,家里特请临近的小道士颖泉每日傍晚到家教习箫、笛、笙等民族乐器。更为可贵的是,在传授演奏技法的同时,颖泉还教杨荫浏抄录曲谱,这为他更好地演奏乐器、深入了解民间音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杨荫浏以聪巧好学的头脑,加上持之以恒的勤学苦练,逐渐成长为颇有造诣的小乐手。功夫不负有心人,大概在10岁左右,有外籍传教士看好少年杨荫浏的音乐才能,收他为学生,教他习英语、钢琴和西方乐理知识。不久之后,由于颖泉无法再到杨家教习民乐,改由一位盲人道士华彦钧(阿炳)继续教习杨荫浏弹奏琵琶、三弦等乐器。在此期间,天赋秉异的杨荫浏还师从堂姐夫章蕴宽学习古琴。清末时期,杨荫浏能够在家庭的支持下悉心学习中外音乐艺术,实属不易。
1911年,年仅12岁的杨荫浏经书法老师黄绪初的介绍,进入历史悠久、班社制度完善、保留着传统传承习俗的昆曲社“天韵社”学习,师从国内知名的昆曲大师、天韵社社长吴畹卿先生学习昆曲、古琴、琵琶、三弦等传统音乐技能。1912至1915年,杨荫浏在无锡县立东林小学就读高小,毕业后又进入私塾读书,并在此期间完成了一百六十余本经史书籍的学习,这些学习经历为其日后进行中国史学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功底。1916年,他进入无锡第三师范学校学习。由于有着文学、艺术的扎实基础,当时身为一名在校学生的杨荫浏在无锡音乐界已声名在外,因此,除了肩负本校的课余音乐活动外,杨荫浏还需要担任当地两所高小的音乐活动指导。由于各科目的成绩非常优异,整体评价也十分优秀,所以校方也支持他用课余时间去参加音乐活动,增加实践经历;学校还特批他可以在每天晚自习时间去天韵社向吴畹卿先生学习。凭借高超的艺术才华和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杨荫浏在多年后成为“天韵社”的接班人,吴畹卿先生将所藏昆曲抄本和祖传乐器交由他以续传承,杨荫浏大公无私地将曲谱油印成册命名《天韵社曲谱》六集,并交由社员学习交流。此举不仅使天韵社社员们有谱可依、提高了艺术能力,而且对于昆曲艺术的传播和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杨荫浏将继承的手抄本《天韵社曲谱》和紫檀木三弦交由国家,现保管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资料室。
青年时期的杨荫浏在参与校外音乐活动期间,时常会遇到琵琶音位不准的情况,这一现象使他开始关注起乐器的定音方法和改良问题。他经常与当地乐器店的店主和匠人交流学习,思考如何对琵琶进行排品以求增强乐器音高的准确性,这样的探索过程也使他跨出了律学思考的第一步。在日后出版的《雅音集》第一集中,杨荫浏明确提出了建设性观点,即琵琶可设十二半音品位的想法,并给出了计算品相排置的具体方法。
杨荫浏对与民族音乐相关的一切事项孜孜以求并勤于实践。他长期与众多道教音乐家和民间吹鼓手保持密切联系,不断学习音乐经验,交流艺术思想;经常参加民间音乐的演奏活动,逐步掌握了多种器乐合奏乐的形式,抄录和保存下了许多珍贵的苏南民间器乐合奏曲谱;在进行民间实践的过程中,杨荫浏虚心向精通传统音乐的艺人和音乐爱好者们求教,学唱民间歌曲,习奏民族乐器,悉心听取关于音律、音韵、用调等多方面的讨论。可以说,这些难能可贵的扎根民间的音乐经历,不仅引导着杨荫浏对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音乐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而且为其日后开启新中国民族音乐研究领域之门做好了实践上的准备。
1922年9月,杨荫浏进入无锡辅仁中学学习英文、数理等课程。由于自幼学习了国学和英语,具有一定的基础,因此他全力以赴攻读数学课程。1923年毕业。当时,有外籍音乐家到无锡采集民间音乐,杨荫浏不仅能够组织民间班社和艺人进行表演,还能担任英文翻译。可以说,青年时期的杨荫浏有着高度的自律和自觉。他熟读中国古典经史文献,学习中西方科学知识,拥有多种民族音乐奏、唱技能,并且有着长期深入的实践经验。与此同时,上述所有方面从不同的角度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个人的成长和思想,使他成为了一位熟知民间音乐事项、掌握实践经验、收集整理传统乐谱、用律学方法参与民族乐器改良、传播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民族音乐人。客观上,青年时期的杨荫浏已具备了成为我国民族音乐学大家的良好“基因”。
爱国之士 立研究民族音乐之志
1923年9月,杨荫浏如愿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起初他主修经济学科,后又改修英国文学专业。在大学期间,他把全部的课余时间都用来学习和研究民族音乐。在兼顾学业的同时,他还担任圣约翰大学的国乐会会长,经常组织和参与校际音乐会,亲自演奏乐器。他还尝试改编古曲《夕阳箫鼓》的演奏形式,以民乐合奏的方式进行演出。校园内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民族音乐是这位优秀青年最大的爱好。
为了解决在以往音乐实践中经常碰到的关于乐器定准定律的问题,作为文科生的杨荫浏选修了高等数学和高等物理等相关课程,这为他日后的乐律学研究提供了科学支撑。此外,为了能够绘制出精密的乐器图示,以供记录民族音乐资料、改良民族乐器、完善音乐教学活动等需要,他又选学了“用器画”、“机械绘图”等相关课程。这些专业课程的学习,为他日后开展长期、大量的民间音乐考察和学术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杨荫浏手绘的百余幅记有详尽尺寸和信息的图谱,为留存我国民族器乐资料、规范民间音乐考察及采录的形式与方法、推动新中国民族音乐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好景不长,进入大学两年之后,杨荫浏却面临着被迫退学的艰难处境。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杨荫浏与大批爱国青年学生积极投身反帝卫国运动。而圣约翰大学的校方公然禁止学生参加爱国游行,并以开除学籍作为威胁,以此打压学生群体的爱国运动。如此违背人民志愿、罔顾民族道义和情感的做法激起了大批爱国学生的愤慨。由于不满校方的无理要求,杨荫浏和大批学生纷纷签名离校,以实际行动支援爱国运动。学生们以满腔热血积极投身反帝斗争,并在多方援助下,开始筹建中国人自己的大学。这一壮举得到了爱国资本家和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有的筹款出资,有的出地建校,有的知名学者义务授课,学校很快于当年秋季学期开课招生,由此正式成立光华大学。
入学后,学生们以民族安危为己任,发奋图强,刻苦读书,杨荫浏也自然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怀着爱国之志,在校办的第一届英语论文竞赛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竞赛金牌,获奖论文题目是《中国音乐史概要》(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ese Music)。于此可以看出,杨荫浏不仅有着卓越的英文和史学功力,而且有着以撰写民族音乐史来明报国爱国之志的伟大愿望。之所以选择中国音乐史为题进行研究,并撰写英文论文,杨荫浏曾在讲课中说明过,其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由于他擅长音乐,熟悉历史,且对民族音乐有着深厚的感情;二是由于他在圣约翰大学修读世界民族历史课程时,看到了由外籍人士编写的历史课本中,有着长篇大论的欧洲历史,以及篇幅较大的古埃及、印度历史,但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和悠久音乐文化的中国,却只用了极其短小的篇幅简单说明,中国的历史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中显得无足轻重。
杨荫浏为此气愤不已并深刻意识到,只有生存在本土且了解本民族历史的人才能写出丰富、翔实的民族史,中国的历史应该由了解中国的人自己书写。因此,尽管知识尚不全面,观点仍待完善,但青年时期的杨荫浏用这篇个人中国音乐史学的开篇之作,向世界各国发出了中华民族有着辉煌音乐文化历史的证明,这是十分可贵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意识。写好中国自己的民族音乐史这一志向直接影响着杨荫浏日后的治学态度,他倾毕生的心血,浇灌在中国民族音乐的大地上,坚持在中国的土地上做植根深处的本土音乐学研究。
杨荫浏常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传统,怀疑自己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那么,人民将失去对祖国的爱,忘记了历史,便容易为列强所吞灭。为了对爱国运动和学生群体予以支持,杨荫浏取民乐《金陵怀古》一曲,填岳飞所作《满江红》一词,发表了爱国歌曲《满江红》,该曲一经推出便得到爱国民众的广泛传唱,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至今仍广为流传。然而,由于时局动荡,杨荫浏因家庭经济困难,未能修满大学学业,无奈中途辍学,开始教书谋生。
身处时局动荡之时 坚守民乐研究之志
1926年,杨荫浏辍学后回到无锡,先后在辅仁中学、县立中学和宜兴中学等学校担任教员。在宜兴教书期间,杨荫浏每晚到当地的“协和曲社”教授昆曲、担任伴奏乐手,还组织“协和曲社”与“天韵社”举办交流活动,促进昆曲艺术在当地的发展。杨荫浏在中学教书的几年间,仍然坚持钻研我国古代音乐的相关理论。为了能够解决古代乐律的一些基本问题,他利用业余时间研读古籍中关于律学的相关记载,细致严谨地解析着古代的律学问题。由于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古代社会对于音声及音律问题总是要与封建迷信学说等玄学观点捆绑在一起,以神秘之虚来解音律之难。一些古代律学研究脱离了声学原理、听觉生理和心理学等科学理论,甚至用人为的唯心观点混淆着人们对律学原理的判断。为了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探究律学本质,杨荫浏从问题出发,一边了解玄学之论,一边运用数理知识反复验证古代律学理论,并最终通过实践证明了古代音律与封建迷信之说并无必然关联。
1929年,杨荫浏应基督教圣公会的聘请,先后在南京、杭州、北平等地翻译教会歌词,他将符合国人歌唱的音韵规律运用到唱词的编译中,既表达准确的词义,又兼顾音韵与音调的协调关系。在离开大学开始工作以来,杨荫浏坚持写作,撰写了《天韵社溯源》《吴畹卿先生小传》《琵琶浅说》等多篇民族音乐类的文章。1929年,杨荫浏编著的《雅音集》第二集出版,收录了百余首琵琶小曲、二十余套琵琶大曲。1932年,杨荫浏撰写的《工尺改制谈》刊发于北平国乐改进社创办的《音乐杂志》。此后,他得到赴北平工作的机会,与燕京大学刘廷芳博士协作完成赞美诗的编译工作。后经刘廷芳的帮助,杨荫浏在燕京大学旁听作曲、西洋音乐史与音乐欣赏等课程,借阅校图书馆所藏有关音乐的外文书籍,学习赫姆霍兹《论音调的感觉》一书中关于音响学的基本知识。
其实,对于音乐物理属性的探索和思考,可以说是杨荫浏唯物主义科学研究的重要构成因素。1934年,他在北平参加清华大学的“谷音社”,进而更加深入地开展了昆曲演唱和理论研究工作,撰写关于昆曲相关问题的文章。应该说,在北平时期的工作与交流经历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时期的学习和探索既为杨荫浏日后开展深入的音乐研究进行了理论储备,与此同时,对音乐领域相关问题的深刻认识也坚定了其从事专业音乐研究的决心。
锲而不舍 踏上民族音乐研究征程
1936 —1937年间,杨荫浏因其丰富的民间音乐经验和知识、极强的传统音乐奏唱能力以及深厚的中西音乐研究功底,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一职,并在燕京大学教授“中国音乐史”课。在传道、授业、解惑之余,他丝毫没有放松对民族音乐理论的深入探索与研究。为了解析中国古代音乐中复杂的“音律问题”,他依据文献所述和历史数据定制了一套铜质律管,并用实证的方法检验了康熙十四律的科学性。与此同时,他大量钻研历史上各乐律著述,并根据对明朝朱载堉“密律”理论的深入解析,撰写中国古代乐律学研究论文《平均律算解》。在教授“中国音乐史”课的过程中,杨荫浏会按不同的音乐史专题,将平时积累的音乐史知识进行梳理以做好备课工作。同时,他还会在音乐史课程中结合音乐实例进行讲解,并总结出人们更愿意听有音乐的史学课这一重要经验。这些在教学过程中的所思所感,也体现在其日后编写中国音乐古代史的过程中,体现在注重音乐实践性和专题性等多个方面。
1937年暑期,杨荫浏回到无锡,在友人的协助下,收集了数十种苏南民间音乐进行研究,观察迥异之处、积攒各家所长,并最终整理成《梵音谱》《锣鼓谱》两部谱集。谱集具有极高的乐谱文献价值,对民间音乐的整理和传承起到重要作用。经过多年的积淀和更加深入的研究后,他于20世纪60年代将这两个成果以《苏南十番鼓曲》和《十番锣鼓》为谱集名出版。1941年初,杨荫浏开始思考琵琶如何定准品位、笛子等管乐器如何开孔,以求创造出简便通行的乐器定音方法。通过不懈钻研,他运用几何原理,为琵琶弦长与品位计量方式绘制成图,称之为弦乐器定音计。此器经实践验证可准确定量出琵琶、月琴、三弦等乐器的音高。这个成果后经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审定出版,由学术审议会授予了二等奖。

1936年,杨荫浏在燕京大学工作时留影

1937年,杨荫浏在江苏无锡家中演奏三弦
1941年底,鉴于杨荫浏在民族音乐领域的建树,他正式受聘为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教授,兼任国乐研究室主任。翌年,国立音乐院开设昆曲选修课,他将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昆曲艺术带入了高等学府。1943年,他开始教授“国乐概论”及“中国音乐史”等课程,为课程所编写的讲义即为日后所著《中国音乐史纲》的前身。抗战时期的国立音乐院资源匮乏、书籍缺失,杨荫浏幼年时期建立了深厚的文史学科功底,仅凭记忆就可援引书中的经典论述。资料贫乏限制学者的思考,而物质生活的匮乏更会考验一名学者的志向。在艰苦卓绝的生活条件下,杨荫浏在国立音乐院教学期间,编著了《国乐概论》《笛谱》《箫谱》《三弦谱》等教材,与曹安和合编琵琶古曲《文板十二曲》工尺谱与五线谱版本。1943年底,杨荫浏的第一部中国古代音乐史专著《中国音乐史纲》成稿,1944年刻板油印但一直未能出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修订版才于1952年正式出版。完成《中国音乐史纲》的成就并未暂缓杨荫浏的音乐史学探索之路,他期待着在史料更为丰富、学术发展更为全面的将来,再写一部中国音乐史,以回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民族音乐文化的先人们。
在此期间,杨荫浏还着重开展了唐人大曲和宋代姜白石词曲的音乐研究,撰写了《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中国音乐史上新旧音阶的相互影响》等文。特别是1942年7月首次发表的《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一文,对民族音乐的定位、发展、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高瞻远瞩的研究理念、颇具胆识的“呼吁”论点,使该文成为讨论国乐发展及其相关问题的经典之作。
1945年,杨荫浏又根据早年入徒天韵社,师从吴畹卿所学的昆曲知识,结合自身实践经验和音韵理论,撰写了《歌曲字调论》一文。同年,杨荫浏受到哈佛大学刘廷芳博士和燕京大学美籍教授范天祥的邀请,希望他能够赴美研究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学。彼时时局动荡,在前途未卜的大环境下,杨荫浏婉拒了邀约。他坚定地认为,研究中国的民族音乐就应该在中国的土地上。从儿时就紧密相连的民间音乐,早已融入了他的血脉、入住了他的心灵。
1946年,国立音乐院迁至南京,但由于校舍尚未建造完工,学校停课待建;直至1947年春,国立音乐院正式复课,杨荫浏继续任教,并兼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中国音乐史的教学工作。在这一阶段,杨荫浏的学术风格逐渐明晰,治学态度也愈发鲜明,“以实践求真知”是其学术研究始终秉承的原则。1947年,杨荫浏在无锡休假期间着手对笛管乐器如何开孔定律的问题进行实验。他从乐器店购买来制作竹笛的笛坯,反复在不同位置开孔,以实验的方式对管律理论展开探索和检验。在制作了数百支“千疮百孔”的笛管之后,他总结出了笛子的按孔大小、开孔位置等因素与笛管类乐器在音律上的关系,并依实践形成的理论制作了便于笛子开孔定音的两把笛尺。在大量反复实践的过程中,杨荫浏能够熟练地制作长短、粗细、音区、调高不同的笛和箫,这说明他已成为真正搞懂了这类问题的“行家”,而非略知一二却大谈理论的“专家”,二者之间的真正差距就是“实践”的重要意义。为求真知,他依照史料仿制了荀勖创造的黄钟笛,并验证了《晋书·律历志》中记载的理论数据,以现代实证研究验证了中国古代管口校正理论。如此重要的理论成果,杨荫浏并未急切发布或用来增加自己的学术资本,他只在搞清楚相关的研究问题,积累知识和经验后,将仅有的两把亲手制作的笛尺,无偿赠送给了经营乐器店的两位朋友,以供其改良和制作出音准更好的乐器。由此可见,杨荫浏轻名利重实践的学术品行,先生所看重的是研究过程及结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而非研究成果所带来的名利效益。
在南京工作和生活期间,杨荫浏经常与清溪琴社的古琴家集会,悉心记录琴家弹奏的琴曲。他根据传统谱本记录演奏谱,再通过弹奏新谱与琴家的演奏反复校正,并依此方法记录当地各派琴曲数十首,辑成谱册,还据此制成“古琴音位表”。此外,为了民族音乐的对外传播,他细致地编订了中英对照的《琴谱》曲集,其中载录了王燕卿传谱的《古琴吟》《关山月》等曲目。在引言中,他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介绍古琴的构造、音位等乐器知识,文中不仅绘制了精致的古琴形制和演奏手势图等,还说明和标注了古琴的弦长音位比值表,并将琴曲中的古文诗词译为英文韵律诗。其对古琴及演奏技术的论述之详尽、描绘之细腻、介绍之全面、理论之深入,对中西方文化差异考虑之周到,绝非只擅长演奏、演唱或律学某一门学科之人所能为之,凡此谱中所现种种,无不让人赞叹。

1948年5月31日,国立音乐院国乐组第二届毕业生留影,杨荫浏(后排左四)、曹安和(前排左一)
建功立业 开创民族音乐研究新局面
如果将我国悠久璀璨的民族音乐遗产视为一座巨大的文化宝藏,那么,杨荫浏先生可以看作是宝藏的继承者和发掘者。1949年以前的杨荫浏更多的是依靠个人经验和社会力量,继承和发掘民族音乐的宝藏,积累深厚的音乐功底,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国家民族音乐研究领域带头人的杨荫浏,开始在祖国日新月异的进步中,在民族文化艺术事业的广阔天地间大显身手,建功立业,成为了我国民族音乐学科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原国立音乐院于1950年迁址天津,与几所院校合并共同创建了中央音乐学院。杨荫浏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研究部研究员,兼任古乐组组长。此时的民族音乐研究工作面临继往开来的新局面,国家和文化艺术界高度重视民间艺术形式的考察与研究工作,众多优秀的民间音乐艺术正待有识之士的挖掘与整理。这一时期,杨荫浏将全部的热忱与精力铺陈在新中国的民族音乐事业上。先生一生高瞻远瞩,此时的他深刻认识到,能够在音乐研究的范畴内开展任何实践工作,对于日后撰写中国音乐史都是有所益处的。
1950年,获上级批准,杨荫浏带着国内罕见的钢丝录音机回到无锡,专程考察当地的民间音乐情况。他重新找到阿炳(华彦钧),希望为其录制演奏,而当时的阿炳长期患疾,形如枯槁,勉强靠乞讨卖艺为生。为了考察和记录他的演奏,杨荫浏为其临时准备了乐器(阿炳的乐器破损严重),架设好录音设备,待一切就绪后,完整、忠实地记录下这位民间音乐家真情实感的动人音乐。三首二胡曲很顺利地一遍就录制完成了。美妙感人的音乐让杨荫浏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有着深厚音乐功底和实践经验的他,深知阿炳的演奏和乐曲是有着极高艺术水准的民间音乐珍宝。杨荫浏没有丝毫的懈怠,不愿错过时代赋予的机遇,在采录下《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三首二胡曲后,翌日又携录音设备约请阿炳录制了《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三首琵琶曲。完成无锡考察工作后,杨荫浏带着采录的音响成果回到当时位于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当院里的专家、领导听到阿炳精彩绝伦的演奏后,无一不被民间音乐博大精深的艺术内涵所震撼。中国唱片社将阿炳的演奏制成唱片,向全国人民分享这一民族艺术精品;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决定聘请阿炳授课,怎奈阿炳病情加重,于采录当年年底溘然长逝,毕生留下的六首佳作成为绝唱。
在这次弥足珍贵的采录过程中,有一件轶事值得人们追忆。据当时在采录现场的曹安和回忆,阿炳在录完二胡演奏曲之后对杨荫浏说:“你我第一次见面,还是在清朝宣统年间。当时你弹着三弦、我拉二胡,一起合奏了一曲《三六》。弹指一挥间,换了几个朝代,我们也都年过半百,如今何不再来合奏一曲《三六》,留作纪念?”杨荫浏欣然同意了这一倡议,拿起琵琶与阿炳开始了合奏。二人心有灵犀、极为默契,阿炳在胡琴上不断加花变奏,杨荫浏则在琵琶上不断花样翻新。二人精妙绝伦的演奏使在场的人们如痴如醉、赞不绝口。曹安和日后回忆称:“两人合奏的《三六》把乐曲演绎得活灵活现、变化多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好的即兴配合,可见两人演奏技艺的高超。”

1950年,杨荫浏表演笛子独奏
此行考察和采录活动被音乐学界公认为是抢救优秀民间音乐遗产的典范之举,不仅奠定了新中国民间音乐研究高水平高标准的学术根基,更是为中华民族乃至世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艺术遗产,对新中国的民族文艺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杨荫浏来自民间,方知民间音乐之珍贵;他熟悉和了解民间艺人,并愿意回到他们中去。可以说,倘若没有他的慧眼识珠和文化自觉,阿炳将难以千古流芳,今人或将无缘聆听《二泉映月》此般感人肺腑之音。此次考察期间,杨荫浏还收录了《苏南十番鼓》《十番锣鼓》等合奏曲,收集了天韵社表现鼓板特色的昆剧十余出,为后世留存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艺术、学术价值的民间音乐资料。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十分重视民族文化艺术的发掘与保护工作。伴随着新中国的全面发展,杨荫浏厚积薄发,1952年出版《瞎子阿炳曲集》《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1953-1954年间,油印或刊发《中国历代乐器说明》《音乐业务参考资料二种》《中国的乐器》《写给学习吹奏箫笛的同志们》等文论,其中《中国历代乐器说明》是其以历次实地考察中所测量的乐器作为参考,依比例绘制而成的中国历代乐器图册,收录一百五十余幅手绘乐器图稿。
1953年,杨荫浏正式赴北京,接受文化部任命,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副所长,参加民族音乐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同年,他参加“智化寺京音乐”考察工作,抄录寺僧保存的乐谱,编写《智化寺京音乐》考察记录。7月,杨荫浏参加第二次赴陕西采访小组,后油印考察记录《陕西的鼓乐社与铜器社》。在此次采访中,他发现当地鼓乐社保存的曲谱与南宋姜白石歌曲所用曲谱有相近之处,这为他日后开展“姜白石歌曲十七首”的译谱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9月,杨荫浏参加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此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国音乐家协会,杨荫浏当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并于1954年被推选为常务理事。1954年3月27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正式成立,并举办建所仪式和音乐会,杨荫浏担任副所长一职。1956年4月,他率领民族音乐研究所对湖南四十余县进行民间音乐普查,编辑出版《湖南音乐普查报告》;同年,发表《对古琴曲〈阳关三叠〉的初步研究》《工尺谱的翻译问题》等学术成果;他撰写的《中国古代音乐的发掘和整理》一文被译成英、俄、日三种文字予以发表。1957年7月,杨荫浏亲赴苏联出席青年联欢节,被聘为艺术竞赛活动民族器乐组评委,并作《中国的民间器乐》等报告,对外介绍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文化。

1953年7月,杨荫浏(右二)采访西安鼓乐时与樊昭明、李石根等留影
倾一生所学 成一代宗师
1959年,杨荫浏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60年,在李元庆先生的支持下,杨荫浏正式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所长。
伴随着新中国的蓬勃发展,民族民间音乐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为了不负祖国和民族的期望,杨荫浏欣然接受了撰写中国古代音乐史的重要任务。自求学之时起,他便有着撰写民族音乐史的愿望,如今,时代仿佛就等待他倾一生之所学,为中国古代音乐史这位巨人树碑立传。然而,中国古代地理范围之广、历史跨度之大、音乐种类之繁多,着实使研究和撰写工作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据曹安和回忆,自接受中国古代音乐史的任务以来,杨荫浏更加勤于写作,每至深夜。杨荫浏编写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是学界公认的史料最为翔实、立论最有根据、理论与实践联系最为密切的音乐通史类权威著作。能够具有如此高的学术评价,除了依靠先生深厚的文史研究功底,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积累的丰富民族民间音乐实践经验,上述双方面的紧密结合,方使先生得以观今鉴古,成就中国古代乐史的丰功伟业。

1956年4月,采访队在湖南长沙岳麓山爱晚亭合影,杨荫浏(左六)、曹安和(左七)
在同一时期,杨荫浏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在习读哲学理论经典之时,不仅批注个人会意之处,还做了毛泽东著作的学习索引。出于对《实践论》的领会和延伸,他力求以科学、客观的视角进行中国音乐文化的剖析和研究,坚持科学、审慎、以实践为标准的治学态度。杨荫浏还批评学界中一切脱离实践、空谈理论的学术作风,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后人在理论研究上陷入空泛无据之谈,树立了在音乐艺术研究中,注重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治学标准。可以说,“客观”和“认真”是他对待一切研究问题的基本态度。

左起:李元庆、查阜西、溥雪斋、杨荫浏、管平湖在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门前合影
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于北京,原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划归中国音乐学院,杨荫浏继续担任所长一职。1966年,他撰写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之辽、宋、西夏、金部分相继出版,后受“文革”影响,不得不暂停书稿撰写工作,他的中国音乐史暂时搁笔于元朝时期,构筑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历史重任无奈被搁置。直到1973年,杨荫浏回到北京,身患脑血管疾病的他在古稀之年,依然怀着对中国音乐的热忱与挚爱,抱着对民族文化的崇敬与自律,以颤抖着的枯瘦身躯重启巨著华章,最终“筑”成了这座中国古代音乐史的里程碑。

1961年,杨荫浏研究宋代歌曲
1969年底,杨荫浏于河北省怀来县“五七”干校工作学习。1970年,随干校迁至河北静海县团泊洼农场,在第四连负责收发工作。“文革”期间,杨荫浏先后两次被借调回京,作为古代史学专家参与音乐文物的考古工作。1971年7月,他协助故宫博物馆鉴定湖北江陵县发掘的彩绘编磬(战国时期),以及长沙楚墓出土的战国瑟,并撰写书面鉴定报告。1972年9月,他与李元庆、李纯一赴湖南长沙,考察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古代乐器。同年,杨荫浏正式调回北京。1975-1977年,《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下册之二、三部分,即中国古代音乐史明清部分撰写完成,并交付油印。

1961年,杨荫浏、曹安和在北京表演琵琶、箫重奏
20世纪70年代,文化部整合中国戏曲研究院(1951年成立)、民族美术研究所(原中国绘画研究所,1953年成立)、民族音乐研究所(原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1954年成立)的艺术科研力量,将三大民族艺术研究所合并为文化部艺术研究机构,至此,原民族音乐研究所的职能和人员全部划归至该机构,杨荫浏继续担任所长,开启了全新阶段的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工作。1975年,文化部艺术研究机构更名为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1978年,文学艺术研究所改为文学艺术研究院,由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兼任院长。1978年,年近耄耋的杨荫浏先生担任文学艺术研究院院级顾问,不再负责相关行政工作。同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中国音乐家协会恢复工作,杨荫浏任中国音协理事。1979年,由李元庆先生正式担任音乐研究所所长,1980年,文学艺术研究院正式改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

1979年,杨荫浏与学生在家中合影(前排左起 :乔建中、杨荫浏、冯洁轩、张静蔚、伍国栋;后排左起: 何昌林、梁永生、王宁一、吴文光、居其宏、魏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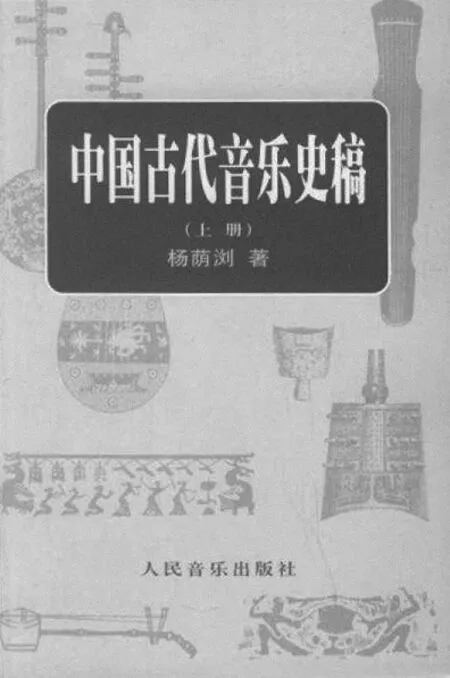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1981年,在中国音乐历史研究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撰写完成,全书共计45万字,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远古至宋代部分,下册为元、明、清三代部分,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于同年出版。在完成《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撰写工作后,杨荫浏迟迟不能放下中国古代音乐的音律问题,他认为,如果古代乐律问题仅是从历史文献的角度进行论述,可能会造成科学性存疑的情况。通过深入研究,他发现某些产生或用于弦乐器的律制在实践中未必符合管乐器的发声规律。管乐器的音律受制于振动形式、乐器形制、以及管径大小、孔径大小等诸多因素。杨荫浏通过反复验证的方式,提出了弦律不应用于管律的观点,并明确说明他对音乐理论研究所持的态度是尊重事实和民间传统,而不教条于书本;他反对因为要勉强造成某种理论的圆满而抹杀事实的治学态度。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不仅体现在对理论知识的研究和实践上,也体现在对于历史文献的质疑上。杨荫浏发表《管律辨讹》一文,不仅证明某些古代文献存误,还提出了不能在未证实的情况下尽信文献的治学观点。
1982年,杨荫浏总结自己关于中国乐律学的研究心得,撰写律学研究成果《三律考》并发表于《音乐研究》;同年,杨荫浏同意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个人论文选集,并开始亲自选订篇目,逐一校定原文。1983年,他因病住院治疗,出院后身体虚弱,甚至无法站立,至年底时已卧床不起。1984年2月25日,杨荫浏先生因病于北京辞世,享年84岁。在辞世的几个月前,他在病榻上校订自己作于20世纪初的旧作,完成了《杨荫浏音乐论文集选》的出版工作。先生是不愿带着未完的工作和学术遗憾离开他所热爱的民族音乐事业的。
结语

1981年,杨荫浏晚年家中留影
回顾杨荫浏先生的一生,先生将全部心血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民族音乐艺术,为新中国民族音乐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先生以其丰富的音乐经历、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强大的音乐技能与学术能力,抱着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不畏艰辛的敬业精神,完成了大量的民族音乐实地考察和历史研究,成就了民族音乐研究的伟大事业。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更是感受到了民族和时代的召唤,倾一生之所学为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生自幼以兴趣为老师,执一生之信念坚守所爱的民族音乐艺术;先生聪慧好学,苦练音乐技能,培养多重音乐能力;先生文史功底精深、学贯古今中外,有着强大的学习能力和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先生注重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考察经验,挖掘了大量民间优秀艺术珍宝,推动了具有本土特色的音乐研究体系的建立;先生长期钻研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结合实证结论,提出独到学术见解,引领学术发展方向;先生以史论观照现存民间音乐,以实地考察发掘历史线索,扩展音乐史学研究的维度,写出能够发声的古代乐史巨著,筑起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里程碑。可以说,先生在撰写中国音乐历史的同时,也因所做的历史贡献而被载入史册,永为后人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