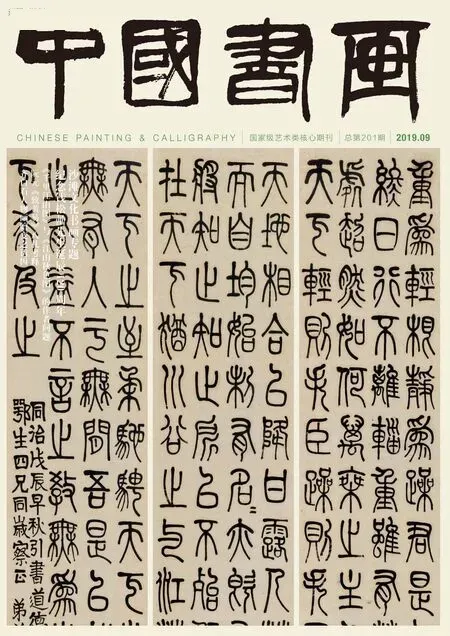日本美术对陈之佛工笔花鸟画风格的影响
◇ 张鲁
近代中国画坛一批赫赫有名的人物均有跨海东赴日本学习的经历,如何香凝(1878—1972)、高剑父(1879—1951)、陈树人(1884—1948)、朱屺瞻(1892—1996)、徐悲鸿(1895—1953)、陈之佛(1896—1962)、张大千(1899—1983)、傅抱石(1904—1965)等,所举各位基本上构成了中国画在近代发展的重要部分之一,他们各自代表了“岭南派”“后海派”“后京派”和“江苏画派”。“岭南派”诸家多有东渡扶桑的经历,留日似乎成了跻身画派的资格与条件。他们对于日本画的“借鉴”或称为“折中”,主要集中在所谓“新日本画”〔1〕的“朦胧体”〔2〕等,不仅师其技,更有摹其迹,有目共睹,无须多述。“后海派”与“后京派”受日本的影响相对较弱,朱屺瞻与徐悲鸿则是将日本作为“窗口”与“跳板”,希望从先于中国接触西方的日本了解更多的关于西方艺术的信息与知识。张大千有特殊性,他在日本修习了染织与绘画,他的中国画创作主要受到了中国画传统的影响,或许晚年泼彩画中对于色彩的控制与把握会有些许日本画淡淡的影子。“江苏画派”的一些现象较之其他要复杂隐晦得多,傅抱石与陈之佛为“江苏画派”的中坚,他们二人的创作实践与艺术成就对于“江苏画派”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之佛的工笔花鸟画不论其表现形式、创作手法、格调意境均受到日本画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本是日本文化的母文化,中国文化是构成日本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代日本美术便是以中国初唐美术为基点与核心,从属于中国文化。日本画早在奈良时期(710—794)、平安时期(794—1192),便开始以中国画作为追摹学习的范本,从中国画出发,逐渐形成所谓的“大和绘”。在其后的镰仓、室町、桃山,甚至是江户时代(1603—1868),日本画的基础与语言元素均可以在中国画中找得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画开始有了不一样的面目。
中国文化在被几乎全盘“拿到”岛国文化〔3〕的日本后总有“水土不服”之处,从绘画角度考量,这不同之处集中体现在审美追求方面。尽管从绘画表象上来看,日本画与中国画确有太多相似之处,但其独特的审美视角与追求,从“大和绘”〔4〕抑或更早起便有所不同。纵使日本画使用的工具与表现技法与中国画几乎相同,甚至我们可以将日本画当作中国画的一个流派,或者衍生品来看待,不过,日本画中的民族性格,对于时间与空间的感怀、对于色彩的迷恋、对于实用性装饰意味的追求,以及对于文学性倾向的展示等方面却异于中国特色。
差异最初就存在,继而分道扬镳也就在所难免。随着日本美术的发展,日本画自然走上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虽然其间不时有力量试图将其拉回“中国化”,然而,日本画还是有了一副属于自己的面孔。明治(1868—1912)以后,出于对“高势能文化”〔5〕的向往,日本画的面貌变得“洋气”了,由于学习中国画传统的不彻底状态,使得“轻装上阵”的日本画“转型”起来负担要轻得多。
甲午战争的战败对中国的影响,除了割地、赔款之外,就是以日本为师。中国对日本的学习涉及了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近代新知。近代中国画的状态确实沉郁低迷,如何发展?需不需要“革命”?都成了问题。西洋的、东洋的统统摆在我们面前,中国学人们慌了,前赴后继地留西洋、赴东洋,整个社会都充斥着迷惘与混乱,这微不足道的画坛自然难以躲避。于是,不论是中国画的创作、美术理论的研究、美术展览的形式、美术教育的开展等均烙印上了“日本主义”〔6〕的痕迹。

图1 陈之佛 梅梢三雀图轴 49cm×60cm 纸本设色 1941年 南京博物院藏

图2 陈之佛 鹰雀图轴 122cm×57cm纸本设色 1944年 南京博物院藏
作为中国赴日本学习工艺美术的第一人,陈之佛选择的工艺图案科十分契合日本美术的本质。装饰与色彩是图案的两大要素,日本美术的显著特征便是装饰性与色彩感,其装饰性与色彩感基本服务于与日常生活相关联的实用性,所以,绘画与工艺的无差别性是日本画的特征与传统,也就导致日本的工艺概念常常在艺术表现中出现。也正是因为日本美术中存在的这种无差别与融通性,才使得日本美术史上“宗达—光琳派”〔7〕这种装饰画派大放异彩,成为日本民族审美特色的一个释放点,对江户时期以及近现代的艺术创作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设计是“宗达—光琳派”的一大特色,它跨越了绘画与工艺美术的界限,创造出最具日本文化与民族特色的绘画艺术,故而在日本留学近五年,深受日本美术“熏陶”的陈之佛能够在工艺与工笔花鸟画之间游走。
日本早期的花鸟画受到了中国花鸟画的影响,在艺术上并没有独具特色可言,其最高的艺术境界追求,便是以中国的花鸟画为标准和目的,尤以宋代花鸟画为最。随着桃山时代(1573—1603,大致相当于明代中期)狩野派〔8〕花鸟画的成熟,具有日本民族特性的花鸟画得以确立。其后,随着“宗达—光琳派”将装饰艺术手法引入花鸟画,使得日本的花鸟画已与中国花鸟画在审美追求上相去甚远。日本花鸟画一方面强调写实性,一方面又追求装饰性,对色彩的色调细微复杂,写生技法精湛严谨,制作精良巧妙,既有纯粹的表面装饰性又有精神境界的美的追求。
日本的花鸟画如此,陈之佛的工笔花鸟画又是如何呢?
2006年,日本东京国立美术馆举办的“若冲—江户绘画”展览,其中展出了“宗达—光琳派”的后继酒井抱一的作品《十二月花鸟图》,其画面感觉、语言技法、图像构成等诸多元素与陈之佛工笔花鸟画如出一辙。酒井抱一生于1761年,卒于1829年,早于陈之佛一个多世纪,陈之佛留日期间浸润于日本美术之中,从其工笔花鸟画作品来看,日本花鸟画对于他工笔花鸟画创作的影响远远大于中国传统工笔花鸟画。这种影响不仅来自强烈的装饰感、丰富的色彩,还来自具体的形貌构成与审美趋向。
一、关于“积水法”
陈之佛在树干、树枝、树叶、湖石,甚至是禽鸟羽毛的表现手法上,利用熟宣纸的不吸水性,让湿度较大的墨迹、水迹和色迹在所需形象内自然收干留下痕迹。对于陈之佛这种“积水法”的具体操作过程,他的女儿陈修范曾记述:
积水法,又称水渍法,是陈之佛多年来从写意画的“水化墨”,没骨画的“撞粉法”中探索、演变而成的一种独特技法,利用熟宣不渗水的特殊性能,造成别有意趣的艺术效果。积水,是指绘制的方法,按照作者的构思,用含水分较多的一种颜色进行描绘,不勾线、不渲染,趁其潮湿时,根据画面的需要,用笔滴上清水或醮上浓墨、石青、石绿点画,再用清水冲开,使聚积的饱和水色,自然流淌,互相渗化,从而达到意想不到肌理变化。水渍,是指积水法最后呈现的艺术效果。即色彩干后,所形成的水渍,斑烂绚丽,天然成趣。这种方法,在他的绘画上运用较多,而且非常成功。像《梅花山茶》的茶花叶片,《寒汀孤雁》的滩头地面,《蔷薇双鸡》中鸡的羽毛等都采用此法。但运用得最多的是树干,用不同积水方法.表现不同的意趣。从《梅树白鹰》《梅花双鸽》《茶梅小鸟》《岁首双艳》《梅花群雀》《樱花小鸟》《睡鹊》《鸣喜图》《和平之春》等画面的树干表现上,可以看出他用得极为娴熟,巧夺了造化之妙〔9〕。
简而言之,其方法即先用一种墨赭色调落笔,趁颜色潮湿未干之际滴上浓墨、石绿和清水,并恰当地控制水的分量、流淌方向和所要覆盖的地方,使其洇开或互相渗透,干后便形成斑斑驳驳的纹理。一般认为“积水法”系由陈之佛创造并擅用的一种表现手法。严格说来,“积水法”古已有之,只是在重视文人画笔、墨的格局下使用率不高而已。然而,这种技法在日本,特别是在“宗达—光琳派”之时,已被广泛使用,且运用得宜,表现适度,充分做到了装饰性与趣味性兼具。我们可以从诞生于18世纪的尾形光琳的名迹《红梅白梅图》中清楚地见到:两株老梅的树干是色彩变化最为复杂的区域,光琳利用矿物颜料的不同性质,让它们在不吸水的金箔上自然交融,形成类似于“没骨法”的扑朔迷离的特殊效果〔10〕。
这里所谓的“特殊效果”,就是陈之佛笔下的“积水法”。
我们能还从酒井抱一《十二月花鸟图》、铃木其一的《渔樵图》《柳荫白鹭图》等众多画家的画作中见到与陈之佛所谓“积水法”如出一辙的没骨叠色积染法。
二、关于禽鸟的造型与设色法
从几幅陈之佛临摹的宋代工笔花鸟画中可以看到,若论其技法的微妙与精到处,无法与宋画相提并论。通常认为,这是陈之佛以小写意观念解释传统工笔技法,然而我们阅读日本的“写生画稿”则能找到其真正缘由。

图5 陈之佛 寒月双栖图轴 86cm×39cm纸本设色 1948年 南京博物院藏

图6 陈之佛 秋塘露冷图轴 82cm×45cm纸本设色 1948年 南京博物院藏

图7 陈之佛 雪芦落雁图轴131cm×47cm 纸本设色1948年 南京博物院藏

图8 陈之佛 桃花春禽图轴102cm×36cm 纸本设色1960年 南京博物院藏

图9 陈之佛 梅枝气鸠图轴104cm×34cm 纸本设色1961年 南京博物院藏
日本16世纪开始出现类似于中国《芥子园画谱》之类的图谱,内容以花鸟类为主,如《鸟类图》卷、狩野探幽的《草木花写生图》卷、尾形光琳的《鸟兽写生图》卷、渡边始兴的《鸟类真写图》卷、圆山应举的《昆虫写生帖》等,后世称之为“写生画稿”。这些图谱的影响面极广 ,为日本花鸟画创作提供了翔实绘制方法与众多的粉本资料。特别是今尾景年绘制,日本明治二十五年(1893)刊刻的《景年画谱》〔11〕,陈之佛曾大量地仔细临摹。然而,正因为是绘画图谱,以图示为主要目的,所以没有完整的绘画作品来得细腻工整,然而恰恰如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陈之佛的工笔花鸟画与之相联系,从中找到陈之佛工笔花鸟画形貌构成的画法根源。

图10 日本酒井抱一(1761—1829) 《十二月花鸟图》屏风(12选3)

图11 日本山本梅逸《樱图》、酒井抱一《十二月花鸟图》与陈之佛画作的比较
还是《景年画谱》,由于是五色木版套印,一是色彩相对少,二是工笔画应有的色彩分染技法,只能依靠深浅度不同的色彩叠加来代替,这也就难免有色彩渐变过渡生硬的痕迹。反观陈之佛的作品,他在设色时同样也主要采用色彩平涂,很少分染,或者几乎不分染的方法,同样也有色彩渐变过渡生硬之嫌,与《景年画谱》中色彩套印的效果十分类似。
三、关于意境的营造
日本是一个相对封闭,多火山、地震的岛国,地域环境、自然风物、宗教意识、中国文化的影响等,这些因素经过相互杂糅、渗透、演变、升华,形成了日本人特有的性格和审美意识。“物哀”“空寂”与“玄幽”既是日本人的精神内核,也是日本民族审美性格的主体,还是日本人审美意境的原则。悲婉与凄怆、柔美与淡雅、萧寒与肃杀、空灵与幽玄、沉静与典雅,日本传统艺术表现出来的情感与意境营造和日本人的内在精神密切联系。
与日本美学性格中的这些独特的美感意境相对应,日本美术中的线条多柔和、纤细,色彩淡雅、柔美,传达着恬淡、古雅、朴素、内敛的色彩意象,追求那种经历时间磨砺之后所呈现出的褪色、幽暗、晦涩的痕迹,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朦胧的、阴暗的、内敛的、洗练的色彩意境,让人观阅后陷入“空”和“暝”的世界。在图式、技法、色彩和审美趣味等作品构成诸因素中,纯技术部分是容易变化的,而不易改变的是由千百年历史文化所酿化出的审美情趣。它是传统艺术中最为本质与核心的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前,陈之佛的工笔花鸟画的色彩意象与意境气息刻意地遵循着幽雅、精炼、静寂、恬适、清淡、深沉、淡泊的日本艺术基本的审美精神,所以,他的工笔花鸟画大多用锈色、暗花青色等灰色调打底,以烘染、衬托画面气氛。在新中国成立后,陈之佛的工笔花鸟画也顺应时代向着浓艳、热烈、激情靠近,但是日本审美趣味的还是时常在他的画作中流露。
日本美术对于陈之佛工笔花鸟画风格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之佛工笔花鸟画对于日本美术的吸收也拓展了他工笔花鸟画的表现领域与表现题材。其工笔花鸟画雅致清幽,恬淡古雅,气息沉静,让人沉醉。

图12 《景年画谱·春 九》与陈之佛摹本

图13 《景年画谱·春 十五》与陈之佛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