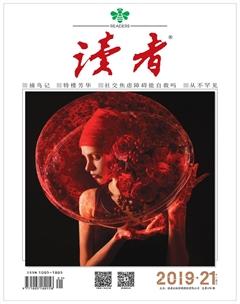生命的延续
闫坤沐
2019年2月,中国器官捐献志愿登记总人数突破100万——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官方网站的首页,截至2019年2月28日,志愿登记人数的具体数字为:1055722人。
协 调
我国从2010年开始试点公民志愿器官捐献,至今已累计实现捐献23219例,捐献器官64087个。从绝对数字来看,捐献、移植数量均已位居世界第二。但由于人口基数巨大,器官的供需依然处在极度不平衡的状态。
通常,在临床发现已经救治无望的潜在捐献者后,器官捐献协调员会出面与家属沟通捐献意愿,如果家属同意捐献,他们会协助家属处理捐献文件,并由医生把捐献者的信息录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系統会综合考量配型、病情严重程度、地域、等待时间等因素,自动匹配受捐者。

俞欢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实际工作中,字面意义上的“协调”大多都会表现为现实中的艰难“劝说”。
当发现潜在捐献者后,俞欢第一时间询问家属是否有捐献意愿,而这常常会被视作一种冒犯。
例如,捐献是无偿的,但接受移植的人为何要付出几十万的费用?这让有些捐献者家属认为,协调员是倒卖器官的人。面对这种质疑,俞欢会告诉家属,这些费用是用来支付器官运输、保存等移植过程中产生的成本,而器官本身仍是无偿的。
还有,如何让家属在捐赠同意书上写下:放弃治疗。
在我国,法律规定的死亡标准是:心跳、自主呼吸停止,血压为零,瞳孔扩散,反射消失。但由于医疗技术的发展,临床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状况:脑干或脑干以上中枢神经系统永久性地丧失功能,但在呼吸机的作用下,病人还可以被动呼吸,维持心跳和血液循环。
这时,患者已经脑死亡,失去了被救活的可能,但家属依然觉得他还活着,哪怕付出高昂的成本也愿意维持这种状态。而根据捐献器官的规定流程,家属需要在同意书上写下“放弃治疗”,然后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拔掉呼吸机,不再呼吸,最终离世——对于本身就忌讳谈死的中国人,是一个无比艰难的过程。在家属挣扎犹豫期间,器官也会不断衰竭,慢慢失去移植的价值。
现实中,很多适合的潜在捐献者都是突发意外,如脑出血或者车祸,这种状况会更复杂。根据我国相关规定,器官捐献要配偶、父母、子女三方共同签字同意,但有时,突发意外去世的潜在捐献者的父母已经年迈,家人甚至不敢告诉老人孩子去世的消息,遑论让他们签字。而在意外面前,家属还需要时间接受现实。有时,在家属同意捐赠后,俞欢会让他们再陪伴亲人一晚,在医疗需求和人文关怀之间寻找平衡。
完成了前期的全部流程后,在摘取器官的过程中,协调员还会代表家属到手术室中见证和监督,并且协助家属办理后事。这也意味着完成捐献并不代表协调员工作的完结,他们还需要处理很多的后续状况。
比起工作中的琐碎与复杂,俞欢还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是:做协调员并没有可以预见的职业发展路径,这也是在中国做器官捐献协调员需要面临的困境之一。
在器官移植事业开展比较早的国家,协调员已经是一个独立的职业,而在中国,他们大多由医院的医护人员或者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经过培训后兼职从事。在成为协调员之前,俞欢是医院ICU的护士。一开始是兼职,但迅速增加的工作量很快不允许兼顾,她只能选择全职。
等 待
一边是对捐献者家属的劝说、协调,而另一边则是捐献受者的漫长等待。这个过程有多折磨人,李成感受过。
2015年4月,他被确诊为扩张性心肌病晚期,心脏壁很薄。医生告诉他,这种情况极度危险,哪怕是上厕所起身,都有可能引发心脏壁破裂出血,人在短时间内就会没命,移植是唯一的出路。
一开始,李成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他在网上搜索“心脏移植”,查到的几乎全是负面信息:花费高昂,死亡率高……他想,花几十万还有可能下不来手术台,不如在家养病。谁知情况越来越糟,他慢慢失去行动能力,甚至连饭都吃不下去。
2016年11月,抱着搏命的心态,他住进了北京阜外医院的ICU。
心脏移植配型的过程像是一场竞赛——一旦有捐献者,医生会同时通知几个等待移植的病人空腹抽血,然后带着他们的血样连夜飞到捐赠者所在地去做配型。与此同时,这两三位候选者会进行手术的准备工作,但只有相关指标匹配程度最高的患者才能获得手术机会。第二天一早六七点,病房的电话铃响起,接听的护士会宣布谁是中标者,然后推着他进手术室,对没能中标的人来说,就是空欢喜一场。
从11月一直等到第二年4月,李成做了8次配型,有3次连手术车都来了,最后还是没做成。2017年清明节期间,李成终于做上了手术,这距离他入院已经过去了半年。
以前有人和他说,做完手术整个人就焕然一新了,他不相信,哪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真做完了,李成最直观的感觉是,血管鼓起来了。以前心脏功能弱的时候,血压极低,抽血的时候看不见血管,针扎进去也不见血往外流,扎好几下才出一点血。手术之后再抽血,针一扎进去血就出来了。
如今,李成偶尔会坐在马路边,看来来往往的人群发呆,庆幸世界的嘈杂还和自己有关。他每两三天就会更新一条朋友圈,主题就一个:今天陪女儿玩了什么。他说,生病以前对女儿的未来有很多期望,但现在只希望她能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快乐就好。
生 存
姚银渊是一个肝移植受者,在浙江海宁市的一个社区工作。生病时,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当地媒体为姚银渊组织了募捐,并且全程记录了他手术的过程。手术半年后,他就回到了工作岗位,并且成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器官捐献志愿者,他以过来人的身份为移植受者和家属提供咨询、辅导。
他组建过一些QQ群,聚集当地接受过器官移植的人,希望大家互相关照、鼓励。但他很快发现,线上聊得不错的朋友,并不愿意参加见面会。
这让姚银渊意识到,如何证明自己拥有参加工作的能力,对很多受捐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有个受捐者,老板知道他做过移植,就说,这人不要。你拿体检报告给他证明一切正常都没有用,他怕你哪天要是不好了,会让企业承担责任。”
姚银渊并没有遇到这种状况,为了让更多人看到移植受者的生活状态,他反而愿意有更多的机会面对媒体。接受采访时,他对病友中的励志案例也是如数家珍:“像老吕,60岁了,他是警察嘛,参加公安系统的运动会,老年组游泳没有人能比得过他。”“还有一个阿汤哥,身体好到什么程度,他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参加铁人三项,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他相信这些正面例子会带来精神力量。
理 解
如何让更多人了解器官捐献、了解这对受捐者的意义,是张珊珊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她是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宣传部的负责人。2014年4月,一个特殊的器官捐献案例在中国发生。
在这个案例中,捐献者夫妇是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女儿蒂安娜7个月大时因为吸入异物导致窒息。得知救治无望后,他们主动提出捐献器官,蒂安娜成为我国首例外籍器官捐献者。
蒂安娜父母作为捐献者代表,参加过一场和受捐者代表见面的活动。
当时距离蒂安娜离世已经一年。一路上,张珊珊都在想:那些移植受者,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感谢捐献者家属?现场的反应出乎张珊珊意料,蒂安娜的妈妈是最激动的那个人,她给每个移植受者都准备了礼物,忍不住抱着他们亲吻。“那一刻我就明白了,对蒂安娜的妈妈来说,她也感激这些孩子让她女儿的一部分还活着。”她并没有沉湎于女儿的离去,反而为她能挽救别人的生命而自豪,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看待生命的方式。
2016年9月,因为一个新闻专题片的拍摄,张珊珊接触到在重庆生活的果果父母。
果果去世时13岁,像花朵一样含苞待放,还刚刚创办了自己的文学社。一天,她在学校突发抽搐,送到医院后被诊断为先天性的脑血管畸瘤突然破裂导致大量出血,经过两天抢救依然无力回天。果果的父母做出把孩子的器官捐献出去的决定——她的一对角膜、肾脏和肝脏分别移植给了5个受捐者,唯独心脏,父母没舍得让它离开女儿的身体。
见到这家人是在果果的告别仪式上。现场被设计成欢送会的样子,家长以果果的口吻写道:“我完成了在人间的使命,我现在要离开了,回到天上去做一颗星星。”孩子穿着蓝色的公主裙,果果妈妈也穿着天蓝色连衣裙,长发垂在肩膀,她给周围人的感觉是,内心极其平静。
张珊珊带着摄制组找了个房间和果果父母坐下来,她向他们表达歉意——在这样悲伤的气氛下还要进行采访。果果父母说:“我的女儿救了5个人的命,她还活着呢。”
因为这些捐献者家属,张珊珊开始深刻理解器官移植捐受双方的关系——这并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伟大付出。对捐献者家属来说,移植受者的存在也是重要的情感寄托,这是一件造福双方的事情。
将目光投向移植受者后,张珊珊开始调整工作思路,鼓励移植受者面对媒体,传达他们的生命力量。而对器官捐献者的家属,比起被歌颂,他们更需要的是大众的理解。
一个江西农村家庭,男孩18岁,在外打工时出车祸抢救无效,家属做了捐献器官的决定。父母回到江西老家,借钱的人就找上门来。村里不相信有人会做这么伟大的事情,有传言说他们把孩子的器官卖了。男孩的妈妈每次出门,背后都有人指指点点,她只好躲在家里哭。
得知此事后,张珊珊特意邀请男孩的父母来参加活动。在上海的宣传活动上,他们被请上台领了一座水晶纪念杯,并且和红十字会会长陈竺合影。这个妈妈激动地说:“现在回去,我就可以把照片摆在家里,告訴他们,我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你们不能再说我了。”
(潘羽荣摘自《博客天下》2019年第6期,本刊节选,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