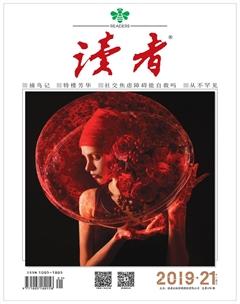秋天的音乐

火车一出山海关,我便戴上耳机听起这“秋天的音乐”。开头的旋律有些耳熟,没等我怀疑它是不是真的在描述秋天,就下巴发懒地一蹭粗软的毛衣领口,两只手搓一搓,让干燥的凉手背和湿润的温热手心舒服地摩擦,整个身心进入秋天才有的一种异样甜醉的感受里了。
我把脸颊贴在窗玻璃上,挺凉,带着享受的渴望往车窗外望去,秋天的大自然展开一片辉煌灿烂的景象。阳光像钢琴明亮的音色洒在这片收割过的田野上,整个大地像刚生了婴儿的母亲,躺在开阔的晴空下,幸福地舒展着丰满而柔韧的躯体!从麦茬里裸露出的浓厚的红褐色是大地母亲健壮的肤色;所有树林都在炎夏的竞争中把自己的精力膨胀到头,此刻自在自如地伸展着优美的枝条;所有金色的叶子都是它的果实,一任秋风翻动,夸耀着秋天的富有。真正的富有,是属于创造者的;真正的创造者,才有这种潇洒而悠然的风度……一只鸟儿随着一串轻扬的小提琴旋律腾空飞起,它把我引向无比纯净的天空。任何情绪一入天空便化作一片博大的安寂。这愈看愈大的天空有如伟大哲人恢宏的头颅,白云是他的思想。有时风云交汇,会闪出一道智慧的灵光,响起一句警示世人的哲言。此时,哲人也累了,沉浸在秋天的松弛里。它高远、平和,神秘无限。大大小小、松松散散的云彩是他思想的片段,而片段才是最美的,无论思想还是情感……这些精美的片段伴随着空灵的音乐,在我眼前流过。那乘着小提琴旋律的鸟儿一直钻向云天,愈高愈小,最后变成一个极小的黑点儿,忽然“噗”地扎入一个巨大、蓬松、发亮的云团……
接下来的温情和弦,带来一片疏淡的田园风景。秋天消解了大地的绿,用它中性的调子,把一切色泽调匀。和谐又高贵,平稳又舒畅,只有收获的秋天才能这样静谧安详。几座闪闪发光的麦秸垛,一缕银蓝色半透明的炊烟,这儿一棵、那儿一棵怡然自得地站在平原上的树,这儿一只、那儿一只慢吞吞吃草的杂色的牛。在弦乐的烘托中,我心底渐渐浮起一张又静又美的脸。我曾经用吻,像画家用笔那样勾勒过这张脸:轮廓、眉毛、眼睛、嘴唇……这样的勾画异常奇妙,无形却深刻地印在脑海里,你嘴角的酒窝、颤动的睫毛、鼓脑门和尖翘下巴上那极小而光洁的平面……近景从眼前疾掠而过,远景跟着我缓缓向前,大地像唱片慢慢旋轉,耳朵里不绝地响着这曲人间牧歌。
一株垂死的老树一点点走进这巨大的唱片。它的根像唱针,在大自然深处划出一支忧伤的曲调。心中的光线和风景的光线一同转暗,即使一湾河水强烈的反光,也清冷,也刺目,也凄凉。一切阴影都化为行将垂暮的秋天的愁绪;萧疏的万物失去了往日共荣的激情,各自挽着生命的孤单;篱笆后一朵迟开的小葵花,像你告别时在人群中的最后一次招手,被轰隆隆往前奔的列车甩到后边……春的萌动、战栗、骚乱,夏的喧闹、蓬勃、繁华,全都消匿而去,无可挽回。不管它曾经怎样辉煌,怎样骄傲,怎样光芒四射,怎样自豪地挥霍自己的精力与才华,毕竟过往不复。人生是一次性的,生命以时间为载体,这就决定了人类以死亡为结局的必然悲剧。一种浓重的忧伤混同音乐漫无边际地散开,渲染着满目风光。我忽然想喊,想叫这列车停住,倒回去!
突然,一条大道纵向冲出去,黄昏中它闪闪发光,如同一只号角嘹亮吹响,声音唤来一大片拔地而起的森林,像一支金灿灿的铜管乐队,奏着庄严的乐曲走进视野。来不及分辨这是音乐还是画面变换的缘故,我的心境陡然一变,刚刚的忧愁一扫而光。当浓林深处一棵棵依然葱绿的幼树晃过,我忽然醒悟,秋天的凋谢全是假象!
它不过是在寒潮来临之前把生命掩藏起来,把绿意埋在地下,在冬日的雪被下积蓄与浓缩,等待在下一个春天里,再一次加倍地挥洒与铺张!远处的山坡上,坟茔,在夕照里像一堆火,神奇又神秘,它那里是不是埋葬着一具尸体或一个孤魂?既然每个生命都会在创造了另一个生命后离去,那么什么叫作死亡?难道,死亡不仅仅是一种生命的转换、旋律的变化、画面的更迭吗?世间还有什么比死亡更庄严、更神圣、更迷人!为了再生而奉献自己的伟大的死亡啊……
秋天的音乐已如圣殿的声音,这壮美崇高的轰响,把我全部身心都裹住、净化了。我惊奇地感觉自己像玻璃一样透明。艺术其实是安慰人生的。
(陈海蓉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骥才散文》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