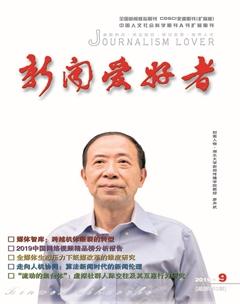“流动的集合体”:虚拟社群人际交往及其互惠行为研究
孙保营 魏晴
【摘要】虚拟社群作为人们线上社交生活的基本载体,从最初的参与、互动到渗透后的利益共享,社群内的人际交往经历了由相互了解到社群关系网络形成,再到互惠利他行为产生的动态过程,成员间自发形成的互惠和互助在虚拟社群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因而,从学理上阐明基于虚拟社群内横向交往关系产生的互惠行为的构成要素、本质特征及现实表现,对于网络群体传播研究及社群组织研究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虚拟社群;人际交往;互惠行为;中介作用
当前,微博、微信、微视频、微直播等具有社交属性的微媒体,以其大量独立的网络发布点,为受众提供了基于网络社交关系进行的即时发布、分享和传播的网络平台。裂变式的多级网络传播模式所建构的人际交往关系,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由地域、血缘“集中控制”的单一、直接的交往模式,个体与他人的交流互动,是基于网络新技术的重塑呈现出了结构及互动方式的新变化。首先,传播媒介的去中心化與垂直化,打破了线上、线下信息传递的形式、结构与规则的技术壁垒,个体可以自由地选择与他人连接的方式。其次,排除亲缘、地缘相关性,线上人际交往更多地表现为相同兴趣点的共享性讨论、某一特定主题的临时集合和以实现商业价值转化为目的的交易行为等。跨时空、跨身份的多人在线活动实现与满足了人们信息共享、情感表达的社会需要,作为载体的虚拟社群则成为人们在参与网络社交时不可避免的交流场域。
虚拟社群将网络中具有相似兴趣爱好或利益趋向的多数人聚集,时间与情感上的持续投入使得社群内的交往活动重复进行。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指出,重复互动的行为在个人习得信任并创造与他人互惠方面有促进作用。[1]网络空间缺场交往是否存在信任基础,学术界结论不一,但对交往的相关研究及实践经验显示:线上社交的便捷性使得低成本获取信息、知识或资源的交换行为更快地发生。虚拟社群成员间的互惠程度越高,个人在社群内的信息输出与情感表达意愿就越强烈,互惠行为越容易积累形成互惠共同体。来自群体的善意与互惠关系的延续维持了社群的良好发展。长期、稳定的社群关系则保障了虚拟社群内人际关系的顺利进行,互惠行为在满足虚拟社群成员异质化需求、建立社群认同、促进群体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一、虚拟社群及其人际交往关系的形成
(一)虚拟社群的释义及分类
英国学者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认为,虚拟社群用来指代由参与互联网交流与讨论而形成的线上团体或者紧密的个人关系。[2]作为一种人际关系网络,虚拟社群借助移动终端设备与社交APP入口产生,并以弱纽带为基础。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则认为,虚拟社群持续互动的动态可以产生互惠与支持。[3]
对于虚拟社群,国内学者也从不同侧面展开了相关研究。黄丽丽指出,虚拟社群是指一群拥有某方面相同点的人在互联网空间中连结形成的一个社会关系网络,拥有与传统社群类似的社会化功能。[4]张品良指出,网络社群是具有稳定群体结构和持续网络互动的集合体。[5]总结相关学者对于虚拟社群的定义,笔者认为,虚拟社群是指以网络虚拟空间为活动场域,由人们自发形成并产生交流互动的社会化群体。
虚拟社群并非传统社群的简单转化,而是基于网络新技术演变创造的新型社群,具有自身的组织形式与分类标准。美国学者约翰·哈格尔三世(John Hagel Ⅲ)与阿瑟·阿姆斯特朗(Arthur G.Armstrong)根据社群满足人们需求的不同,将社群分为兴趣社群、关系社群、幻想社群与交易社群4类。[6]兴趣社群以微信、微博、豆瓣等社交网络为依托;关系社群以地缘、血缘、学业或工作关系为支撑;幻想社群为了解新事物、探索新领域提供平台;交易社群以服务消费者为目标,为实现资源互换提供平台。以维系点存在时间长短作为分类标准,虚拟社群可以划分为临时、短期和长期虚拟社群。社群维系点存在时间长短对社群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7],例如以新闻为主题的短期社群,新闻事件从发生到发酵,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吸引人们的眼球,产生话题讨论,同时在事件尘埃落定后话题消失,讨论随之结束。
(二)虚拟社群人际交往的基本形态
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虚拟社群是一种产生于网络社会的新型社群形式,不遵循实质社群的沟通和互动模式,有其特殊的互动法则,作用在不一样的现实层面上。[8]“人—移动终端—人”的间接互动方式与实质社群中“人—人”的直接互动方式不同,传播的去中心化与受众的碎片化使得依赖于受众端的虚拟社群关系表现出流动多变、随聚随散的组织特征。
虚拟社群的人际交往基本形态,首先是基于某种共同点的、流动的多数人的集合。它把分散的、有相似社会化需求的、兴趣爱好相同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以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同时,参与讨论的单个成员身份可以是多变的和流动的。虚拟社群以人为中心,是人与人、人与物连接产生的大量异质“关系束”。比如,微信用户大多加入多个微信群,且能在不同的微信讨论群组中快速切换;又如在微博上对公共事件的围观与表达,往往还没等到事件结束就又兴致勃勃地投入到另外一个事件的热议中[9]。
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呈现出非持续性和非紧密性的动态特征,没有“共同的目标”追求和需要完成的共同任务,形成了暂时或长久的人际关系。英国人类学者邓巴(Dunbar)[10]、动物学者里德利(Ridley)[11]推算出人们日常进行面对面沟通的上限为150人,而一个微信群上限人数为500人。根据我们的日常使用习惯与用户参与行为,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每个人都能与他人进行互动;多数人采取的是一种“围观”的态度,没有地理位置约束,在不同社群中学习其特有的传播符号、沟通语言,只关注焦点人物传达的信息与意见,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虚拟性、匿名性的交往与互动方式,导致成员之间相互认知度和认同感较差。老成员的流失、新成员的加入、中坚力量的聚集、意见领袖的诞生,如此往复使得虚拟社群的人际交往一直处于流动多变、随聚随散的自运转状态。
二、基于横向交往关系的虚拟社群互惠行为
自媒体传播创新性地构建了“线上和线下”双重循环性并充满流动性、交互性的虚拟社群。社群内组织关系的建立不再依靠血缘、地缘的实际相连,所有参与者通过点对多的发散性传播,共享着彼此的专业资本、社会资本和人际资本。许多线下活动开始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进行组织和实施。一种观点的产生在虚拟社群中可以延展出各种不同的触角,从“陌生人”那里获得帮助或资源变成非常寻常的事情。
(一)互惠行为形成的条件
网络空间交往行为充满流动性与不连续性,从最初的参与、互动到渗透后的利益共享,并非所有的社群都可以实现。选择不同的环境与人群,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不同的生命力与灵活性,个人愿意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给其他成员,成员可以对他人的帮助产生回报的预期,都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1.技术发展
通过日趋成熟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和多元化的社交平臺,分散的个体聚集后自组织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渠道,降低了线下交流双向的时间和空间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交往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环境。同时,互联网传播的即时回馈机制与自媒体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适应了现代人碎片化的沟通需要,且网络空间中知识、信息的爆炸性传播给了个人超需求量获得实践技能与行动规则的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实现线上向他人求助提问,参与群聊的人皆可实时接收到他人的沟通和提问信息,虚拟社群中的“你来我往”式互助,得到了更大范围、更高效的链接与匹配。每一个用户都可以是信息、知识或资源等的发送者,同时也可以是接收者。从互惠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是赠与者和接受者,都在这个组织中受益,交往的价值得到了最大化的实现。[12]
2.重复互动
美国学者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Putnam)指出,普遍的互惠规范主要形成于横向互动的关系网络之中,个人基于自身需要或相似的兴趣爱好、利益趋向等目的,在网络中相聚并产生交流、互动的愿望。多重动力机制作用于现代人垂直化、情绪化、价值化的社交需求,产生了基于资源、信息、情感共震的反复互动。虚拟社群成员之间重复持续的互动形成了趋于稳定的交往关系,在长期的交往关系中,人们期望自己的付出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得到回报。[13]这种内含在社会交往体系中的回报预期,促使个人履行回报的义务。如若只受惠而不施惠,那么他将在人际关系中处于劣势,甚至受到他人的谴责。
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指出,成员之间反复互动可以发展出一种可靠的信誉、信任、声誉与互惠机制,它能够解决合作中的困境问题。[14]在人际交往与社群参与过程中,成员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兴趣和利益,不断相互熟悉和了解,形成了社群关系网络。成员间的重复互动以及各种社群参与之间的关系网络重叠交叉,使信息得以逐渐在网络中充分传播,降低了合作风险,个体间会形成对共同收益的预期并做出实现这些收益的合作选择。成员之间的互惠、互助就在自发形成的高频率人际交往与合作中表现出来。
3.感知相似
感知相似性(perceived similarity)是指用户在社交网络上感知到他人与自己相似的程度,主要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性别、职业、文化背景等)、心理特征(如生活方式、兴趣爱好)等方面。荷兰学者丽塔瓦尔·楚赫(Rita Walczuch)等站在群体的角度认为,相似的人作为一个群体,更容易相信对方是友善的,[15]出于对他人友善的印象评分,意味着你有更大可能愿意做出帮助他人的举动。
4.声誉评定
美国学者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D.Alexander)早在1986年就已经提出了“间接互惠”的定义,现实生活中“你帮助我,我帮助你”的直接互惠模式虽然广泛存在,但已不能适应以互联网科技为“桥梁”的现代人际交往模式。现代社会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我帮助你,我所得到的帮助不是来自你而是其他人。[16]比如:我们通常会在自己熟悉的社群中寻找有用的信息来源并给予回应,而你所获得的效用信息或资源通常来自群内你并不熟悉的其他人,你与他之前可能并不存在互动或帮助的关系,且你们关于寻找和得到效用信息的对话并非是隐秘的,而是在社群其他人的“围观”下进行的,这些围观的观众正是起着声誉评定的作用。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D.Alexander)提出声誉评定机制,并揭示了声誉在间接互惠中的重要作用。在参与者众多且对他人“声誉”信息观察困难的“异质”虚拟社群交往中,声誉可以在参与者之间通过闲聊进行传播,因此在个人需要做出是否帮助他人的决策时,会基于对社群内成员的声誉“评定”做出减少行动失败的判断。
(二)互惠行为的基本特征
1.行动的即时性
虚拟社群人际交往中的参与者,是拥有自身社会生活情境与价值意识的独立个体。人们在参与虚拟社群讨论前,通过教育习得知识,通过生活经历沉淀出面对问题时的方法与经验,以及兴趣爱好、职业需要等,使得人们具备了某个方面的专业素养和自我认知,这些自我认知成为与他人沟通交往中的一部分社会资本。提供帮助给他人的一方,借助以往的社会经验和知识结构及时做出回应;接受帮助的一方,依托网络技术可以即时收到来自他人的解答。参与双方进行了利他行为的交换,受惠方满足了参与社群的功能性需要,同时借助移动终端设备对施惠方的付出做出即时性的感谢,从而达到双方共赢的结果。
2.回报的延时性
社群内的一次性互惠行为并非是简单的利他互换,更是一种人情互惠。这种人情交往的“延时”回报与储蓄相似,能够为人们提供某种保障,从而在群体内部建立起一种互惠机制,表现出“给予—收受—(等待)—回报”的周期性特征。[17]简单来说,在一次互惠行为中,受助者只是接受了他人的帮助而没有给予同等利他性补偿,因为对给予者的需求信息暂不明确,回报的义务只好延续到日后的社群交往中。回报的延时累积作为虚拟社群中互惠规范形成的基础存在,通过规范的建立、互惠行为的加深、成员间情感的交流、信息与资源的交换互助等,保障了社群中人际关系的顺利进行。
3.行动的低成本
在现代社会,人们花费大量时间游荡于各种社交网络及社群中,个人对于知识和技能的习得,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自媒体对信息的拓展及知识的爆炸性传播。同时,在超越时空距离的线上虚拟社群交往中,基于分工基础上的具体信息和知识的有效交流,降低了个人在知识、技能实际学习过程中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对于资源的拥有者而言,分享信息给他人的成本是低廉的,且不改变自身的拥有量,而对于接受者则可能受益匪浅。此类人际交流频率高。高频率的交往互动意味着人们获得回馈的概率增加,人们愿意参与并主动提供帮助给他人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成员间互助的“善意”与回报预期的实现,也使得社群互惠行为发生的整体成本更低廉。
(三)互惠行为的表现
虚拟社群通过长期互动与交流,形成了类型不同、维系时间长短不一的人际交往关系,不同关系内含的义务感不同。在不同交往机制的作用下,虚拟社群成员在参与范围、程度、形式和内容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不同虚拟社群人际交往关系形成的互惠行为也不相同,主要包括利益互惠和情感互惠两个方面。
1.利益互惠
基于关系建构的虚拟社群,通过社群内部的互动、交流、协作和相互影响,发现群体及成员的需求,产生利益互惠行为。其重点在于,将社群组织者手中掌握的、可以用来约束社群内用户的一些利益工具,同满足社群用户需求与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进而用以调节、规范和引导社群内用户的人际交往行为[18]。当持续的互动建立紧密的联系、弱关系变为强关系,将社群关系实现利益化,利益互惠就成为可能。
社群内利益互惠的“媒介”主要分为内容信息与实体商品。如像“罗辑思维”“吴晓波频道”等知识型社群,主要提供内容产品,成员从社群组织者手中得到了有关知识分享及其附加的“好处”及“福利”。社群组织者从社群参与的大多数人手中得到关于自身形象以及内容价值的肯定,从而实现下一步商业化的目标,例如“罗辑思维”的出版物就有超亿元的销售业绩。而像一些基于商业化运转的产品类社群,主要提供的是实体商品。比如,在一个以“锤子手机”为主题的“发烧友”社群中,存在许多为了销售手机而进行社群内互动的隐藏品牌方人员。现实的利益考量是人们在社群内进行付费行为的主要出发点,利益诱导也随之成为社群内隐藏的常用销售手段之一。通过虚拟社群内成员持续、反复地关于“锤子手机”性能、外观以及性价比的交流,一部分群内成员产生了购买产品的需要。在购买行为实际发生时,利益互惠行为随之发生。销售者得到了销售手机的实际利益,购买手机的参与者虽付出了成本,但同时也满足了自身的现实需求,即利益满足。
2.情感互惠
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指出,只有当交往双方建立了“朋友”这样一种关系时,互惠才能成为现实。[19]成员之间基于网络人际交往产生的感情是虚拟社群内互惠的基础。互惠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是隐藏在这些形式背后的是关心、爱心、同情、感动、感激等情感上的因素。
清华大学学者侯莹在研究情感互惠与群体互惠时,基于北京抗癌乐园的个案谈道:北京抗癌乐园病友之间除了日常病情信息方面的交流外,更多的是心理上、情感上的交流。在抗癌乐园癌友们之间互惠行为的核心与实质是双方情感上的交换。正是乐园内部癌友们之间这种情感上的互惠,才使得加入这一抗癌群体组织的癌症患者能够在心理和精神上始终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20]
在虚拟社群中,基于情感交流产生的交往互惠也很常见。即某种情感的关联方均同时担当了付出与受益的角色,付出不是手段,受益也非目的。现实生活中的高强度工作与生活压力,使得个人在表达自身情感、宣泄情绪时顾虑过多,反而压抑了自己的表达欲望与情感交流。这时,线上虚拟社群的匿名性与流动性,反而满足了个体自由表达情感的需要,进而在社群交往中缓解了现实生活的情绪压力。情感互惠多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生活、工作等现实感情生活的倾诉与倾听;二是因为不满当下而进行的自我批评与他人的评价和鼓励;三是社群成员对于某一情感的集中表达。
(四)互惠行为的中介作用
互惠行为多呈现出不定对象、时间、形式以及非双方、非等价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行为特征。互惠行为是维系社群内资源供给良性循环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在调配成员社会资本、满足异质化需求、建立社群情感认同以及促进社群内合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求助者获得所需,就意味着社群内有人在提供信息和资源。依据自我知觉理论(self-perception theory)[21],虚拟社群内的互惠利他倾向会内化为资源贡献者的主观倾向。简单来说,受惠者从他人的施惠行为中会形成关于社群内提倡互惠行为的主观判断,使他们从主观上认定和接受互惠行为的存在。这种自我知觉使得用户可以清晰地感知到群体间对于逃避互惠行为的排斥。逐渐地,当虚拟社群内的用户认为大家都期望为他人做出贡献时,那么个人更倾向于表现出奉献的意愿和行为。因此,互惠行為的发生在促进虚拟社群内人际交往、信息及资源共享中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
网络的匿名性、在线社群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弱关系”连接等,皆强调了“信任”这一基础。信任从社群内成员彼此了解、交流互动的人际关系中产生。虚拟社群是关系的集合体,社群内互惠表现为成员彼此间的善意。互惠行为越频繁,成员间的善意越突出,信任感越能得以建立并发挥作用。这是社群认同感、社区凝聚力和志愿主义的一种具体体现。基于互惠交换获取所需越有预期,人们越想参与社群交往,因为这样可以满足自身的需要,更好地融入社群[24],社群内部的人际互动与资源供给也会得以良性循环。
三、研究总结与不足
(一)研究总结
本文以虚拟与现实相交融的网络在线社群人际交往为切入点,通过挖掘存在于虚拟社群中的人际交往基本形态,并依据虚拟社群流动多变、随聚随散的人际关系特征,分析发现: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基于某种个体需求的连接点,是成员参与虚拟社群人际交往的基础与维系点,且作为个体参与社群讨论时,因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地理位置约束,身份是流动的。这种充满流动性、交互性的缺场交往,为社群成员间接互惠行为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快速发展,虚拟社群中彼此陌生的每个人都可以是赠予者和接受者;较高频率的交往互动意味着人们获得回馈的概率增加,成员之间的互惠、互助得以自发形成;友善的社群环境与闲聊时的“声誉”传播,使得个体在行动时得以参考并减少了行为的不确定性。每个人都在这个组织中受益,交往的价值在虚拟社群中得到了最大化的实现。成本低廉的互惠行为调配了社群内的稀缺资源,达成了社群内普遍的信息与资源共享,回报的义务在虚拟社群中延续。在这一过程中,成员内化了社群的价值观和目标,最终产生了对社区的情感和价值认知,虚拟社群线上合作成为可能。
本文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即以“互惠”的观点研究虚拟社群中的人际交往过程及其社群内关系建立的核心要素。强调了在虚拟社群这一新型交往场景中,人际关系的变化及其特有的表现形态,同时描述了互惠行为作为社群人际交往的中介因素如何实现价值转化的作用特征。
(二)研究不足
因为各成员在社群人际交往中的参与度和对互惠事项推进的贡献度存在差异,以及虚拟社群中的人际交往可能存在社会伦理问题,本文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还有局限性。随着网络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一些随时有可能发生在虚拟社群中的社会问题及伦理失范现象,亟待研究解决。
(本文为2020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资助性计划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0-ZZJH-464)
参考文献:
[1]Ostrom,E.(2003).Toward a behavioral theory linking trust, reciprocity, and reputation. In Ostrom, E. & Walker, J. (Eds.), Trust and reciprocity: Interdisciplinary lessons from experimental research. New York,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47.
[3]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79.
[4]黄丽丽,冯雯婷,瞿向诚.影响虚拟社群信息分享的因素:多层分析视角[J].国际新闻界,2014(9):20-34.
[5]张品良.全媒体环境下网络虚拟社群发展及社会管理创新[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5):105-112.
[6]Hagel,Armstrong.Net gain: expanding markets through virtual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Interactive Marketing,1999(1):55-65.
[7]杨嵘均.网络虚拟社群的内涵、特征及其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2-13.
[8]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05.
[9]黄彪文,殷美香.在个体与集体间流动:论虚拟社群的参与动机与交往基础[J].国际新闻界,2014(9):6-19.
[10]Dunbar,R.(1998).Grooming,gossip,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1]Ridley, M. (2000). Genome: The Autobiography of a Species in 23 Chapters. New York, NY: HarperCollins.
[12]曾凡木.移动互联网、线上分享与青年自组织的互惠机制:以S市新庭小区80群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18(8):64-70.
[13]方亚琴.社区互惠规范:形成机制、类型与特征[J].学习与实践,2016(1):98-107.
[14]Ostrom,E.Building Trust to Solve Commons Dilemmas:Taking Small Steps to Test an Evolving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in Levin,S. A.(ed.):Games,Groups and the Global Good.,New York:Springer,p207-228,2009.
[15]Walczuch,R. Lundgren H.Psychological antecedents of institution-based consumer trust in e-retailing[J].Information & Management,2004(1):159-177.
[16]Alexander,R.D.(1986).Ostracism and indirect reciprocity: The reproductive significance of humor. Ethology and Sociobiology, 7(3/4),253–270.
[17]趙巧艳.象征交换与人际互动:侗族传统民居上梁庆典中的互惠行为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6(1):43-49.
[18]陈朋.互惠式治理:社区治理的日常运作逻辑[J].江苏社会科学,2014(5):97-104.
[19]方亚琴.社区互惠规范:形成机制、类型与特征[J].学习与实践,2016(1):98-107.
[20]侯莹.情性互惠和群体互惠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14.
[21]Yan Y, Davison R M. Exploring behavioral transfer from knowledge seeking to knowledge contribut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2013,(6):1144–1157.
(孙保营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魏晴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7级传播学专业硕士生)
编校:赵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