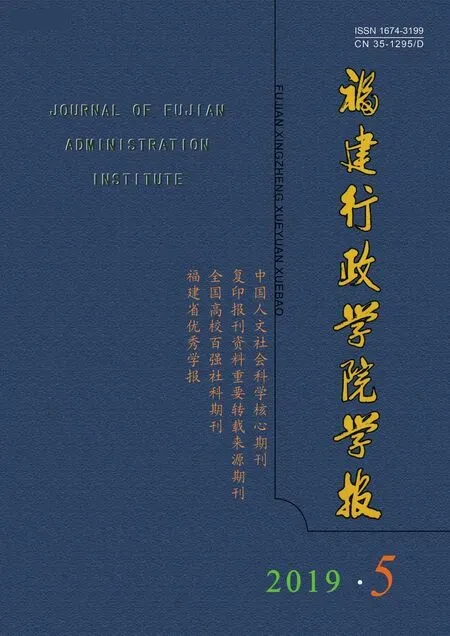互联网时代政治传播: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
吕邈航
(《福建行政学院学报》编辑部,福建福州350001)
政治传播是各国都颇为重视的政治战略问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论述中,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1]报告虽然并未直接提及“政治传播”,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党和政府对政治传播的重视,以及对其引导公众、塑造共识的深切希望。互联网的技术革命为新时代的政治传播提供了机遇,但也带来了挑战,如何积极利用互联网提升政治传播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实现有效的政治传播,这是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互联网时代政治传播的特征
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传播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然而学术界对政治传播的界定仍不一而足。“政治传播是一种过程,一种有多种因素在其中相互影响的过程:政府及其辖设的社会事业机构与公民的选举行为两者不断地向对方传达政治性影响因素。”[2]这通常被视为政治传播的最早定义。美国学者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认为,政治传播是“对可能直接或非直接地产生鲜明政治影响的信息的构建、传送、接收和处理”。[3]邵培仁认为,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种形式传播政治信息,以求影响信息接受者态度和行为,从而推动政治过程的行为。[4]本文从广义的角度出发,将政治传播视为一种“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5]政治传播不是“政治”和“传播”两个关键词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由政治统摄的传播,其政治性直接体现在传播内容和传播目的上。早在1960年,美国学者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科尔曼(James S. Coleman)就开始研究政治传播在维护政治体系有效运行方面的作用。他们的研究指出,政治体系任何功能的有效履行都离不开政治传播,没有传播的政治将寸步难行。[6]
传播学泰斗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认为:“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和应用,宣告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7]媒介即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媒介革命改变了由社会环境建构、以个人感官认知的意义世界,我们制造的工具反过来塑造我们的认知、感觉、态度和行为。从这个角度看,以去中心化、交互性、开放性、自由平等性为特征的互联网时代,引起了政治传播主体、内容、路径的诸多变化。
一是传播主体多元性。传播主体是信息的发布者,“谁”发布的信息可谓传播的起点。在我国的政治传播实践中,与社会总体形态相对应的“国家(政党、政府)”被认为是政治传播的主体[8],主导着政治传播的过程。在党管媒体的原则下,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发出的是同质的信息,传播主体是单一的。但互联网这种廉价、开放、快捷的社会平台极大降低了传播成本,消除了公众表达的障碍。“人人都是自媒体”,政府无法作为“把关人”严格控制个体化的普通民众在互联网发布政治信息、表达政治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发布者和接受者的界限被打破,普通民众也成为了政治传播的主体。
二是传播内容的复杂性。传播主体的多元化直接引起了传播内容的复杂化。“把关人”理论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那些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得以传播。“把关人”的失灵使个体化、多样化、复杂化的传播内容有机会进入传播过程。于是,民间的与官方的、精英的与大众的、主流的与非主流的、民主的与反民主的,不同的信息、观点、主张同时出现在互联网平台。
三是传播渠道的可选择性。囿于技术的限制和信息的匮乏,传统媒体是单向的、固化的,受众不能在信息流中进行自由选择。互联网发展突破了传统媒体手段的限制,网站、邮件、微博、微信等诸多渠道为民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项。民众不仅可以自主选择不同的传播渠道,甚至可以筛选想看到的信息、过滤不想看的信息。进入21世纪以来,算法机制、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将为政治信息的传播渠道提供更多可能。
可以说,互联网中任何一个网络节点都可以产生和传播信息,且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这种网状结构颠覆了传统大众传播“中心点―受众面”式结构。[9]受互联网的影响,现代政治传播最初垂直的、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开始呈现水平的、横向延展的多向传播趋势。政治传播不再是独白式宣传,还需要互动和反馈。政治传播主体的多元性、内容的复杂性、渠道的可选择性使预测传播效果更为不易,大众传播时期的经验和规律可能不再适用,有效的政治传播面临着新的问题。
二、互联网时代政治传播面临的问题
(一)互联网对政治传播影响的复杂性
人类每一次技术突破都会引发一系列乌托邦式的想象,广播在产生之初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带来民主和分权的传播技术[10],电视被认为可以带来“无所不在双向传播”并使电子民主成为可能[11],人们被乐观情绪所包围。互联网的出现将这种技术神话推向新的巅峰。《数字化生存》的作者、MIT媒体实验室主席和共同创始人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曾深信,互联网将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它能促进全球共识,创造一个更加和平与和谐的世界。[12]但随着对技术认识的不断深化,我们对其评价也更为全面和客观。就互联网而言,我们承认其在提供便利生活、促进经济发展、增进自由交流等方面的巨大贡献,但也逐渐注意到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在《数字化生存》出版20多年后的今天,尼葛洛庞帝不得不承认,互联网并没有让人类迎来“大同世界”。
互联网在政治传播中扮演的角色也经历了从“神话”到“现实”的转变。持积极态度的学者认为,互联网新媒体等数字传播载体的蓬勃发展带来了丰富的政治信息,并使政治动员信息的传播更加便捷,这为政府部门和政治参与个体带来了新的机遇[13];互联网赋予公众更多的话语权,使其在网络政治传播场域中“关注什么”这一层面具备了“反设置”能力,进而影响政府议程[14];互联网技术特性带来了传播思维的变化,不仅能扩大公共空间,对民主化进程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5]随着研究的深入,在技术革新与各种其他因素错综复杂的影响下,对互联网积极作用持怀疑态度的学者逐渐增多。他们认为,互联网的内在结构造成了传播的不平等,政治信息的传播仍掌握在少数精英和机构手中,“赢家通吃”使网络政治的民主化充满局限[16];互联网语境下,话语建构、传播载体和监测方式的变化对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出挑战[17];社会化媒体在增加政治互动、畅通政治表达渠道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风险。[18]
(二)互联网时代政治传播面临的问题
1.政治话语权从精英转向大众。近代以来,政治话语的建构和产生一直由少数政治精英完成,政治话语的传播和扩散则由传统媒体承担。随着平等观念被广泛认同,政治权利得到普遍保障,具有数量优势的普通民众话语权得到提升,但民众的政治表达通常通过精英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讲,精英更重视价值和理想目标,普通民众更关注现实生活,二者各有长短并互相补充。互联网特别是新媒体的使用打破了精英和大众的平衡。没有精英作为中介,互联网使民意表达更为直接、便捷、畅通,但同时也更为随意、主观、缺乏规范性。同时,互联网使民众在数量规模上的优势实实在在地转化为话语权优势,能够吸引眼球、获得点击量的信息和观点更容易进入政治议程,精英色彩浓厚的严肃内容和宏大叙事无法在传播效果上占据优势。精英的话语权被严重稀释,原本处于政治话语体系外围或边缘的普通民众成为网络的主角。[19]
2.海量信息导致政治流量和关注度降低。互联网突破了信息载体的界限,其所承载的海量信息使人们免于信息匮乏,同时又使人们面临有效信息、优质信息筛选难的困境。政治流量是互联网使用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一方面是由于政治信息在互联网海量信息中占比并不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治信息无法吸引网民的注意力以至于点击率低。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娱乐新闻等人们“喜闻乐见”的信息过多吸引了网民的关注,抢占了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官方媒体也希望利用新媒体转型增加影响力、扩大政治流量,但效果并不显著。以2018年登上微博热搜的“紫光阁事件”为例,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紫光阁》杂志社官方微博点名批评某说唱歌手传播负能量,其年轻的粉丝群体为了消除微博内容对偶像的负面影响,按照字面含义将“紫光阁”理解为一家饭店,并通过买热搜话题“紫光阁地沟油”制造舆论进行“反击”。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微博热搜事件一方面反映了青年亚文化群体对于官方新媒体的无知,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一些官方新媒体并没有引起公众的足够关注。
3.戏谑的语言方式影响主流价值观。网络事件的核心是话语。[20]45在互联网中,话语就是行动。杨国斌认为,网络动员是一个情感动员的过程,“戏谑”是其中重要的表现风格[20]41,通过调侃、幽默、恶搞和无厘头,可以达到近似于网络狂欢的效果。在政治文化方面,戏谑的信息处理方式在对英模形象的重新解读中尤为常见。以“雷锋”这一英雄形象为例,后革命时代强调雷锋作为“好人”的道德符号意义,雷锋精神则是“做好事”的代名词。而网络上则通过对雷锋的恶搞,讽刺转型时期道德滑坡的现象,在题为《雷锋叔叔的现代生活》的网文中,作者借“雷锋”之名影射现代“活雷锋”做好事反而成为“被告”的荒诞现实。[21]在恶搞的热潮下,网民甚至开始“考据”雷锋的“初恋女友”。[22]同雷锋相对应的是对反面人物“周扒皮”的“考据”,文学作品《半夜鸡叫》中压榨农民的恶霸地主周扒皮经过网民的“挖掘”反而成为“令人同情”的对象。[23]这些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好玩、有趣,“戏谑”对信息的解构和重构,其本质是对信息所表达的符号含义的重新定义,实际上反映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
4.网络谣言泛滥引发信任危机。谣言是最古老的传播媒介,互联网传播的即时性、互动性、匿名性为谣言的泛滥和蔓延提供了温床,以至于有学者称“后真相时代”(Post-truth Era)已经到来。[24]美国早期谣言控制学说代表人物罗伯特·纳普(Robert Knapp)认为,谣言是社会失序的结果,是社会态度和动机的一种投射。[25]日本学者涩谷保(Tamotsu Shibutani)则认为,谣言并非一种反常之举,而是一种日常的社会行为,是社会群体解决问题的工具形式。[26]当由官方控制的媒体无法满足人们获取信息的需求,且人们“对新闻的需求与集体亢奋的激烈程度呈正相关”时,谣言的语境就出现了。谣言提供了一种同官方真实不同的信息,其扩散显示了对官方渠道的不信任。[27]84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谣言”定义为虚假信息,因为大量“谣言”后来被证明是事实或部分事实,这也是谣言总是有人相信的重要原因。互联网上经常出现谣言和官方发布信息交替出现并争夺点击和流量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常有舆情反转,即“随着事件的细节、过程逐步明朗,舆论焦点开始转移,网民质疑、批驳或同情的对象不断发生变化甚至反转。”[28]30网民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被放大,中国的网络舆论场呈现“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的特征。[28]30政府部门通过删帖、封号等方式控制谣言常常适得其反。网民通常认为被删除的信息可能是真相,于是想方设法挖出被删除的内容,而一旦这些被删除的内容被证明是真的,势必对政府部门的公信力造成打击。胡泳甚至认为,在当前的语境下,像从前那样讨论谣言的失真已经没有意义,“谣言”反映的是社会集体信念,是群体对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矛盾的解释,而从这个角度看,“谣言”就是真实。[27]91
5.网民的群体极化放大认知偏见。在互联网新媒体刚刚兴起时,美国知名学者杨采·本克勒(Yonchai Benkler)认为,互联网将打造一个比传统公共领域更加动态化、多元化、民主化的“网络化公共领域”。[29]然而随着互联网深入到人们的生活,本克勒描述的网民在理性思维下发挥集体智慧、权衡多种观点、尝试不同方案、放大最具价值信息的“网络化公共领域”并未出现。互联网特别是新媒体利用算法机制精准生产和推送信息,不仅满足了用户个性化的信息需求,还聚合了具有相近观点、兴趣、情感、价值观的人形成网络社群(Network Community)。在这座“信息孤岛”中,社群成员既轻松地获取了政治信息,又在相互加强和情绪渲染的语境下不断放大认知偏见,网络舆论场的“极化”愈发凸显。这种另类空间(Alternative Sphere)是极端思想的温床,社群成员盲目相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讨论的内容是真实的,并自动过滤异质信息,但“相信只有自己正确,这是一种可怕而危险的自大。”[30]美国政治传播学者兰斯·班尼特(Lance Bennett)悲观地认为,数字媒体的发展对民主化公共领域的瓦解有不可推卸的责任。[31]
互联网时代政治传播的问题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并可能不断强化的。但我们仍然要相信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比如,普通民众话语权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的政治参与,也使有益的议题进入政治议程;增加政治流量的尝试可能增强官方媒体的影响力,《人民日报》微博就是转型的成功案例;对戏谑的语言方式加以利用,可以通过调侃消解负面政治新闻的不良影响,缓和政民关系。把握互联网政治传播中的面临问题、分析其产生原因,就有机会找到政治传播有效进行的现实途径。
三、互联网时代有效政治传播的影响因素与优化路径
(一)互联网时代有效政治传播的影响因素
1.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点和矛盾都直接反映在互联网中,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的加剧、文化价值观的变化等都在互联网上得以呈现。同时,互联网的发展又使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出“后总体性社会”的特征,自由流动的资源产生、自由活动的空间增多,国家不再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社会结构的变化削弱了政治的统摄作用,使政治、媒体与资本的博弈充斥于现代政治传播,“政治逻辑”追求权力控制,“媒介逻辑”追求事实真相,“资本逻辑”则追求经济利益。[32]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媒介和资本的力量,冲击了“政治逻辑”的控制力,“政治”向“媒介”与“市场”妥协,政治传播理性和公共性被削弱,并异化为商业性、娱乐性的政治消费。
2.人类认知缺陷。世界顶级脑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在多年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人类的行为总体上基于情感,而非基于理性,可谓“我感觉故我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研究基于非理性的集体行为,并否定性地将其称为“乌合之众”。[33]今天人们则越来越能正视情感的影响,并开始对此加以利用。互联网以及衍生的算法机制等技术都试图理解人们想要什么、感觉到什么,并基于此推荐信息。“说服最终基于如何将我们的神经网络和传播网络结合起来。”[34]77被技术影响的传播网络同人类带有认知缺陷的神经网络相结合,不仅激活了情感,更加强化了偏见。[34]77在这种传播网络的包围下,人们开始按照“不是选择对的,是选择我觉得对的”来进行选择,理智退场,认知缺陷被不断放大。
3.互联网技术革新。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去中心化、自由平等性等特征,在其影响下政治传播的诸多要素都发生了相应变化。正如前文所言,这些变化包括政治传播主体、内容和媒介的多元化,受众界限的模糊化,以及政治传播效果的不确定性。政治传播迅猛转型使传统的传播机制以及传播中的关键角色“人”一时难以适应,这个过程中必然产生新的问题。
(二)互联网时代有效政治传播的优化路径
1.坚持党和政府在政治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吸纳其他传播主体作为补充。政治传播是在“政治”引领下的“传播”,具有明晰的政治属性。虽然互联网打破了党和政府在政治传播中的垄断地位,但作为一种“带有政治目的”的传播,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取代党和政府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这既是政治传播“政治性”的要求,也是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必然选择。坚持党和政府在政治传播中的主体地位,一方面要坚持党性原则,强调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另一方面要提供客观、真实的政治信息,传递正确的价值取向。当然,坚持党和政府在政治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并不是固守其唯一的主体地位。正视传播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就要实现多元互动,并发挥社会组织和个体等政治传播主体在监督、评价、议程设置等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将其发布的信息作为对官方政治传播内容的补充,特别要及时核实负面的政治新闻,督促相关部门解决问题或解释误会;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其发布的信息选择社会公共问题进入议程设置,使输出的政策内容更符合民意。
2.加强政治传播内容建设,提供有效的信息公开。根据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st)和利奥·波斯特曼(Leo Postman)的谣言公式:“谣言=(问题的)重要性×(事实的)模糊性”[35],事情越重要或模糊性越强,谣言就越大;同理我们也可以推出,只要事情重要性为零或不具备模糊性,谣言就不会产生。既然重要性无法为零,那就要尽可能降低模糊性,使谣言止于真相。这就要求加强政治传播的内容建设,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这是民众了解政府、监督政府行为的直接途径,也是推进简政放权、优化政府服务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政府工作人员要树立“公开是惯例,不公开是例外”的自觉意识,积极主动公开信息,了解民众信息获取习惯,做好官方网站和新媒体内容推送。针对网络上出现的谣言和虚假信息,要及时、准确、详尽地加以反驳,杜绝以技术化、操作化的方式粗暴应对公众舆论和公众的反馈意见;同时,要善于将民众的声音吸纳到国家、政府、政党、社会的未来建设当中,使其转化为新的、优质的政治信息,预防民众在无法获知真相的情况下,通过情感渲染、制造舆论“倒逼”政府公开信息这种削弱了政府公信力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使信息公开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可操作化。因此,要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与义务,并对未能履行责任和义务的责任人进行追责;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序和范畴,保证政府行为的公正性;细化信息公开的内容,确保信息真实有效,避免陷入形式主义,同时注意信息安全和相关保密规定。
3.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促进高质量媒介融合的发展。早在2014年,习近平就曾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媒介融合发展的理念。一方面要普及“传统媒体+互联网”这种形式上的媒介融合,将传统媒体生产的内容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传播,扩大影响力。这可以视为媒介融合的初级阶段,简单地将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嫁接起来,媒介“融”而不“合”。另一方面要推动高质量的媒介融合发展,这要求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新媒体的优势的有机结合:在传递以事实为依据的政治信息时,要强调传统媒体信息加工的特点,即提供客观、真实、可靠的信息;在传递政治观念、政治理论等抽象政治信息时,可以偏向新媒体的特点,通过调整文风,适当将说教意味浓重的话语用既有温度又有深度的语言进行转述,提高感染力,强化政治传播效果;在面对负面的政治新闻或政治评价时,可以将传统媒体的特点和互联网新媒体的特点相结合,以严肃的态度、严谨的语言方式传递解释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再以调侃等轻松的形式消解民众的不满。
4.提升民众互联网媒介素养,强化正确政治传播意识。在互联网时代,普通民众既是信息的生产者又是信息的消费者,其媒介素养的提升尤为重要。培养民众的互联网媒介素养,最基本的是从技术层面提高其互联网应用能力;作为政治传播的主体,民众要提升信息生产素养,即负责任地发布信息和言论,并对其发布的信息和言论负责;作为政治传播的受众,民众要提升其对信息的辨识、分析和判断能力,不能对看到的政治信息全盘接收或全部否定。互联网是有缺陷的公民学校,提升网民的公民意识要先培养其理性思考、互相尊重、平等互动、宽容妥协的能力,这样才能防止网络暴力,开展有序讨论、增进互助交流。只有将网民培养成合格的、负责任的公民,才能保证政治传播从始至终的畅通。
四、结 语
在政治传播中,政治是基础,媒介是工具,人则是政治传播的起点和终点。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并没有政治传播的概念,政治传播通常以宣传的面孔出现。宣传在产生之初被看作维护民意的武器,但随着社会环境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宣传的单向度灌输、强制性宣布、信息筛选等特点使其具有了某种负面色彩。中共中央宣传部中的“宣传”英文翻译从“Propaganda”到更为中性的“Publicity”的转变就体现了一种观念的调试,意味着以传统操作的“旧宣传”向现代公共关系操作的“新宣传”转变。这不仅是一种形式的变化,更是实现有效政治传播的一种战略转型。特别是在经济增速放缓、绩效合法性面临困境的今天,提供客观的政治信息、引导理性的公众讨论、传播政治文明,在双向沟通中互相理解、达成共识、巩固民主制度尤为重要。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传播范围广、速度快、多元化的特点,但也要警惕过分运用传播技巧可能导致的长远伤害,以及在政治正确或调侃戏谑外衣下的极化群体和极端观点,要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发生。这就需要“作为起点和终点”的人成为客观、理性、宽容的现代公民,具备独立思考能力,能够进行理性讨论,辨别虚假信息,保证政治传播从始至终的有效与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