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框而出”:艺术理论的重构
毛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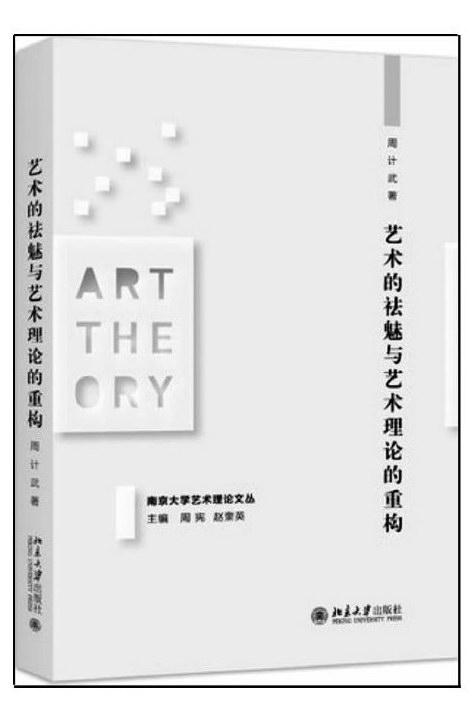
近年来,周计武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艺术理论的前沿问题,《艺术的祛魅与艺术理论的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是他多年积累的成果,也是他对“现代性与艺术终结”这一既有研究的延伸与推进。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艺术理论建构。艺术理论不同于文学理论和美学,也有别于艺术史和艺术批评,而是体现鲜明的“居间性”特征。它一方面融入哲学的思辨领域,一方面又渗透于各门具体艺术的肌理之中,并不断“建构属于自己知识体系的相关概念、范畴、方法和原理”。作为艺术学科的基础理论,艺术理论需要对不断变化的艺术和文化现象予以回应。同时,当代学者也需要以不断变化的方式对艺术理论加以评断,使之依据自身的学术逻辑,不断生成新的观点、见解和方法论范式。
在《艺术的祛魅与艺术理论的重构》一书的导言部分,作者提纲挈领地阐明了本书的核心诉求,亦即“在现代性语境中,以观念史的方式探讨了现代主义、先锋派、后现代主义、当代艺术等艺术思潮,辨析了艺术的自主性、纯粹性、新之崇拜、形式的非人化、艺术的先锋性与当代性等现代艺术观念,以及艺术‘祛魅论、艺术体制论、现代主义终结论等前沿话题”。由此出发,本书从四个层面展开讨论。其一,是对艺术“祛魅”之现代性文化逻辑的揭示;其二,是对现代艺术之观念生产及其内在张力的解析;其三,是对后现代视域下艺术危机及其社会一文化根源的发掘;其四,是对当代艺术在“理论旅行”中诸种具体问题的关切。我们可以从上述内容人手,探寻作者对艺术理论当下境遇的深度思考与创造性建构。
一
本书第一部分为“艺术的祛魅”,主要探讨艺术在现代性语境下的“祛魅”与隐形重构。如果说,在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话语体系中,“祛魅”(Disenchantment)意味着科学与理性对古老宗教、信仰、价值体系的消解,那么,作者在此给“祛魅”赋予更丰富的意涵。他指出,“艺术祛魅”包含了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第一,世界的祛魅使艺术家失去了自文艺复兴盛期以来享有的崇高地位与社会尊严。第二,媒介技术的变革改变了艺术表征的语言、观念与运行机制,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第三,在现代文明的语境下,人们在内心深处不再认同艺术的使命、价值和意义,艺术面临“合法化”(legalization)的危機。“艺术的祛魅”一方面来自艺术自身的形式变革与认同危机;另一方面,也源于现代性背景下更深层次的文化一政治冲动与话语纠葛。正如后现代理论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所言,伴随艺术边界的消解、艺术性的消散,艺术陷入危机之中:“关于作者、观众、阅读、书籍、体裁、批评理论,甚至文学观念都突然变成了问题。”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对艺术的命运持悲观态度。他强调指出,在祛魅的世界中,艺术固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同时,也获得了空前的机遇与广阔的生长可能。具体说来,正是接踵而至的“危机”为艺术家带来了强大压力,逼促其从庸常、刻板、亦步亦趋的生存状态中振作起来,并自觉投入艺术形式的实验与艺术观念的革新。如现代主义便是这种实验与革新的典范形态,它以颠覆与反叛的姿态出现,践行了一种“非人化”(dehumaniza-tion)的内在逻辑。现代艺术拒绝对现实生活的映射,而是表现为一种张扬激进的批判,进而对文化传统和艺术陈规加以不留余地的冲击与破坏。现代艺术的这种反叛性同时也加剧了“非人化”的表现形态,为芸芸众生带来了深刻的断裂感和沉痛的危机感,使之对技术理性所造就的制度“铁笼”有所警醒。因此,作者不无洞见地指出,“在‘异化的世界或许只有‘异化的形式,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在具体分析了现代艺术观念转型的症候、深层动因以及形式特征之后,作者还重点阐释了黑格尔(G.W.F.He-gel)的艺术解体论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视觉艺术思想,尤其对“光韵”“祛魅”“讽喻”等核心范畴加以细致辨析,从而进一步深化了自己对艺术之当下命运的诊断。
毫无疑问,在艺术的危机中,蕴含着突破与更新的能量。尤其是当我们进入一个“图像时代”时,当代视觉文化研究对整个艺术理论的重构更是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一方面,它从建构论的视角反思了传统艺术理论的范式和视觉经验的演变逻辑,为理解现当代艺术的深层意义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它打破了艺术理论内部分析(如艺术鉴定、形式批评与风格研究等)与外部研究(艺术社会史、图像学与图像志、精神分析与心理批评等)的两分法,广泛借鉴了符号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模式,开启了“新艺术史”(New Art History)研究的思潮。可见,艺术的祛魅并非一种“凋敝”或“隐退”,而是隐含着从形象到意蕴的复杂经验更新,隐含着“破框而出”的新的可能性路径。作者的这一发现,是对从黑格尔到阿多诺(Theodor Adorno)到丹托(Arthur Danto)再到贝尔廷(Hans Belting)等学者的理论回响,也是对艺术在当下的丰富可能性的恰切揭示。
二
本书第二部分为“现代艺术的张力”。该部分讨论了现代艺术观念的生产与再生产,现代艺术范式的内在张力,以及先锋派的文化悖论等重要问题。如果说,本书第一部分主要从理论层面对艺术的现代境遇进行总体界定,那么,这一部分则试图深入现代艺术的肌理之中,发掘其中所裹挟的具体的、深切的经验性事实。
在古典艺术中,如何借助线条、形状、光影、色彩等手段创造视觉真实,是艺术创作者的主要任务。但到了现代艺术阶段,那种不断渐进的艺术史观逐渐消失,代之以流动、变化和偶然的表现形态,以及对传统艺术观念的挑战与质疑。上述状况无疑体现了鲜明的危机意识。如果说,现代艺术以艺术的自主性(autonomy)为前提,刻意拉开艺术与世界、艺术与非艺术、精英与大众、雅与俗的距离,那么,后现代艺术则失却了雅俗之间、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明确界限。人们沉溺于各种符号的挪用、拼贴、杂糅的“混搭”风格,精英意识也逐渐被嘲讽的审美立场所取代。从古典艺术到现代艺术再到后现代艺术,这个过程不仅意味着艺术风格的变化,更反映了艺术观念与审美价值的更深刻演变。
艺术面临着危机,但也必须在危机中延续下去。正是基于这一信念,作者緊接着分析了现代艺术的创作机制,以及艺术观念的生产和消解。通过从艺术话语到艺术观念再到艺术体制的细致考察,作者认为,现代艺术的最突出表现,莫过于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张力结构”。具体说来,作为一种难以忽视的文化现象,现代艺术不是一种夺人眼目的“符码”或“姿态”,而是体现了理性与感性、短暂与永恒、进步与回溯、形式与意蕴、分化与去分化、功利与非功利等因素的对话与纠葛。这种张力结构通过先锋艺术中“审美与政治”
“越界与传统”“建构与颠覆”“媚俗与创新”“革命与日常”等因素的并置而得到了绝佳体现。在第七章中,作者特意以先锋艺术为例来探讨这种张力关系:“作为现代文明危机的表征,它(先锋艺术——引者注)既表达了前所未有的断裂、危机、衰败与虚无感,也以不断探索的勇气、勇往直前的反叛精神和自我献祭的立场,为我们塑造了未来社会的幻象。对进步主义者来说,它是革命的旗帜;对保守主义者来说,它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作者看来,先锋艺术是一种动态多元而充满张力的现代性范畴,具有“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实验锋芒。其中,创造与破坏水乳交融,难以分割。唯有对陈旧的艺术观念、艺术技巧、艺术形式进行质疑,对旧有的文化教条、创作标准和权威准则进行挑战,对艺术的感知和体验进行更新,才能实现艺术的真正创造——这便是先锋艺术的宗旨所在。在此,我们注意到,先锋艺术蕴含着蔑视主流、不断探索的精神品格。作者不无匠心地借用“雅努斯面孔(Janus faces)”来揭示先锋艺术所固有的双重性或矛盾性:激进与虚无、反叛与苦恼、前卫与庸俗、破坏与创新,等等。它们经过历史的沉淀,最终成为先锋艺术的精神气质:拒绝平庸、蔑视权威、抵制媚俗。这种精神气质将贯穿于先锋艺术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有先锋存在,它总是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站在人们认为是现代的任何事物的前沿。”9作者对这种“张力结构”的发现,无疑打破了传统视域中关于现代艺术的种种“神话”或“宏大叙述”,为研究者揭示了现代艺术耐人寻味的更复杂面向。
三
本书第三部分为“后现代转向”。该部分主要把研究放置于后现代转向(the postmodern turn)的学术视野中,思考后现代语境下的艺术命运、艺术危机及其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并重点讨论先锋精神的衰落、美学阐释的困境与当代美学价值的危机。
关于“现代”(modern)与“后现代”(postmodern)之间的复杂关联,学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也引发了“现代主义”(modernism)守卫者和反叛者之间的激烈争论。作为一种哲学文化领域的重要现象,“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不仅标志着文化领域的裂变,还预示了认识论意义上的范式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质变后的必然结果。对于“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研究者主要有两种理解。一是断裂论。这种观点认为,在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某种激进的断裂。“后(post)”意味着反叛、超越与反思,后现代主义不仅是一个时间范畴(产生于现代主义之后),更是对盛期现代主义的质疑与颠覆,它所表达的,是对理性主义的不满和对宏大叙事的质疑。二是转向论。这种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并非对现代主义的决裂,而更莫过于后者的转向与延伸。现代主义对伟大、经典和原创性的关注,逐渐让位于后现代主义的嬉戏、拼贴与反讽。后现代主义既质疑、批判了体制化的现代主义,也延续了现代性的内在批判精神。“后现代主义之父”哈桑曾用“不确定的内在性”(indetermanence)来概括后现代主义的主导特征。从不确定性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后现代文化中那种疯狂的反叛和瓦解一切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试图突破西方文化的传统障碍,对西方数千年来形成的形而上思维模式和现存的、确定的规范、体系和权威加以挑战。在哈桑看来,后现代主义不再具有超越性,不再关注精神、价值、真理、等级、权威等范畴,而是对主体的内缩和对客体的内在适应。“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会导致断裂化和零散化,“内在性”(immanence)则会通过越来越走向一体化的语言媒介而导致全球化。从不确定性到内在性,我们看到疯狂解构意志下潜藏的一种创造力量,这是人的心智中固有的、内在的、充满活力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作为对现代主义的继承还是断裂,在后现代的土壤中都生长出不少值得玩味的新鲜文化景观。
正是基于对后现代的敏感意识,在《艺术的祛魅与艺术理论的重构》一书中,作者结合具体案例,对艺术在后现代语境下的走向及其命运进行了阐释与描绘。他主张“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观念与话语体系。第一,审美的、理论的和伦理的三个文化领域失去了自己的自律性;第二,文化与社会、雅文化与俗文化边界的断裂;第三,文化经济,即文化的生产、流通与消费逐渐变得‘去分化,尤其是文化体制与商业体制界限的消解;第四,在话语表达模式上,后现代主义打破了能指与所指、表征与现实之间的确定性,使现实本身成为问题。这种去分化的过程也就是文化要素之间‘距离的消失或‘内爆的过程。对艺术而言,就是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与商品、高雅艺术与媚俗艺术以及艺术内部界限的消解过程”。在具体的讨论中,“危机”与“重构”成为作者一再强调的关键概念。他从“先锋精神的衰落”“当代艺术的阐释危机”“当代美学的价值危机”等层面入手,展现了后现代语境下美学与艺术所面临的琐屑化、碎片化、浅表化、商品化、日常生活化的境遇。同时,作者又并未停留于学界对于“后现代精神”的一般性论断,而是在后现代艺术“分裂”“破碎”“消解意义”的表象下见出了更深刻的范式调整与观念变革,并最终揭示了一种重构艺术的超越性与神圣性的可能。这种对后现代艺术的恰切诠释,其实也遥相呼应了哈桑等学者对后现代精神之辨证意涵的发现。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先锋”(Avant-garde)的深刻理解。在他看来,先锋象征着一种精神,一种气质,一种批判性的否定力量。历史上的先锋派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运动,在观念上发挥过革命性作用,并启发了后现代主义。“先锋精神”所凸显的是其本身所蕴含的精神内涵与批判力量,这是我们理解后现代艺术的重要切入口。在书中,作者特别分析了后现代主义与先锋派之间所具有的家族相似关系:“后现代主义依然保留了一种形式上的‘先锋派特征,但它的内容或多或少受到政府和财团组织的操纵,因此,先锋精神渐渐地削弱了。”到了20世纪70—80年代,随着艺术体制的后现代转型,艺术观念、艺术风格、批评模式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先锋精神逐渐让位于文化的放纵和消费主义的享乐。作者特别谈到了艺术界中“共同体”(communi-ty)角色的转移,诸如博物馆逐渐成为艺术革新的把关者,艺术资助制度从“市场制”向“后市场制”的转变,等等。后现代艺术体制的生成,意味着后现代艺术抛弃现代主义的自律体制,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对抗性和异质性。在这一境况下,当代艺术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由此出发,作者从“当代艺术之争”“当代艺术的合法性”“合法性的危机”“美学的重构”等四个方面来考察西方艺术观念及其美学体系,并对如何重构我们时代的美学范式做了严肃思考。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当代艺术观念的形成并非单向度的。一方面,它在寻求阐释的普遍有效性;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西方艺术不断被挪用、转化或吸收。“当代性”(contempo-rariness)是当代艺术的核心特征,体现了对艺术边界的消解,对现代主义话语的消解,以及对单一艺术体制的反抗。笔者认为,这或许是先锋精神的一种表现。在当代性不断改变艺术、艺术品和艺术家的定义,不断使艺术形式失去内在确定性,不断冲破传统的审美感知方式并改变艺术的价值功能之时,何谓当代艺术?当代艺术何为?艺术需要被重新界定。
四
在本书的第四部分,作者描述了当代艺术在“理论旅行”中的语境错位,同时,考察了中国当代先锋艺术的运作机制、形象类型及其表征模式。这一部分之所以令人兴奋,不仅在于它与我们身临其境、既熟悉又陌生的本土先锋艺术息息相关,还在于两个格外引人注目的问题。
首先,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來,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在理论旅行中的语境错位问题。众所周知,在20世纪80—90年代的10年间,中国艺术在全面引进西方先锋艺术的艺术语言、方法、风格和程式的潮流中,借助外来的“薪火”演绎了中国当代先锋艺术的本土景观。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便会发现,在理论旅行中语境错位的境况下,中国的先锋艺术从西方学到的首先是“反叛”和“追新逐异”,是先锋精神不断“革命”的本色。在这种精神的召唤下,中国当代的先锋艺术从“告别革命”开始,逐步走向去神圣化、去政治化和世俗化,进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呈现碎片化、脸谱化、平庸化、祛魅、打破符号等级制等先锋艺术的“新世相”。而今日流行的所谓“三M党”(Mar-ket/Museum/Media),则是中国先锋艺术之特征的更直观表现。有人认为,除了照搬和模仿,中国当代艺术没有本土的文化精神和独立的价值判断。但实际上,艺术的界定与建构,会随着时空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当代艺术的中国符号必定会打上当下的本土经验与问题意识的烙印。在这种轨迹清晰的历时性演变过程中,表面上显现的语境错位,实则体现了与不同语境中文化艺术精神的高度相似性,即作为先锋精神之象征和图腾的“反叛”“尚新”和“革命”,也即先锋精神所体现的激进的美学锋芒。我们看到,在中国本土,自近现代以来,在“启蒙”与“救亡”的主旋律之中,也一直或隐或显地贯穿着此种激进的美学锋芒。实际上,反叛、尚新和革命从来都不止一副面孔。因此,同样的精神完全可能在不同的语境中以不同的面目,甚至相反的面目和更加激进的姿态再次出现和再次演绎。“85新潮”也好,“后85新潮”也好,其实与晚近的先锋精神高度吻合,只不过是借助不同的装扮演出了似曾相识的历史场面而已。
其次,作者以不无幽默的笔调勾勒了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招牌式形象。米歇尔(W.J.T.Mitchell)认为,“形象”(images)并非能指与所指的简单聚合,而更莫过于一种独特的生命形式:“最好是把形象看作一个跨越时空来自远方的家族,在迁徙的过程中经历了深刻的变形。”在中国先锋艺术的独特氛围中,同样孕育着诸多别具一格的形象类型。对此,作者有明确认识。他从纷纭多样的当代艺术谱系中提炼出“光头”“傻笑”“呆滞”“傻乐”“无聊”等五种招牌式形象,并对其进行了细致描绘与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还选取一些具体的形象个案,做出了独到的阐释与解读,从中可看出他对中国当代先锋艺术的持续关注与深入思考。从深度剖析现代性语境中的西方先锋艺术和先锋精神,再到将视线横移到当代中国的先锋艺术,让我们在反差和错位之中也能惊异地发现诸多似曾相识之处。这种对比和剖析的典型意义在于:在一个开放的世界格局中,不同文化和艺术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既有清晰可辨的差异性和异质性,同时也总存在某些“回光返照”式的呼应关系。中国特色的先锋艺术同样也在反叛之中持续不断地追新逐异,持续不断地保持破坏与创造的革命精神。傻笑、傻乐、光头、呆滞、无聊的视觉形象虽然带有几分苦涩和尴尬的模仿的无奈,其实也不妨被看成一种睥睨一切,同时又远离主流和大众的叛逆与先锋姿态。
作者进一步谈到,当代艺术是一种混杂的文化现象,多方力量共同决定着当代艺术的走向。这些力量相互博弈、彼此制约、相互共生,它们之间有契合、勾连,也有背离、对抗。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将走向何方,我们尚无法知晓。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它在不断保持反叛先锋精神的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卷入艺术生产的全球资本逻辑之中。它除了保持自身的本色之外,也会跟随资本主动或被动地调整自身的发展走向。因此,无论是艺术的危机,艺术史的危机,还是艺术理论的危机,它们所隐含的意义都是双重的。在这之中,包含着人们对艺术和艺术理论更大的期许,而需要变化的,往往是我们自己的态度、观点与立场。
五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作者在西方艺术史的叙事逻辑下,探讨了当代艺术的表征策略与话语范式。借用贝尔廷的经典命题,作者强调指出,当代艺术是一种“破框而出”的艺术事件。作为一种象征性事件,它打破了原有的艺术体系和艺术史叙事模式,并正在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范式。这些变化会深刻地改变我们观看艺术、体验世界的方式。在面对不断变化的艺术实践,以及不断被质疑的艺术史书写、艺术批评、艺术的文化身份等问题时,这种思考无疑是对当代艺术实践和艺术面貌的清理与反思。可以说,本书凝聚了作者这些年细致入微的学术思考,既有对中外艺术创新问题的理论回应,也有对艺术理论这一新兴学科的理性追问与批判反思,从而体现了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真切的现实关怀。
总体上看,周计武教授的《艺术的祛魅与艺术理论的重构》一书带给我们如下启示。
首先,是以艺术经验为原点的研究姿态。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常见病症,在于从西方理论出发,对具体的艺术经验或现象予以“观念先行”式的解读与诊断。在此过程中,研究者所关注的是文本分析和既有理论的对应,鲜少对中国语境下衍生的独特问题加以自觉剖析。本书的一个突出特质,体现在鲜明的“在地化”色彩。作者始终秉持一种“自下而上”的视域,试图通过对中国当代艺术这一独异现象的敏锐分析,从中提炼出包含着本土经验与本土气质的理论命题。无论是作者对当代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与流变的勾勒,对当代艺术家群落演变状况的描画,还是对先锋艺术视觉表征方式的呈现,都体现了这种理论建构上的本土化尝试。同时,作者还植根于本土历史传统,在面对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下,努力对艺术重新界定,努力对中国当下的艺术形式、艺术氛围、艺术观念等进行有力度的阐释。在习惯步西方后尘,以至于常常陷入“自我矮化”困境的中国人文学界,上述研究态度必将带来难能可贵的借鉴。
其次,是一种艺术社会学的理论自觉。艺术并非纯而又纯的审美客体,自诞生伊始,它便与人类的生息繁衍、耕作渔猎、婚丧嫁娶、仪式祭拜等活动保持着紧密关联,并始终充溢着丰富的“社会性”因素。在这个“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越发占据主位的当代语境下,生产、消费、市场、资本、声誉、名望、趣味、话语权等因素对艺术的渗透显得更加明显。如沃特伯格(Thomas E.Wartenberg)便提到,我们在肯定艺术的批判性与自主性特征的同时,也必须承认“某些艺术,尤其是通俗艺术在业已确立的社会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S.Becker)则断言,艺术创造绝非远离尘世、苦心孤诣的行为,相反,“所有的艺术工作,就像所有的人类活动一样,包括了一批人,通常是一大批人的共同活动。通过他们的合作,我们最终看到或听到的艺术品形成并且延续下去”。在“协同合作”这一点上,一幅凡·高(Vincent van Gogh)的杰作和一部好莱坞电影并无实质性区别。作为对上述倾向的回应,作者在本书的撰写中展现了艺术社会学的理论洞见。纵观全书,无论是对艺术的合法化危机的诊断,还是对现代艺术机制的深入剖析,抑或对艺术“天才”的陨落历程的勾画,无不体现了作者将艺术置于一个更宏观的“艺术界”(Art World)之中加以综合分析的尝试。这种艺术社会学的立场不仅有助于对艺术加以更恰切界定,在所谓“审美主义”(aestheticism)风潮大行其道的当下,也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警醒之效。
最后,是一种开放的,不断游移、变动的研究视角。有学者指出:“艺术不是一个天然的范畴,而是一种文化的建构;因而它根本上是不稳定的,永远地遭到重新定义和重新建立。”诚如此言,艺术并非凝滞、僵化的实体,而是蕴含着难以穷尽的生长空间。艺术不具备一个不容置疑的本质,而是呈现种种家族相似的复杂形态,并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而不断调整与更新。对此,作者深有体会。他多次提及,艺术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打破“边界”的过程。正是以边界的消解为契机,当代艺术为我们带来了“混杂、挪用、仿制、拼贴、模拟、戏仿、当代性”等一系列全新景观,进而使艺术理论获得了更丰富的研究对象与思想资源。这种不断“破框而出”的冲动为研究者提供了某些新的路徑与策略,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窥见当代艺术发展的完整版图。无可否认,由于学术积淀等方面的原因,本书并未将一些现今艺术理论的前沿问题(如艺术中身体的极端表征,全媒体时代的艺术生态,艺术中的时间意识与空间拓展,以及人工智能与艺术的复杂关联等)纳入关注视域,但上述缺憾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作者的后续研究带来了宝贵思路。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作者的“破框之旅”还将继续。
(责任编辑 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