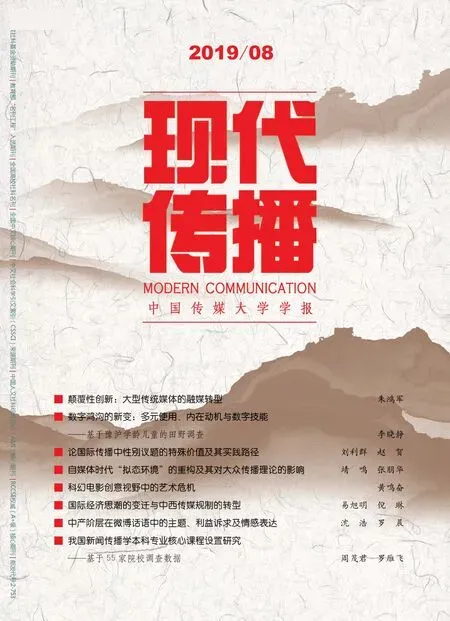后真相视角中的网民情绪化传播*
■ 宋 凯 袁奂青
一、后真相及其本土化
(一)“后真相”的缘起与发展
“后真相”一词及其相关事件的讨论,近两年来迅速飙升。英美两国在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使用该词的频率,2016年较之前一年飙升了2000%①。笔者在GoogleTrends②上以“后真相”为关键词,采集了2016年—2018年的“相对兴趣指数”数据,采集对象为:全球(除中国外)、美国和英国三种数据类型(图1),可以清晰地看到“后真相的相对兴趣指数”在2016年11月达到了最高峰,这正好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时间点。

图1 “后真相”的相对兴趣指数分布图
《牛津词典》将“后真相”列入“2016年年度词汇”,它将“后真相”定性为一个形容词,意为“似乎客观事实在塑造公众舆论方面的影响力低于情感和个人信仰的相关或所指情况”,并表示“后真相”一词需要与特定名词相联系。③
(二)“后真相”在我国的本土化色彩
1.草根现象:从政治到社会公共事件
“后真相”现象缘于西方国家的政治事件,然而我国有关“后真相”现象的讨论爆发于2017年1月,此时发生的“江歌案”成为了我国社交媒体上的第一个“后真相”舆情事件。此后,社会公共话题“后真相”舆情事件成为了我国网民关注的焦点。进入2018年以来,“后真相”舆情事件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微博平台④,如图2所示,经笔者统计,发现2018年后半年出现了465个热门舆情事件,都是我国网民较为关心的社会公共事件,且更热衷于参与意见表达和分享,在我国社交媒体舆论场中形成了众多社会公共热点话题。从数据上看,24%的热点舆情事件属于公共卫生类舆情,占比最高。

图2 微博热门舆情事件类别占比
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⑤我国民众更关注社会公共领域舆情热点话题,同时有着更强的情感表达诉求,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社交媒体平台发展迅猛,舆情事件的传播速度已经完全超越我国传统媒体,海量的UGC信息相互碰撞而泛化出热点舆情事件,这也给“后真相”舆情事件的产生提供了能够滋养其生长的暖床。
梳理我国近年来本土化“后真相”舆情事件,公共卫生类舆情事件最具代表性。其中,笔者以“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事件、“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事件、“丁香医生起底权健骗局”事件为例,采集、抓取了新浪微博相关数据,构建了公共卫生类事件舆情指标,如表1所示。首先,通过影响力指标说明,这三起公共卫生事件在微博平台广泛传播,并且从话题指标和传播趋势来看,这三起事件均引起了网民的极大关注和广泛热议。其次,“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事件的所有数值在同类事件中均为最高,这表明该事件的传播覆盖人群范围广泛,同时舆情持续时间长,形成了“长尾效应”,这体现出在该事件的传播中,有众多网民不断地参与进来,产生了信息的交互。再次,从这三起事件舆情的峰值传播量和速度的对比上看,事件越是与网民息息相关,网民就有更多的表达诉求,更愿意参与讨论。这些UGC内容不可避免地携带着每一个网民的情绪,因此在舆论场中呈现出了情绪化狂欢的舆情景观。

表1 公共卫生类舆情事件舆情指标
信息来源:微博、知微事见。
2.众声喧哗:网民的情绪化狂欢
一方面,近年来,我国网民规模持续增长,众多网民争相成为传播者,通过生产和传播信息,满足自身的情绪表达诉求。个体情绪事实上是对外部刺激的心理反应,当受到外部刺激引发情绪后网民倾向通过网络评论释放情绪,传播者的一个重要传播动因就是情绪驱动⑥。正因如此,UGC内容本身就夹杂着网民的情绪。在网络舆情事件中,网民更倾向表达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在评论中更容易出现群体极化,网民更容易产生极端情绪,出现正负双峰分布的情感内容⑦。因此,在“后真相”舆情事件中,海量的碎片化信息不断重构着网民对事件的认知和判断,却无法还原真相,网民只能根据不完整的信息而盲目作出决策和表达意见,而这往往就饱含着情感的控诉,信息便成为了情绪的载体,甚至是情绪本身。生产信息成为了创造情绪,传播信息变成了传递情绪。
另一方面,在社交媒体带来的高参与性和高互动性的传播过程中,网民也被埋没在超载的信息海中,信息的同质化现象严重。海量信息埋没了真相,网民因认知不同而态度不同,因媒介接触不同而产出偏见。社交媒体圈层为网民构建了一个个“信息茧房”。在“信息茧房”中,海量同质化的信息不仅禁锢了网民的认知,也同质化了他们的情绪,这使得网民无法判断信息的真假,只能根据相似信息的数量,唯“多数论”,认为“多数即真理”。同时,携带着相同负面情绪的信息在不断地转发传播中,强化着网民产生情绪的共鸣,这使得他们的情绪反馈不断恶化,进而在不断宣泄中形成了情绪化的狂欢。在“后真相”舆情事件中,形成了以“情感”“态度”“成见”为先,“真相”“认知”“客观”在后的话语特征。
针对前文所述三个公共卫生类舆情事件,笔者根据网民评论抓取,对网民舆论进行词频分析,如图3所示,发现词频较高的词,如:良心、良知、愤怒、黑心、惊心、可怕、虚假等,均为饱含着丰富情绪的词汇。

图3 网民舆论词云图
在充斥着假信息、谣言、八卦等不良信息的“后真相”时代,我国网民对于公共卫生类舆情事件的传播,呈现出了人云亦云式的情绪化狂欢现象。在社交媒体的舆论场中更是强化了其传播效果,网民情绪化的只言片语成为社会交往和诉求表达的常态。
二、“后真相”舆情事件中网民的情绪宣泄
(一)谣言滋生助长恐慌情绪传播
公共卫生类舆情事件容易出现事实让位于情感的“后真相”现象,这就成为谣言滋生的沃土。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事件中,就有80起谣言被辟谣,这些谣言的话题数量占据话题总量的16%,然而剩下84%的话题都是真实的吗?笔者统计了在2018年7月23-24日,该事件在传播峰值时候就出现的主要谣言有:《铁证!所有证据指向武汉生物和长春长生,触目惊心》《长春长生疫苗老总高某是前吉林省高官之女,典型的官二代》《国产疫苗都有问题》《疫苗无用,损害健康》等。这些谣言报道中,冠以“专家”“学者”等不真实的信息来诱导网民产生对真相的误导性理解,所谓的“权威”和“可信度”,仅仅是微博“大V”和公众号运营人员出于“博眼球、求关注”的炒作目的。同时,文中很多不实信息增加了网民的恐惧感,诱导他们进行着情绪的宣泄。这些信息在不断形塑网民恐惧感的同时,也被当作了“真相”。
事实上,在网民自认为掌握了“真相”的时候,真相和事实也就变得不重要了,因为网民的情绪和表达已被支持和满足,同时社交媒体也提供了有的放矢的话语空间。换句话说,谣言被作为“社交货币”嵌入进了社交网络。谣言在社交网络传播时有时会扮演社交货币的价值:通过自己的分享表明自己是一个“懂得很多”“掌握一定知识”的人,进而赚取更多的社交货币⑧。这是网民在媒介接触中普遍存有的心理动机,尤其是我国网民的中老年群体,他们关心自己的子女,这与他们的社会角色、媒介接触心理均相符合,加之不断被公共卫生类舆情撩拨的情感神经,就会对谣言产生认同,实际上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
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网民对谣言的认同携带着情感的宣泄渗透入各种各样的话题圈子。网络谣言在传播结构上最大的变化是圈群化传播,圈群化是和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网最为接近的网络结构,是最适宜谣言传播的结构⑨。在同一个或者相嵌套的圈层中,网民便会由于拥有相似的认知而产生情绪共鸣,而在不同的圈层中,网民便由于认知不同而形成了“马太效应”,甚至迫于群体压力与趋同的从众心理,而形成群体极化现象。
(二)舆情反转导致网民情绪波动
“舆情反转”是我国媒体中的一句用语,概括为某一类的舆情现象。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民众的意见、意愿发生偏转,指受众在获得特定信息后对事件做出的相反论定,通常情况下,舆论反转会发生在事件发生后的不同阶段,而受众在各个阶段所表现出的观点也存在着较大差异,舆论反转往往借助特定的媒介载体进行信息传播⑩。
舆情事件中的舆情反转现象往往出现在该事件的次级传播过程中。这是因为,一方面,事件中的假消息和谣言被更有话语权威的媒体机构或相关组织辟谣后,网民的情绪随认知而变,这时就会出现舆情反转;另一方面,随着事件曝光出越来越多的细节,甚至与此前的信息完全相反,也会舆情反转。
舆情事件的不断反转导致网民情绪随之波动。在“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事件中,由于“众多证据”爆出,网民开始产生了恐慌、愤怒的情绪,在“专家辟谣”后,网民情绪变成了对公共机构发布信息滞后的抱怨,以及对辟谣信息真假的质疑,最后在“兽爷声明”后,网民又产生了对假冒者的愤怒情绪。在这个过程中,网民的情绪并未被平息和消除,实则是多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因此在舆情反转中,网民的注意力和情绪输出发生了彻底的转向,转去讨论“百日破疫苗会不会导致婴儿痉挛症”“起底长春长生生物公司后台”和“中国疫苗本身面临的监管和质量问题”等话题,但网民认为自己是在追究“长生生物等疫苗造假”事件的“真相”而宣泄情绪。殊不知,这正是“后真相”舆情事件中所呈现的传播效应——由于网民的情绪化传播和认知偏差所带来的舆情反转,进而也是在谣言被辟谣后所带来的事件反转,反而更加强化了网民的情绪反转及宣泄。
(三)信任异化加剧负面效应溢出
信任异化是由政治不信任演化而来的一种社会逆反心理。在我国,信任异化与全社会的诚信危机密切相关,反映在社交网络上就是与网络民粹相伴生的舆论反转无度、伪民意泛滥和后现代情感立场上。“后真相”舆情事件中的信任异化问题是指在社会公共话题相关的舆情事件中,网民对公共机构所提供的信息产生质疑的一种社会心理。而这种心理的呈现,“后真相”舆情事件中的网民对谣言的认同和舆情反转便是其原动力。同时,这种心理的出现也与发布信息的公共机构的公信力较为薄弱有关。因此,信任异化也是较为宏观层面的“后真相”舆情事件所带来的传播效应,正是这种心理,导致了网民对公共机构所提供的信息产生质疑而产生逆反情绪。
在“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事件中,公共机构的微信公众号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子话题。例如:界面的《长生生物疫苗造假案情未了,康泰生物董事会离奇改选》一文,将该事件与“康泰生物董事会改选”相联系,分析对于股票的影响;政事儿的《疫苗造假事件和三起行贿案》,该文将“疫苗”一事与法律案件相关联,使网民产生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医信妇儿频道的《疫苗造假的背后:不止狂犬疫苗,出事儿的还有百白破》,该文依据不实报道,加深了网民的恐惧情绪;医联App的《该如何相信你,国产疫苗?》一文,更是将网民的情绪宣泄扩大到了国产疫苗上。这些文章与“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事件毫无关系,也并不是关于事件真相的符实报道,却能不断地撩拨着网民的情感神经。在舆情事件的真相上,这些公共机构似乎都只是在蹭事件热度,利用网民的关注获得访问流量,并不是去报道真相。然而,网民的信任则建立在对“后真相”舆情事件的情感宣泄上,网民在接收到这些纷杂的信息后,只能进行着自我的情绪表达,这是彼此之间取得共识的逻辑所在。被异化的信任不再追寻终极的真相判断,而是漂浮在碎片化的表象和情绪化的抗争中,驱动信任的是情绪而不是真相,以至于信任行为呈现无原则倾向,谣言成为信任的对象,真相出场后反被不信任。其背后原因就是真相的传播速度慢于谣言,当真相抵达网民群体的时候,网民对谣言的认同已根深蒂固。并且,尽管传统媒体已在社交媒体上拥有身份标识,但不代表其能够有充足的时间通过“议题设置”而还原真相。在媒体机构争先“抢快”的时效性竞争下,信息依旧是碎片化的,其信息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也在这种碎片化的状态下被不断消解。因此,“后真相”舆情事件所带来的传播效应就是对网民造成了使其产生信任异化的社会心理,致使我国网民对于信息普遍呈现出了质疑和怀疑的心理和情绪。
三、社交媒体中“后真相”舆情事件传播机制研究
(一)社交媒体导致传播者复杂化
自社交媒体出现以来,传播者的角色就已被颠覆,从作为单一信源的、传统的身份变成了多元化、复杂化的身份标识,不仅有传统媒体机构,还有社会公共机构、个人意见领袖、普通网民和网络水军等自媒体。在这样的传播实践中,精英话语垄断被打破,生产信息的权力被解放了出来,众多信息主要由各种各样的自媒体所生产,他们更是承接了话语权力,也随之带来了多元观点的表达。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论指出媒介的物理特性决定了它的传播偏向,媒介的偏向会催生新的文化,形成特定群体的权力垄断,社交媒体正是凭借其物理属性而实现了话语权力的传递和转移。因而在实现话语赋权后,传播者生产信息的动机也不再一致。并且,自媒体在社交媒体上幻化成一个个“节点”,这个节点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机构和组织,但难以辨别彼此,并对其信息把关。因此,信源的不确定性和社交媒体的“弱把关”能力,使得网民情绪难以控制,进而在舆情事件中爆发了情绪化传播,使得“真相”让位于了“情绪”,成为了“后真相”舆情事件。
此外,网络水军虽然不是信源本身,但是属于传播者中最能推动信息传播的推手,他们受背后自媒体所给予的利益驱使,便拥有了与信源传播者相一致的动机。随着大数据和算法在信息传播中广泛应用,网络水军能够精准把握受众的注意力,通过机器计算,筛选并推送受众与其相关的信息,而受众则往往喜欢和自己观点和情绪相符的信息,并表达出来反馈回传播者。因此,“议程设置”在这个传播过程中则变成了“情绪设置”,通过受众意见和情绪的反馈而加工信息影响受众。最后,网民的观点和持有的情绪不断地加以固化,便会导致认知不平衡,失去应有的理性思考与判断力,形成“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这便导致了更加复杂的情绪化输出与传播。
在人际传播中,网民也具有了传播者身份,他们的意见和情绪在传受一体的身份变化中,通过社交媒体而外延至其他网络的传播过程中。社交媒体不仅给予了网民话语权力,使得“人人拥有麦克风”,同时其物质特性也使得人们传播和进行意义分享的能力增强。然而,这种意义分享使得意见和情绪在网络中如病毒般扩散和传播,最终导致了“后真相”舆情事件的爆发。
(二)传播内容生产的“编码—解码”过程
一般认为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真实”和“客观”,人为影响新闻写作的主要因素有五个,包括个人影响、组织的影响、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媒体惯例和规范以及政治经济因素。由此可见,由于专业水准和业务能力的限制,自媒体人员的新闻写作和信息生产更会受到这五个方面的干扰。
一方面,关于个人的影响,可以认为在每一个客观活动中都有主体性的因素。而社交媒体中传播者的媒介素养参差不齐,其主体性因素就更能干扰信息的生产。在信息生产过程中,传播者选择信息的主题、视角、事件排序,和在标题和正文中选择描述这些事件的词语,无一例外是主观的。同时,受众也在主观上,想要获得能够被自己的能力理解、分析、判断和批评的信息。因此,人的主观性就完全体现在这样一个“编码—解码”的传播过程中。
另一方面,关于组织的影响,可以被认为是一些组织对媒体有本质性的权力,或者一些传播者可能会倾向于某些组织,因此当他们生产信息的时候,他们会受到该组织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影响。例如在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事件中的“新闻失实”现象,政治家们通过操控媒体,制造“假新闻”和“谣言”,利用社会上存在的偏激情绪,不断发表煽动式言论,曲解事实,乱编故事而操纵选民,获取支持。而在我国的社交媒体传播实践中,社会公共机构、自媒体等,都有其自己的利益动机。作为传播者,组织的属性、该传播节点的作用和利益目的等对信息的生产产生多重干扰。他们可以为了流量、访问量、阅读量和粉丝量,在信息生产时就极大地满足受众需要和阅读习惯,然后通过吸引广告投入等商业活动进行变现。个人意见领袖和一些普通网民,他们就更需要通过一些产生信息的手段,塑造在传播过程中的个人价值,带来流量和关注而变现,例如信息“标题化”“题文不符”“说反话”等。而网络水军更可以接受利益集团背后的利益关系而将信息传播出去。因此,在组织的影响下,复杂化的传播者可以为了其利益目的而罔顾、扭曲或篡改真相和事实本身,在信息生产中模塑出一种“真相”和“事实”。
(三)社交媒体传播渠道滋生“后真相”舆情呈现
社交媒体与社会公共事件的相互型塑,便在社交媒体舆论场中引发了“后真相”舆情事件。各种各样的自媒体不断发声,填充着传播场域,当网民获取真相的难度越来越高和传统媒体发声越来越“滞后”时,话语权便落入各类自媒体和社交平台手中,消解着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互联网下的“后真相”表现出“四化”的特点:信息碎片化、去中心化、部落化和偶像化。因此,传统的传播渠道被各种App所取代,无数传播节点构成的多元传播路径,在传受一体化的进程中变成网状传播结构,从而增加了网民从权威信源处获得完整信息的难度。并且,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不断消解着网民的耐心,受众成为了传播者们的首要争夺对象,时间便是争夺中的关键因素,这相对变相地减少了留给传统媒体进行事件事实调查的时间。
网民在媒介接触时,对信源和内容具有心理选择性。他们往往更加倾向于从自己喜欢或信任的自媒体获取信息,信源代替了信息的内容,成为人们甄别信息真实性的重要标准之一,网民将传播者的诚意看得比真相更重要。自媒体为表达出诚意,便会在符合其既定利益的目标下,迎合网民的喜好与需求,推送其主观上乐于看到的信息,与之站在同一立场,从而产生情绪共鸣。
(四)社交媒体促使受众形成社群和圈层
社交媒体重构了受众的身份,一方面,他们成为传播者;另一方面,受众也构成了网络社会中的社群和圈层,这正是由于网民有着相似爱好和相似观点所构成的,社交媒体本身就为网民提供着情感交流的空间。
此外,在“过滤气泡”的作用下,不同社群和圈层所获取的信息是不一致和不对等的,尽管讨论同一事件,但所携带的情感和立场也是不同的,群体之间便会出现情绪的对抗性传播。即便是在一个群体内,根据沉默的螺旋理论,单个网民实际上也受迫于群体压力,当发表与群体意见相左的观点时,要么被群体意见所针对,要么就保持沉默或与群体意见相一致,情绪也会在压抑中爆发和传播。因此,在受众身份的重构下,在社交媒体舆论场中,“后真相”舆情事件爆发的概率被大大增加。
四、反思与展望
在传播者身份复杂化、传播渠道多元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由于种种利益关系和不同信源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网民的情感神经被不断地撩拨和刺激,因此他们的言论往往携带着情绪化的表达,在传播场域内呈现出了“后真相”舆情事件这一负面传播现象的爆发。“后真相”时代是一个传播媒介迅猛革新与社会不断加深型塑进程的时代,任何一个负面现象和其传播效应的产生的确可以归因于媒介技术的发展,这也是不断解析现存社会负面现象所得出的结论。然而,技术是中立的,数据和算法也不带有任何偏向性,因此真正客观的反思应该是重新审视人本身,如何提升传播者的媒介素养,如何重拾网民信心,如何重塑能够凝聚社会共识的媒体力量,使网民的言论表达回归理性。
社交媒体所代表的新兴媒介值得我们不断研究,探讨将其技术应用在有利于缓解“后真相”舆情事件的正面引导亟需加强。当媒介技术的发展、应用,与其用户的媒介素养相匹配的时候,网民才会更加重视追求新闻事件的真相。我国公共卫生类“后真相”舆情事件的爆发,也映射出我国社交媒体舆论场生态环境的建设任重而道远。媒介环境的建设不仅是媒体机构的职责所在,更是每一个网民的基本责任。对于“后真相”的治理,我们还需从未来智能媒体建设出发,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通过媒体、平台、技术、政府机构的各方努力,充分掌握“后真相”舆情事件的传播态势,不断健全完善监管机制,使新闻报道回归真相。
注释:
① Dossey,L.(2017).Post-truth,Truthiness,andHealthcare.Explore:The Journal of Science and Healing,13(3),pp.147-154.
② 数据来源:https://trends.google.com/trends/?geo=US。
③ Oxford Dictionaries.WordoftheYear2016is….Available at: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word-of-the-year/word-of-the-year-2016.Accessed 12 Jan 2019.
④ 数据来源:知微事见,http://ef.zhiweidata.com/#!/index.
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⑥ 唐雪梅、朱利丽:《社会化媒体情绪化信息传播研究的理论述评》,《现代情报》,2019年第3期。
⑦ Yardi S,Boyd D.DynamicDebates:AnAnalysisofGroupPolarizationOverTimeonTwitter.Bulletin of Science,Technology & Society,2010,30(5),pp.316-327.
⑧⑨ 李彪、喻国明:《 “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话语空间与传播场域研究》,《新闻大学》,2018年第2期。
⑩ 张相涛:《基于传播学的角度看舆论反转的构成因素》,《传播与版权》,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