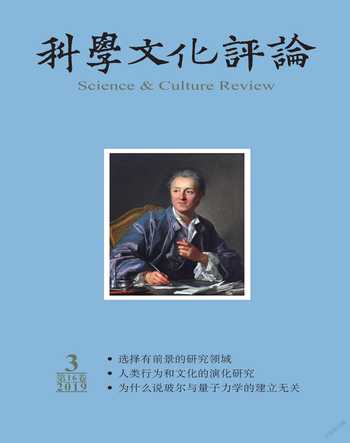人类行为和文化的演化研究
摘 要 人类行为和文化的演化研究以生物演化论为理论基础,是自进化生物学发展出来的一个重要学术传统。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这类研究已大致分化为文化演化、进化心理学和人类行为生态学这三大研究领域,研究者广泛分布于生物学及人文社科各学科。以人类的独特性为理由拒斥行为和文化演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不妥当的。严格说来,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并非持所谓的遗传决定论观点。这类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都是跟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相似的。细查进化论及其历史以及有关的科学哲学思想,可以发现,这类研究可免除“证据不足”或“缺乏可证伪性”的批评。
关键词 进化心理学 人类行为生态学 文化演化 遗传决定论 假说演绎法
中图分类号 N09: Q-0
文献标识码 A
一 引言
以进化论来研究人类行为和文化,不仅是进化生物学的一个悠久而重要的传统,在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里也是如此。
达尔文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非人类的生命世界。相反,他终生对人类行为和文化的演化研究保持着盎然的兴趣,这表现在他的《人类的由来》《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等重要著述上。在20世纪上半叶涌现出的那批优秀的进化生物学家里,无论是为著名的进化综合奠定了理论基础的费雪(R. Fisher)、霍尔丹(J. Haldane)、怀特(S. Wright),还是现代综合的实际完成者杜布贊斯基(T. Dobzhanski)、迈尔(E. Mayer)、辛普森(G. Simpson)等人,都多多少少是达尔文传统的继承人。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汉密尔顿(W. D. Hamilton)、威廉斯(G. Williams)、特里弗斯(R. Trivers)、普莱斯(G. Price)、梅纳德-史密斯(J. Maynard-Smith)等进化生物学家的工作又为行为生态学或社会生物学这一新兴学科打下了理论基础(行为生态学指的是对动物行为和环境之间的进化关系的研究)。他们不仅对人类行为和文化的演化研究身体力行,其工作也构成了这一类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1], pp. 9—19)。
人类行为和文化演化研究发端于西方,逐渐也在我国和其它许多国家发展并扎下根来。例如,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多位学者与英国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合作,基于进化生物学里著名的广义适合度理论探讨了川滇交界的摩梭人“走婚”习俗的进化基础[2],就属于这一类别。这类研究已广泛渗透进伦理学、美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传统领域。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逐渐形成了文化演化、进化心理学和人类行为生态学这三大较为著名的新的研究领域[3, 4]。就传统人文社科的各学科而言,也逐渐形成了进化心理学、进化人类学、演化经济学、进化社会学、进化伦理学等新学科或研究领域。它们与上述三大领域的基本特征都在于以进化论为基础理论,相互之间也往往是重叠、交叉的关系。例如,一个人类学家采纳进化的视角,所以可视为进化人类学家,但如果他在具体理论主张等方面跟进化心理学家更一致,他也可能同时被看作进化心理学家。主要由心理学家从事的进化心理学研究,近些年来最为活跃,发展势头最好,也最为著名。
本文的主旨在于借助进化生物学和科学哲学等方面的知识,评估现代人类行为和文化演化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正当性,并澄清关于这类研究的一些误会。
二 理论
人类行为和文化演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由达尔文奠定了基本框架的生物进化论。就人类行为和文化演化研究的理论基础而言,这类研究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主要在两个问题上存在实质性分歧:其一,进化论是否主要适用于非人类的生命世界,而不应过分向人类行为和文化领域渗透?其二,影响人类生存状况的是否主要是后天环境因素,遗传因素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1. 人类社会现象跟其它现象的区别
关于上述第一个问题,反对者的主要理由在于,人类社会现象跟其它现象具有根本区别,因而本来主要应用于其它生命的进化论原则上不应涉足对于人类行为和文化的解释。在这类观点中,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 Dilthey)19世纪后期提出的看法大概是最著名的。依狄尔泰的看法,“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是根本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原因就在于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根本区别,即只有人类才有意识、意志,因而“他与自然的其他部分相区别”([5],页6—7)。德国唯心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一大传统,而狄尔泰是这一传统的著名人物,所以他的观点影响很大。但是今天的神经科学界几乎普遍认为,与之相反的观点才是正确的。这就表现在一些西方神经科学家在2012年发布的“剑桥意识宣言”上宣称,并非只有人类具有意识活动的神经科学基础,非人类的动物也是如此,也能表现出有意向的行为①。这个宣言是面向社会大众而非科学界发布的,这似乎表明,发布者认为他们的观点是为神经科学界广为支持的。
早在40年前,美国进化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和努南就已指出,尽管人们常常认为,只有人类才有意识、先见之明、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使用语言和符号的能力、文化,但很多生物学家发现,有些灵长动物物种也可能拥有这些特征,跟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黑猩猩可能拥有这全部五个特征[6]。例如,按照美国进化生物学家威尔逊的看法,如果把文化界定为通过学习和模仿而习得、传播的行为,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文化是动物界里最发达的,而文化变异广泛存在于非洲黑猩猩各种群([7], p. 213)。甚至灵长目动物群体里也普遍存在着社会层级和统治秩序([8], p. 227)。
进一步说,人跟其它生命之间存在重大差别并不构成拒斥生物学和进化论的充足理由。昆虫和灵长动物与其它生命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所以有昆虫学和灵长动物学这样专门研究昆虫和灵长动物的学问。如果能找到人类与其它生命之间的多种区别,也许我们能发现,昆虫或灵长动物与其它生命之间的区别更多。而昆虫学和灵长动物学都接纳同样的生物学原则。试想,是一个人和一只猴子之间的差别大呢,还是一只猴子和一棵草(或一个病菌)之间的差别大呢?也许很多人会认为后一种差别更大。而生物学用同样的原则来理解猴子和草。既然如此,有何理由拒绝用生物学和进化论既解释人又解释猴子的行为呢?
2. “遗传决定论”
关于对上述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文化演化学者跟主流进化心理学及人类行为生态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文化演化学者认为,文化主要指社会里传播的信息,对人类而言就是思想、观念、价值观、知识等。文化演化学者除了分布在进化生物学界,主要分布在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美国人类学传统上包括文化人类学(也称为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和生物人类学(或称体质人类学)四个分支,人类学的学生往往在四个分支内都受到教育。人类学家通常受到学科传统的影响,或多或少承认文化因素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能在美国人类学界找到一些著名的文化演化论者。
文化演化论者的基本观点是,除了发生在基因层面的选择和演化,也存在文化演化,基因演化和文化演化之间也常常存在种种交互影响。他们认为,存在着众多不同的文化现象,它们在促进文化载体生存和繁衍等方面具有差别(变异),文化在代际或同侪之间传承(相当于“遗传”),不同文化被人们接受的程度于是也往往不一样(选择);换言之,像生物演化那样,文化演化也应在传承、变异和选择的框架内加以解释。上述观点也常常被称作“二重传承理论”或“基因-文化协同演化理论”[4, 9]。
文化演化学者重视后天因素即文化的影响,演化研究领域之外的人应当很容易就能接受这种论调。而常遭人们诟病的,则是集中体现于主流进化心理学及人类行为生态学的强调遗传因素影响的观点。主流或狭义进化心理学,其理论原则由美国学者涂柏(J. Tooby)和柯斯梅(L. Cosmides)等人于20世纪80—90年代在一系列论文里详加阐发。另外一部分学者在具体理论原则上和涂柏等人不太一致,但他们同样也主张在达尔文主义框架内研究人类心理、行为,所以他们也常常被称为进化心理学家[10]。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英国进化心理学家邓巴(R. Dunbar)等人,他们也强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主张研究文化演化。
人类行为生态学领域里的学者以人类学者较多,此外也包括心理学者、生物学者等。它与主流进化心理学都主张以达尔文理论和广义适合度理论为基础理论,但在具体理论观点、研究方法上存在一些微妙的差别。其中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人类行为生态学倾向于把现有人类行为看作适应良好的,有利于个体的生存和繁衍;进化心理学则认为,人类的心理和行为是在漫长的进化史上形成的,以前形成的时候是适应良好的,现在则未必[4, 11]。关于人类行为生态学近年来的发展概况,可参阅几位西方人类学家2013年发表在国际行为生态学学会机关刊物《行为生态学》上的論文[12]及当期发表的几篇对该文的评论,由此也可管窥进化生物学界对其的接受程度。
主流进化心理学家的研究工作常常令人误以为他们持有遗传决定论的观点。玆以涂柏、柯斯梅及其弟子利伯曼关于人类亲属识别的研究[13, 14]为例来说明。在他们看来,在长期自然选择-演化的过程中,人类的亲属识别能力(例如识别他人是否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广泛存在,人类就较为普遍地在识别别人与自己的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决定是否避免与别人的性关系,是否对别人做出奉献(利他行为)。他们实际上认为,即便历史上有一部分人缺乏亲属识别能力,由于他们更易于卷入乱伦而导致近交衰退等原因,他们留下的后代会趋于减少;相反,具有亲属识别能力的人的后代会趋于增加,并将这种能力遗传给后代。
首先,严格说来,涂柏等人的推理和论点并非所谓的遗传决定论,他们不过是潜在地认为遗传因素对亲属识别能力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而已。事实上,行为通常都受到遗传影响的观点是现代生物学里的常见看法。杜布赞斯基在其经典名著《遗传学和物种起源》里讲道:“人类的遗传仍是人类的基本,它能使人表现出各种所谓社交和文化的行为。”([15],页285)饶毅认为:“可以说,所有行为都一定有基因参与……”[16] 不过,在进化生物学、进化心理学和人类行为生态学研究者中,恐怕从来没有人认为,所有或多数行为都由遗传或基因完全决定或起主导作用。
其次,涂柏等人的推理和论点体现了标准的进化解释的逻辑。由于遗传的观点是进化逻辑的一个基本方面,要从进化的角度对行为做出解释,必然要涉及到遗传因素影响。从另一方面讲,一旦认识到遗传因素普遍影响行为,认识到行为之变异(在涂柏等人的例子里,变异指的就是人们具有各异的亲属识别能力),就会进一步认识到会发生选择和演化。可以设想,即便遗传因素对亲属识别能力的影响很小,在漫长时间内也会造成具有重要进化意义的后果。牛津进化生物学家威斯特等人把涂柏等人的上述研究看作“自己人”的工作,看作对动物亲属识别研究的延伸,看作在著名的广义适合度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工作[17],这是毫不奇怪的。
主流进化心理学有时遭到的一个具体的批评是:强调遗传因素而忽略了文化因素对行为的影响。据笔者所知,从未有进化心理学家完全否认文化会影响行为。他们只是认为,文化的基础在于个体的心理和行为,而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又是为自然选择所塑造的;简言之,文化根源于自然选择和演化[18],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对行为是没有独立而重要的作用的。
3. 路翁亭和古尔德的批评
对主流进化生物学及行为演化研究的最著名批评者大概算得上美国左派科学家及进化生物学家路翁亭(R. Lewontin)和古尔德(S. Gould)。而他们的一篇常被引用的有关论文是1979年发表的对所谓“适应主义纲领”的批评。在该文中,古尔德和路翁亭承认,大致自进化论的现代综合以来,即“在过去的40年里,适应主义纲领支配着英美的进化思想”[19]。适应主义纲领,其基本含义指主流进化生物学的还原论倾向,即一个有机体被分解为各个性状,然后考察各性状经由自然选择的适应性过程(即各性状变得趋于促进个体生存和繁衍的过程)。涂柏等人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纲领,因为他们抽取了人类的亲属识别能力并考察了其适应性过程。古尔德和路翁亭认为,在还原论纲领之外,也存在其它正当的研究路径,例如考察生态环境对有机体个体的影响与有机体进化的关系。在笔者看来,至少从字面来看,与其说他们反对适应主义纲领本身,不如说他们对此纲领之流行感到不安——他们在文章最后明白无误地说,他们反对“完全聚焦于适应主义纲领”,而倡导采纳“多元主义观点”来研究演化问题[19]。
古尔德和路翁亭都曾批评主流进化生物学和行为演化研究的“生物学决定论”或“遗传决定论”观点([20],页279—280;[21],pp. 9—25)。在宽泛的意义上,也可以说他们的批评不错。具体说来,既然主流进化生物学家认为行为通常都受遗传影响,这就意味着遗传为行为等性状设置了限制,例如基因決定了一个人不能徒手跳跃10米的高度。当然,进化研究者通常都既承认基因的作用,也承认环境的作用,也不一般地承认某一方的主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并非遗传决定论者。另外,相较于主流进化生物学家,很可能在路翁亭和古尔德心中,遗传因素的影响确实较小。左派科学家通常是一些对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忧心忡忡的人。如果人的行为真的受先天因素影响较大,这自然就意味着世界能被改变的程度降低了,即左派科学家自然就会对其中的某种政治、社会含义不满。笔者认为,这应该是路翁亭把达尔文理论、生物学乃至于整个科学都视作“意识形态”或“超级社会建制”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它们反映并强化了某一历史时期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和思想([21], pp. 9—25)。
关于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原则,还有一个误会。涂柏和柯斯梅的早期著作曾经强调,现代人类的心理和行为倾向早在石器时候就已形成。但他们后来做了澄清,即他们从未默守这种固执的看法,而人类的有些心理倾向也可能在石器时代之后产生。他们的早期著述确实有着“石器时代心灵”一类表述,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人类现有行为都是适应性的行为,跟环境配合良好,所以他们曾强调人类心理往往在石器时代形成,当时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当今时代则未必,希望以此扭转人们的错误看法([22], p. 177)。
三 方法
研究方法分为两大类别:其一,经验研究中使用的技术性较强的资料/数据收集方法和资料/数据分析方法;其二,跟一般理论原则联系较紧的思维方法,或者说在理论原则引导下实现研究目标的具体路径。
1. 资料收集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
不同领域、学科的进化研究在偏好的资料收集方法上有一定差别。人类行为生态学研究者往往喜欢收集民族志(ethnography)材料,即在非西方的特别是前现代的社会里做实地考察(fieldwork),收集有关族群的数据。这种方法也属于人类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季婷等人的研究方法[2]基本上也属于这一类别。进化心理学家则受到心理学学科传统的影响,常常偏好进行心理学实验、问卷调查或访谈来收集关于较小样本的数据。文化演化研究者或者说二重传承理论论者有时则喜欢以计算机仿真的方式取得数据[4]。跟近些年来实验经济学的兴起相联系,演化经济学家也常常采用计算机仿真和博弈实验等方法。进化社会学家受本学科传统影响,常常使用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或访谈所取得数据。
在以上资料收集方法中,除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其它方法跟生物学等学科学者采用的方法是相似甚至一致的。例如,人类学家的实地考察大致就相当于生态学里常见的资料收集方法,而计算机仿真方法也是自然科学里常用的方法。应当注意,不同领域或学科之间的区分仅仅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有时不同方法之间也可能存在交叉。例如,人类学家博伊德(R. Boyd)和经济学家费尔(E. Fehr)等人曾经对全球15个非西方族群进行博弈实验研究[23],他们就把实地考察与实验法结合了起来,而他们做的研究属于文化演化研究。再者,我们恐怕也没有很好的理由完全拒斥在进化研究中使用通过问卷或访谈取得的数据。而在资料分析方法上,除了进化伦理学家等哲学学者通常只进行纯粹的理论思辨之外,进化研究者在经验研究中广泛采用统计分析,显然这与生物学研究里流行的统计分析基于同样的统计学原理。
2. 证据不足和缺乏可证伪性的批评
人类行为和文化演化研究特别是进化心理学研究的理论解释常常受到经验证据不足及缺乏可证伪性或可检验性的指控[24]。现代人类演化研究的典型的理论解释方式是:⑴给定某种常见行为或心理倾向A,A完成某种任务α,A受某一个或多个基因影响(遗传);⑵设想在历史上也存在其它行为或心理倾向B和C等(变异);⑶相较于B和C等,A更能促进个体或其亲属繁衍,于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一个或多个基因就趋于成为更常见的基因,A于是也逐渐成为更常见的行为或心理倾向(选择和演化)。这种解释方式实际上就是美国进化心理学家平克的“逆向工程法”,基本原理和依据来自达尔文([25], pp. 21—23)。
这种解释方式也是为研究行为演化的进化生物学家所广为采用的,尽管他们在著述里不一定将这种理论解释明确或完整地呈现出来。例如,美国著名进化生物学家特里弗斯曾经跟威拉德于1973年提出特里弗斯-威拉德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预测是:在有性繁殖的物种里,若某些假定条件成立,则条件较好的母亲更可能生儿子。根据特里弗斯的回忆,这个理论的酝酿和发展始自威拉德提出的一个粗糙的思想——如果条件较好的母亲生儿子,则她更可能留下较多后代[26]。而他们在论文里讲到,若某种群满足某些假定条件,则“自然选择必定会有利于……调整性别比的一个或多个基因”,即促使条件较好的母亲更可能生儿子的基因会“脱颖而出”,在种群中的频率会趋于增加[27]。这实际上是基于逆向工程法而提出了理论解释,尽管这一解释在论文里没有完整地呈现出来。在季婷等人关于摩梭人走婚习俗的研究中[2],根据植根于达尔文理论的广义适合度原理进行推理,实质上也暗含着曾经存在基因选择过程的解释。
进化研究的理论解释证据不足,指的就是缺乏证据来证明存在上述那一类自然选择过程。根据进化生物学史,这也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在问世后的几十年内遭到的最严厉指控之一。达尔文认为,生命演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然选择。但他无法像放电影那样把这一过程展示给别人看,堵住别人的嘴。有“达尔文的斗犬”之称的赫胥黎(T. H. Huxley)乐于接受达尔文进化思想中的其它成分,却一直很难接受自然选择理论。赫胥黎认为,如果能用人工实验经选择而培育出一个新物种,这也相当于为自然选择理论提供了证据,但从没有这样成功的实验([28],页345—387;[29],页245)。概而言之,以缺乏证据为基本理由来拒斥现代人类行为演化研究的那些人,相似于达尔文时代不愿接受自然选择理论的那些人。
至于这种批评,即进化研究的理论解释不具有可证伪性或可检验性,因而是非科学的,其中关于可证伪性的观点渊源于波普尔。确实,这样的进化解释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似乎想象不出什么经验上的例子来驳倒这样的解释。但是应注意,其一,在波普尔的思想体系里,一个理论或理论解释不具有可证伪性固然就意味着它是非科学的,但这不一定也意味着它没有科学地位或科学意义。波普尔曾经认为自然选择理论不可证伪,因而属于形而上学而非科学,但可以以之为基础发展出各种可证伪的科学理论([30],页177)。显然波普尔并不主张生物学家丢掉自然选择理论。同理,如果我们完整地接受波普尔的思想,即便进化解释没有可证伪性,这也不构成要求进化研究者拒斥这类解释的充足理由。其二,波普尔强调理论系统或科学系统而非单个理论本身的可证伪性——“经验的科学的系统必须有可能被经验反驳”,“应当把理论系统的可反驳性或可证伪性作为分界标准”([31],页17;[32],页367)。按照波普尔的论述,即便进化研究的理论解释本身是不可证伪的,如果进化解释的推论是可证伪的,即其理论解释系统是可证伪的,仍然可以说进化研究是科学的研究。
前已述及,自然选择理论在其提出后的几十年里都受到证据不足的指控,而这一理论本身似乎也是不可证伪的。这种情况很可能在其它现代自然科学学科里也存在。例如,依牛顿第一定律,若不受外力作用,任何物体都将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既然世上不可能存在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因而,可以说牛顿第一定律本身既缺乏证据支持,也没有可证伪性。因此,如果我们不采用双重标准的话,我们就只能说,如果单纯因为现代人类演化研究的理论解释本身证据不足或缺乏可证伪性而斥其不是科学或不是好的科学,那么牛顿和达尔文的工作理应受到同样的指控。其次,现代科学的一大特征在于假说演绎法的应用,这不仅适用于牛顿及其之后的力学研究[33],也适用于达尔文及其之后的进化研究([28],页 269—270;[29],页20)。而在采用了假说演绎式的论证结构之后,是可以得出可检验或证伪的推论的,这就使得它们符合波普尔的方法论原则。例如,可以以牛顿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等为前提条件进行演绎推理,推论出某小行星的运行轨道。这样的推论原则上是可证伪的,尽管如拉卡托斯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科学实践中,即便这样的推论不符合观察,也常常很难导致科学家真的把作为演绎推理的前提条件的科学理论拒斥掉([34],页13—14)。在现代人类演化研究中同样如此。例如,季婷等人在广义适合度理论等条件下进行演绎推理,得出了摩梭男性更倾向向姐妹的子女投入这一可检验或可证伪的推论[2]。在上述涂柏等人的亲属识别研究中,涂柏等人也在广义适合度理论等条件下进行演绎推理,得出了几条可证伪的推论,例如,若其它条件一样,与兄弟姐妹共同生活时间较长的人更倾向于为兄弟姐妹做出利他行为[13]。
3. 进化心理学的模块说
在人类演化研究中,进化心理学的模块说也容易引起批评。按照涂柏和柯斯梅在其经典论文里的看法,现代进化心理学的一个主要理论假说是:人类祖先(特别是石器时代从事狩猎、采集的人类祖先)面对着各种各样影响生存、繁衍的问题(例如择偶、寻找食物),就通过自然选择逐渐在漫长的进化时间内形成了各种各样专门化的心理机制(模块),每一机制都专门负责解决某一具体问题[18]。
进化心理学家主张研究一个个模块的思想也就是所谓“领域特殊性”(domain specificity)或模块性(modularity)的思想,即他们认为我们在进化史上更容易形成各个具体的心理机制,不太主张笼统地探究人类一般心理(上文中涂柏等人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亲属识别模块的研究)。巴斯在其著名的进化心理学教科书里给出了三点理由:⑴一般性心理不能指导有机体正确解决适应性问题;⑵即使一般性心理能正确指导有机体的行为,它们也会犯下太多错误,从而对有机体来说代价高昂;⑶人类在生活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成功的解决方案”必然千差万别。我们从巴斯的理由也可看出,进化心理学并不绝对否定人类可能形成一般性心理机制。总之人类可能就求偶、亲属识别等频繁出现的问题形成一个个模块,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有些乱七八糟的问题都只是偶尔出现,这时人类也可能为处理这些问题形成一般智力等一般性心理机制([35],页63—66)。
在笔者看来,首先,姑且不论人类是否有进化而来的一般性心理机制,从实用或工具论的观点看,模块性的思想也有助于抓住一个个具体问题,使经验研究持续进行下去。其次,模块说体现了现代科学和进化生物学的还原论倾向,即把整体分解為各个部分而分别研究的倾向。放宽历史的视野,可以说,模块说并不包含实质性的崭新思想,它不过是用稍带心理学特色的新的语言对路翁亭和古尔德1979年就批评过的主流进化生物学的适应主义纲领[22]的重新表述而已。而在几十年之后,美国进化生物学家阿尔科克([36], pp. 35—36)仍然在其著名的教科书《动物行为:进化分析》里把这种主张研究一个个性状的适应性的适应主义方法当作动物和人类行为演化研究的正当方法介绍给读者。
四 结语
经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发展,现代人类行为和文化演化研究已经大致分化为文化演化、进化心理学和人类行为生态学这三大研究领域,总的看来,对这类研究的一些流行的批评或保留意见是对这类研究、进化生物学及其历史以及有关的科学哲学思想缺乏足够了解的结果。第一,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表明,人类并非在具有意识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因而仅仅以人类的独特性为理由拒斥行为和文化演化研究是不妥当的。第二,尽管进化心理学等演化研究者有时受到遗传决定论的批评,但他们通常既承认遗传也承认环境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而不一般地假定某一方的决定或主导作用,因而可以说他们并非遗传决定论者;而我们一旦像很多生物学家那样意识到遗传因素通常都会影响行为,意识到行为变异的广泛存在,并且也熟悉达尔文主义演化论的话,很可能很容易就意识到可以以演化论为基础来探讨行为演化。第三,行为和文化演化研究的多数数据收集方法跟生物学等学科相似甚至一致,这类研究的常用数据分析方法跟生物学等学科一样采用基于相同统计学原理的统计分析。第四,达尔文提出其理论之后的几十年内,同样面临着今天人类演化研究面临的证据不足的批评;人类演化研究采用了现代科学里盛行的假说演绎法,是可以得到可证伪或检验的推论的,因而这类研究是符合波普尔的科学划界理论的。第五,进化心理学主张研究一个个心理/行为模块的思想不过是主流进化生物学长期以来采纳的适应主义方法的另一种表述而已。
如果堅持认为遗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较小(路翁亭、古尔德等左派生物学家很可能这么看),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既然演化的发生是以行为等性状的可遗传性为前提的,也可合理地怀疑,生物演化论到底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上才适用于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换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讲,对遗传因素的认识是接受人类行为研究的进化逻辑的一个枢纽。
人类行为演化研究有时给人留下要抢走传统人文社科饭碗的印象:“如果从基因中能找到社会行为的解释,那么遗传学的发展就足够了;如果生物因素能完满地解释心理和行为,那么心理学还有什么必要呢?”[37]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廷伯根曾经主张,在动物和人类行为研究中应区分行为的最终解释(原因)和直接解释(原因),最终原因指自然选择[38]。这一区分已为进化生物界广为接受。从演化论的观点看,一种行为在某种群或人口中是趋于减少还是增多,最终要经受自然选择即有差别的繁衍成功的考验,因而可以说自然选择是最终原因。但是,从来没有人排斥过对行为的直接解释,即基因、环境或其交互作用对行为的直接影响(例如观看有暴力内容的视频对儿童暴力倾向的影响),而直接解释是传统人文社科研究的一个重点。行为演化研究者的基本目的固然在于寻求行为的最终解释,他们同时又认为,行为的最终解释和直接解释都是需要的,不可偏废某一方面。
参考文献
[1] Alcock, J.. The Triumph of Sociobiolog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季婷等. 中国摩梭母系社会“走婚”婚姻的进化生物学研究进展[J]. 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 2016, 46(1): 129—138.
[3] Brown, R.. Why Mechanisms Shouldn’ t be Ignored[J]. Behavioral Ecology, 2013, 24(5): 1041—1042.
[4] Winterhalder, B., Smith, A.. Analyzing Adaptive Strategies: Human Behavioral Ecology at Twenty—Five[J].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2000, 9(2): 51—72.
[5]狄尔泰. 人文科学导论[M]. 赵稀方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6] Alexander, R., Noonan, M.. Concealment of Ovulation, Parental Care, and Human Social Evolution[A]. Chagnon, A., Irons, W.. (Eds).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Human Social Behavior: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C]. North Scituate, MA: Duxbury Press, 1979. 436—453.
[7] Wilson, O.. 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12.
[8] Lopreato, J., Crippen, T.. Crisis in Sociology: the Need for Darwin[M].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9.
[9] Feldman, W., Laland, N.. Gene-Culture Coevolutionary Theory[J].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1996, 11(11): 453—457.
[10] Mameli, M.. Evolution and Psychology i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A]. Dunbar, R., Barrett, L.. (Eds). Oxford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1—34.
[11] Symons, D.. On the Use and Misuse of Darwinism in the Study of Human Behavior[A]. Barkow, H., Cosmides, L., Tooby, J.. (Eds). The Adapted Mind[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37—162.
[12] Nettle, D., Gibson, A., Lawson, W., Sear, R.. Human Behavioral Ecology: Current Research and Future Prospects[J]. Behavioral Ecology, 2013, 24(5): 1031—1040.
[13] Lieberman, D., Tooby, J., Cosmides, J.. The Architecture of Human Kin Detection[J]. Nature, 2007, 445(7129): 727—731.
[14] Lieberman, D., Tooby, J., Cosmides, J.. Does Morality have a Biological Basis?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Factors Governing Moral Sentiments Relating to Incest[J].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2003, 270(1517): 819—826.
[15]杜布赞斯基. 遗传学和物种起源[M]. 谈家桢等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5.
[16]饶毅. 欲解异性恋, 须知同性恋[J]. 科学文化评论, 2012, 9(5): 63—74.
[17] West, S., Mouden, C., Gardner, A.. Sixteen Common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in Humans[J].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11, 32(4): 231—262.
[18] Tooby, J., Cosmides, L.. 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ulture[A]. Barkow, H., Cosmides, L., Tooby, J.. (Eds). The Adapted Mind[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9—136.
[19] Gould, J., Lewontin, R.. The Spandrels of San Marco and the Panglossian Paradigm: A Critique of the Adaptationist Programme[J].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B, 1979, 205(1161): 581—598.
[20]古尔德. 自达尔文以来: 自然史沉思录[M]. 田洺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21] Lewontin, C.. Biology as Ideology: The Doctrine of DNA[M]. West Concord: House of Anansi, 1991.
[22] Laland, N., Brown, R.. Sense and Nonsense: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on Human Behaviou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3] Henrich, J., Boyd, R., Bowles, S.. et al. (Eds). Foundations of Human Sociality[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4]江景涛, 董国安. 进化心理学: 研究方法与评价[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4, 36(1): 117—121.
[25] Pinker, S.. How the Mind Works[M]. New York: W. W. Norton Press, 1997.
[26]罗力群. 罗伯特·特里弗斯: 桀骜不驯的卓越进化理论家[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8, 40(5): 132—141.
[27] Trivers, R., Willard, E.. Natural Selection of Parental Ability to Vary the Sex Ratio of Offspring[J]. Science, 1973, 179(4068): 90—92.
[28]迈尔. 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M]. 涂长晟等译, 成都: 四川出版集团, 2010.
[29]鲍勒. 进化思想史[M]. 田洺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
[30]波普尔. 无尽的探索[M]. 邱仁宗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31]波普尔. 科学发现的逻辑[M]. 查汝强等译.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8.
[32]波普爾. 猜想与反驳[M]. 傅季重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33]李醒民. 哲人科学家眼中的科学理论的认知结构[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2, 34(2): 1—6.
[34]拉卡托斯.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 兰征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35]巴斯. 进化心理学[M]. 熊哲宏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36] Alcock, J.. Animal Behavior: An Evolutionary Analysis[M]. Sunderland, MA: Sinauer, 2001.
[37]叶浩生. 有关西方心理学中生物学化思潮的质疑与思考[J]. 心理科学, 2006, 29(3): 520—525.
[38] Tinbergen, N.. On Aims and Methods of Ethology[J]. Zeitschrift für Tierpsychologie, 1963, 20(4): 410—433.
Keywords: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human behavioral ecology, cultural evolution, genetic determinism, 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