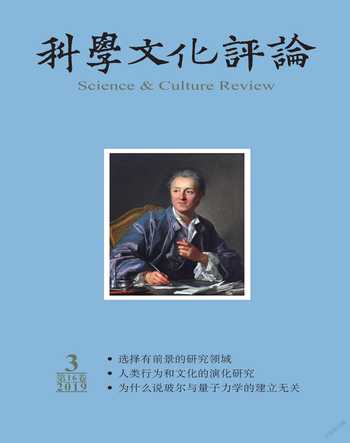豪尔吉陶伊眼中的吴健雄
梁慕宇
摘 要 匈牙利享誉国际的科学史家伊什特万·豪尔吉陶伊可能是国外研究诺贝尔奖史著名学者中唯一从技术层面指出过吴健雄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原因的人。他指出,吴健雄为李政道、杨振宁的理论发现提供了实验上的证据,应该与李、杨一起获得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吴健雄所以未能获奖,一是因为她的实验发现公布太晚,未能得到当年的获奖提名;二是因为吴健雄的实验并非是唯一证明杨、李理论的实验,有资格当选的候选人多于3人。更由于女性的获奖者人数很少,吴健雄被诺贝尔奖遗漏的事实便显得更为突出。部分学者在探究吴健雄未能获奖的原因时,所以会出现一些偏颇的结论,可能与对诺贝尔奖遴选程序和准则,特别是对颁奖《章程》的缺乏了解有关,因而未能把该不该授奖与能不能授奖区别开来思考。
关键词 豪尔吉陶伊 吴健雄 诺贝尔奖
中图分类号 N09: O4-09
文献标识码 A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我国学者和出版界翻译出版的国外有关诺贝尔奖的著作中,最全面论述诺贝尔奖,也最受我国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学和科学社会学界青睐的有两部:一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朱克曼(H. Zuckerman)所著的被国际学者誉为诺贝尔奖社会学的权威研究著作《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二是匈牙利享誉国际的科学史学家豪尔吉陶伊(I. Hargittai)所著、出版后获得国际学术界广泛好评的《通往斯德哥尔摩之路——诺贝尔奖,科学和科学家》。
这两部著作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用了不少篇幅谈诺贝尔奖的“第41席占有者”(指那些做出了諾贝尔奖级科学贡献却未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的问题,并在附录中列出了一份“第41席占有者”名单,但包括附录在内的整部著作均未出现过吴健雄的名字;后者则在3处11次提及吴健雄。豪尔吉陶伊认为,吴健雄做出了可获得诺贝尔奖的贡献,并从技术性层面上评析了吴健雄被诺贝尔奖委员会遗漏的具体原因。这在我们能见到的国外研究诺贝尔奖的著作中是罕见的。
豪尔吉陶伊是匈牙利大学的化学教授,匈牙利科学院、挪威科学院和欧洲科学院三院院士。他曾于2001年12月应邀出席瑞典皇家诺贝尔奖百年纪念大会,被邀到瑞典皇家科学院就该书的重要内容作过报告。匈牙利与我国没有国家利益冲突,人民和科学家之间向来关系友好。对于像吴健雄那样做出了杰出贡献而未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豪尔吉陶伊不分国籍、种族和性别,充满同情和人情味的理解([1],页299、337),但寻找被遗漏原因时他又总是客观和理性。豪尔吉陶伊在该书中评述了吴健雄对证实李政道、杨振宁提出的“弱作用中宇称可能不守恒”这一理论发现的杰出贡献,指出了吴健雄未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个主要的具体原因,评述了吴健雄被诺贝尔奖遗漏所产生的影响。下面依次予以介绍和试作解读。
一 吴健雄的实验发现应被授予诺贝尔奖
在书中题为“发现”这一章中,豪尔吉陶伊评述了诺贝尔奖级水平的科学成果[1]。评及李、杨关于“宇称在弱作用中可能不守恒”这项二战后最伟大的理论发现之一时,吴健雄的名字出现了2次,是和李、杨的名字一起出现的,而且是只有吴健雄的名字与李、杨名字一起出现([2],页292)。
科学中有教条,逾越它们会被认为是亵渎。但实际上还是会发生这样的事,即因为某人挑战了教条而做出了开创性的发现。在基本粒子物理学中发现了宇称破坏,就为此提供了一个漂亮的说明。手性(handedness)在日常生活和生物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我们在镜子里观察左手的时候,它看上去像是我们的右手,反之亦然。然而物理学家曾经还是相信物理学定律没有左右的区分。这个几何学原则被叫做空间反射对称,并且被表述为宇称守恒定律。每个人似乎都相信这条定律,只有两个年轻的物理学家除外,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杨振宁。他们提供了如下的可能性,弱相互作用可能通过空间反射操作而改变。他们向实验物理学家提出了挑战,吴健雄和她的同事们完成了相关的实验,一个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教条就这样被推翻了。([1],页124)
科学家都有这样的共识:任何科学的理论发现,无论其多么伟大,在未经实验给予证实之前,都只能是一种科学假说,其真理性未明确,还未能获得科学共同体承认。显然,在豪尔吉陶伊眼中,以实验证实李政道、杨振宁的理论的正确性的首功应归吴健雄。
科学史的事实是,李、杨二人提出“弱作用中宇称可能不守恒”的惊人观点之后,由于李政道与吴健雄是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工作的同事,同时吴健雄与李、杨关系友好,又是当时β衰变研究方面的权威物理学家,加上她的对实验前景的智慧眼光,她是第一个接受李杨求助、接受李杨提出的4个验证实验方案(第一个即为β衰变实验)挑战的人,是第一个在1956年12月就在实验中发现宇称在弱作用中不守恒的人,她还是第一个在将自己实验发现的论文投到物理学界最权威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当天(即1957年1月15日),通过记者会向世界宣布了自己实验发现的人([3],页182、187、192—194;[4],页45—51、67—69)。正是她的这些举动,使李、杨的科学发现获得了实验证实的惊人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也使李、杨的发现迅速获得了世界物理学界的承认,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伟大的科学理论发现,从而于1957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首开了物理学领域凭前一年成果获奖的纪录([5],页118),创下整个诺贝尔奖史自然科学领域迄今从获奖论文发表到获奖的“等待”时间最短、既空前又“绝后”的最快获奖纪录。在整个“宇称在弱作用中不守恒”的伟大科学发现过程中,吴健雄确实是属于诺贝尔“遗嘱”所规定的在物理学领域做出最重大发现、对人类贡献最大的人之一([1],页3),她确是豪尔吉陶伊认为的那样,是够资格、应该可获取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
二 吴健雄未能获奖的两个主要原因
但是,为什么吴健雄1957年未能与李政道、杨振宁一起分享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且此后直至1997年去世,她都未能获得这一科学殊荣?在豪尔吉陶伊看来,主要原因有两个,下文将一一说明。
1. 吴健雄的实验发现发表晚于诺贝尔奖提名时间
任何作出了杰出科学贡献的科学家要获得诺贝尔奖,其前提条件是需要有提名权的人提名推荐其为诺贝尔奖候选人。豪尔吉陶伊指出,诺贝尔基金会为执行“诺贝尔遗嘱”而制定的《章程》第7条规定:“除非得到有提名权力者的书面举荐,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获奖。”([1],页17)按照诺贝尔奖颁奖的程序和惯例,每年秋季,由各学科的诺贝尔委员会给一部分有权提名的科学家发出征询,征询下一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有提名权但未接到征询信的科学家也有权推荐下一年度的获奖者名单。但无论谁提名推荐,名单必须在次年2月1日前送达诺贝尔基金会;如果推荐名单未能及时提交,则不予考虑([1],页17;[6],页1112)。豪尔吉陶伊认为:“吴健雄应该与李政道、李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奖,但是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另有想法,从技术角度讲,吴健雄很难得到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提名,因为她的实验在那一年1月份才公布。”([1],页318)
豪尔吉陶伊所指的“1月份才公布”,应是指1957年1月15日,吴健雄和莱德曼将自己的实验论文投到《物理评论》当天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史无前例”的记者会上,对自己的实验发现的公布([3],页193),和参加同年1月30日召开的空前盛大的(有全球约三千名物理学家参加)美国物理学会年会,提交会议论文并和莱德曼(A. M. Friedman)、泰勒格第(V. Telegdi)就各自所做的证实宇称不守恒的学术报告([3],页195)。在此之前的1956年12月,吴健雄的实验结果就已证实“宇称不守恒”,当时她出于慎重,只让李政道、杨振宁2人知道,并要求他们保密。后虽因李政道提前泄露,也只是在少数科学家中流传“私布”,吴健雄本人则从未在任何场合公布过自己的实验结果。吴健雄实验结果最后一次公布是1957年2月15日她的实验结果论文在《物理评论》上发表。显然,参加美国物理学会年会和在《物理评论》上发表论文,对当年诺贝尔奖提名时间来说确是太迟了。但1957年1月15日吴健雄在记者会上的公布,有人要提名推荐她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时间上还是来得及的,李政道、杨振宁不就是在此时之后,因其假说获得了实验证实一致之后才可能获得别人提名推荐,才会获得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吗?吴健雄为什么当时却不可能像李、杨2人一样,获得别人提名推荐呢?这主要是因为诺贝尔奖评委会有规定,推荐人提出获奖名单时,必须书面陈述理由,并附上已经发表过的能说明理由的资料([7],页1112)。而吴健雄的实验论文在提名推荐诺贝尔奖名单时,还没有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因此就是有人想提名推荐她,也会因无法“附上已经发表过的能说明理由的资料”而作罢。李政道和杨振宁2人则不同,他们的理论发现论文早在1956年10月1日就已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提名推荐他们的人并不存在这种困难。
应该说,诺贝尔奖评委会对提名推荐人的提名推荐作这样的规定,是符合科学界的学术传统与共识的。默顿在其创学科的经典代表作《科学社会学》中,在专章谈“科学发现的优先权”时,就提出了科学共同体承认“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的判定准则与判据:“科学界的精英内层的联系网,通常都能保证他们知道在自己的领域内有什么他们通常所谓‘有意思的工作’正在取得发展。传达这种关于谁正在做或计划做什么的消息大都通过非正式的途径——口述、电话或信件。但是,尽管著名的科学家们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这种非正式的联系却不完备,而且无论如何,当事情到了判定科学研究成果归属权的问题时,不能代替以出版物形式进行的联系。而科学界的准则,是把首创权及其附属的报酬划归首先予以发表的科学家。”([7],页246;[8],页384—442)科学是严肃、严谨和严格的,诺贝尔奖的提名推荐也是如此。吴健雄等在哥伦比亚大学以记者会的方式而不是等待以学术会议和出版物的方式公布自己的实验发现的行为,当时在科学界并不是大家所乐见和认可的。杨振宁那时还和李政道合作很好,关系亲密,与吴健雄也向来关系友好,但他也认为用记者会方式宣布一项科学研究成果是“令人生厌”的,是“不大有格调”的,所以虽然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人士一再督促他去参加记者会,但他都没有出席([3],页193; [4],页69)。吴健雄实验的合作者、国家标准局的科学家们不愿出席记者会,也是因为他们“对于哥大的这些宣传活动,也感觉颇不受用”([3],页193)。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们虽然相信吴健雄实验结果是正确和可靠的,但谁也不会去违反诺贝尔奖评委会的规定,冒然对她作诺贝尔奖的提名推荐。事实上,1957年吴健雄确是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推荐,就连她自己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有提名权的科学家,也没有人给她提名推荐①。
2. 吴健雄未曾单独占有实验发现的优先权
豪尔吉陶伊认为,吴健雄虽然因为她发布自己的实验发现太慢而错过了当年的机会,但“物理学奖评奖委员会和科学院等下一年,再把吴健雄包括进去一起颁奖,也是很容易的”。然而,“吴健雄的实验并非是唯一证明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理论的实验,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她没进获奖名单的原因。根据也投入实验的莱德曼(1988年物理学奖得主)的说法,李政道和杨振宁提供了好几种特定的实验方法,吴健雄只看到了一种是可以实现的”([1],页318—319)。确实,在李政道和杨振宁1956年10月1日发表于《物理评论》上的获奖论文中,提出了4种实验方案供实验物理学家们检验“宇称在弱作用中可能不守恒”,这4种方案都是弱作用过程,分别是β衰变、Λ衰变、π-μ-e衰变序列与Ξ-Λ-p衰变序列([4],页60)。吴健雄选择的是β衰变,芝加哥大学的泰勒格第选择的是π-μ-e衰变序列方案,用的是照相乳胶方法,与吴健雄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工作的莱德曼也是选择π-μ-e衰变序列方案,但用的是电子学方法。3人的实验小组起步时间早晚不同,实验方法各异,是互相独立进行的([4],页61、62、67),但实验结果的论文都是同一天即1957年1月15日寄达《物理评论》编辑部的,吴健雄与莱德曼的论文于2月15日在同一期发表,泰勒格第的论文则在后一期3月1日发表,但论文发表时编辑部注明的收稿日期也是1月15日([3],页192—195)。還应指出的是,在1月15日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自己用实验证实李、杨理论的,除吴健雄外还有莱德曼;在1月30日开始举行的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对与会科学家作实验发现学术报告的,除吴健雄外还有莱德曼和泰勒格第。会中,还有布鲁克海汶国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劳(R. R. Run)领导的实验小组和加州大学的阿瓦瑞兹(L. W. Alvarez),也报告了与他们3人相同的实验结果([3],页195)。
所以,无论从记者会发布到在美国物理学年会作报告发布,还是论文在《物理评论》上发表,吴健雄与莱德曼、泰勒格第3人,都属于“互相独立、几乎同时”作出同一科学实验发现。吴健雄在科学共同体眼中,按前述默顿所概述的科学界的传统和承认科学发现优先权“最终以出版物发表为据”的准则,吴健雄未能独占这一实验发现的优先权,只能与莱德曼、泰勒格第3人平等、共同占有。
195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赛格雷(E. Segre)的看法,支持了豪尔吉陶伊的上述观点。他在谈到1957年“宇称的瓦解”过程时说:“就在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论文发表后不久,由另一位中国物理学家吴健雄领导的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华盛顿特区国家标准局的一组物理学家,以及另外二组物理学家,各自独立证明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简直就是一种神话。”([2],页287—288)“当年10月,诺贝尔物理学奖宣布授予李和杨。没有人感到惊奇,……我爱管闲事地想着,斯德哥尔摩的那些贤者们是否也会将吴健雄包括在内,但他们没有。”([9],页320)从1958年开始到1964年,吴健雄先后有4年共获得7人提名推荐[8],但她始终没有获享诺贝尔奖这一科学殊荣。为什么“没有”?就因为她没有能独享证明李、杨假说的优先权。
按科学共同体承认科学发现优先权的准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传统颁奖做法,总是在有2个以上科学家“互相独立,几乎同时”做出同一重大科学发现时,如果这项成果值得并可能授予诺贝尔奖,都会令这些“互相独立,几乎同时”做出这一科学发现的科学家共同分享奖项。这方面的事例在百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史上大约有10起之多。例如: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由德国的梅耶(M. G. P. Mayer)和詹森(J. H. D. Jensen)共同分享,因为他们各自创立了原子核壳层结构理论([10],页102—104);193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由美国戴维逊(C.G. Darisson)和英国汤姆逊( G. P. Thomson)共同分享([10],页55—57),他们发现了电子在晶体中的衍射现象;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由里希特(B. Richter)和丁肇中共同分享,因为他们发现了J/ψ粒子([10],页133—136);1977年,吉耶曼(R. Guillemin)和沙利(A. V. Schally)因分离、鉴定和合成了控制脑下垂体前叶激素分泌的下丘脑释放因子而共享诺贝尔生理医学奖([10],页526—528)。可见,这种奖励的准则和方式已成为科学共同体承认与奖励科学发现优先权的一种共识。因此,诺贝尔奖委员会如果要给最先以实验证实李、杨“守称在弱作用中可能不守恒”的吴健雄以诺贝尔物理学奖,就至少也应给莱德曼和泰勒格第共同分享。
但是,应该不应该,值得不值得授奖,与能不能授奖并不是一回事。因为诺贝尔奖的颁发,不仅有学术上的标准,还有其它非学术方面的“规矩”。直白地说,就是诺贝尔基金会为执行“诺贝尔遗嘱”而制定的颁奖《章程》所规定的遴选程序和颁奖准则,每个学科的诺贝尔奖委员会都必须遵守执行而不能违背。例如,《章程》第4节规定:“奖项可以平分给两项工作,每一项工作都要值得获奖。如果两个或者三个人共同完成了一项值得获奖的工作,奖项就应该同时颁发给他们。但是任何情况下,一种奖都不能同时授予三个人以上。”([1],页15)显然,《章程》对奖项人数限制在3人以下的规定,成为了吴健雄应该、值得授奖却未能获奖的关键原因。在此情况下,诺贝尔奖委员会只能作出这样的抉择:要么吴健雄、莱德曼和泰勒格第3人一起被授奖,这样获奖者人数加上李、杨就成5个了,这违反了《章程》的规定而不可执行;要么3个“几乎同时,互相独立”以实验证实李、杨假说的实验小组负责人都不授奖,只奖首先作出理论发现的李政道和杨振宁。
类似吴健雄的情况在诺贝尔奖史上曾多次出现。例如,197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只授予相互独立,几乎同时创立弱电统一理论的三位理论物理学家,而于1973年首先观察到弱中性流,验证这一弱电统一理论预言,证明弱电统一理论正确的欧洲核子中心的实验物理学家哈赛尔特(F. J. Hasert)却没有获奖;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互相独立,几乎同时提出统一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三种力的标准模型的2位理论物理学家,而于2012年互相独立,几乎同时发现标准模型预言的希格斯粒子,证实标准模型理论正确的欧洲核子中心的两个不同实验中心和团队,即ATLAS(环形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实验物理学家和LHC-CMS(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上的紧凑缪子探测器(CMS))的实验物理学家却无一人获奖[11, 12]。前例有平等理论发现优先权的理论物理学家已有3人,再奖实验物理学家就违反《章程》不许超过3人的规定了;后例有平等理论发现优先权的理論物理学家虽然只有2人,但有平等实验发现优先权的实验物理学家却至少也有2人,再奖实验物理学家就变成共奖4人了。
上述包括吴健雄在内的事例,都是实验物理学家未能获奖的例子,是否就可断言是诺贝尔奖委员会“偏重理论”而“轻视实验”[13]呢?显然不是!因为这是诺贝尔奖委员会受困于《章程》对颁奖人数不超过3人的规定而不得已作出的决定。其所以如此决定,则是因为上述几例中,从整个“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弱电统一理论、标准模型理论的确立全过程来说,都是理论物理学家先获得理论发现,然后才有实验物理学家去做实验证明理论发现正确。是理论发现在先,属于首创者,是优先权的应当占有者,诺贝尔奖委员会只有这样决定,才能既尊重首创又不违反《章程》的规定。这可以说是科学共同体承认科学发现优先权的一种形式。正如默顿所说的那样:“科学界的准则,是把首创权及其附属的报酬划归首先予以发表的科学家。”195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首先发现“切伦科夫效应”的苏联实验物理学家切伦科夫(P. A. Cherenkov)和后来对这一效应作出理论解释的两位苏联理论物理学家弗兰克(I. M. L. Frank)和塔姆(I. E. Tamm),因为在这一发现全过程中,作出发现的实验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人数总和恰好是3人。如果最先作出实验发现“切伦科夫效应”的切伦科夫的导师瓦维洛夫1958年还活着①,就只能授予首先作出实验发现的切伦科夫与瓦维洛夫,而无法授予后来对实验发现作出理论解释的弗兰克与塔姆。理由是诺贝尔奖委员会要既尊重首创又不违反《章程》有关一个奖项授奖人数不超过3人的规定。但不能据此反过来说诺贝尔奖委员会是“偏重实验”而“轻视理论”!
可見,首先承认和奖励首创者的科学发现优先权,向来在科学共同体的主流意识中是有共识的。豪尔吉陶伊在评述像吴健雄一类该获奖而未能获奖的科学家,所以未能获奖的原因时说:“某位科学家在颁发诺贝尔奖时被遗漏的情况,对于相关个人来说这是最痛苦的了,这种情况可能是信息不足、信息错误、评价不准确、竞争、憎恶或者类似情形的结果,也可能是其记录证明有资格当选的候选人多于三个。”([1],页299)吴健雄未能获奖的原因可能不止一个,但除了首先承认和奖励李、杨理论发现的首创权外,“有资格当选的候选人多于三个”无疑是“一个好理由”([1],页299)。
三 吴健雄被诺贝尔奖“遗漏”的影响
豪尔吉陶伊在其著作“未获奖者”[1]一章中,除了在重点评述1957年李、杨二人因瓦解宇称守恒神话而获取诺贝尔奖时,两次专门直接明白地从技术层面提到吴健雄未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主要原因外,第3处提到吴健雄,是在该章长篇幅(占5页)评述德国女科学家迈特纳不应被诺贝尔奖委员会“遗漏”这件事,同时提到了吴健雄与另两位女性科学家被“遗漏”所产生的影响。豪尔吉陶伊在评述迈特纳被“遗漏”时说:“她是一位女性,在诺贝尔奖历史上被遗漏的大部分是男性,这一点是事实,但是由于女性获奖者很少,就使得迈特纳、吴健雄、乔斯林·贝尔和伊莎贝拉·卡勒几个人没有获奖的事实更为突出。”([1],页317)“迈特纳的被不公正地遗漏这件事,不仅萦绕在科学史家、女权主义者,而且也索绕在相关的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成员的心头。”([1],页315)
豪尔吉陶伊对吴健雄等4位作出过重大科学贡献的女性科学家,虽然充满同情心,对她们被诺贝尔奖委员会“遗漏”也有不满,但他也仅是评述到此而已。他并没有用感情代替理性去进一步评述,也没有因为迈特纳、吴健雄等4人是女性科学家和有东方人在内,就断言诺贝尔奖委员会有“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等倾向。客观理性,严谨求实的态度,是科学家和科学史家必备的品格,也是科学社会学家和诺贝尔奖社会学家难能可贵的品格,值得从事这些方面研究的学者学习借鉴。
豪尔吉陶伊在他的书中结语“前言”中就指出过,诺贝尔奖“每年10月份公布获奖者名单以及每年12月颁奖的时候,全世界都会作报道,但是对于遴选的程序和颁奖所依据的准则,人们却了解得很少”([1],页11)。部分研究者在研究吴健雄等华人未能获奖的原因时是否也有这种缺失呢?是否也是他们研究结论出现某些据穷理乏的偏颇之词的原因之一呢?如果我们了解科学社会学中关于科学共同体承认科学发现优先权的准则,又了解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遴选程序和准则,了解颁奖必须遵守的《章程》的具体规定,再加上能与诺贝尔奖委员会评委作换位思考,把够不够资格获奖、应不应该授奖与能不能授奖当做不同的两件事区分明白,而不是只停留在单一的学术标准的思考论证上,可能我们的研究结论与判断就会更接近客观实际,更理性公正。
豪尔吉陶伊在书中对吴健雄被诺贝尔奖“遗漏”的原因说得具体明白,有根有据。他不但从学术标准考虑问题,充分肯定吴健雄在瓦解宇称守恒过程中的杰出科学贡献,认为她应该与李、杨一起分享诺贝尔奖,同时也注意到诺贝尔奖遴选的程序和准则,颁奖必须遵守的各项具体规定,特别是关于每项资金分享人数绝不超过3人的规定,认为像吴健雄这类科学家面临的情况是“有资格当选的候选人多于三个”,这是可以更好地解释像吴健雄这一类科学家本应获奖却终未得奖的原因的“一个好的理由”([1],页299)。由此可见,在研究类似吴健雄这一类科学家的诺贝尔奖问题时,除要考虑遴选的学术标准外,还要同时考虑其它非学术标准,或学术外的“社会标准”。即既要研究他们够不够水平获得诺贝尔奖,还要研究按颁奖《章程》规定,结合他们面临的实际情况,考虑诺贝尔奖委员会能不能授予他们诺贝尔奖。这应是豪尔吉陶伊看吴健雄的眼光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1]伊什特万·豪尔吉陶伊. 通往斯德哥尔摩之路——诺贝尔奖、科学和科学家[M]. 节艳丽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7.
[2]埃米里奥·赛格雷. 从X射线到夸克——近代物理学家和他们的发现[M]. 夏孝勇等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4.
[3]江才健. 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吴健雄[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4]杨振宁. 杨振宁文集[M]. 上海: 华东师范范大学出版社, 1998.
[5]季承. 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0.
[6]蔡华文等. 诺贝尔奖获金得者传(第4卷)[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7]哈里特·朱克曼. 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M]. 周叶谦, 冯世刚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8]蔡华文等. 诺贝尔奖获金得者传(第3卷)[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9]埃米里奥·赛格雷. 永远进取——埃米里奥·赛格雷自传[M]. 何立松, 王鸿生译. 上海: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9.
[10]杨建邺. 20世纪诺贝尔奖获奖者辞典[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1.
[11]潘国驹, 谈谈上帝粒子——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J]. 物理, 2013, (12): 887.
[12]曹庆宏. 粒子物理、加速器和“副产品”[N]. 科学时报, 2014-10-17: 14.
[13]肖太陶. 吴健雄——诺贝尔奖亏待了的华人科学家[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5, (3): 98—106.
Keywords: István Hargittai, Chien-Shiung Wu, Nobel Pr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