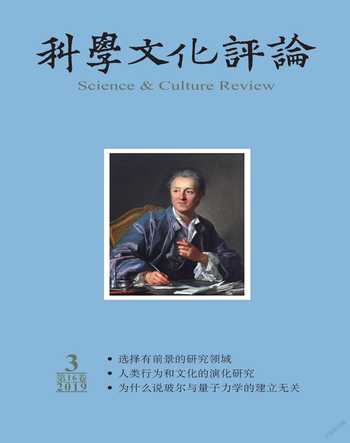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风雨岁月(1957—1985)

访谈整理者按 1952年組建北大数学力学系时的六人筹备组当中,林建祥是目前唯一健在的成员。林建祥,1928年9月13日出生,福建福州人,1946年毕业于福州英华中学,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林建祥从清华调入北大,在数学力学系工作了多年,曾任系党总支书记,承担了行政和党政工作,长期参与北大数学的建设。1984年,林建祥曾到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访学,回国后转入北大计算机研究所,2000年又随北大电教中心转入新成立的北大教育学院教育技术系工作。林建祥从他个人的视角讲述了北大数学力学系在1956年之后遇到的一系列波折,涉及计算机发展、“反右”及“文革”后出国访学等内容,并就其中一些历史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访谈时间:2017年9月27日—12月14日
访谈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林建祥教授家中
一 两位计算机专家
张勇(以下简称“张”):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以下简称数力系)在1956年之后,既为国家培养了急需的计算数学人才,还组织研发了多台计算机:北大一号、北京一号、北大二号(即红旗机)([1],页149)……提到红旗机,就不得不提张世龙①了,请您谈谈张世龙与计算机的事。
林建祥(以下简称“林”):这都跟张世龙有关啊!当然首先是把张世龙从教学研究科科长这个职位调到数力系,这个是经过副校长江隆基②批准的。一方面张世龙在校一级层面上表示自己愿意去搞计算机业务;另一方面我们也跟江隆基说,真正要搞计算机的话,需要张世龙。张世龙这个事是我亲自跑到江隆基家里和他当面谈的。我跟江隆基反复讲“张世龙跟数力系有长期的渊源,在建数力系的时候他就参加进来了,张世龙钻进去了,并且是有一定理解的,相信他到数力系肯定会搞成的”。江隆基的意思是说“实在没别人的话,就只能学校割爱牺牲了”。这话我还记得。北大要建立计算数学专业,一定要有计算机。这个事,程民德、段学复③也知道只能靠张世龙了。
调他来的前后,我记得已经有实验室房子了。然后就要买设备、调实验员嘛,很快就有了计算机整体的设计图,我记得当时慢慢安装了双稳态的触发器。张世龙做了一个很大的机柜,机柜的每个双稳态上面都有一个闪光灯。每个触发器有个标志,它的状态用闪光灯来表示。这个东西慢慢调出来能计算了,就是“北京一号”④。开始大概每秒100次,到大跃进时,张世龙也慢慢筹划了速度更快的机器。设计机器时,采用几地址,以及一批程序的命令构成指令集也有一个过程……这些东西,张世龙跟董铁宝①一起商量后,“北大二号”就慢慢成型了,当然“北大二号”这时还是纸面上的。1958年春天,在做“北大二号”的时候,中科院计算所已经成立了,并仿做苏联的БЭСМ计算机②。当时计算所的所长有一些问题,就把张世龙请来咨询。结果发现张世龙对整机非常懂,就请他重新按照他的理解去设计新机器。新机器跟БЭСМ计算机是不一样的,是脱离了北大的一个新机型。结果张世龙果然和其他人一起设计出来了,他实际上是代表北大,去参与了计算所接受的来自上面的任务。
张: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搞计算机也发动群众了吧?
林:1958年进入暑假,北大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上海参加复旦大学的群众运动。柯庆施就说可以大量发动群众来做尖端科学,他大概有一篇《乘风破浪》③的文章,这是柯庆施跟随毛主席的一个标志。学校派的人从复旦回来以后就在全校传达并动员。北大的“群众搞尖端”受到上海影响非常大,当然数力系的计算机在所有尖端当中最引人瞩目,因为计算机在大家的理解中是非常新的东西。大跃进中间盲目搞群众运动使得后来出现很多问题④,大家说怪罪柯庆施这篇文章。
北大去复旦参观学习“尖端”以后,“计算机大兵团作战”也开始了。那个暑假,数力系1958级有一批学生提前入学,我挂帅来帮助张世龙组织整个计算机的大队伍。做计算机的时候,需要做存储器,第一步就是烧制磁芯。当时组织队伍来检验磁芯合格不合格,如果不合格的话,计算机的存储是做不起来的。工作量很大,我们一天三班倒,用人海战术发动群众做计算机。1958级的学生后来还回忆了入学时我就去动员他们来参加计算机大战的事。
数力系在暑假做计算机的时候,我们就体会到群众运动是不够的。后来许多系继续按照发动群众这个思路搞“超声波”,等等,就有非常多的笑话了⑤。
张:北大的计算机领域,除了张世龙之外,另一个人就是董铁宝了。请谈谈您了解的董铁宝。
林:在搞计算机的过程中,张世龙和董铁宝之间有很多合作关系,我对计算数学、有限元的理解也是后面慢慢凑起来的。我和董铁宝之间也不好说有什么深交,但董铁宝非常信任我,很多事情都跟我商量,我还曾经借给董铁宝房子住。董铁宝的专长应该是叫断裂力学,它需要计算机的支持。董铁宝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当时那里是计算机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他在美国接触到伊利阿克(ILLIAC)机。董铁宝研究断裂力学的计算时,那时候在美国可能已经出现有限元计算方法的苗头了,他可能对有限元方法比较熟悉①。
后来冯康不是大力做有限元嘛。实际上,冯康做有限元时,身边有一个人叫做黄鸿慈,就是我们第一届计算数学的学生,毕业以后分到了计算所。到底有限元是冯康独立提出来的呢,还是黄鸿慈也起了很大作用呢?这还是一个未清楚、有争论的事②。冯康的有限元不能说完全是他自己提出来的,黄鸿慈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计算机更深的方面董铁宝就不一定做了,但搞计算数学的人还是应该提到他的。在北大,董铁宝应该说更多是和力学有关系。
“文革”中间我被关在另一个地方了,董铁宝出事的时候,我们跟他没接触。他的死我是事后才知道的,后来又通过一个力学专业的校友转述,我才大概知道前后经历。“文革”中间的情况非常复杂。董铁宝去美国留学之后回国,“文革”时被当作“特务”。我从侧面了解到“文革”中他出事了,这事的原因就跟董怀允③之死一样,都是一个谜。
二 风波不断
张:数力系的前5年是很顺利的,没有什么大的政治运动。但1957年6月8号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似乎是个转折点,由此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后来系里很多学生被打成右派,这事的起因?
林:先有“肃反”,再有“右派进攻”,再有“反右”。张景中的事也是点名的案件④。反右的时候,我是总支书记,所以学生工作我也要负责。张景中等被批判前,当时找他们谈话是我出的主意。丁石孙⑤也提了建议,后来我决定派他和江泽涵、段学复等系里主要几个教授去进行说服工作。这个事比较遗憾,不过“文革”后他发展得也很好,当了院士。
真正的问题所在是肃反。1955年暑假的肃反运动,上面布置了要发动群众。其它系都发动群众,全校都在做。因为这是牵扯到人家政治生命的啊,在这个环节上,我是支部书记,对数力系的教员没有发动,上面就说这是林建祥右倾。不是所有的党委成员都认为我右倾,我有印象的是党委里面负责这个事的副书记谢道渊,说我右倾。这个事说我右倾也不怪他,我没发动群众,不就右倾了嘛。为什么我不发动?虽然大批的人都有材料,但是当时检举材料相当多都是捕风捉影的,没有核实就发动群众,我认为是不妥的。我当时看了材料,1952级的学生里被检举的有很多,很多都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我们就不发动。比如我就保了一个1952级的学生,叫做叶江湖,他在上面是有典型材料的。我保这个人,过几年也成了问题,刘沙①就抓住了这个事情。当时党总支成立以后,专门派1954级的学生干部陈良琨去做专案,花了一、两年的时间。经过重新审查了叶江湖的专案之后,发现叶江湖确实没有问题,做了结论,我们没批判是对的。
张:1958年高校中发生了“教育革命”,“插红旗、拔白旗” 轰动一时[2],当时全国的焦点武汉大学数学系还来北大数力系传授经验。数力系也不例外,出现了一系列的乱象:学生把老师赶下台,低年级为高年级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3],页149)……您能回忆下当时的经过吗?
林:党委认为在肃反过程中间,数力系发动群众不够,所以要派一个人把我替掉,就是老干部刘沙。她是1957年冬天时来干党总支书记的,我就变成党总支副书记了②。我见到刘沙时并没有什么看法,我当时说我们还是应该虚心向老干部学习,意思是说年轻的党员提拔得太快。我做系秘书的时候才20多岁,太年轻了。最开始我们关系还是不错的,我很尊重她。我生活上有很多困难,比如刚结婚遇到了房子问题,每星期要在和平里和学校之间来回跑,这样就影响工作了。刘沙还是关心的,就想各种办法在北大给我安排房子。一开始我很感激刘沙。后来是因为1957——1959年之间,在很多问题上我和刘沙有了分歧,我跟她解释我们前几年是怎么做的。并且后来有一些东西,我不同意她了,我就跟刘沙反复解释为什么我不同意她。
當时刘沙支持韩启成在系里发动教育革命了,我当然是不赞成的,这也是我跟她的分歧所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在1957年就有苗头了,起初学生批判老师,稍晚一点在1959年时学生编书。
1957年底处理右派结束了,之后1958年上半年的“红专大辩论”也是教育革命的一部分,在北大是陆平①布置的。数力系很多非常好的学生都被批判了,有的学生虽然没有被划右派,但是只专不红也受批判。
红专大辩论的同时已经开始了“教学改革”。到了暑假,计算数学的学生是做计算机。因为“理论脱离实际”,数学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是去工厂联系实际。但结果是什么呢?大部分工厂都提不出有意义的数学问题,因为工厂刚刚开始,还没到这个水平。所以满腔热情去联系,一问人家需不需要数学啊,大部分都回答:我们现在不需要!后来把这一部分人也弄去搞计算机了。
1958年教育革命,刘沙是发动不起来的,听了陆平号召以后,韩启成把学生发动起来了。1958年暑假之后,陆平布置要建立共产主义新北大②,刘沙是要坚决执行陆平的意见。当时韩启成是根据她这个态度在学生中间发动群众,他理解的是学生可以批判老师了,共产主义的新北大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内容,他也不明确,那个时候他听从毛主席说的话。我们听了毛主席的话也不一定就跟了,我们认为应该要有科学的精神嘛,但韩启成可能就跟了。北大的学生运动也不一定是陆平自己指挥的,没想到他的口号一下被刘沙接了。刘沙支持,然后韩启成响应并把它具体化,学生就开始批判老师了。
武汉大学数学系来北大这个事③,我没有亲自见到,因为1958年整个暑假我在那里搞计算机啊。我是从报纸上知道了武大这个事④,齐民友⑤强调抽象理论是重要的。武大批判齐民友的时候,刘沙已经上台了,他们来的话,应该是先找刘沙。
张:1958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政策响遍全国。数力系的许多教员被下放到门头沟,您当时也被下放了吗?
林:丁石孙、萧树铁、吴光磊等都是第一批。因为我跟刘沙有矛盾,她就让我去下放。1958年底,我是第二批下放到门头沟的,但是在那劳动了一个月就回来了。党委调我回来时说还是去党校吧,下放要经过很重的劳动,容易把身体搞垮了;到党校不参加劳动也可以得到思想改造,所以我就去党校了。
一起上党校的是一批老干部,这些人在大跃进中被认为是比较“右”的。我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去上党校。党校当时的学习很时髦,先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开头,然后我们的各种“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党校的教员就根据暴露出来的问题,结合上面的精神来备课和讲课,这就更有针对性了。当时我们听的课确实是不错的,针对下面的问题来讲,这不是挺好嘛。
后来到了八届八中全会,开始有大批的材料,党校里的这些老干部都有资格看,让我们看完以后就放出来。意思是说这些问题以后一个一个都要解决,就是说先反左嘛,大家讨论以后发现了很多问题。我自认为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我当时的意思是说“这样来看,中央这一年的工作多少是有一点问题的。会出现那么多问题,是不是中央还是有一点失误?失误是不是不能完全要底下负责,中央还是要负责的”。我讲了这些话以后呢,人家把它记下来了。后来反过来要批判彭德怀了,整个形势翻过来了,那么所有这类讲话都成了问题了,讲出来问题就等于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然后一个老干部就跟我说“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不能随便说了,不是前面那个大鸣大放了”,所以我就不说了。
张:1959年下半年,庐山会议召开,彭德怀受到批判。之后形势变成反“右”,数力系出现了“党内专家”一案,据说您也被加了顶“漏网右派”的帽子①?
林:我在党校时就是系里的副书记。后来从党校回来,组织认为我在党校学习了,而系里需要副系主任,所以提拔了我。结果没想到我又拖了一个尾巴。在党校我们“大鸣大放”时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党校结束后竟然把我说的话传到北大党委里面了。后来我了解到那一批参加党校的人回到各个单位,有一些说过话和写的大字报比较多的人,大概都成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我也不可免掉,有一些比较谨慎的人就保下来了。
刘沙之所以批判我,就是抓住我的这个尾巴了。开始批判我的时候,我不做检讨,还是可以辩论的。结果批判了一个月批不下来,没有人来批我,党委也非常头疼,后来就升级到党内专家一案了,我的党总支副书记就没戏了。后来我把日记交出来就是更深一层了,当过几天的副系主任就被撤了,正式开除党籍是拖了一年多以后。
批判党内专家一案,全校先从法律系河北河南的代表团开始。北大副校长邹鲁风带头,这个事当然是比我这个事大得多了。他被批判了以后,理科这边就出了“以专家向党自傲”①的案子。应该是到了10月,跟文科那边相对,理科有3个人——文重、孙亦樑、我,被认为是党内专家,这也是陆平布置的嘛。后来在全校批判孙亦樑,我没有经过全校的阶段。系里开大会批判了两次,这之后让我反复去检查思想。我就在图书馆不断地写检查,写交代材料。日记本交上去以后,就又升级了嘛,后期就到工厂劳动了。完全怪罪于刘沙也不对,不是说老干部不好,而是说不同出身的人经历不一样,对党的认识也不一样。如果工作中我们碰到一起,她不能理解你,你也不能理解她,那么到一定时候就利用这个来整你了。
张:聊聊这个“上交日记”事件的经过。
林:反右时,我看了大量大字报,脑筋里有过各种想法。这是个人的思想,脑子里有想法就记录下来了,将来再验证它到底对不对,目的就是这样。
真正的原文是说什么呢?日记的原话有几段我可以说一下:“过去毛主席都是正确的,民主革命时代都是正确的。但是现在革命已经过去了,到了建设时期了,那么毛主席是不是完全正确,还要经过历史的检验……”我特别讲了,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提倡独立思考,意思是说这里面是有问题的。我把当时的心理活动写下来了,思想是什么情况,希望刘沙审查吧。
在写交代材料的时候,我去交了日记。当然不交上去的话,问题怎么会提到这么高呢,意思是说我怀疑毛主席了嘛。我认为日记没到这个程度啊,我是暴露思想,要正确来分析啊,审查也可以全面来看。没想到交上去之后,刘沙他们反而觉得问题这么严重,把它歪曲理解了。我在工厂劳动时,这个问题就挂在那。开除我的党籍是在1960年底,从交日记到被开除之间还隔了一年多。
张:您被开除党籍之后,还在从事什么工作吗?
林:之前首先是去系里的力学工厂劳动。陈耀松搞了一个力学工厂,我下放了就跟工厂里那些工人一起劳动。
数力系年底正式给我一个开除党籍的处分。当时我还在力学工厂劳动,李龙堂说我在数学分析上还是有基础的,让我回到教学岗位帮助邓东皋①做辅导。总之就是在工厂当着李龙堂的面签了字,就被开除党籍了。
邓东皋当时给1960年入学的那一班讲课。时间应该是1961年春天,我是下半学期参加进去,跟邓东皋做了一年半的习题课。1960年底,邓东皋被派去学辩证唯物主义,回来后他就准备自己来写一个有特色的教科书。那个教科书写了之后好像很快就出版了,当时我们就和他一起探讨习题课怎么做。在邓东皋那干了三个学期,就到了1962年夏天。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听到了整个1959年的案子都要重新甄别的消息。
三 平反之后再遇“文革”
张: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党内外针对反右倾中的冤假错案纷纷进行了甄别平反[4]。北大党委也采取了措施([5],页584—589),您的案子在北大得到平反了吗?
林:陈毅迅速从中央调一批干部,下到基层整社整五风。我爱人当时在河南,到下面一看真是非常严重,很多人都没饭吃②。下放的干部也是跟着一起饿肚子嘛,她就听到要平反了,让我慢慢等吧。
七千人大会时,我的案子在北大没有立刻平反,党内专家一案是北京非常大的案子,所以拖得比较晚。给我平反,实际是由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亲自批准的。之后党委的张学书亲自宣布给我平反,我就正式恢复党籍了,这是在1962年6月份。
正式平反之后,我提出我的身体不好,要恢复工作的话,无论如何需要休息一年。一年后陆平就找我谈了一次,正式代表党委向我道歉,表示批判我他是有责任的。我说我不一定做总支的工作了,他说无论如何要恢复副系主任。所以1963年我恢复工作后的职务是副系主任,抓的第一件工作是重新进行工资调整,我就变成讲师了。
张:1964年春节,毛泽东召开了教育座谈会,指示要把大学课程砍掉二分之一[6],数力系当时是什么情况?
林:后来还有了社教运动①。我记得陆平本身就不积极,也没有实际贯彻。他的意思是说,毛主席的话我们要想一想,也不一定马上就执行。那么既然不是严格执行呢,我们就可以有一定的空间了。陆平说的嘛,所以我们数力系其实也没有照做。当然教育部发文说大纲要重新修订,要把各个课的大纲压缩,这个是抓过的。修订的话,是砍一点还是真正砍那么多呢?没有那么认真,毛主席还说过考试“可以交头接耳”。陆平就说毛主席说话随便一点,说的任何话不一定都认真,这个话是有的。
陆平在这方面是不积极的,后来搞了社教运动来整陆平。当时整陆平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因为他是把1959年我们这些人的案子都平反了。聂元梓是哲学系的总支书记,对党内专家一案肯定有意见。聂元梓认为陆平重用了大量知识分子党员,而且出身都不好。
张:提到聂元梓,就不得不提聂元梓等人于1966年5月25日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当时数力系在“文革”初期的情况怎么样?
林:社教运动中间开了两次国际饭店的会议②,把牵扯到的重要干部都调去了。数力系中陆元灼③、我、李龙堂等也参加这个会。当时明确让我们一个一个表态,请大家说说自己在社教运动中间到底是什么态度。那一天,我对社教运动的态度是含含糊糊的。我在这个地方比较拖泥带水,没说清楚,他们对我不是太满意。
“文革”开始前,可能就是在四、五月份吧,要提另外一个事情。因为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长是清华原来的统战部部长,他对我很了解。所以他说北工大缺乏干部,如果我能够调到那去,对于北工大的數学系非常有好处。而且不仅是系一级,如果我去的话,看起来是做理学院的干部。北大党委同意了调走这件事,所以在5月25号大字报出来的那一天,我正好到北工大去报到。当时的校长请我吃饭的时候,有人进来汇报说北大已经贴大字报了。吃完饭校长说让我赶快回去看看跟我有没有关系,我马上回来就在当时的大饭厅前面看到了大字报。那么我就知道了聂元梓针对的就是国际饭店会议,这等于是为社教运动、为国际饭店会议翻案。后来就明确说不让我去北工大了,意思是说一定要我留在北大参加完全部运动。北工大也可能是认为北大党委要卸这个包袱,怕我在“文革”中间捅篓子,如果我到北工大了,就跟北大没有关系了嘛。当时在中国这个局面,绝对是跑不过去的。这说明在反对聂元梓这个事情上,一开始不是太明确。
看完大字报我就回昌平200号了,当时数力系中心是在昌平。关于“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是6月2号的《人民日报》贴出来的。《人民日报》是代表毛主席的声音嘛,肯定了5月25号的大字报是马列主义大字报。那天我们在昌平,听了以后大家当然是非常震惊的。因为5月25号晚上,周总理办公室紧急调集所有北大的党员开了一个干部会,表示5月25号的大字报是不对的。后来工作组就进学校了,因为广播和《人民日报》宣告党委已经不行了,很快陆平等人全部都被打倒了,我们也回校本部了。6月18号,学生已经非常自由乱来了,相当一批人都被拉出来了,那是非常系统的斗了。
“文革”中,在数力系批判我的名义就是认为1959年批判我是对的,让我承认了就完了。上面在数力系里拨了一批人要参加劳动改造,我也是这个队伍里的。所谓的劳改队,劳改内容也在变化:在校内劳动、去石家庄劳动、去香山劳动、到东郊劳动……在学校劳动,有时打扫厕所,有时去拔草。2年后,就被关到民主楼那边,这就是“牛棚”。丁石孙也在那,关了几个月。从牛棚出来以后,因为“一号命令”,所以我们就到鲤鱼洲去了。
张:1969年秋,正常的教学和科研都基本停止了。数力系的教员很多都被下放到了江西鲤鱼洲,谈谈前后的体会。
林:1969年底到了鲤鱼洲,住了一年九个月。1971年回到北京,回来后我在食堂里又劳动一年,在“文革”中间又教了6年书。数力系大部分去了鲤鱼洲,还有很少一部分留在北京,去鲤鱼洲的人跟留在北京的人还是不一样的。留在北京的应该说是比较正确的人,那么到了鲤鱼洲,说明我终归有一些“问题”嘛。在北京办学的同时,后来我们在鲤鱼洲也招生办学。慢慢就开始培养工农兵学员,有一部分工农兵学员是在鲤鱼洲,有一部分是在北京。北京方面,当时邓东皋是留下来的,他是给工农兵学员办学的负责人。
“文革”中我没有被开除党籍,内部多少次讨论要开除我,但都没有结果,都有反对意见。到底应该给我什么处分一直在拖,有很长时间我什么活动都没参加。
能不能把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合理地设计,使得效果更好?下放的人都是有一定“问题”的,上面就归结为我们不理解中国真正的国情、农民的贫困。我的意思是说,对于知识分子花这么大的代价与工农结合,得到这样一个锻炼,也不能说不好,但是中国整个一代人的命运就被改变了啊,代价太大了。
下放劳动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响,还要说另外一面。我在鲤鱼洲劳动时,经常挑着一百多斤在田埂里跑来跑去。锻炼了这么长时间,回来以后整个体质是变好了。“文革”刚刚开始时,因为手术开刀取脓包的原因,我身体实际上非常糟糕。以前年年冬天我都要感冒,后来我不感冒了。丁石孙先到门头沟,后到鲤鱼洲,他的身体也很壮了。应该说那几年的锻炼对丁石孙还是有好处的。有很多农民的情况,下去之前他是完全没想到的。在北京附近还有如此落后的村庄,他的自述里也承认了这一点。丁石孙后来去做民盟中央主席,跟这些经历也有点关系吧。后来在鲤鱼洲,我们吃得相当好,已经能够生产猪啊、牛啊……
四 恢复声誉、出国访学
张:“文革”结束,1977年打倒“四人帮”后,数学系成立了批判四人帮的领导小组来平反冤假错案。丁石孙和邓东皋是主力,在大是大非面前措施得力,您的案件的彻底解决对于数学系的影响深远①。当时您了解的情况和感受如何?
林:丁石孙已经说过一些这方面的事了,但我还需要再补充一些后续的情况。
“文革”后,丁石孙给我彻底平反了。反过来,如果当时不给我彻底平反的话,就等于把北大党委都抹黑了。在20世纪50年代,数力系的工作是学校里最突出的。结果我都被批判了,批判我就相当于批判校党委的政策。我被开除党籍的时候,党委一直在保我。因为刘沙是外面进来的,所以他们也没办法。
“文革”中间,当时中国数学会的会议停了十几年没开。后来把数学会组织起来,然后1978年在成都就开了“文革”后第一次中国数学会年会,我被选为数学会的副秘书长。齐民友是副理事长,因为他写的文章比较多,业务水平高。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从反右到“文革”之间的多年时间里,数学界有两个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武汉大学批判齐民友,现在给齐民友平反。如果他的主张不对的话,那么数学会整个就没有根据了嘛,我们都是支持抽象理论的;另一个就是我在北大被批判了,也算是数学界里非常荒谬的事情,也给我平反了。所以说丁石孙给我平反是得到了数学界普遍的称赞,影响不只是在北大。数学界基本都知道这个事,把这两件事情放到一起了。如果说不给我们平反的话,以后数学界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科学研究环境。平反是好事,但我对他们说,数学会副秘书长不要让我来做。因为过去的数学会我都没有认真参加过,一下子把我提到副秘书长的位置……他们说这是落实党的政策啊。因为不在我身上去落实的话,就不能体现党的政策,那么这样讲也对啊。
然后我再补充得确切一点。1960年的一次数学会年会在上海开,当时应该说“理论脱离实际”被重点批判了。但1960年我在北大已经被打倒了,所以我就没参加这个会,那可能是刘沙去参加的。当时在上海开的这次数学会会议上,真正谈到了当时数学的教学改革。当时陆定一提出来了数学该怎么教学改革,是不是“太强调理论了”这一类问题。那时北师大有个叫做丁尔升①的老师,他当时在那提了一个中学教改的新教材,而且是关肇直、江泽涵等人都赞成的。应该说那个教材的思路很高,而且做得也比较好。1960、1962年以后,教材在全国用了一段时间,反应都很好。可是在“文革”中间却又把丁尔升这个事情整个批了一遍,把1960年时用得效果比较好的教材也给批判了。所以后来拨乱反正的时候,除了齐民友和我的案子被平反,北师大也把丁尔升的教材这个案子给平反了。
所以在成都的数学会会议上,当时的秘书长是华罗庚的学生王寿仁,两个副秘书长,一个是我,一个是丁尔升②。这就是落实政策,那个会等于是给多年来被批判错了的人平反,相当于数学界十几年后的拨乱反正嘛。
张:1978年,教育部派遣首批访问学者赴美进修,数学系的姜伯驹和张恭庆得到了两个进修机会[7]。您在“文革”结束后,也曾出国访学。谈谈这段经历③。
林:改革开放早期,教育部与学校派一批年长成员,作为访问学者到国外学习。后来我有幸也有机会,但需要先把外语补习好。在补习外语期间,意外地遇到了在北大俄文楼讲课的西蒙①(Herbert Alexander Simon)教授。我感到他讲的内容非常新鲜,有巨大的吸引力。我就斗膽向张龙翔校长请求,就到西蒙教授所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去向他学习,幸运的是很快得到了学校的同意。
但是想到在“文革”期间,自己业务没有长进,如今有机会跟西蒙这样的大师,不知能否学到东西,我心中很纠结。第一次见到西蒙时,有一段谈话。我说:“多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我的数学与信息技术都没有学好,下决心在这里好好学习。”没想到西蒙教授却这样说:“你年纪已大,不需要与年轻人一样努力去写好论文。我们这里很开放,所有系的报告都可以自由听。我们每个系都很有特色,你走一走就知道了,这对于你很有好处。如果有问题或碰到障碍,可以告诉我,我去协调。”于是我每周一得到各系的报告题目,就自由选择去听。
1984年4月到1985年底,在匹兹堡一年九个月的经历中,我前后走了十几个系,思路大开。计算机系当时有四个方向:理论、软件工程、自然语言、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是个大中心,除了科学计算外,还负责教学与学校管理的有关服务工作。机器人研究所有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以及机器人方面的研究。心理系主要有符号加工系统,而当年又从加州找来辛顿(Geoffrey Hinton)这位专攻神经网络的大师,我就直接听他的神经网络课。工科、经济管理学院都有计算机实验室,而且使用远程交互的先进辅助技术。连艺术学院都充分利用了计算机。每个系确实有特色,更重要的是,每年还有综合多学科的研讨会。
我在回国前,曾给当时的校长丁石孙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我详述了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一年多的所见所闻,觉得很有价值,希望对他办新的北大,对学科建设能够赶上新的时代起一些作用。回国后也曾直接谈过,对于国外新进展的新看法,我们有些共识。但是由于当时实际情况困扰着他,恐怕没有时间系统思考。
张:现在您被大家所熟识,是因为您在教育技术方面的研究[8]。这个是从美国回来之后的事吧?
林:当时卡内基梅隆大学每年都有跨学科的研讨会,20年共20届。开放的心态与制度、学科整合中间互相促进是他们科研取得大量创新成果的原因,当时正值计算机大量用于教育。卡内基梅隆大学是当时教育技术研究的中心,各个学科都有令人注目的创新,而且教育技术方面每年有多次会议,给了我一个清楚的印象:计算机对于教育是十分有用的。
回国后,我立即参与组织北京CAI(Computer Aided Instruction,计算机辅助教学)学会、全球华人计算机学会,大力宣传把计算机用于教育领域。计算机的多个重要应用领域中就包含了认知与教育,当时我想到国内特别需要把计算机应用于教育,犹如在天上发现圣火,急于设法传到人间。从卡内基梅隆大学回来后,我离开了数学系,调到了计算机研究所。1991年,我63岁了,实际上没到退休年龄,因为那时候已经变成教授了,我可以到65岁退休。1991年我卸任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当时有几个选择,后来我明确就选择了继续搞教育技术。因为那时我已经是北京地区CAI学会的理事长,把整个北京、天津的学校都组织起来了,来推动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发展。当时北大有一个电教中心,我决定不当所长了以后,就到了电教中心。2000年到了教育学院,我才真正接触并全面了解教育技术。
致谢 作者与林建祥教授的访谈历时3个月,期间林建祥教授对内容做了多次核查,并同意公开发表。林建祥在与作者进行的10余次线下对谈以及多次线上讨论过程中,提供的相关史料有助于作者完成本文。林建祥教授的耐心配合、较为完整的记忆以及对于历史淡泊的心态给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作者从他身上看到了北大数学力学系老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纯粹。
参考文献
[1]徐祖哲. 溯源中国计算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2]罗平汉. 1958年的“教育革命”[J]. 党史文苑, 2014, (19): 27—34.
[3]王则柯. 五十年前读北大[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
[4]李先明, 董业勖. 1961—1962年党的甄别平反工作[J]. 党史文汇, 2009, (8): 54—57.
[5]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等. 北京大学纪事(上册)[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6]周全华.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D].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1997. 9—10.
[7]叶晓楠. 努力开创中国低维拓扑学研究——访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姜伯驹院士[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9-05-01: 06.
[8]林建祥. 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建设(高效)策略探讨研究[J]. 电化教育研究, 2014, (6): 4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