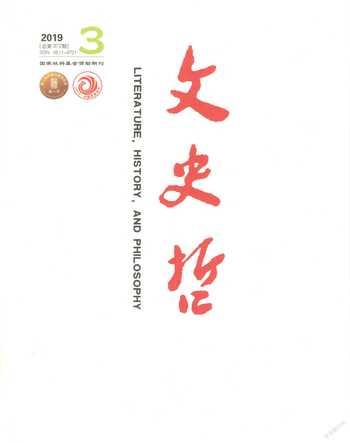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
摘 要:从晚清到民初,正是中国从传统帝国之宗主权向现代国家之主权、传统帝国之疆域向现代国家之领土转化的关键时期,所以,政学两界的舆论也从晚清的“寻求自强”转向民初的“保全国土”。“五四”之前中国边疆意识之觉醒,与日本政界的步步进逼难以分开;对四裔历史认识之资源,也和日本学界的满蒙回藏研究息息相关。中日关系的这种复杂纠葛,正是“五四”前夕“救亡”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以浮田和民《中国之将来》一文的发表为标志,“五四”之前日本有关中国保全和割裂的言论,对中国社会上下造成强烈刺激。以往学界用“启蒙”和“救亡”双重主题描述“五四”并无不妥,只是,“启蒙”和“救亡”的次序宜调整为“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过程,碰上了启蒙性的新文化思潮,二者结合促成了这场五四运动”。“救亡”始终是现代中国的中心话题和巨大力量,“启蒙”则是局限于精英世界的话题,远远没有成为民众世界的共识。因此,“启蒙”至今仍是国人未竟的使命。
关键词:五四运动;救亡;启蒙;主权;宗主权;领土;疆域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3.01
一、“保全”还是“割裂”:从浮田和民《中国之将来》说起
五四运动的前六年即1913年,袁世凯当政。这一年,《东方杂志》和《独立周报》两大刊物同时用几期的篇幅,连载分别由吴涛和逐微翻译的浮田和民著《中国之将来》。在《中国之将来》中,这个在近代中国影响很大的日本学者,对中华民国的未来充满怀疑,觉得袁世凯政府不仅不是共和制度,而且也没有“中等社会”的制约,所以,对这个独裁君主式的人物有没有能力统治好中国本部十八省,尚存有疑问,更不要说“保全十八省以外之属地”。
浮田和民认为,蒙古在俄国支持下已经宣告独立,西藏得到英国保护,并要求中国政府“永不得干涉其内政,(中国)徒拥宗主国之虚名而已”,而满洲更是全部成为“外部之势力,非复属于支那者矣”。他觉得,“改革支那之第一要义,当先削其领土,减少人口”。当然,汉族地区是例外,“欲分割其本部,断断乎有所不能”。在他看来,可以分别治理的,在十八省之外,也就是满蒙回藏区域①。
这个说法不是浮田和民一个人的私见,也不是民国之后日本人才有的新策,如果再参考差不多同时代的中岛端的《支那分割之运命·附驳议》(1912)②、酒卷贞一郎的《支那分割论》(1913)③、内藤湖南:《支那论》,东京:会文堂书店,1914年。,就明白这几乎已是日本政界和学界的共识。如果我们把时间再上推至晚清,就可以看到,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和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原本中国人心目中的蕞尔小邦居然打败堂堂的天朝上国,迫使大清朝签订城下之盟。这不仅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巨变的关键,也是世界各国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的起点。同样,更是日本上下重新思考日中关系,并且重新界定“中国”的开端。
1894年海战的失败与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比1840年鸦片战争的结果更让中国人感到难堪。因此我一直强调,中国思想世界的真正转变,也就是从“传统内变”不得不转向“传统外变”,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时代葛兆光:《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71-679页。,正如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页。。民初中国的普遍观念与民众情绪,始终在这一事件的延长线上。1895年后的几年里,在有关未来中国命运之大讨论中,最让中国知识人深受刺激、震动和难堪的文字,一篇是日本人尾崎行雄(1858-1954)的《支那处分案》,一篇是有贺长雄(1860-1921)的《支那保全策》[日]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载《清议报全编》第5辑“论中国”(横滨新民社辑印,第92页以下);《支那保全论》,飞天道人译(《亚东时报》第5期,1899年,第4-8页)。这两篇文章或类似内容的演讲,都曾被翻译和刊载多次,可见在中国关注者之多。如前者,还有演讲《支那灭亡论》(《清议报》第75-76册,1901年11月2日),以及单行本《并吞中国策》(王建善译,上海:开明书店,1903年)。其中,《支那灭亡论》卷首”译者按语”痛心疾首地指出,尾崎行雄是主张分割中国的人,但是他指出中国的病根,却“殊足发我国人之深省,语曰:知病是药,忧国者当可以察受病之根,而求下药之法”。。这两篇文章把日本对中国的两种策略,以及中国所面临严峻的生死存亡问题,坦率地摆放在所有中国知识人的面前。特别是1899年1月31日《亚东时报》第五号发表“飞天道人”翻译的有贺长雄《支那保全论》,这篇原刊于日本《外交时报》的文章,一开头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中国应当被“保全维持”,还是“不免割裂”《支那保全论》这篇文章,与东亚同文会以及近卫笃麿、大隈重信的亚洲主义观念一致,影响非常广泛,也被多次翻译和刊载。此后数年还刊载于《外交报》第29期(1902年11月14日)、《经世文潮》第4期(1903年8月8日)。有关“支那保全论”的历史背景,可以参看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三章《亚細亚主义的基本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97-100页)。有贺长雄参与中国政治极深,由于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之策略,1913年有贺长雄曾经担任袁世凯的顾问,并在“二十一条”交涉中,反复往来于中日之间,所以,他之于中国的观点在日本政界影响也极大。?
二、晚清到民国:“寻求自强”到“保全国土”
查看晚清民初的报刊,会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有贺长雄和尾崎行雄的这两篇文章,在此后若干年里不断地被中国知识人提起,可见它们给中国人心头留下的刻痕之深。
不过大体上看,晚清最后那十几年里,似乎“变法图存”也就是维护帝国之存在更为重要,国土被分割的危机感,或捍卫大一统的紧迫感,似乎还不那么紧迫,至少还是第二序而不是第一序的事情,因此,“寻求自强”优先于“保全国土”。不要说章太炎、刘师培、汪精卫等强烈主张汉族民族主义的所谓“革命派”,就是在主张维护大清帝国疆域,要求在帝国内部变革的所谓“保皇派”那里,某些边疆地区的主权和边缘族群的归属,似乎也还不是现在所谓的“核心利益”。1894年,忧心于国势的谭嗣同,就曾建议把新疆卖给俄罗斯,把西藏卖给英吉利,“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谭嗣同《上欧阳中鹘书》:“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以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费若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盖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万万方里,以至贱之价,每方里亦当卖银五两,是新疆已应得十万万,而吾情愿少得价者,以为十年保护之资也。”(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61-162页);1898年,就连捍卫大清帝国疆土最卖力的康有为,也觉得如果推行新政缺钱,不妨把西藏这种荒远之地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夏孙桐在《书孙文正公事》中记载,孙家鼐曾问康有为,“国家财力只有此数”,施行新政,面临高昂的费用怎么办?康有为回答说不用担心,“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如果“朝廷果肯弃此荒远地,可得善价供新政用”(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一,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影印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32年本,1973年,第120页);在康有为《日本变政考》中,他也以日本把库页岛(桦太岛)卖给俄国,和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为例,建议对于“其边远之荒地不毛,以虚名悬属,不关国本”的地方,可以出售以筹新政资金(《康有为全集》第四卷之《日本变政考》卷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4页)。。
可是在19世纪末,放弃朝鲜和割让台湾,对帝国毕竟是一个巨大而惨痛的刺激。1895年之后,如何维护帝国疆域和族群的完整,逐渐成了君臣上下不能不关注的问题在维护大清帝国疆域和族群问题上,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人可以作为代表,如杨度《金铁主义说》就说,“以今日中国国家论之,其土地乃合二十一行省、蒙古、回部、西藏而为其土地,其人民乃合满汉蒙回藏五族而为其人民,不仅于国内之事实为然,即国际之事实亦然”。并且特别强调,不能失去一部土地一种人民,“必使土地如故,人民如故,统治权如故”。见刘晴波主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2-304页。。无论是排满的革命派还是护清的保守派,都开始关注这一事关“国土”的问题,进入20世纪之后,“保全领土主义”已经成为话题[ZW(]参看杨度《游学译编·叙》(1902,《杨度集》第一册,82页)、胡汉民《排外与国际法》(《民报》第6号,1906年7月)、汪精卫《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民报》第6号,1906年7月)关于“领土保全主义”的讨论。。就连过去并无行使主权之意识的海洋权益,也在日本的刺激下成了动辄牵动帝国上下神经的事情。以南海为例,1909年,一艘中国渔船发现日本人西泽吉治在东沙岛挖鸟粪,消息传回国内,引致广东掀起一波抵制日货的运动。在民间抗议的压力下,大清政府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两广总督张人骏和日本驻广州总领事达成协议,日本承认中国对东沙的主权,西泽退出东沙岛,换得十三万银元补偿。同时,张人骏还派出船只,用了三个星期巡航西沙群岛,并且绘制了新地图。要知道,绘制地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标示主权,即这片海域的归属[英]比尔·海顿(Bill Hayton):《南海》(The South China Sea: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林添贵译,台北:麦田出版,2015年,第 91-92页。,而“主权”或“海权”,并不是传统帝国而已经是现代国家的观念。不过,由于那个时代的大清王朝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争取国家主权的这一努力,很快便化为泡影。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毕竟不同。辛亥革命并不止是一姓换了一姓,而是新桃换了旧符。无论你说辛亥革命是成功还是不成功,它毕竟是按照共和制度建立的现代国家即主权国家。所以,尽管孙中山原本也是汉族民族主义的提倡者,也曾为了争取日本支持,试图拿某些主权和利益作交换孙中山《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函》(1914年5月11日)提出,“今日日本宜助支那革新,以救东亚危局,而支那之报酬,则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转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第34页(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三编据“大公报出版部”1933年本影印)。,但根本上,他仍然不仅有大中国一统之思,也有大中国的主权意识。早在1901年,他就曾针对有贺长雄《支那保全论》和尾崎行雄《支那分割论》提出,中国“从国势讲没有保全的理由,从民情上讲没有分割的必要”孙文《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原载日本东邦协会编《东邦协会会报》(1901);又署名“逸仙”,发表于1903年日本东京出版的《江苏》第6期。。前一句说的是当时的大清帝国应当被推翻,后一句说的是传统中国民众在感情上仍倾向于大一统国家。
更何况,中华民国肇建以来,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守派,都背负不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罪名,只能同意“五族共和”,希望新的中华民国维持大清帝国的疆域和族群内藤湖南《支那论》曾指出,中国现在提倡“五族共和”,只是维持过去领土的一个保守主张,并非中华民族图发展的积极理念。。
三、民国之初:从宗主权到主权,从疆域到领土涉及传统帝国之范围,为什么要用“疆域”一词,而涉及现代国家之范围,则用“领土”一词来表达,葛剑雄《历史上的中国:中国疆域的变迁》(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序言”讲得很清楚,可供参考。
因此,过去革命派那种偏激的汉族民族主义,似乎在辛亥革命之后渐渐退潮,就连当年激烈倡言“排满”、要建立汉族中国的章太炎,也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改了口径说,“南方大定以来,鄙人即主张保全领土”从辛亥革命之后,这种思潮很快就被接受,如原来主张“排满”的邓实等办《民国报》,就宣布要“以汉族为主体,同化满蒙回藏,合五大民族而为一大国民”;民国成立之后的1912年3月,黄兴等人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同年5月,袁世凯在北京也授意成立“五族国民合进会”,以汉人姚锡光为会长,而以满蒙回藏汉各一人为副会长。参章太炎:《在长春各界欢迎会上演说》(1913年2月22日),见《章太炎全集》第一四卷《演讲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3页。。甚至为了一统,他建议在西藏建铁路干线,“移民实边”;在新疆设总督管理,以维持统一局面;担忧东三省的土著“对中国之感情不如对于外国之深”,所以,建立了所谓“统一党”分别参见章太炎:《在统一党南通县分部成立大会上之演说》(1912年4月8日)、《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改党大会上之演说》(1912年3月2日)、《在统一党欢送会上之答辞》(1912年12月23日),见《章太炎全集》“讲演集”上,第165-170、182页。。而作为统一新中国的理想,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也接受“五族共和”的政治理念,宣布“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JP2]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原载《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1912年),收入《孙中山文集》,北京:团结出版社,2016年。。在25天后拟议的《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中,不仅有“大中华领土无论现在及将来,在区域中者,受同一政府之统治”的表述,而且特别说明“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临时约法》第一章,见《申报》1912年2月1-2日,第3版。杨天宏在《清帝逊位与“五族共和”》(《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一文中,特别指出《临时约法》的重要性,批评近年来片面强调《清帝逊位诏书》重要性的做法,指出“将《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视为中华帝国没有像其他帝国那样四分五裂的原因,甚至将其拔高到與奠定了民国政制及法理基础的《临时约法》姊妹篇的地位,有违历史,非伦非类,难以服人”。。显然,在共和制国家刚刚建立时,就像晚清帝国割让台湾那样把领土割出去,被列强特别是日本撕裂,这是数亿国民尤其是知识人绝不可能接受的。当时,参与起草和讨论《临时约法》的一些代表就指出,这既是为了保全领土完整,避免国际承认的麻烦,也是为了防止蒙藏等处的“反侧之形”和外国的“明攫暗取”夏明华等编:《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0-202页。。而此后,尽管袁世凯当政,他也只能反复声明蒙古、西藏、回部“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蒙人、藏人、回人“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1914年5月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更明确用“帝国疆域”和“民国领土”两个不同的概念,宣布“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陈荷夫:《中国宪法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404页;方素梅:《民国初年的制宪活动与民族事务》,《民族研究》2011年第5期。。
必须注意到从“疆域”到“领土”这一转变,意味着作为现代国家,中国的“主权”问题开始凸显:帝国时代含糊的“宗主权”逐渐转为明确的“主权”,笼统的“疆域”(或传统所谓“藩属”“羁縻”“土司”之地)逐渐被确认为有边界的“领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根据现代国际准则和国家观念,明确区分“内”(领土)、“外”(藩属)的意识,也与近代中国与日本的外交往来有关,并在新的形势下被迫逐渐明确,日本学者冈本隆司曾引用1876年江华岛事件后,日本公使森有礼和李鸿章在天津有关“邦土”的对谈。李鸿章就解释“清日修好条约”中的“所属邦土”一词,指出凡是交纳赋税、受政治管辖的中国各省,就叫做“土”,而不交赋税、不受政治管辖的周边各国,就叫作“邦”。这一点参看冈本隆司:《中国における“领土”概念の形成》,载冈本隆司编:《宗主权の世界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4,第292-321页,特别是第299页;又,他的另一篇论文《“主权”の生成と“宗主权”—20世纪初頭の中国とチベツト·モングル》一文,对主权与宗主权的区分也有所论述,可以参考。见《近代东アジアにおける翻译概念の展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现代中国研究センタ-研究报告,2013)。。民国政府建立之后,不仅陆续颁布有关西藏、蒙古的法规,设立专门机构加强蒙藏地区的管理,更以现代国际通行的法律形式,确认领土主权[JP3]冯建勇:《重构国家认同:民初中央政府对蒙藏边疆地区之统合——以1911-1915年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4期。。以前面提到的海洋主权为例,民国肇建,“海权”就被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1912年,海军、外交、农林三部就讨论过领海界线。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民国政府就拟议设置海界,并由统帅部牵头,预备发布“公海与领海之界址”“五四”之后的1921年到1922年,更在海军推动下,设立了一个专门讨论海权问题的“海界委员会”。主席倪文德指出,“海界关系军务、税务、渔业”这三方面的国家权利。他们一方面按照“主权在我”的原则,一方面尊重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对公海、领海、内海、海岛等等问题,参酌英、美、法、日等国的情况,反复讨论,制定了一系列的划分领海的方法,遵循国际惯例议定中国领海范围为三英里约十华里。在1922年,成立了海道测量局,开始进行划界工作。参见陆烨:《海界委员会与民初海权意识》,《史林》2014年第6期;刘利民:《民国北京政府海界划分问题考察》,《安徽史学》2018年第5期。。
当然,对于中华民国来说,更重要的仍是作为陆地边疆的满蒙回藏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卷(1912-1916)上册第3章《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和善后大借款》,详细论述了民国建立之初中俄有关外蒙古问题以及中英有关西藏问题的交涉过程,可供参考。。此时的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于满蒙回藏虎视眈眈,始终不视之为中华民国之疆土。民国之初日本即试图“伸张南满以至所谓东部内蒙古之势力”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17页。,两年后又借世界大战的机会,甚至企图占有原来被德国控制的山东半岛。同时,在这几年里,前面提及的中岛端《支那分割之运命附驳议》、小寺谦吉《并吞中国论》、川岛浪速《并吞中国书》等表达日本并吞或分割中国之野心的文章,陆续在中国被翻译出来,更加警醒了中国知识人。“五四”之前的那几年,在中国的报刊上,反复出现这些惊心扎眼的消息,更刺激着中国知识人的神经,如“日人之蒙古视察”(1913)、“日人热心研究满蒙”(1913)、“日人之我国经营蒙古观”(1915)、“日本拟设置满蒙领事馆”(1916)、“日人谋我满蒙之感言”(1916)、“日本拓殖满蒙之新计划”(1916)。
“五四”虽然发生在1919年,对国族存亡和疆域得失的焦虑,却在此前几年就逐渐酝酿成熟。特别是,皇权笼罩下的大清帝国于1911年终结之后,在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之下,不仅更多的国民对公共事务有了相对丰富的了解渠道和参与热情,而且迅速增多的报章杂志与新式学校,更提供了资讯传播平台[ZW(]有关那个时代各种新闻媒体、印刷出版、新式学校对思想转变的作用,参看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载氏著《时代的探索》,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这使得来自日本的种种刺激,成为传染感情和形成运动的动员力量,这正是“五四”能够成为运动的缘由之一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的《导言》中,虽然也指出五四运动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但由于他把五四运动界定在1917年到1921年这段时间,对“五四”之前这些历史背景,叙述得就较为不足。。
四、东邻的刺激:日本舆论与中国反应
问题是,如何维持“五族共和”?如何捍卫领土主权?当时,很多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人却没有想清楚。从1913年之后,南北和议、袁氏窃国、青岛事件、二十一条,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才提醒人们高度注意,也恰恰是日本对于满蒙回藏鲜的觊觎,刺激了人们对这个既是政治问题又是学术问题的日益关注:“中国”究竟应当有多大的疆域,“中华民族”究竟应当包括多少族群?
日本的舆论倾向几乎一边倒[日]犬养毅:《支那の将来》,转引自杨栋梁主编,王美平、宋志勇著:《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4卷(1895-1945),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4-186页。。以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的若干著名日本学者为例,我们不妨对当时日本的舆论倾向,作一个大略估计。从这些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在日本主流政治和思想界來看,他们普遍认定,虽然中国需要保全,但这个“中国”只意味着是“本部”,而中国本部就是在长城以南,满蒙回藏都不在其中。前面提到过内藤湖南1914年发表的《支那论》,而与内藤湖南并称明治、大正年间日本“东洋学”两大领袖之一的白鸟库吉,比内藤湖南更早,在1912年和1913年就在影响很大的杂志《中央公论》和《东洋时报》上预言,辛亥革命后,来自外国的压迫会更多,将来蒙古、西藏、满洲也许都会被取走,而中国能够守住的最多是十八行省。他认为,如果中国守住十八省,那么,满洲就是俄国、中国和日本,甚至是俄国、英法美德和日本三方相互较量的地方[日]白鸟库吉:《满洲问题と支那の未来》,原载《中央公论》(明治四十五年六月)第26卷第六号;《支那の国体と中华民国の现状》,原载《东洋时报》(大正二年八月)第一七九号。二文均收入《白鸟库吉全集》第10卷,东京:岩波书店,1971年,第146-158页,161-178页。。
有关民国初年(1912-1919年)日本政界与学界对中国的观察、想象和图谋,中国学界近年来已经有较详细的研究,有的学者把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观”称之为“中国亡国论”杨栋梁主编,王美平、宋志勇著:《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4卷(1895-1945),特别参见第5章《中国亡国论的应验——分裂满蒙》。。[JP2]近年,日本学者藤田昌志也在《明治、大正の日本论·中国论》中指出,从明治时代的胜海舟、福泽谕吉、中江兆民,到大正时代的吉野作造、内藤湖南、北一辉等,虽然立场各异,但有关中国领土的看法却大同小异,与一开头我们引用的浮田和民相似,说明这恰恰是日本上下的共识[日]藤田昌志:《明治大正の日本论·中国论》,东京:勉诚出版社,2016年。。他们普遍认为,处于弱势的中国,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的政府,保全十八省就算不错,至于那些满蒙回藏之地,中华民国最好不要多管。
毫无疑问,这与日本帝国的扩张野心相关。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也就是中国的晚清时代起,日本就对满蒙怀有领土要求,这一点,我们从明治年间突然风起云涌的满蒙研究就可以看出。1908年,白鸟库吉在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支持下,建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陆续出版《满洲历史地理》(1913)、《朝鲜历史地理》(1913),建立“白山黑水文库”,在1915年更出版《满蒙研究汇报》,大大推动了日本上下对朝鲜、满洲、蒙古的历史研究与现实关切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44-245頁。。这一动向引起中国的极大警觉,正如1914年一个名为“静观”的中国人在《雅言》杂志上所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囊括南满,俨若己有,及近年以来,见俄人在外蒙之活动,日益生心于内蒙古。(日本)朝野上下,一德一心,有并吞满蒙之意”静观:《满蒙处分论之谬误》,《雅言》第1卷第7期,第27页。。
“朝野上下”和“一德一心”观察得都很对。的确,这不仅是日本学界的倾向,也是日本政界的倾向。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日本陆相即著名的山县有朋就在《对清政略概要》中提出,“日本必须在此适当时机出兵满洲”。这一时期,日本也在满蒙地区积极扶持宗社党肃亲王耆善和一些蒙古王公,推动“满蒙独立运动”郭宁:《寻求主导:日本与承认中华民国问题(1912-1913)》,《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3期。。所以,1915年2月2日中日双方讨论“二十一条”时,日方大使日置益也承认,“本国一般之议论,有主张吞并满洲者,有主张分割中国者,此等议论,在贵国人民闻之必多不快,然本国人民确有为此等主张者。是虽欲亲善,而仍不免生出误会”。日置益同时也承认,“自两国报纸上观之,舆论之感情极为相反”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107-108、109页。。
然而,日本这类“极为相反”的看法,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报刊上发表,就提醒了中国国民,也刺痛了中国知识人。就像前引静观《满蒙处分论之谬误》所说,“若日本苟并吞满蒙,实无异为引起中国瓜分之导火线”静观:《满蒙处分论之谬误》,《雅言》第1卷第7期,第28页。。由于日本对南满洲和东蒙古地区的利益欲求几乎是直言不讳,而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无理要求,更是激怒了中国民众,所以,尽管青年毛泽东也曾倡言中国要分成二十七块,在和友人通信中却说,中国“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指日本),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然入中原”刘晓原曾指出,早期毛泽东在为《大公报》撰写的文章中,也曾表达过中国分裂论,觉得中国“索性不谋总建设”,而“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最好分为二十七国”,但很快放弃了这种极端的说法。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卷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4页。另参看刘晓原:《边缘地带的革命:中共民族政策的缘起(1921-1945)》,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5页,第26页。。
这段话大概很反应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心病。心病来自日本的虎视眈眈,但有意思的是,医治心病的某些药方,却也和日本的启迪相关。
五、政治与学术:谁来证成现代中国合法的疆域与族群?
前面说到,在重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过程中,有关“满蒙回藏苗”等民族和边疆问题逐渐凸显。如何从历史中说明这些族群和疆域的来龙去脉,在法律上论证这个包拢四裔的“大一统”中国在现代的合法性,在政治上使这些不同族群认同新的共和制国家?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并没有准备好。有关边缘区域和族群的很多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学界却还得依赖和中国立场相左的日本,不得不说是一个绝大的笑话。
所谓“五族共和”的中国,究竟算不算所谓的“民族国家”,也就是当时国际流行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中国仅仅等于“中国本部”,中华民族仅仅等于“汉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则满蒙回藏等族群和疆土将有分离出去的理由。所以,在民国肇建的那几年里,吴贯因、李大钊、孙中山都建议,不分满蒙回藏汉,“凡是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可问题的另一面是,大清帝国两三百年间的扩张,已经成了一个庞大帝国,理藩院、盛京将军和六部分别管辖的区域与族群,又实在太复杂,只要看看乾隆盛世所绘《皇清职贡图》,就明白帝国之内的区域与族群差异性有多大。中华民国推翻大清帝国,把亚洲最古老的帝制中国改造成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可是,如果原封不动地继承原有疆域和族群,则必须从“传统帝国”到“现代国家”、从“臣民”到“国民”,——从“差异性统治”到“同一性管理”,不能不有一个根本转化。
然而,说起来容易,族群差异和文化认同毕竟有所不同,民族并不是说同化就同化的。那么,回到帝制时代那种分别治理之策吗?恐怕也行不通。在1919年“五四”之前的那些年,日本人对袁世凯的“国体变更”十分关注,他们觉得中国真怪,“四年以来,既定国体为共和,今乃复昌言帝制”;他们看到袁世凯“多授予满蒙王公以勋章,又渐唱五等封爵之制”,可那不是现代国家而是传统帝国东京·飘萍:《日人所谓变更国体之里面》,《申报》1915年9月7日,第3版。。国内也有人对“五族共和”这个说法提出异议,说为什么新的共和国,一定要把众多族群合为一体?但也有人提出了另一问题,为什么中华民族是五族而不是六族?1917年,申悦庐《中华民族特性论》就说“五族共和”不正确,“盖就中华民族而言,实有汉满蒙回藏苗六族”申悦庐:《中华民族特性论》,原载《宗圣学报》第2卷第8期(1917年12月)。申氏这篇文章,在1943年重新发表在《东方杂志》第39卷第19期。。同一年,夏德渥撰写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也建议,在汉、藏、蒙、满、回之外,加上“苗”,统称为“华族”夏德渥:《中华六族同胞考说》,湖北第一监狱石印本,1915年检定,1917年印行。参看吉开将人:《苗族史の近代(三)》,《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纪要》第129卷(2009年11月),第32-33页;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8-119页。。
可是,民国之初的政治家和学问家们大都是汉族,而平常的关注也只在核心区域,他们对满蒙回藏苗真的有所认识吗?他们真的了解这些过去被视为“蛮夷”的族群吗?这些中国之边缘的族群究竟能不能认同中华民国并使它维持一统呢?这些问题是政治的,也是学术的。要知道,学术取向总是和政治状况相关。陈寅恪曾说,“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取向之细微”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陈寅恪文集·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63页。。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学术之转移,也常常来自世局之变迁。原本,对于满蒙回藏苗的研究,汉族为主的传统中国学者并不甚措意,当时有关边疆或民族领域学术研究,也多从日本转手引进。尽管嘉(庆)道(光)以来,也有所谓“西北史地之学”和“蒙元史重编”等新学术取向,但坦率地说,之于边疆民族问题的关注,不仅是被日本野心刺激出来的,对边疆民族的知识,也往往是从日本转手引进的。
谭汝谦曾经统计过中国翻译日本著作的数量金耀基《中日之间社会科学的翻译(代序)》指出,1895年以前,中国只译过一册日本社会科学方面的书,但1895年甲午战争后,到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译日本书“高达中国所译外国书籍的总数百分之六十,俨然凌驾翻译欧西著作之上,显然出现了日本文化入超的现象”。见[日]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31页。,指出晚清到民国之间,新知识和新思想往往转手自日本,所以,我才说那个时代“西潮却自东瀛来”葛兆光:《西潮却自东瀛来》,《西潮又東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7-66页。。[JP2]如果回到那个时代作一番统计,就可以看到,1919年前中国学界可以参考之有关满蒙回藏苗的著作,竟然大都来自日本学界或转手自日本学界。1910年1月7日,《申报》发表一篇“时评”,题目是《日本人而竟研究中国乎》,其实日本人热心研究中国,国人早就知道,但用了这个题目,还加上“而竟”二字,不免故作惊讶。这篇文章对学者服部宇之吉和外务省官员阿部守太郎建立支那研究会,“一时海陆军人、新闻记者、学者、实业家等从风响应”,表示非常“不可解”,并说:“中国者,吾人之中国也,乃中国人不自研究,而必待日本人集会研究,抑独何也。”见《申报》1910年1月7日第一张第5版“时评”。
可这就是现实。特别是,在满蒙苗藏回等边缘区域和非汉族群的研究领域,中国学界反而只能借助日本人的研究有关西藏,光绪三十三年(1907)有西藏调查会翻译日本西藏研究会编《西藏》(成都:西藏调查会,1907年),有1908年四川杂志社翻译日本山县初男《西藏通览》(四川杂志社;此书又有1909年成都西藏研究会译本,有1913年北京陆军部重译本);关于满洲,有1906年富士英翻译冈田雄一郎《满洲调查记》。。我也注意到,那个时代中国有关“四裔”的研究,往往需要参考日本的成果。日本学界的研究,不仅涉及地域和族群相当广泛,而且深入和细致程度,也比中国先行一步甚至几步。诚如陈守实所说,在中日、日俄两次战役之后,日本的研究视野,“自台湾、福建、朝鲜、东三省、内外蒙古,西至新疆”陈守实:《东西洋汉学家考证中国边疆史地的态度问题》,《襄勤大学师范学院季刊》1934年第1期。。以东北地区为例,不仅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军方就编撰了《满洲地志》(1889),一些日本军人也出版有《满洲纪行》(岛弘毅,1879;菊池节藏,1886)关于这一方面,也可参考张明杰:《近代日本人涉华边疆调查及其文献》,《国际汉学》2016年第1期。。至于后来被翻译成中文、有关满蒙回藏的著作中影响较大的,如考察苗疆有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1903),研究西藏有河口慧海的《西藏三年》(1909),讨论满洲有鸟居龙藏的《满洲人种考》(1910),研究蒙古有河野原三的《蒙古史》(1911)[日]河野原三:《蒙古史》两卷本,欧阳瑞骅译,上海:上海江南图书馆,1911年。;此外,还有令中国学界相当反感的矢野仁一的《蒙古问题》(1916)等等仅仅以《东方杂志》为例,第九卷九号(1913年)有翻译自日人的《蒙古风俗谈》《云南土司一览》;第十卷七号(1914年1月)有章锡琛翻译的《中俄对蒙古之成败》;第十卷十二号(1914年6月),有许家庆翻译井上禧之助的《满洲之石炭》;第十三卷三号(1916年3月)有病骥译《日僧入藏取经记》(即河口慧海之事);第十四卷七号(1917年7月)有君实翻译日人的《中国之喇嘛教与回回教》和《西藏语之特征》。。
这些著作在“五四”前夕,陆续传入中国或翻译成中文,日本学界对四裔的研究,深刻地刺激了中国学界。顺便可以一提的是,1917年,《新青年》第3卷第3号特别发表了以治中国四裔之学见长的桑原骘藏《中国学研究者的任务》,这篇文章曾给正在回国途中的胡适以很大的启迪[日]桑原骘藏:《中国学研究者的任务》,J.H.C生译,《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胡适阅读之后的反应,见《胡适日记全编》第2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14页。。
小结:五四运动大背景的再认识
虽然,如今都把“五四”叫做“新文化运动”,也更重视“五四”对“文化和思想启蒙”的意义,但1919年“五四”运动的直接刺激和现实缘起,毕竟还是针对国土分裂,尤其是“二十一条”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中,虽然也说到“五四”之缘起,一方面是有“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激起的爱国热情,一方面是试图从科学和民主重估中国传统以建设一个新中国。但是,他整部书的重心,还是在强调后一方面即启蒙的意义。对于前一方面的来龙去脉,论说得不太充分。其实,关于“主权”的焦虑和危机,才是五四运动的重大背景。举一个例子,“五四”时期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强调的就是“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应当说,它更是国族危亡刺激下的救亡运动,而日本因素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只是后来有关“五四”的各种研究著作中,讨论“启蒙”意义的多,而讨论“救亡”影响的少;讲它激起新文化新思想的多,讲它刺激国家与族群意识的少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周策纵先生的名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这里顺便要说,我仍然觉得,把“救亡”和“启蒙”看成是近代中国史的两大主线,这一判断虽然简单却没有大错。现在回头来看,广义的五四运动就是“救亡”和“启蒙”两大主题的交织。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早就说过,“五四”是“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现代中国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笔者同意这个说法,只是有两点补充。第一,有必要把这一叙述的次序,稍稍修改一下。由于“五四”之前精英阶层和民众世界的情绪,更多来自国土分裂的危机感,因而这段表述不妨改成:“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开展过程中,碰上了启蒙性的新文化思潮,二者很快结合在一起,共同促成了那场‘五四运动’。”第二,过去很多人认为,20世纪上半叶,在“救亡”和“启蒙”两大主题之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笔者却觉得“启蒙”似乎从来没有压倒过“救亡”,因为“救亡”始终是现代中国的中心话题和巨大力量,而“启蒙”却是精英世界的话题,远远没有成为民众世界的共识。因此,“启蒙”至今仍是一个未竟的事业。
[责任编辑 刘京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