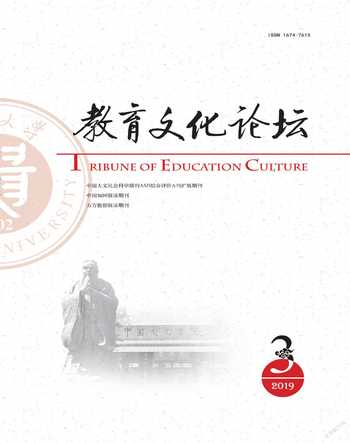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实施的特点及启示
曲铁华 刘盈楠
摘 要:民国时期,中国特殊教育开始进入由外国人创办向国人自办的转折。在特殊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特殊教育立法逐步完善,政府逐渐成为设办公立特殊学校的主体,创设了具有特殊教育特色的课程体系。同时,在推进特殊教育实施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政府重视力度不够、社会关注度不高以及师资体系不完善等问题。这给予当今我国发展特殊教育以重要启示: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特殊教育观;从法制和财政两方面提升政府对特殊教育的扶持力度;构建科学合理的特殊教育课程体系,以及建设科学化、专业化的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体系。
关键词:民国时期;特殊教育;特殊教育实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9)03-0001-12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9.03.001
Abstract: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special education began to enter into a transition from the establishment by foreigners to the self-management by the Chinese people. And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special education, it presented the following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1) The legislation on special education was gradually improved; 2) The government had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body of setting up special schools; 3) A curriculum system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set up.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it also exposed such problems as the government’s lack of focus, low social attention and imperfect system for teach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ll this give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in China, i.e., changing the concept and setting up the correct special education view, enhancing the government’s support for special education from the legal and financial aspects, constructing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curriculum system for special education and building a scientific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system for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Key words: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pecial education; implementat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近代中国,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传入,特殊教育思想也逐步深入到中国内部,以朝臣、文人等为代表的部分国民,由此接触到有关特殊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并且通过纲领文献和书籍,阐述关于特殊教育的观点和设想。虽然这些论述并非精深的集中论述,但也是有关在中国本土实施特殊教育的理想抱负,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启发民国时期民众关切特殊教育的作用。
除此之外,我国已在19世纪70年代拥有了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第一所近代特殊教育机构北京“瞽叟通文馆”及第一所聋哑学校山东登州(今蓬莱)“启喑学馆”。以这两所学馆为代表的一小批特殊教育机构随后相继设办,中国的特殊教育事业改变了之前中国“盲哑之儿童,贫则乞食,富则逸居”[1]的局面,并在外国传教士的努力下,正规的兼具“养”与“教”的特殊教育形式在中国开始出现。但统观近代到民国初期,我国特殊教育几乎由外国传教士垄断,特殊教育的教育权依旧未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国民也尚未采取真正自发的、主体性的措施来推动特殊教育的进程。民国时期,伴随着平等观念的明晰、教育观念的革新、国民民族意识的不断高涨,中国特殊教育终于开始进入由外国人创办向国人自办的转折。
一、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实施的特点
(一)特殊教育立法逐步完善
特殊教育的立法,广义上指的是各级权力机关依照特定职权和程序制定各种特殊教育法律文件的专门活动,狭义上指的是国家专门立法机关或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指定的特殊教育法的专门活动。在近代中国,针对特殊教育的立法,基本上没有专门的立法机关。因此,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广义上的特殊教育立法,即各级权力机关的立法活动。
近代中国,在外国资本、政治、文化的大舉渗入之下,中国社会开始发生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国人的思想意识不断革新,尤其是西方有关特殊教育理念与设施的传入,更使国民人权意识迅速高涨,对于残疾人特殊教育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终于开始了有关残疾人教育权的立法进程。
民国政府成立后,为了能够符合国民对于“公正”“平等”等理念的追求,特殊教育作为教育领域内长期被忽视的一隅被提上日程,首次载入了国家法令。1912年,由临时政府成立的中央教育部重新制定的《学制系统案》中的《小学校令》,最早对特殊学校做出了法律性规定,提出“由城镇乡立初等小学校或高等小学校;由县担任经费者名某县立高等小学校;由私人或私法人担任经费者,名私立初等小学校或高等小学校”[2]51等规定,对盲哑学校的办学主体、经费管理等方面,做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自此,政府开始正式介入特殊教育的管理及相关法案的制定,盲聋哑学校在中国学制中开始有了正式地位,中国的特殊教育开始步入法治化的轨道[3]261。
但是,《小学校令》做出的规定,多是针对当时尚未成型的国人自办特殊教育事业的,对于当时在特殊教育体系中占据主体的教会特殊教育学校,并没有实质性的规定与管理;且由于当时盲哑学校基本由教会设办,部分规定如“初等小学校由城镇乡设立之”[2]51也就失去了实际的教育对象,缺乏实践的可能性。《小学校令》作为较早的有关特殊教育的法令,可以说是最初的不完整的雏形与构想,可借鉴性很少,也不够系统。
民国初期,民国政府尽管已经幵始意识到应该利用政策的力量来干预和保护特殊教育,但总体而言还很不完善。1915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国民学校令》。该法令在关注儿童教育权及父母或监护人在儿童学龄期间有让其入学的义务的基础上,针对特殊儿童给出补充内容,在第24条中指明:“学龄儿童(指满6周岁以上至13岁的儿童)如以疯癫、白痴或残废不能就学者,区董报经县知事认可后,得免除其父母或监护人之义务。”[2]53这条有关“就学”的条款,表明我国的初等教育已经开始进入义务教育阶段,且政府在逐步加强对特殊教育的关注,对残疾人就学身份的认定也逐渐正规化。但在具体实行中,这种在政府指导下的强制性的初等教育,依旧将残疾人从教育对象中划分出来,指明需要通过县级部门的专门认定,以作就学的相关处理,表明政府在关注特殊教育对象的问题上还没有做出足够公正平等的划分。特殊学校虽已被纳入政府教育体系的考量范围,但依旧在某种程度上被“另类”处理。
1922年,教育部公布了《教育系统改革令》,也就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壬戌学制”。其中提出的“对精神上或身体上有缺陷者,应施以相当之特种教育”[4],对特殊教育的对象给出了比较明确的定义,有意识地呼吁政府对特殊教育意义的重视,急切呼吁政府要改变之前忽视或者轻视特殊教育的做法,以尽到人类博爱天性下的职责,对不够健全之人施以特殊教育,以增长他们的知识,提升他们生存的幸福感。
1933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修正》提出:“非中华民国之人民或其他所组织之团体不得在中华民国领土内设立教育中国儿童之小学。”[5]495法案指明中国的初等教育必须由国人来创办,从根本上禁止了外国人继续来华创办初级教育机构的可能性。同年10月,教育部对法案进行修正,指明之前中国原有的由教会创办的小学(包括特殊小学),必须在程序上向中国政府注册,换由中国人出任校长;在中国不能够再建立任何一所新的教会小学(包括特殊学校)。此次修正,彻底杜绝了教会在中国垄断或者说掌握特殊教育学校管理权的可能性。
随后的1943年,国民政府再次颁布《修正私立学校规程》,指出“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境内设立教育中国儿童之小学,其专为教育其本国儿童而设立之小学应受所在地主管教育机关之管理”[5]653。外国人在华办学的权力进一步被限制,针对外国人设办特殊学校的规章制度基本完善,除却管理权,国民政府開始逐步掌握初等特殊学校的经办权。
1945年之前,虽然国家对特殊教育的关注度及所涉方面不断提升与扩大,但依旧难以堪称全面,针对特殊教育的法律更未成体系,不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与计划性。抗日战争胜利后,更多关怀国计民生发展的学者,开始注意将教育中的公平、平等等理念运用到特殊教育领域,尝试从关怀的角度出发,注重特殊教育中的均等问题。
1946年12月,胡适与朱经农等提交议案《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章》,修正后正式纳入民国宪法,成为第158至167条。这份议案的核心思想,便是教育机会均等。胡适等人提出,无论种族、贫富抑或是身体上的差异,都不应成为评判是否具有受教育权的条件,所有人均应接受6年的免费教育。并且胡适等人进一步提出了教育普及的构想,认为只有在教育机会均等的基础之上,兼之以公平、平等、人权思想的宣传,才可实现教育普及的良好局面,使得不论是健全者还是身体或精神有残缺者,皆可得到与自己条件、需求相适应的教育,从而得到身心尽可能全面的发展。
1947年,南京政府召开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徐警予等25人联合提出的《提倡盲哑教育案》被送交教育部。提案指出,中国的盲哑人数量在世界上最多,且如此多的盲哑人的背景下“而全国公私立学校不及四十所”[2]65,这与我国庞大的盲哑人口极为不符。因此,亟需广设特殊学校,招收数百万的盲哑学生,并大力培养特殊学校师资,为中国的特殊教育前景,奠定雄厚的专门人才基础。《提倡盲哑教育案》提出了具体的盲哑教育发展计划,包括盲哑教育的目的、原则、要求、步骤及方法,内容涉猎极广,包括中央、省府、县府、私立盲哑学校的设立,提倡设立盲哑教育司专门负责盲哑教育的发展和推进,设立编译馆和印书局以加强相关理论的宣传等,堪称全面而具体。该份《提倡盲哑教育案》虽被国务会议商定为“参考”,而不具备法律效力,但也为同年教育部所制定的相关法案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同年提出的《改进全国盲哑教育案》直言盲哑教育发展缓慢,尤以特殊学校师资缺乏、设备简陋为显著问题,因此,发展特殊教育刻不容缓。法案提出“公布盲哑学校规程,加强学校管理”[2]70,“各省市应即增设盲人学校及聋哑学校,并应于今后五年内先行各自分批设立省立盲人学校及聋哑学校各二至四所,以应即(亟)需”[2]70,将增设特殊学校正式提上议程。随后产生的《改进全国盲聋哑教育计划草案》,进一步就盲哑学校的设立与管理提出规定,并对盲哑教育课程、教学、研究等方面提出构想。
综合以上两部法案构想,及结合我国盲哑教育的现实境况,教育司同年又制定了《盲人学校及聋哑学校规程(草案)》,并在其中拟定了中国特殊学校分为初级、中级、高级的构想。此外,还对中国特殊学校设置及管理、编制及课程、训育、设备、成绩及考察、学年及休假、转学及休学、经费及待遇、学校行政等做了细致的规定,旨在健全特殊教育制度,推动全国特殊教育事业在统一的指导下得到发展。
特殊教育的立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近代的立法活动使中国的特殊教育事业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使其有法可依、有序可循。通过立法,我国特殊教育开始逐渐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普及化与大众化进程得以落实与推进。并且,特殊教育终于获得法律正式的保障,为其后来专门法规的制定奠定了法理基础,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整个民国时期,国家从未针对特殊教育而专门制定独立的、成体系的特殊教育法。也就是说,特殊教育一直未曾获得应有的地位,只是作为“普通教育”或者“社会教育”的一部分、一个类别而存在,是一般教育法律的连带性规定。也正因为思想意识上未能给予特殊教育以相适应的地位,民国时期有关特殊教育的法律条例,通常都过于简短、不够全面,且更多停留于理论层面,没有与社会实情紧密贴近,更没有做出实践操作的指导。
此外,民国时期有关特殊教育的规定,在制定过程中,缺乏对于特殊教育法案落实情况的跟进意识,也就出现了对于特殊教育所存在问题监督及惩罚措施的法律空白。综而言之,民国时期特殊教育的相关立法,并未形成独立的、完整的、层次丰富的法律体系。
(二)政府逐步成为设办公立特殊学校的主体
20世纪30年代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华设办的特殊学校,可以说几乎由外国教会包揽,国人方面,整体而言对于特殊教育事业皆处在不热心参与并且冷眼相看的状态:一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皆将残疾人群放在末端,并未给予根本上的重视;二是由于国家思想未足够开化,物质基础也未跟上,难以给特殊教育提供足够好的环境以供其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下,外国教会也就垄断了在华特殊学校的主办权。
20世纪初叶之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逐步深入,民权意识、民主意识、民族意识不断在国民心中觉醒,再加之已有在华教会对于关爱、善心等理念的宣传与感召,中国民众或者说仅仅是朝廷中较为具有影响力的官员人物,才开始关注到了教育领域中的特殊教育事业。但他们的关注是十分有限的,一般皆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发表看法,发展特殊教育仅指向于强振国威。
清朝管学大臣荣庆在整顿学务时,就从国家富强需要人才的角度出发,提出“荣庆曰近查阅各省考试毕业生之成绩多不堪造就,观东西各文明国,盲哑皆能加以教育,造就成才,我国人士岂皆不若各国盲哑之知识乎”[3]279,表达了对于“我国人才的知识与能力不够卓越,甚至比不上外国的盲哑人”现象的批判,提倡给盲哑人也施以教育,一并充作振兴国威、提升国力的人才基础。随着关注特殊教育的官方人士逐渐增多,中国民间人士开始设立特殊教育机构,在教会对特殊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增加了中国因素,打破了教会独揽中国特殊教育事业的既有格局。
但总体而言,政府在这方面的行动依然迟缓,除了对部分特殊教育机构提供资金上的赞助和政策上的支持外,政府并没有承担起设立公立特殊学校的职责,也就是说,民国初期特殊教育主要还是依靠教会、个人以及少数慈善组织发展的,政府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但特殊教育只依靠上述主体来发展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庞大的特殊教育群体必须由政府来进行统一负担,这不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从经济及人才效益角度进行考虑。当时的学者通常认为,设置特殊学校花费巨大,且经过漫长教学过程的残疾人,也并不一定能够立刻进入社会所提供的岗位,进行生产劳动、创造社会效益,设办特殊学校,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
陈鹤琴认为这种论断过于狭隘,他指出:“教育的对象本来是‘有教无类’,而国家对儿童犹父母之对子女,必须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他们身心智力的差别而遂不顾到他,忽略了他的前途、他的幸福。要知道2700多万特殊儿童没有享受教育的机会,就等于使国家多了2700多万废人,这对国家是何等大的损失?反过来说,如果给他们以特殊教育,他们就可以好好地发展,而增加了极大的力量。”[6]政府以及学者应该站在更宏观的角度,也就是全社会的层面,对于特殊教育投入、产出比率问题进行考量:对于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残疾人士,每多一名残疾人接受教育、学成之后迈入社会,就会使社会减少一份持续进行养护的负担,而且国家重视特殊教育的举动,也会在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因此,由國家承担起发展特殊教育的重任,是一件增利减负的事情。并且,教育和慈善之间终究是有区别的,教育是国家民生发展的重要奠基,需要有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跟进来进行扶持,慈善相对而言,更多的是进行爱心的浇筑,以及对需求短期的满足。由零星的、不成体系的私人或团体组织的特殊教育,终究缺乏雄厚的经济力量与科学的理论指导,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会有缺漏,只能称为慈善之举措,并不能提升到对整个国家民生有益的程度来谈论,“如果把教育2700多万特殊儿童的责任委诸他们,其不能胜任是无疑的”[7]。因此,发展特殊教育事业,只能依靠政府,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外,更直率地说,“须知限制(残疾人)此种机会,将必然的加增国家将来负担此等不能自给者之义务。此不啻国家收回智识的实业的进步之机会,而使盲哑儿童成为不能自立者。此国家已经且正在支出其从前遗忘此阶级之罚金”[3]280,政府这样做只是为了弥补之前轻视忽视盲聋哑儿童这一人群的失职的过失。因此,纵使在短期内在特殊教育事业上有较大支出,也是应当面对并且毫无怨言的。种种愈来愈科学的看法,推动着人们对于特殊教育事业的关心,加之政府“提供教育”本身,也被看做一个国家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是符合一定的历史发展趋势的,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残疾人群作为“国民”的一部分,其教育问题自然被包括进国民政府的责任中,“政府设办特殊学校,向残疾人群提供公立特殊教育”正式提上了日程。
1929年,前身系1927年成立的南京盲童学校的近代中国第一所公立盲哑学校南京市立盲哑学校于南京建立,标志着政府正式承担起特殊教育事业兴办的责任,成为与外国教会、私人及社会团体并肩的力量。该校经费由市教育局划拨,市府委派陈子安担任校长,“同年八月,增设哑科,以符名实”[8]103。盲哑学校的宗旨十分具有关怀色彩,是为了能够使盲人识字、哑者说话,使他们都能够成为独立谋生的国民,减少社会上无业游民以及纯粹瓜分国家收益的人,学校必须要成为“善堂”以致力于其宗旨。
当时,在国民的观感中,教会学校依旧是最为“正宗”的特殊教育学校,之前所自办的特殊学校,不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远远不能与教会学校比肩。因此,为了打破国民心中这一固化认知,政府着力经营,力图把南京市立盲哑学校建设成中国公立特殊学校的模范。在此属意下,在政府力量的推动以及资金支持下,在学校的用具设备、师资、教学等方面都极其用心且质量皆属上乘:重视职业教育,增设聋哑职业科,训练学生的劳动技能尤其是手工工艺技能;在编制上将盲哑生分为两科,按照盲生哑生的实际人数与需求编制组别。到1935年,学生共有64人,教师配备12人[9];1936年时,盲生与哑生数量持续上升,已达92人[3]283。且南京市立盲哑学校1936年全年经费为11 258元,以同年南通私立盲哑学校为例,经费仅为2 400元,公立与私立盲哑学校经费之比可达4.69,足见在政府支持与推动下,公立盲哑学校经费之多、发展之快,规格也是逐年提高。
作为公立特殊教育学校翘楚的南京市立盲哑学校,将特殊教育的权利重新规定回义务阶段,一反私立学校收取高额学费的趋势,堪称是特殊教育学校在国民义务教育部分中的正态表现。之后,不论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在四川地区的奔波,还是抗战胜利后迁返南京,学校都没有终止在特殊教育中的探索及奉献,依旧是“全国盲聋教育之楷模”。
民国时期,除中央政府之外,各地方当局也设办了各种规模的特殊学校。影响较大的有北平市立聋哑学校、湖南省区救济院聋哑学校、杭州盲童学校、广州市立瞽女教养院等。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的公立学校陆续增加,有些是一开始即为政府承办(谓之公立),有些则是由之前的私人承办转为公立。
民国时期,从最初的政府对于境内特殊教育机构视若无物,到后期在学者以及民间推动下,终于开始承担起承办特殊教育的责任,特殊教育終于在国内开辟了一条相对稳定的道路并逐渐踏上正轨。总体而言,在政府支持下出现的大小规模的公立学校,使得外国教会几乎垄断中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公立学校开始有了一席之地,这个改变实属有益,也成为中国特殊教育事业的一种新型范式,即公立特殊学校。公立学校相对于私立学校,在质量上更加上乘,价格更为低廉,加之入学门槛的降低,使得更多贫苦人家的子弟有了可以跨入教育门槛的可能,这也是近代政府在“为国民提供教育”基本要求的实现。
此外,教育的大门尤其是特殊教育的大门,朝更多的贫困阶级大开,这也是社会公平、平等不断得到实现的体现。更多贫苦人家子弟得到教育机会,不仅进一步启发了国民关注国民教育尤其是特殊教育,而且有助于提升国民对于教育公平的认知水平,愿意群策群力为国民教育增砖添瓦,这整个过程,堪称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学校由外国人创办到国人自办的历史转折。
(三)创设具有特殊教育特色的课程体系
所谓特殊教育,“特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受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因为特殊教育面对的不是广大的普通人群,而是少数且有特殊身体缺陷的残疾人群;二即为教育内容的特殊性,因为受众的特殊,所以课程、教材、方法、设备都要据此而做出改变,是不同于普教教学中的方针、方式、方法的。课程作为其中最能够直观带来教育成效和体现教育功能的方面,在特殊教育的实施中尤其重要。
民国期间,对于特殊学校的教学,最基本的目标可以用当时烟台启喑学馆的表述来概括:“该校致力于对孩童们完成三个方面的训练,一是语言和文字方面的训练,从而使这些手段成为聋哑孩童们能够与同伴(正常人群)交往的工具;二是生活自理能力方面的训练;三是生活责任感和谋生知识的训练。”[3]129几乎所有特殊学校的教学课程,大致上都是围绕着这几个方面来设计的。这三个目标可以说是从交往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及劳动能力设定的最基本的目标,但其实真正做到并持续而圆满地达成是有很大难度的。
首先,特殊教育的课程与普通学校的课程设置是有区别的;其次,20世纪后教会所掌管的特殊学校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大多数特殊学校的学科、课程设置也按照西方模式设办,采用的是相对新式的学科分类。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特殊教育课程的设置,更多地表现出了多样性、时代性和趋新性,尽可能地关照到社会现实以及传统所承,在原有的课程基础上,虽与普通学校课程有较大区别,但依旧表现出可能接轨的倾向。在此背景下,特殊学校的课程致力于满足特殊教育对象的需求,其中部分则具有教会学校的特点,大体可以划分为基本的生活自理类课程、培养技能以良好生存的职业技能类课程、满足交往所必须的语言文字类课程、培养生活情趣的艺术类课程,以及由于教会学校广泛存在而延续下来的宗教类课程。
1.生活自理类课程
对于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本身,如何在社会上良好生活、具备生存能力是基本要求,对于盲人与聋哑人更是如此,如果盲人与聋哑人缺失生活自理能力,那么后续的所有课程都无从开展。在生活自理类课程中,首先进行的是特殊教育对象独立行动能力的训练,具体来说,就是从基本的如何摆好正确的姿势姿态、用姿势姿态组合成为正确的步伐,到运用步伐进行较为良好的独立行动的过程。在具备了独立行动的能力之后,接下来便是训练他们的生活技能和生活习惯,例如,自己从晨起到穿衣到洗漱到出门行动的这些基本过程,也通过一定次数的训练,让残疾人往自己独立生活的目标靠近。但仅仅学会生活习惯也是不够的,因为人所处的居室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家中,特殊教育对象也需要掌握在户外行动时所需要的自理能力及相关的劳动技能,全面地对其各项感官进行最大程度的开发与锻炼。
独立行动能力、生活习惯以及在外劳动技能的养成,都属于通过锻炼学生的官能来达到提高其独立生活能力的课程内容。除了可以直接表征于外在的能力锻炼之外,民国时期的特殊教育课程,也开始关怀到了学生的心理状态及心理素质,并通过训练培养学生对自我、对社会、对人生的的良好心态和良好规划,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心理训练的课程中,教师会帮助学生明确社会规则及规范,学生通过社会心理技能训练,能够逐步明白美德的重要性,学会区分善恶是非。一位哑生就讲述了通过课程学习之后对于“好学生”的概念理解:“一个好学生,他睡起都有一定的时间,寝室能够清洁,他的被褥能够折叠得很整齐;进教室读书,他能守规则;他的衣服洗得非常清洁,他在工作时作工非常发奋;课余的时候又勤快又清洁……如果同学能这样去做,才可算是一个好学生。我们才可以把他做一个模范啊!”[10]从这里可以看出,做好社会心理技能的训练,可以使残障学生学会思考自身在生活习惯、知识学习等方面的不足,谋求上进、获得进步,最终学会悦纳自我,肯定自己的存在价值与生活、学习能力。
不论是训练残疾学生的自理能力,还是进行他们的社会心理训练,都有一个恒定的原则“量力而行”——“量力”即指依据残疾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施教。在教授课程时,应时刻参考学生的心力和体力,既不可以超过他们所能承受的負荷,给他们以心理和体力上的双重压力;也不可以设置远低于他们能力的量度,使得他们产生自我怀疑、减少自信心。例如,对于失明的人,我们并不应仅仅致力于让他们的眼球看到东西,而是更应关注他们失明后的状态是否变得更好,是否可以更好地感知事物。在遵循“量力而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达到生活自理类课程的终极目标,也就是润物细无声地让学生养成良好的文明修养,具备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习惯的养成需要日积月累,尤其是面对特殊教育对象。除“量力而行”的原则之外,民国时期的特殊教育,十分注重从细微处开始进行课程教学,即从最普通最浅近的事物开始,让学生们通过固定的长期的训练,养成自然的习惯。并且通过良好内容的学习,提升知识水平,涵化内在修养,具备良好的文明素质。在这个过程中,心态的锤炼是很重要的:一是要教会残疾学生“知足”,即即使拥有身体的缺憾,也要看到世界的美好;二是教会他们要有更高的层次即“自忘”,能够通过文化的熏陶及认识的提升,眼界不再仅仅聚焦于身体上的残缺,而是能够超越身体层次关注到人生的快乐以及希望。如果能够达到这层终极目标,那么不仅设置生活自理类课程的目的达到了,而且还能够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享受生活的能力,这是更高层次的目标。
2.职业技能类课程
职业技能类课程也可以称为工艺课,即教授手工的课程。俞寄凡指出:“究竟为什么要教授手工?现在把他的理由写出来,自然能够明白。(1)明了关于物体的观念。(2)利用手指。(3)强韧筋肉。(4)总言之,就是职业教育的准备。”[11]以手代目,教孩子们使用手指不仅和教他们独立思考、独立工作一样,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教育手段,而且还能帮助他们专心于某项工作,也同时能够修身养性。对于残疾学生,要根据学生群体的需求和特点,创设各类职业训练。手艺上的训练最直接的作用即是为了未来的职业做准备,如果能够掌握几门手艺,那么在就业方面要容易得多,即使未能够被人正式聘用,也可以凭借自己的手艺进行简单就业养家糊口。只有培养残疾人能够顺利就业的能力,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个人潜能,让他们未来在社会上有一方生存之地。
工艺课的开办某种程度上来说,必然带来工艺产品的商品化过程。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从目的上来说,也是为了让受教育者能够赢得胜利、学会生产。福建灵光学堂在职业训练类课程的设置上较有特色,采取半工半读的形式,有效地维持了学校的生存发展。1898年创建的时候,学堂共招收了男生七八人,从事编织席垫和麻绳等工作。后期学校规模逐步扩大,到1914年时工艺课已较有规范,学生们在工艺课上编织草席、门帘、绳子和冬天用的垫子。工艺课也划分了席科、竹科、棕科、信封科等细致的种类以供学生选择,这些工艺生产一方面锻炼了盲童的工作与生活能力,为他们能够更好地走向社会奠定基础;一方面通过学校工艺产品的市场化运作,工艺生产走向社会,通过适当买卖增加了学校的经济收入,为学校的运营提供了及时的经费补充。
在民国时期大大小小的特殊学校中,傅步兰所办的学校在理念上是较为先进的。衡量一所学校办学效果的好坏,重要的衡量标准,即是其学生毕业后的发展与职业归宿,在特殊教育学校毕业的盲童能够自给自足,有一份养活自己的职业是非常重要的。由此,职业的训练成为课程的主要目的所在。傅步兰的理念中,学校的各项课程更多要突出“教育”的因素,即工艺课虽然有市场化的成分在,但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营生,而是要成为教授给学生技能的职业教育。上海盲童学校起初设立了工艺科,而后扩大为工艺部,并在1914年将工艺课列为学校最重要的课程之一。在此规划下,学生们得以有机会学习多种技艺,在毕业后谋求生活并服务社会。
3.语言文字类课程
民国期间,语言文字类学科逐渐受到重视并且越来越规范化。语言文字类课程在特殊教育中又称残疾弥补类学科,是特殊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最主要学科,分量最重。因为特殊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弥补学生生理上的缺陷,还在于要使学生获得综合能力的提升与全面发展。因此,语言文字类课程的内容,也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划分。对于盲童,主要依靠触摸来进行识读,并辅之以一定比例的听读;聋人则是口语发音以及手语训练为主要内容。语言文字类课程非常看重学生沟通能力的培养,“教学方法:盲哑学生,形体缺陷,既迥异于众人,则普通教学方法,自然多半不甚适用。哑科大概多用手势表演,次看口学话;盲科多用讲述,以手摸习。”[8]104此外,还关注思考能力的培养,通过对各类事物概念的认知来培养学生对事物的认知与操作,在学习过程中锻炼思维能力。
在盲童的教学中,近代中国特殊学校的盲文教学以盲点字法为主要形式,以西方的盲点字法为基础,将具体的教学方法进行归类,包括字母教学法和拼音教学法两种。上海盲童学校在盲童教育的课程设置中,堪称最丰富也最富有远见卓识:首先,学校在当时地方语言千差万别的中国背景下,强调“文学”类别课程中语言文字的统一,“文字皆用官话授之,以期语言统一,所用教科书乃本校特制,不久当即出版,以便各盲人院采购”[12],具有前瞻性;在教学理念上,傅步兰强调“我们的目的是训练和教育,而不是提供生活场所”[13],指出不可以将“养”与“教”混为一谈,更不可因为注重学生的养护就弱化教育,应明确区分二者并重视教育方面的实施。
在此理念下,该校治校者将文化课的目标,确立为提供给盲生以和正常学生基本相同的教育。学校按照中国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开设课程,并且购置与普通学校相同的教材,以供学生们学习。校方认为,只要有相同条件的硬件设施、科学的教学方法、完整的图书资料,盲生的学习效果与普通学生不会有过大差别,盲生也可以顺利毕业直至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取得更高学历。在此倡导下,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盲生也可拥有尽可能便利的学习环境以供自由而深入地进行学习。
在针对聋哑人的残疾弥补类课程中,重要的并非解决听力上的问题,而应该是解决沟通手段上的问题,也就是让聋哑人能够在与普通学生的沟通中克服差异,达到更有效的沟通。在教学中主要采用的是口语法和手语法,口语法即利用聋哑者的双眼看教师的口势动作,然后在模仿中不断强化、加深印象,经过一遍遍训练,逐步让学生们能够说出简洁的语言;手语法是指纯粹凭借含有手势、手语、手势语、手指语的手势动作来传达聋哑人的意见,相对其他方法更为简便直接,较容易使人学习,又可细分为单手语法和双手语法。
在开设残疾弥补类课程的学校中,烟台启喑学馆较有代表性,学馆对于初入学的聋哑学生,先教授他们单音节的发法和对应的手势,在学生熟练记忆后再教给他们难度更大一些的单字例如牛、马,其后再由单字的教学进阶为好几个单字的复合字甚至语段的学习。最终,“如骑马、牛奶一类的印成若干纸片,照以上说的法子,凑合成书,钉成书本,名叫《启哑(喑)阶段》,若念完了《启哑(喑)阶段》,凡普通学堂念的书就都能念了。”[2]1269
除了基本的对于讲说能力和唇读法的训练,学校还注重制定更适合学生的具有实用性和通用性的教科书。1907年,启喑学馆编制的教材《启喑初阶》出版,并作为中国聋教育语文的教科书,首次印刷上了赖恩手势图作为教学内容。《启喑初阶》后来长期作为中国聋校的教科书,多次再版,书中的内容既可以让学生们看图识字,也可以让学生们学习如何正确地发音说话。如果教师尽心尽力地全部教授,学生跟紧教师进度,全部学完,聋哑生便可达到小学毕业的知识水平。语言教学是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聋哑学生,更是核心内容、重中之重,民国时期烟台启喑学校在聋哑教育上的不断调整和进步,也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语言教学方法的与时俱进。
作为残疾学生,尽可能弥补其身体上的残缺,使身体功能尽量接近正常人,而后才能身心双修,健康心智,这个是语言文字类课程的最终目的。通过每日的训练和知识的教导,学生可循序渐进地提升语言文字能力和文学修养,最终温润心灵,丰盈精神世界。
二、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实施的问题
民国时期,国家一直处于动荡状态,国情极不稳定。频繁的战争给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也使得刚刚发轫的特殊教育事业在实施时缺乏稳定的生长环境。虽说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特殊教育是不断发展的,但终究因频繁的战争消耗着大量内力,在整个教育事业中一直处于夹缝中生存的状态。
教育一旦失去了丰厚的发展土壤,就无从稳定、持续地发展。民国时期普通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十分艰难,特殊教育事业更是如此。战争期间,一些公办学校和具有较强官方色彩的学校,因失去校舍而不得不迁移到异地重新办学;剩余的部分学校在重创中减开支、减人员,中断了蓬勃发展的趋势,勉强维持着运营;一些学校干脆因国家情势险恶而被迫中止教学,不得已停办;更有部分学校在战争期间被日伪接管,校务被重新组织,教学秩序被打乱,饱受蹂躏。
(一)政府重视力度不够
民国时期特殊教育虽从正式起步开始逐步发展,但总体而言发展较为缓慢。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政府虽然逐步提升了对于盲哑教育事业的关注度与物质扶持力度,但总归没有给予与当时特殊教育需求所相匹配的重视与支持。
从我国1929年创办第一所公立盲哑学校开始,其后20年间,政府仅仅创办了11所盲哑教育机构[14],数量上寥寥无几。不仅数量上欠缺,国民政府在经费上也没有给予盲哑教育事业应有的扶持。经费问题是近代以来我国教育事业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战乱背景下,国民政府多口惠而实不至,根本无暇给特殊教育以实际关照。北洋政府时期,“全国教育经费,仅及军费四分之一”[15],“每年教育经费仅占岁出总额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15]。国人兴办盲哑学校所需的经费,主要依靠私人捐助,经常会遇到经费缺乏问题,教育的发展多欠充实。
北平私立聋哑学校校长杜文昌,在20世纪20年代时为筹募学校经费,曾带着两名学生奔赴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等省份大小学校进行表演;1936年,杜文昌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演,呼吁征求赞助员1万名、募集基金5万元以充作学校基金[16]。40年代,杜文昌率领两个学生历经3年到南洋宣传学校的教育理念以进行学校资金的募捐,到了1947年,由于物价波动过巨、生活困难,“一切未能依如预算,复以筹措维艰,故现经费深感支绌,困顿之情况已达极点”[2]1222。杜文昌迫于境况艰难,向教育部呈文来申请政府拨款以维持教育。国家形势动荡、百业萧条,社会捐款吃紧,北平私立盲哑学校的经费,可以说数年来异常拮据。
(二)社会重视力度不足
民國时期,虽然部分社会人士对特殊教育事业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但总体来看,特殊教育事业一直未能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特殊教育的实施,也就无从获得相关舆论宣传和所需的资金、政策支持。有人曾指出:“我国近来学校林立,不过注重文学、工艺数大端,未有涉及盲童者。非弃之如遗,实以此等废民不屑教也。推其原故,其不能尽义务者盖有二焉:一、上等社会之家,丰衣足食,不知艰苦,偶见盲童,以为此等废人,有何作为,遂弃焉置之,有劝为而不愿为者;二、下等社会之家,竭己之能力工作,仅足偿其衣食,何能顾及盲童,其义务之心,有勉为而不愿者。”[3]279也就是说,动荡社会的大背景下,富裕人家不知疾苦,更不知残疾人具体的标准、境况为何,所以即使有富余的财产,也丝毫不会顾虑到将其分发给残疾人以助其生活;对于本就贫困的人家,自身的温饱难持,即使有扶持帮助残疾人之心,也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他们不可强求之,更不用说性情本就淡漠之人。
由此,特殊教育的实施,就缺失了社會极富与极穷两个阶层民众的关注与支持。除却这两部分群体,民国时期也就只有部分热衷特殊教育的社会人士和盲哑群体,一直致力于发展特殊教育了。再加之对于当时从事特殊教育的人,一没有国家定向扶持的资金,二没有专门的政策倾斜。因此,若缺乏一定耐心与毅力,很少有人愿意涉足并长期致力于此事业的实施与发展。
(三)师资数量不足与质量不高
民国时期,特殊教育事业除了经费困难,师资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一是数量极度缺乏,二是质量不高。对于师资缺乏的问题,民国时期国人已发表相关阐述:“教育事业清苦繁琐,教授聋哑儿童,先需备具牺牲精神与特殊技术,而教授时又非具菩萨心肠,与之同化不为功,故皆望而生畏,习之者寡。自欲使聋哑教育,不为教育界之点缀品,尚有待于努力也。”[17]特殊教育事业本就较为清苦,如果不具备专门的才干学识以及满怀热忱,既不能胜任,也不会坚持。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未能设立专门的盲聋师资学校培训盲聋教师,国内能造就特殊教育教师的学校,除教育部特设盲哑学校高中师范科、滇光瞽目学校的师范班(该班专招收盲人训练)、成都的基督教代办盲人师资训练班外,其余各校皆为小学制,很难说能够成规模地造就师资。因此,每年受过特殊教育师范专业训练者不过十余人,远远不能满足对师资的需求。
师资严重缺乏的情况下,部分学校就只能降低特殊教育师资标准的门槛,在教师的专业化程度等方面作出让步,让并没有受过完整的、专业的培训的人来担任教师,进入特殊教育教师体系。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也就造成了当时中国特殊教育教师漫不经心、滥竽充数现象的出现,盲聋教师的整体质量也就无从谈起。此外,大多数教师很难懂得盲人心理,也不愿去体验盲人是怎样了解周围事物的,这是阻碍特殊教育落实的非常大的阻碍。因此,特殊学校师资的专业化自非易事。
三、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实施对当代的启示
(一)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特殊教育观
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决定着该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水平,反之亦成立。同时,整个社会对于特殊教育的认识与看法,也直接影响着特殊教育的发展水平与状况。让每一个残疾孩子都能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是办好特殊教育的基本内涵和目标取向,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和新愿景。正是因为拥有特殊教育,才使得盲生能够接触阅读,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才使得聋人能够倾听世界的声音,带来心灵的慰藉;才使得庞大数量的残疾人群体,可以更加深刻地感受世界的美好、拥有生活的愿景。
民国时期受传统文化较为丰沛思想资源的影响,人们对残疾人多采取“散而不养”的态度,虽也具有尊养残人的习俗、慈善为怀的观感,以及天下大同的愿景,但总体而言,对残疾人的关注,多从心理的慈悲出发,并未建构起完整的特殊教育体系。要创办教育,首先要变革的就是民众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将残疾人边缘化甚至歧视的传统看法,不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要积极转变对于特殊教育存在的固有观念,摒弃轻视甚至忽视特殊教育的不良趋势,转而关爱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对象群体,重视特殊教育发展,积极为整个中国的教育大业添砖增瓦。发展特殊教育事业时,应时刻将公平与质量作为追求目标,用公平来强调每一个学生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用质量来作为标杆,提升学生切实接受到的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此外,还要注重特殊教育的内涵建设,提高特殊教育质量,促进残疾学生在思想品德、智力水平、身体健康、艺术修养、实践能力等方面全面发展。政府也要提升对特殊事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将特殊教育放在国家各种各类教育发展的优先地位,采取多种切实而有效的措施,加快各类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最终达到提高我国特殊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最终目的。
(二)从法制和财政两方面提升政府对特殊教育的扶持力度
1.建立内容完备的法律体制,给特殊教育发展以坚实的保障
民国时期,政府先后制定并出台了第一次在近代法令中提及“盲哑学校”的《小学校令》(1912年),提及父母及监护人对特殊教育儿童付有让其入学义务的《国民学校令》(1915年),对特殊教育对象及目的进行较明确划分的《教育系统改革令》(1922年),对私立特殊学校进行详细规定的《私立学校规程》(1929年),规定了中国人自己创办特殊教育机构的主权的《私立学校规程修正》(1933年),以及民国后期的《改进全国盲哑教育案》(1947年)等法律法令,这些法案从多个方面对特殊教育进行了规定与管理,也使中国特殊教育事业逐步迈入法制化轨道。但总体而言,依旧存在“内容不够深入全面”“只作为连带规定而非专门章程出台”等多种问题。因此,总体而言,未能够在民国时期给特殊教育的实施提供良好、平稳的法律环境。
于1994年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教育条例》,近年来多次修订,从法律上逐步保障了我国残疾人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促进了残疾人教育事业的发展。《条例》从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继续教育、教师等方面作出规定,提出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应当保障义务教育,着重发展职业教育,积极开展学前教育,逐步发展高级中等以上教育,在统筹规划、合理配置特殊教育资源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特殊教育机制。但应充分认识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特殊教育的发展与其他教育相比还略显薄弱。因此,应不断根据特殊教育形势的变化和社会需求的转变,来修改、完善特殊教育的相关法案,给特殊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法律支持与保障。
2.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给特殊教育充足的经费支撑
进入21世纪,国家越来越重视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特殊教育办学规模及适应对象逐步扩大,政府对此的财政性拨款总量虽然逐年增长,但仍无法满足特殊教育发展的需求。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逐步跻身世界经济大国行列,综合国力空前增强,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为我国加大特殊教育投入提供了较大的回旋余地。政府的普惠性教育政策和工程项目,优先支持特殊教育,并针对特殊教育实际专门制定了特殊的政策措施。
残疾学生群体相较于普通学生群体,本就具有身体上的弱势,教育成本也随之显著升高。因此,各省(区、市)要密切结合这些特点,在制定各阶段的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时,有意识地向特殊教育领域倾斜,以保证教育的落实和质量的保障,为残疾学生提供较好的资金支持,以建立具备良好基础设施、校园环境和师资队伍的学校。
除此之外,政府还应加大对特殊学生的扶持力度,比如在学生不具备自理能力的学前教育阶段,以及将与社会接轨的高等教育阶段,优先对残疾学生进行资助,并提升资助的力度,找准发力点;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则应实行高中阶段的免费教育,尽可能创造最便利的条件给残疾学生,让他们进行知识的学习和生活技能技巧的巩固。
(三)构建科学合理的特殊教育课程体系
民国时期,随着社会的不断演进、学术的不断发展,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科设置、课程体系也随之更新,由中国旧有的具有笼统性、模糊性特点的知识谱系,逐步演化为分门别类、按学科划分的模式框架。民国时期特殊学校的课程大而化之,主要划分为生活自理类、语言文字类、音乐类、工艺类、宗教类等类型。这些课程既带有一定成分的西方理念的影响,也兼收了中国特色的教学法,总体而言,能够做到从残疾学生自身的情况出发、因材施教,为我国当前构建特殊教育的课程体系提供了不少可借鉴的经验。
大力落实并推进素质教育导向的课程与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残疾学生核心素养和综合素质,是发展特殊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环。特殊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相应的特殊教育课程体系需要独具特色,但要明确从教育培养人的本质看,特殊教育也是素质教育。因此,当代推重要根据“发展素质教育”的要求和残疾儿童身心特点,深化课程与教学改革:
首先,在课程目标和课程体系的建构上,要根据新时代我国人才需求和党的教育方针,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突出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职业能力的锻炼。此外,特殊学校要在课程方案和各科课标与普通学校逐步靠拢的同时,根据残疾学生的个性差异、特殊需要,因材施教,增强课程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提供尽可能多类别的课程以供选择,通过个性化、生活化、综合化课程,提高学生的生活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职业能力,促进他们全面和谐地发展。
其次,在具体的课程实施过程中,要随时注重关注残疾学生,将残疾学生作为主体,培养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自主性,激发他们积极思考的同时,教会他们主动学习、感受学习、学会学习,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四)建设科学化、专业化的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体系
民国时期,师资贫乏是拖累中国近代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最具紧迫性的“尤切”的问题。许多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充任教职员,个人素质、教学能力和职业水准都均属平平,再加之特殊学校师资的待遇较低,工作又极为忙碌,当时的教师队伍远远不能够达到特殊教育师资的标准以及专业化程度。而对于一所学校而言,有合格的教师乃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在培养师资、挑选教师方面,应精益求精,如何认真都不为过,力求做到最好,不能碍于客观不利条件或者急于完成指标而急功近利,降低标准。
特殊教育师资培训目标的确立,是引领整个师资培训过程的旗帜,也能深刻体现出师资培养体系的科学性及规划性。由于教师面对的教育对象是聋哑人也就是特殊人群,因此,大小目标的确立都要以人为本,从聋哑人的自身条件、情况、基础出发来制定,为后期更好地实现奠定基础。要时刻关照到聋哑人由于身体缺陷所带来的在生活中与他人交往的困难与被动,克服畏难情绪与抵触心理,敦促他们拥有良好的心情、健康的体魄及正常的社交生活。
综上,在特殊教育教师的培训目标中,首要的应该是对教师的培训,以让教师对学生进行合格的语言文字方面的教学。通过语言文字方面的教学,让学生能够了解词句、篇章的含义和思想,进一步学会表达自我,学會与人沟通以及获取他人信息再进行反馈。第二个目标是让教师能够良好开发聋哑人的手和脑:开发双手可以令其具备较好的操作能力,以积累生活经验,也为后期的职业工作打下基础;开发大脑,是能够让聋哑人手脑并用,听懂并听从教师的指挥。在对学生进行手脑、语言等方面的训练中,心理的训练、信念的培养也是必须协同进行的。通过在良好教学氛围中给学生以讲解和温柔的指导,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自身存在的意义,以及具备生活的奋斗目标,能够砥砺自我以具备信心,不断努力,超越自我。
建立培养目标之后,要确定特殊教育师资资格认定的相关内容。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首先应当具备必要的资历和学历——这是基本的硬性规定,以保证教师具有基本的专业素养与文化修识;其次,因为教师要负责学生的语言文字方面的课程以及艺术类课程,所以在专业技能上,教师要熟练掌握阅读、写作等基本科目的知识。此外,由于还有艺术类课程的教授任务,所以教师也要对于绘画、音乐、手工等方面技能有所了解。最后,作为一名教书育人的教师,教育对象又是相对特殊的学生,因此,最重要的资格认定是需要教师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性格特质:教师需要充满爱心、耐心、善心,才能够平等关爱地对待学生,教师还需要乐观、向上、积极,才可以传递给聋哑学生正确的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
在确立了培训目标以及资格认定内容后,就进入到具体的学校教育过程,也就是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中教学方法的基本训练。总体而言,普通教育教学法的许多经验原则,在特殊教育领域也是适用的,但由于教育对象的不同,教学方法也必定会随之不同。对于盲童,盲文的教学十分重要,教师要学会通过训练学生的不同感官来推动学习进程;对于聋哑人,教师要尤其注意一切有关“口”的训练,口型、嘴巴的动作都是最直观的传递给学生的信息,要清楚明了、由简至繁地进行讲解,才有利于学生的模仿和学习。此外,不论是盲生还是聋哑生,都要注意学习环境的建设,以及在学习环境中相较于普通教学更加夸张、幅度更大的教学方式与身体语言的运用,这样能够更好地刺激和陶冶学生的学习欲望,使学生保持丰厚的学习兴趣。
总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办好特殊教育,指明发展特殊教育是推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推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这意味着我国要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特殊教育,时刻坚持以人为本,深刻体现出国家对特殊教育的情怀与重视。
参考文献:
[1] 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四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106.
[2] 顾定倩,朴永馨,刘艳虹.中国特殊教育史资料选:上卷[G].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 郭卫东.中国近代特殊教育史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4]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G].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807.
[5] 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民国编:下[G].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
[6]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四卷[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406-422.
[7] 吕静,周谷平.陳鹤琴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542.
[8] 盲哑学校最近概况[J].首都教育研究,1931,4(1).
[9] 蒋永才,狄树之.南京之最[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406.
[10] 张进德.怎样才是一个好学生[J].盲哑(创刊号),民国二十五年(1936):35.
[11]俞寄凡.日本东京盲学校的手工教育[J].新教育,1922,4(1).
[12]傅步兰.盲童学校[J].中华教会基督年鉴,1914(1):132.
[13]朱怡华.上海盲童学校历史调查简记[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4(6):51.
[14]宋来祥. 民国时期国人盲哑教育的实践和理论探索[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
[15]整顿财政计划[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资料汇编:笫三辑:财政(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6]杜文昌在中央广播电台讲演[N].中央日报,1936-10-20-21(4).
[17]孙昱森.一年来之盲哑教育[M]//上海新闻社.一九三三年之上海教育.上海新闻社民国二十三年(1934):56.
(责任编辑:钟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