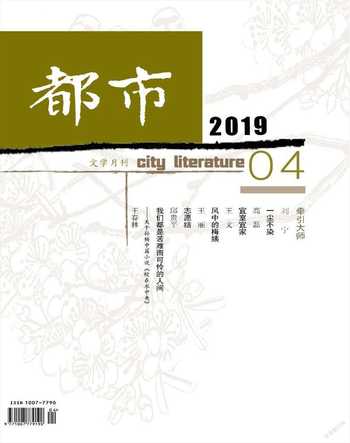遥远的木瓜河
余旦钦
河床两岸的堤坝被河沙塞得失去了从前的俊俏和伟岸,河上一座古老的石板桥被河沙这条大鳄整个吞进了肚里,河床变成了一个了无生机的沙漠,只有瘦得像丝带一样流淌的一线河水,被河沙挤在对岸的堤坝下发出哭泣般的声音。
死一般寂静的“沙漠”上稀稀落落地长着一些鸡婆柳,被洪水冲得七零八落,不成形状。鸡婆柳的枝丫上挂着洪水留下的泥草和破碎的塑料袋子,像鲜嫩的青草被霜打蔫了一样耷拉着脑袋。
不敢相信这就是伴我度过童年时光的那条纯净而风光旖旎的木瓜河……
前年盛夏时节,父亲打电话说,树根和竹根又闹翻了,树根还到县里的纪委去告了竹根的状,你回来劝劝他们。
树根和竹根,是一对亲兄弟,也是我的两个堂弟。
父亲的话牵引我回到了梦里的故乡。站在堤坝上,望着眼前的这条魂牵梦萦的河流,小时候和他们玩耍的一幕幕便像成群结队的蚂蚁一样从我记忆的洞穴里爬了出来……
河的两岸,竹木林立,藤蔓缠绕。穿过堤岸那条野草茂密的小路,眼前豁然开朗,闪烁着光斑的那一江碧水便映入眼帘,站在堤岸的高处鸟瞰,那一江景色更加迷人。碧绿的水依偎着堤岸,堤岸的倒影沉静地映在清澈的水里,那么纯洁,那么质朴。堤岸因为有水而灵动,水因为有连绵的堤岸而秀丽。灵动秀丽的一江美景,似乎透出一点禅意,使此时走近它的人觉得特别亲切,感受到一种大自然的温润和宠爱……
夏天的江水,清凉、透明。每到中午,趁大人们睡午觉了,我和树根、竹根就相约着偷偷地溜到江里去玩水。江边的树丛里,蝉鸣声此起彼伏,树荫下的浅水滩上,几只白鹭在悠闲地玩耍,它们相互交喙、追逐、嬉戏、打闹,静谧中透着生机。每次来到江边,我们先要在河堤上扯几根细叶杨柳,绕一个圈,学着电影里小兵张嘎的样子,把它当草帽戴在头上。然后小心翼翼地四处张望,见阳光下没人走近,便躲到树荫里,把身上的衣服扒下来挂到树丫或搁到水泥墩子上,赤裸着身子,嘻嘻哈哈地跳进水里,惊得那几只白鹭啪啪啪地扇动着漂亮的双翼,划一道美丽的弧线遁入了对岸的丛林……
河水清澈透底,我们双手撑在水底的沙子上,双脚伸出水面不断地扑打,练习游泳,溅起的水花犹如一朵朵白牡丹把河面装扮得更加美丽。我们闭着眼睛练习了一会,如跛脚病人丢掉拐杖尝试走路一样,到水深的区域去练习游泳。这时,我发现树根和竹根不见了。正在我东张西望的时候,树根驮着竹根从旁边一个篮洞一般的深水区突然拱了上来。原来,竹根一不小心掉进了那个深水氹里,树根是弟弟的保护神,目光像追光灯一般时刻照在他的身上,当发现弟弟掉下去的刹那,他就一个鲤鱼打挺扎了下去,及时把弟弟从水底捞了上来……
我们就是在这样清纯的河水里惊慌失措地泡大的,留在我记忆里的白江河像纯情少女一样质朴和美丽。
走下河堤,我来到一株皮肤粗糙的老樟树前,发现它旁边的那个水泥墩子不见了,仔细找了一阵,才在沙子里依稀看到它的顶部平面,记得这个水泥墩子顶端离河面有一米多高,小时候我们下河玩水时,爱把脱下来的衣服搁在上面,现在这个水泥墩被沙子埋了,顶部与河床的水平面一般高低。
河床中央的几台淘沙船像长颈鹿一样孤寂地站在那里,淘沙船上的斑斑锈迹,在向人们诉说着淘沙生意的萧条和惨淡。前段时间,随着城市周围的沙石资源越来越枯萎,边远地区的沙石开始变得金贵起来,一时间,沙石市场风起云涌,这河床一下子似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金矿”,农民们趋之若鹜。树根也到乡里的信用社借款二十多万元,与人合伙买了一条淘沙船,如一叶小舟驶进了无序开采沙石的滚滚大潮。昔日一片死寂的河床上,顿时变得热闹非凡了。特别是到了夜晚,船上发动机的轰鸣声、挖沙机那种生铁碰撞石头的撕裂声和传输履带上的沙石倾泻到船上的轰响声,把整个河床闹得像集市一样喧嚣。挖沙机和运沙船上那强烈而惨白的灯光,把整个河床照得如同白昼,灯光周围那一圈一圈尘埃一般密集的飞蛾,在光影里盲目地上蹿下跳,使本来喧嚣的河床变得更加躁动不安。在河床两边窄逼的村道上,运沙车辆的发动机声音如病危老人有气无力的喘息。树根看着那场面,就如望着一个机器轰鸣而又花花绿绿的钞票制造车间,眉毛尖上都是笑意。
可是好景不长,淘沙船开动才十多天,政府就开始出手整顿了,工作队到路上设了卡,禁止运沙车辆通行,说沙石是国有资源,无证开采既属非法行为,也破坏生态环境。树根花重金买来的淘沙机械和淘沙船,就像一堆废铁被抛弃在这野外的河床上朝曬夜露,树根的发财梦也如一个鼓胀的气球爆裂在这残酷无情的河滩上。
我在河堤上站了一会,便来到了树根的家里。这是伯父留下的一栋土坯子房,掩映在绿树丛中,视野开阔,整个河床尽收眼底。我端起茶杯进到厅堂,墙上,屋顶漏水冲刷出来的几线痕迹格外醒目。厅堂的泥巴地凹凸不平,还有几处烂泥一样的鸡屎,几只鸡婆“咯咯咯”地从身旁摇摆着跑了出去。树根是哥哥,住房子的东边,竹根住西边。我见竹根的门上挂着锁,便问道,竹根不在家呀?一提到竹根,树根的脸色一下子涨得通红,唾沫星四溅地咒道,咯只忘眼猴,到处死人,哟子就不早点死了他,将来肯定要遭凶死的……
当哥的为何这么恨弟弟?
竹根前年当上了村里的支部书记,新官上任,他很想为村里办几件实事。他把硬化村里的公路摆在第一。从有想法的那一刻起,他白天黑夜,上蹿下跳,把县里该跑的部门都跑了一遍,该拜的菩萨都拜了一遍,一年下来,真让他跑出了名堂,争取到了近三百万元的扶贫贴息贷款。
树根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夏天的一个夜晚,两家人都坐在地坪里乘凉,树根以兄长的口吻说,村里那路你一定要包给我修,我和上中村的胖狗屎讲好了,他有工程队,又有资格证,也有垫底资金。竹根想都没想说,那肯定不行,这是个大工程,解放以来村里的头个大工程,上级有规定要招标的,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树根说,你这是蛤蟆叫,谁不晓得招标跟和尚做道场一个样,是做给别人看的,走走过场而已。竹根知道跟他讲不清,就起身回屋里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刚起床,树根端碗炒饭跑到竹根房里边吃边说,昨夜我想了一夜,今早也打电话问了别人,霸蛮要修这条路怕是不行,那你就要修路的人用我的沙石,这总不死人吧?你看我借几十万块钱贷款买一条臭尸淘沙船,丢到河里快变成废铁了,这样下去恐怕只有死路一条。竹根闷了一会说道,要人家中标的公司肯用你的,别个要看沙石好不好、价格合不合适,我肯定要向他们一道推荐村上几个沙场的,他们用哪家的,是由他们说了算的。树根一听就有来气了,你这个书记一宗屁眼大的小事都做不得主,有谁信嘞?当了个绿豆芝麻官就开始哄起老兄来了,莫一只忘眼猴样六亲不认。说罢,拂袖而去。
结果是,树根既没包到路,也没人用他的沙石。这下就把当哥的惹火了,竹根回去一次,树根就要骂他一次,骂得他眼都开不得。从此,树根就把弟弟当成了冤家死对头。
树根一脸愤怒地说道,你怕他是个蛮好的东西,前几天,镇上来了三个干部在他家吃饭,村上三个干部陪,一餐吃二百多块,我看见村会计当场给了他现钱,这不是大吃大喝是什么?上面不是说要打苍蝇吗,他就是一只狗不吃、猫不闻的臭苍蝇。还有今年“七一”建党节,我听到几个村干部在这地坪里商量的,带着十几个党员去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每人还补助五十块钱,这不是变着法子旅游、变着法子发钱吗?我是向县纪委告了他一状,我要让他坐牢,让他把牢底坐穿!
等他骂完,我还是尽了尽当哥的责任,劝了他几句,我说,你不能怪竹根,他这样做是对的,真要是路给你修、沙石也用你的,村上其他人会答应吗?你们是亲兄弟,亲兄弟都到纪委去告他,别人就告得更快。再说,你不能为挣两个小钱而不顾兄弟情面,这样做,别人瞧不起,兄弟也心寒,你爸要是知道你们兄弟结到这步田地,恐怕要气得从坟墓里爬起来了。说到这,他露出一口黑牙,嘿嘿笑了一声,也安静了很多,但很快又是一臉愠色。我知道,他的怨恨情绪一时半会还很难平复。
在我离开的时候,树根一直在后面默默地跟着,走到堤坝上,他指着不远处的一条船说道,那船是我跟胖狗屎合伙买的,本钱都没有赚回来,县上就禁止非法淘沙,人背运时,盐罐里都生蛆。我说你降低点价钱,稍微亏点把它卖出去。他说有谁要嘞?我说帮他联系一下其他地方的沙场老板,看有没有人要买这样的船,他说那就劳烦你。直到这时,我才看到他的脸像解冻的山溪一样有了鲜活的笑容。
时值正午,阳光毒辣地炙烤着大地,河床沙漠上的热浪灼得人喘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