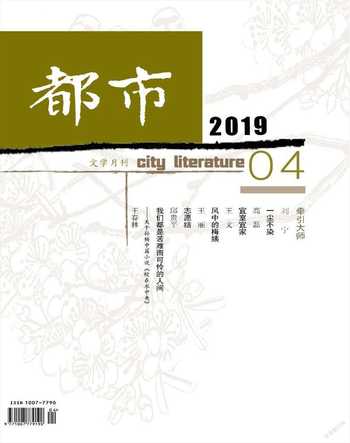风中的梅姨
王丽
1
起风了,像一阵阵纷杂的脚步。风里裹着落叶飞跑的声音,不用看,梅姨都清楚那些落叶此时的状态,很不情愿地被风追逐着,驱赶着,一路跌跌撞撞,身不由己却又无可奈何。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老了如同落叶,落了也就落了,可是大勇刚满32岁,风华正茂,血气方刚,还是一枚鲜绿的叶子,怎么说落就落了呢?这样想着,梅姨的泪又来了。
刚过霜降,夜就长得望不到边,她索性坐在一片黑暗里。这是大勇家的客房,床上还残留着大勇的气息,儿媳郝小芬坐月子她来伺候,大勇就睡在这张床上,梅姨还想到每次他下夜班回来,怕吵醒卧室里的妻女,也会轻手轻脚地进门,然后睡到这张床上。被子上儿子的气息是那样熟悉,这味道是种专属。梅姨猛的披上被子,裹紧被角,背部绵延而来的温暖,仿佛大勇此刻就伏在她背后,双手搂紧她的脖子,妈,想啥呢?
大勇啊!梅姨在心里无声地喊道,掩住被角哭得双肩战栗。
大勇是他的独生子,一年前大勇父亲病逝之后,她想卖掉用来栖身的房子,前来投奔儿子,老友静茹跟她说,你现在身子骨这么硬朗,才六十出头就跟着儿子过,天长日久儿子容得,儿媳能容得吗?还不如一年去两趟权当度假了,平时远远地互道问候,见了反而更亲!梅姨觉得她说的不无道理,便作罢了。孙女暑假里,她又去过那个北方小城,中秋儿子一家来她居住的山城过的团圆节,还住了一晚。相聚就是个盼头,有了盼头日子过得就快,一晃就霜降了。
大勇心很细。第一次发工资就給梅姨买了一套化妆品,他知道爱美的母亲最怕老去。一连数天,梅姨成了穿梭于广场舞队列里的花蝴蝶,抹得满脸放光,没少在那帮老姐妹面前显摆。
五天前的中午,梅姨忍不住给儿子打了电话,大勇正在上班,通话里机器的马达声很响,儿子的语速有些快,妈,有事吗?
没事。我就是想……梅姨本来想说,我就是想你了,可又觉得矫情,想着他那么急促的话音,班上肯定很忙,于是回答,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那你忙吧!
凌晨四点儿媳小芬的电话惊醒了她。小芬说大勇病了,很重。进了医院,让她过来看看。很重?什么病?到底咋了?在梅姨连珠炮的追问下,小芬支支吾吾,这让梅姨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拉上行李箱就奔向火车站。一路上她都在祈祷,老天爷啊,你已经把老刘带走了,不要再让我儿子有什么闪失了!
梅姨没想到与儿子的最后一面是在重症监护室,更没想到小芬与那些朋友们切切盼她来,是等她做最后决定,让她亲手拔掉呼吸机的插管。
亲家!小芬妈走过来,她一把握住梅姨的手,梅姨触到她手上的凉意。昨晚抢救了一晚,今天又是一天,ICU病房是按小时收费的,一天下来五千多……
患者是脑干出血,出血量大,我们尽力了!主治医生一脸无奈。
小芬脸色惨白地靠在ICU病房外的墙边,冲梅姨喊了一声“妈”,便抽噎着语塞。
梅姨走进ICU的那刻呆住了。大勇安静地躺在病床上,他的圆脸上罩着氧气面罩,像是睡熟了。胸脯在呼吸机的作用下艰难起伏着,病房内有节奏地响着呼吸机发出的“呼———嘁”的声音,恍若一声声冗长的叹息。
大勇,妈来看你了!梅姨泪水泛滥。她知冷知热的儿子,她健壮如牛的儿子,已经听不到她的呼唤了,梅姨依恋地抚摸着他的头发,像小时候安抚他睡觉一样。活着,只是呼吸之间,人一旦没了那口气,便真的不存在了。即便是借助呼吸机,可是梅姨觉得,大勇还留着一口气呢。
进病房前小芬妈的话在她心头炸响:医生已经说了这只是在靠时间。小芬他们家的房子还借着债呢……这分明话里有话劝她拔插管。梅姨的手哆嗦得厉害,觉得自己就像个残忍的刽子手,她不想去拔掉插管,尽管监护室外的人都认为这很不理智。可是不这样做又能如何呢?医生已经判定他脑死亡,早已不能自主呼吸,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她明白自己今天必须做个决断,而室外的人也在等着这个决断。突然,身后有开门的动静,小芬妈揽着小芬走了进来,还有那位戴着口罩眼神清澈的主治医生。梅姨浑身发冷,她抖索着伸出手去,背后像是生了眼睛,看到小芬妈迫切的眼神像一种无形的牵引,带着理性的决绝。这眼神让梅姨心寒,如同一支支利箭嗖嗖飞来,把她的心脏扎得千疮百孔。可她却又不得不接受这眼神的暗示,她心痛得发颤,觉得有种无用的悲哀。
医生,你说,真的没救了吗?梅姨的声音里带着作为母亲的哀求,她希望医生的回答能够给她一点光亮,能够挽回让她拔插管的决定。哪怕儿子成为植物人也好,她愿意养他,伺候他。但是,主治医生却很肯定地点了点头,像是疾风中的雨点,把她心头希望的火星完全打熄了。
三分钟的沉默却同三天那般漫长。大勇,别怕,妈来接你回家!梅姨手一抬,呼吸机停止了工作。大勇!小芬扑到病床上,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
梅姨顺着病床瘫软下去,黑暗无情地覆盖了她,从眼前到心间。
2
举行完遗体告别仪式,亲友大都散尽,梅姨与小芬却发生了激烈冲突。梅姨想立即带着儿子的骨灰回老家安葬,可是小芬死活不让。梅姨很意外,她努力撑住软绵绵的身子,用喑哑的嗓音说,落叶归根,天经地义,你不要这么不讲理!
妈,我求求你,不要把大勇带走。就安放在郝家祠堂里,这样离得近,我跟朵朵去看他方便!小芬泪眼婆娑。
七年了,还是这么自私!梅姨在心里鄙夷地骂道。她胸脯起伏着,之前蛰伏在她心间的恨,瞬间被小芬这个无理要求所激活,并以野火燎原的态势迅速蔓延。
大勇是个懂事的孩子,从小到大很少让梅姨两口子操心。七年前,大勇本科毕业,梅姨跟老刘旁敲侧击地让他考事业编,盼望他能端上“铁饭碗”,再找个当地女孩,安身立命地过日子。可是,大勇却轻描淡写地说,坐机关没意思,他想到外面闯闯。
那样也行,好男儿志在四方。老两口一厢情愿地认为大勇会到北上广那样的大城市历练一番,做梦也没想到他竟然跑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北方小城就业,干机械加工,更可气的是他居然要在这个小城跟一个叫郝小芬的成家。后来梅姨才知道,小芬是大勇的大学同学。梅姨心里像埋下了一颗雷,在她眼里,儿子遇上小芬之后才开始叛逆,别着性子跟父母唱反调,不定小芬动用了什么伎俩。她断定大勇千里迢迢追随小芬回老家,是受了小芬的蛊惑。
老两口迅速结成攻守联盟,打电话时老刘苦口婆心劝大勇回来,他托人给找份体面的工作。养儿防老,你说你走得那么远,我和你妈老了依靠谁?别忘了你是独生子。而梅姨则在旁边故意大声哭泣。可他们的软硬兼施还是没能把大勇从小芬身边叫回来。大勇结婚的时候,老两口没去参加婚礼。每每想到大勇的好几个同学都进了政府机关,梅姨心里总会浮起一股恨意:要是大勇不被小芬诓走,现在说不定也穿着笔挺的西服走进市府大院了。
直到朵朵降生,两代人之间的坚冰才逐渐消融。如今大勇客死异乡,倘若当初他不来这个连鹌鹑都不愿安家的地方,他至于把命搭上吗。
梅姨的恨意升腾着,咬牙切齿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要不是你,大勇能没吗?你毁了他的前程,又妨他丢了性命。你说,他那么年轻,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小芬的抽噎声戛然而止,吃惊地望着梅姨,可能想不到面前这个慈眉善目的婆婆会说出如此恶毒的话来,她眼神里含满悲凉,妈,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小芬妈嗖地一下窜过来,亲家,你怎么骂人呢!大勇是在晚饭后发的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怎么能怨小芬呢?你骂我闺女妨人,你儿子才够祸害人的,他一闭眼撒手去了,留下这孤儿寡母的,怎么过啊!还有那些买房欠下的账怎么还?天啊,这没法过了!小芬妈一屁股坐在殡仪馆门前的台阶上,双手拍打着地面,歇斯底里地哭嚎。小芬爸过来拉她,她也不起来。
现场一片哭声,一片混乱。梅姨仿佛孤身站在一艘行驶的船上,周围惊涛骇浪,她脚下没根,感到阵阵晕眩。小芬的确可怜,可她还有朵朵,她还年轻,人生有无限可能。而自己呢,一个老太太从此对着清锅冷灶,对着漫漫长夜,孤苦伶仃,直到油尽灯枯。生病的时候,恐怕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她心里绝望的茅草在不断生长,其实她很想像小芬妈那样哭天抢地发泄一番,那样或许还痛快点,但她想给自己留点尊严,她坚持着不能垮掉,她要把大勇带回家。
两头都不想妥协的局面僵持着,半个小时过去了。大勇厂里的工会主席还没走,他面相精干,一看就是个明白人,他分别劝慰了小芬母女,看她们平静下来,又跟梅姨商量,大姐你看你现在身体虚弱,这样独自带着大勇回去我们也不放心,要不暂且把大勇的骨灰安放到祠堂,等过几天咱跟小芬沟通好,再让人陪你护送他一起回家。梅姨觉得他说话在理,便点了点头。
从祠堂回来,梅姨心中的恨还处在风口浪尖,怎么也平息不下去。她一回家,就快步走到客房里,“砰”的一声带上门。那声响裹挟着一阵风,让小芬战栗了一下。
小芬妈见状,站在门口不依不饶,摔什么摔,谁还怕你似的!继而是小芬制止的声音。儿女亲家的关系就是这么脆弱这么微妙,没有了儿子的关联,所谓的亲家还不如路人。梅姨苦笑一下,很后悔没有把老友静茹带来,有她在,好歹自己不会这样孤立无援。她想给静茹打个电话,却瞬间被无望包围。梅姨坐在床上,又披上了那床被子。
她没想到的是,更大的煎熬却在后面。
3
一夜秋雨,天冷了下来。早晨站在门口叹息,都能看到嘴里冒出的白气了。已经第七天了,小芬还是不肯让步。自从婆媳俩在殡仪馆门前闹过之后,她对梅姨已经没有从前的客气,吃饭时也不叫她了,而是由朵朵叫她。梅姨乐得这样,她不想跟小芬说话,也不想跟她同桌吃饭,总是等她们吃完她才胡乱扒拉上几口,尽管桌上留给她的菜是没有动过的,但凉哇哇进到肚里,如同吃进去一股气,总是横冲直撞地在肠胃里打架,梅姨难受极了。
小芬自生孩子后便没出去工作。梅姨觉得她就是懒,说什么照顾孩子,只是好听的托词。朵朵都上一年级了,家里还拉着那么多饥荒,怎么在家里闲得下去,害得大勇没白没黑在厂里加班,他突发脑出血,八成是累的吧?这几天,梅姨的眼泪几乎没断过,眼睛花得更厉害了。
朵朵上學之后,屋子里就剩下相对无言(更确切地说是虎视眈眈)的婆媳俩。室内的空气里都带着火星,梅姨强忍着,她怕一高声就成了导火索。沉默是无言的抗争,她想用这种方式让小芬妥协,除了这样她还能怎样呢?一味吵闹,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何况她吵得过小芬,吵得过尖嘴薄舌的小芬妈吗?眼前这个沉闷得让人窒息的屋子她一刻都不想待,但为了大勇能落叶归根,她只有硬挺。
大勇厂里来人了。那个说起话来滴水不漏的工会主席来送抚恤金,是按大勇十个月的工资支付的。主席分得很公平,说这是厂里的决定,按照法律的有关条款执行的。小芬得40%,梅姨跟朵朵各得30%,梅姨拿着应份的三万块钱,泪水止不住地流。她轻轻摩挲着那些纸钞,扑簌簌的,一连串泪滴到了上面。工会主席看着心酸,大姐,别伤心了,你这样拿着现金不方便,要不我让小刘陪你存上吧。
梅姨摇了摇头。十个小时后,梅姨才咂摸出工会主席说她拿着现金不方便的真正含义。
晚饭后,小芬妈来了。梅姨估计是小芬给她打过电话,说抚恤金已发,她才像一只闻着腥味的猫立马上门了。梅姨现在视她为仇敌,猜测大勇骨灰盒不让她带走的主意是她出的,不然她怎么不规劝小芬放手呢。
梅姨坐在床上,拥着那床棉被。屋子里很静,小芬与母亲嘀咕着的对话声清晰地传来。小芬妈满是怂恿的口气:你得管她要,就说还借着债呢,朵朵上学需要花钱,她还小,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你婆婆有退休金,还有老房子,冻不着饿不着,说不定哪天再找个老头嫁了。再说隔着这么远,老死不相往来都有可能。你跟她说,让她把抚恤金交出来,你就答应让她把大勇的骨灰盒带走。
梅姨气得哆嗦成狂风里的树叶,她这才明白工会主席让她存钱的原因,原来就是怕被小芬抠唆走。小芬怎么回答的,她已经听不下去了,她想一脚踹开门,劈头盖脸给小芬妈一巴掌,可自己却缺乏那种勇气。她只能扑倒在床上哭。
大勇买这个两居室时,梅姨老两口给拿了十万块钱,老刘的退休工资还高点,梅姨退休前是下岗职工,保险交的是最低基数,退休金低得可怜。十万块当时没拿空家底,本来他们想再过上几年去山南海北地旅游,手头宽松,生活质量就有保证,有个病灾也不用大勇操心。哪承想老刘退休后只两年就查出癌症,与病魔抗争了一年,积蓄花光了,人也没了。眼下小芬竟然还算计着儿子留给她的抚恤金,梅姨从枕头底下拿出那沓钱,抹了一把眼泪,我就是捂得长毛,也绝对不会拿出来。不让我带大勇走,我就待在这里,看看谁能靠过谁!
4
早上起来,室内清冷。小芬在阳台上晾晒衣服。梅姨看到她昨天脱在客厅里的一件外套已被小芬洗了。小芬听到响动,回头说,妈,快吃早饭吧,在锅里温着。梅姨并不领情,她捕捉着小芬对她态度的转变,心想这也许就是要钱的铺垫吧。
今年的秋天格外漫长,都快立冬了,树叶也没落多少。楼前的银杏树满身金黄,静默在秋阳里,看上去有种肃穆的美丽。它是在等候风起吧,而自己又得煎熬多少个日子?梅姨正叹着气,听到小芬开门的声音,大勇厂里又来人了。
这次来的是办公室刘主任,还带着大勇生前两个要好的工友,梅姨认识他们,自从大勇出事,他们已经来过多次,跑前跑后,梅姨看着他们就觉得亲,就想掉泪。
刘主任是来送捐款的,他说厂里知道大勇家里困难,于是发出倡议,全厂干部职工纷纷伸出援手,一千多人共捐了十万七千元,厂里的分配方案是给梅姨五万七千元,其余五万给小芬母女。梅姨握着刘主任的手,感动得泪水涟涟。
大勇是厂里的骨干,他走了,家里的困难我们不会坐视不管。刘主任的话如同一团火,听得梅姨心里暖暖的。小芬接过钱,表示着感谢,对分配方案的事没有半句反驳,这让梅姨稍稍心安。其中一个工友姓仉,他对小芬说,嫂子,大勇是我的铁哥们,如今他不在了,买房子借我的那一万块我不要了,我媳妇也答应了。
小芬满脸通红,看不出是尴尬还是心虚,好久都说不出话来。
刘主任问梅姨用不用安排人跟她去把钱存起来。梅姨立即答应,她回房拿出那笔抚恤金一并带上。回来后看着那张银行卡,梅姨忍不住落泪,这是儿子留给她的养老钱啊!
可是这张银行卡还没捂热乎,事情就发生了转变。
傍晚朵朵的哭闹声惊得梅姨立马跑向客厅。她想参加老师推荐的特长班学钢琴,可是小芬不同意。
朵朵一看梅姨过来,像只小猫一样偎到她怀里,哭得更欢了。朵朵有着圆圆的脸庞与晶亮的大眼睛,漆黑的两道眉毛像用墨刷上去似的,简直就是大勇的翻版。梅姨一看到她哭,心里就像刀绞一般,不能让她这么小就被钱难到。
学钢琴一年得一万块。反正厂里送来的钱我不能动,我得给她存着。小芬主意已定。
那好,这钱你不给朵朵拿,我拿。只要孩子想学,我就是拼了老命也供她!
奶奶!朵朵用额头蹭着她的额头,奶奶,等我学会了弹钢琴,我天天弹给你听。这样的许诺何等熟悉,梅姨耳畔立刻回响起大勇小时候的话,妈妈,等我长大了给你买面膜,给你买口红,给你买……他用胳膊做了个最大的环抱姿势,买好多好多化妆品。
那些话就像昨天刚跟她说的,那样清晰。可是竟物是人非。梅姨抱紧了朵朵,泪如雨下。
朵朵懂事地揩去梅姨脸上的泪水,去卧室写作业了。这时房门被敲响。进来两个身材清瘦的男子,小芬认识他们,忙不迭地喊着杰哥,准备茶水。
那个杰哥像有心事,欲言又止。另外一个年龄稍长的人见他这样,便对小芬说,大勇出事我们都很伤心,要是手头宽裕,小杰也不会来,他妈病了,动手术需要大笔的钱,只好来找你了。不是有句老话吗,父债子还,夫债妻还……
我没钱。没等那人说完,小芬回答得很果决。
我们有借条,你要是不讲理,咱只能去找讲理的地了!那人拉起小杰,满脸怒气地走了。
小芬“呜呜”哭起来。朵朵听见忽地从卧室里冲出来扑到她身上哭。梅姨听着哭声,心里纠结极了,对于他们房子的借款,她是不想管的。大勇没了,这房子就是小芬的,那么所有的债务也该她来偿还。可是想到那句“夫债妻还”,梅姨心里沉甸甸的。
你说,这套房子到底还欠着多少钱?梅姨耐着性子,尽量压低声音。小芬抽泣着,快还完了,就差这三万了。杰哥两万,小仉一万。随后,她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小仉说那一万不要了。
梅姨真想骂她一番,但还是忍住了。人家那是工友情谊,人没了,但债还在。咱能没有诚信吗?
梅姨决定明天去银行提取四万块,除了还债,还有朵朵的特长班费用。当她说出这个打算后,小芬止住哭声,望着梅姨,眼神由诧异变得柔和,继而泛出了泪花。她动了动嘴唇,想说点什么,但终于什么也没说,陪着朵朵去写作业了。梅姨回屋摸着那张银行卡,觉得它已经薄了不少,心下一算,取出四万块,钱只剩一半多点。看来即便存银行也是白搭,这钱还得往外出,并且是她心甘情愿往外出的,她并不后悔。
5
回到房间,梅姨跟老友静茹通了好久的电话,静茹很担心,埋怨她老不接电话。梅姨向她哭诉了这几天的遭遇,忧虑自己已是孤家寡人,将来恐怕臭在屋里都没人知道。
靜茹安慰她,有这帮老姐妹不会丢下她。市里还有“失独者联盟”,经常举行活动,难过的时候可以去散散心。将来实在没有行动能力了就去养老院,到时候她陪她去。静茹儿子在澳大利亚,几年都不回来一趟,去养老院养老的话题她不知在梅姨面前说了多少遍。一番规划说得梅姨心里不再那么空落与凄凉了。
这天有些特别,是朵朵的生日。小芬买了生日蛋糕,梅姨也很想朵朵能过个快乐的生日,跟大勇在世时一样。她不想朵朵的童年充满阴影,那样不利于她成长。朵朵喜欢吃麻婆豆腐,小芬不会做。梅姨早早做好等着她放学回家。等待的过程相当漫长,客厅里坐着的婆媳俩谁也不说话,有几次小芬想主动说,但触碰到梅姨冷漠的眼神,只能保持着沉默。
小芬妈这几天没有上门。梅姨估计小芬早向她汇报了那四万块钱的事,所以她才沉得住气。不来也好,家里也消停。
忽然,一阵欢畅的笑声打破了室内的安静,确切说是大勇的手机响了。两个人都不禁一怔。大勇设置的手机铃声是朵朵五个月大时的笑声。这笑声天真无邪,乐不可支,像清脆的风铃,溪水的欢唱,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感觉听着她开心的笑,再大的难事也不是个事了。梅姨与小芬不约而同站起来,却谁也没有去接电话,任凭那笑声阳光般泼洒于室内的每个角落。
这铃声是多么熟悉,小芬听了近六年,而梅姨也听了无数次。两人都惊诧地望着手机,眼神里充满期待。似乎大勇就在这屋里,他从未走远。等一会儿,他就会一个箭步走过来,拿起手机,响起浑厚的声音,哪位?
可是笑声还是在她们的等待中渐渐消失了。梅姨与小芬不由对望一眼,“哇”的一声哭出来。哭声里,她回想起小芬坐月子,大勇打电话央求她过来照顾。进门的那刻,大勇冲她眨眨眼,妈,小芬是我选的,你对她好点儿。
从小芬的哭声里,梅姨毫不怀疑她对大勇的爱。大勇的离去她是猝不及防的,大勇去世后的这九天里,她定是如自己一样痛彻心扉,彻夜难眠。就算将来改嫁,这个她爱了近十年的男人都是一道很难越过去的坎儿。
妈,小芬走过来,一把抱住她。我昨晚做梦了,大勇说,要我对你好……梅姨感到她的一串泪滴到了自己脖子上,温温的热。她忍不住抱紧小芬,感到她单薄的身子在颤抖,仿佛梅姨才是她的依靠。
俩人哭够了,后来一看手机,小芬又哽咽了,说那是大勇设置的备忘录的铃声,他怕工作忙忘了女儿的生日。梅姨点点头。
一天后,梅姨带着大勇的骨灰回家了。临走前,她把那张银行卡交给了小芬。小芬不知,梅姨现在连给大勇买墓地的钱都没有了。小芬执意跟她一同回老家,但梅姨没让。她同时带走了大勇的手机。高铁靠站的时候,她就用自己的手机拨给大勇,那笑声便欢快地在车厢里跳跃,有个哭闹着的孩子听到那笑声,也不由停止哭叫,好奇地循声寻找,继而随着那笑声而笑了。
到站后,外面刮着大风。出了高铁站,风更大了,把梅姨的头发都吹乱了。风中的梅姨边走边想,得尽快给大勇买好墓地,无论如何让他跟老刘挨着。等明年清明,小芬和朵朵一定会回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