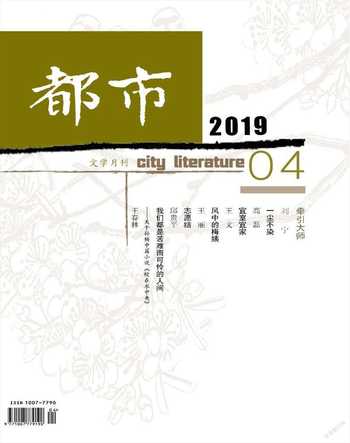一无所知的Lin和西西莉亚
白琳
考完试之后有差不多一个月的假期,我开始了20天的博物馆之旅,在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走了一圈之后,我给西西莉亚教授发了讯息。我说真好啊,现在我对那些现代艺术终于清晰起来了,这次我可不是瞎子哦。
她回我说,Dearest Lin,这是我2019年听到的最好听的一句话。
我刚入学就考了一门西西莉亚的课程。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拿到零分试卷。我们一共考了二十几道题。前十道是看图填空,后面五个是写五个世界知名现代美术馆,然后再写五个意大利艺术家的名字。最后还有几个名词解释。
我一个也写不出来。
考试的中间有人问意大利艺术家写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达·芬奇行不行,她大概没想到有人这么会钻空子,勉强答应了。但就这样我也没能写出来,因为我只晓得中文怎么写,不知道英文的拼法。
后来我对于人名也常常搞得一团糟,主要是因为等我们开始上课之后,好多地名人名都是英文混着意大利文。我有时候念英文,有时候念意大利文。和我一样情况的不在少数。每次做报告,遇到名字的问题,同学们就总是混着念。意大利的同学更偷懒,好多发音都直接用他们的母语。有时候觉得非常不公平,欧洲人学语言实在是太简单了,很多单词都长得很像。
这也没有关系。教授们的出产地也五花八门,有时候他们自己也会混,因为除了英文授课之外他们也要用别的语言授课。有一次N教授讲了十分钟我觉得听起来十分艰辛,直到后面才有人说教授你是不是在讲意大利语,其他人才都反应过来。
可就是这么半猜半明白地进行。
现代艺术实际上是最有利于写作的一门课,因为有时候光作品名字就可以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再加上你站在一幅作品面前根本都不知道这个艺术家是要搞什么,所以就有更广阔的空间去胡思乱想。
我们这个课是个考试最多的科目,学期末的正式的考试之前要有四次小测试,一次笔试,一次口试,一次艺术品分析,一次艺术品赏鉴。后两个都要结合策展来写,算是小论文,或者说艺术评论。说起来不是特别为难,实际操作起来就很困难,每一次的测试都需要大量地看资料看展览。每一个馆收费都是10欧左右。一定要说的是,在意大利,只要是艺术和考古专业的学生,美术馆、博物馆,以及各大景点,几乎都可以免费去看。在购票处出示证件就好。就这样,我有时间就跑到馆里去看画。事实证明多看一定是有帮助的,虽然一开始什么都看不懂,但不知不觉之中,很多莫名其妙的名字就被记住。我缺少的知识真的是太多,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就感觉头皮发麻。最开始看展的感觉是在受罚,无法真的很自在地随意享受视觉盛宴,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品鉴艺术家的作品。西西莉亚的课要求我们学会赏析现代艺术,要搞明白流派风格,所以不断地看,多看,就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一次又一次的看展览,确实是学习艺术的最根本的办法。看的多了,哪一个人哪一种风格,就会清晰地浮现出来。
我第一次选择认真了解的艺术家是Osvaldo Licini,然后我就跑去看了GNAM。
Licini的画大部分都是断手断脚,作为第一个要做的报告,我选择了他的Amalassunta系列。他的抽象语言是非典型的,注重几何学,一种充满抒情性的几何学,这在Castello、1933年至1936年方尖碑等作品中表现得很明显,然而Licini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1950年威尼斯雙年展展出的Amalassunta系列。人的本能、梦幻、下意识领域是Licini艺术创作的源泉。他觉得人的头脑活动要从理性与逻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理性、道德、宗教、社会以及日常生活经验,都是对人的恶精神,人的桎梏。唯有无意识、梦幻和神经错乱,才是人类精神的真正活动。老实说我只能欣赏他满腔的热烈情绪,但是我根本读不懂他的画。他画过一只鸟,他说“我非常欣赏叛逆的天使,爱它叛逆的尾巴,有时我喜欢咬这个尾巴”。然而那只“羽毛美丽”的鸟里面并没有鸟的任何形象,画面里就只出现了两个眼睛似的圆点,还有一张更像一片叶子的嘴。
我需要一个人来给我讲他的画,所以我去了馆里就拜托馆员给我讲他的作品。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为我解答。后来我了解到这边的博物馆美术馆的馆员并不一定是专业出身,有很多都是聘用来的年纪比较大的普通人。无可奈何之下,我开始站在一幅画前面,和每一个驻足在这里超过三秒钟的人搭话———尤其是看上去十分有艺术气质的人———通常他们都留着大胡子,或者扎着长头发。我说请你讲讲这幅画,然后我收到了很多句:真的不好意思,很抱歉我不知道。对不起我也看不懂。还有一个人说,哦,你不觉得这个画很恶心吗?恶心死了。
我做到最后发现我大概选错了题目。或者我应该从西西莉亚讲过的内容里选一个来说比较合适。后来我们在GNAM里进行了第一次的口试,老实讲那次报告我做得很糟糕,与其说我是在做报告,倒不如说我抛出来太多的问题。我五分钟讲完Licini,用了另外五分钟问问题,比如说你知道为什么他总喜欢把月亮和Amalassunta联系起来吗?他是不是太喜欢蓝白红三个颜色了?
我最后拿了一个不太好的分数,但是相较于第一次的零分,我想也没有太过丢脸。其实,我早已做好了准备,决定一点也不掩饰我的无知,基于这样的心理建设,在每一堂课上,我都非常坦白,所以缺陷也暴露无遗。甚至有一节课后让西西莉亚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几乎所有她讲出来但是我没有拼写下来的艺术家的名字,那是一个庞大的人群。她就那么一个个帮我拼写。整个学期我都非常疲惫,在竭尽全力地补课。就这样我两个月内为了这门课跑了不下十次的现代艺术馆,看了十几个画廊,三四个博物馆。
刚开始的时候我非常累,因为这门课和其他的课程内容相去甚远,至少在时间段里,差着好几百年。每一次跳跃到这门课,我都感觉自己翻到另外一座山头,和之前不在同一个时空。同样,这门课上相关的内容总是充满不可理解的很多散点,有人把所有的东西都包裹起来,有人把吃完的残渣装在墙上,有人将摔裂的碎片重新粘合,有人把垃圾塞到透明的纸箱。有人什么都不做。有人的头上顶满了瓜果蔬菜,有人的腿像长颈鹿的脖子那么长,有人的脖子又像长颈鹿的腿那么长。
我记得写完第一篇艺术评论的时候身边是一个装着剩可可的马克杯,朱红色的,边缘有一圈黑线。可可已经冷掉了,我懒得去热,端起来喝了好大一口。电梯井有声音忽上忽下。那时候好像是夜里三点半,第二天要去交作业。我写了一个柏拉图的洞窟这样的艺评,讲一个美国现代艺术家的一个装置艺术。为了找到自己适合写的题材,我和同学一起去看了展览,遇到奇奇怪怪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有一个画廊里全部都是陨石,但是陨石不是艺术品,挖掘陨石的过程才是。所以我们在地下室的黑洞里观看了一部分挖掘陨石的纪录片。比如我们还去了一个类似太空的展馆,那个馆被布置成球体的模样,在那里必须坐到地上才可以感觉到不被窒息。再比如有个艺术家最喜欢弄出来人的脑子肠子———当然都是假的。还有一个中世纪时期的建筑里面贴着很多标语,很多国家很多字,很多社会性内容。涉及人权,战争,生活以及性。那是玩文字游戏的一个展览,我根本看不懂。好在同行了一个学霸,懂好几国文字,加上日文中文英文我能够勉强一猜,再有翻译软件帮助,倒也硬着头皮看了下来。比较好看的能够理解的就是有个人一直在画花,画了很多。画廊的墙壁上也是她画的花,作品和展厅融为一体;再就是有一个画家画了一本小说。文字很少,图片很多。图片大到可以占据整面墙,而印刷使画幅缩小,被框在书本常见的尺寸中。那个画家看了很多诗集,也写了诗集,明显更加文艺。他画的大部分是人物,常常没有嘴,或者是嘴里流着鲜血。我手机里还留着一张在那个美术馆里的照片,照片里却没有画作,而是美术馆白色墙体上的一句话:你以为你是谁,敢评判月亮。
艺术评论就是从这些作品里生发出来的。和课堂上一样,我们都努力地去理解别人。然后对不能够理解充满抱歉。这世界总是缺乏理解。西西莉亚带我们看了很多很不错的展览,也拜访了一些艺术家,一个吸毒的拍鬼片写小说的人,一个每天扛着一大袋布片去台伯河里把布浸湿,然后扛好几公里回家拿各种材料涂抹,挤压,最后成为缝纫匠的人。一个不断重复copy一张照片直到最后成为完全不同于照片的作品的人。一个把肠子脑子倒进模具里的人。没错,那个人就是我在画廊里看到的那些肠子的创作者。我们走进她的工作室的时候,工作室的正中央还摆着一堆没有灌好的器官模型。原来器官模型都是用废纸盒子折成的,看上去很寒酸,一点也不像艺术品。
人都是这样稀奇古怪地活着的。在每一只眼睛里,都有别人无法理解和看不懂的地方。但是,有什么不好呢。
大概个性使然,2018年的最后一段,过得紧迫又刺激。我每天都像是打了鸡血,要把自己搞不明白的所有东西搞过一遍。时间从来没有那么紧缺过,我迫不得已记住了很多艺术家的名字,也迫不得已去看了英文书。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仍然只会成为一个答不出来题目的张口结舌的人。
交了第一个艺术评论文章,我才觉得自己有一点适应了这样的节奏。当很多事情扑面而来的时候,常常忙得毫无条理,一切结束回头再看,又觉得在无条理之中线条清晰。我很久没有写英文了,所以第一篇文章写得磕磕绊绊。后来拿了25分。这不是一个好成绩,大概算是中等。西西莉亚改得非常仔细,每一段都标注出她认为好的,或者不好的内容,甚至帮我改掉了拼写错误。西西莉亚在文章的后面写,Lin,你下次写文章可不可以简单一点,就用最简单的句子就好。你看你用简单句的时候非常清晰地表达了你的想法,只有这样,读者才会了解你要表达什么。
我觉得西西莉亚传达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艺评不能是艺术品。艺术品拥有一个模糊的大空间,而艺评要求体现精准的专业度和个人喜好。另外,语言与语言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分歧。英文和中文比较起来,确实在逻辑上要更清晰一点。我尚在一个慢慢过渡的状态,一切语言的碰撞都是那么明显。很多时候,我的讲述的顺序、措辞,都让教授们感到困惑———我们有两套思考方式。但同时,这种不同的思考方式也常常让他们感到有趣和新鲜。
虽然看到了这样的评语,却无益于我的第二次艺术品分析。因为我在收到第一份文章反馈的时候已经上交了第二份报告。我们的课程几乎是要逼疯人的节奏,作业一个接一个地来,让人目不暇接。即便这样,也比经济系医学系甚至文学系法律系的人幸福得多。我在报告中快要崩溃的时候一个文学系的朋友说他们要在两周内阅读完毕《尤利西斯》意大利文版本。考试的时候教授把那本书随手一翻,念出来一段话,请她来讲这话前后都有些什么内容———根本没有办法拿中文书来省时省力。
所以,几乎没有人能够跳过大坑迅速成长,只有不断掉进陷阱然后一次一次赶快爬出来才可以。就是这些大坑磨炼了人,让我们从坑里面爬出来的速度越来越快,连疼痛都懒得理会。
刚开始的一阵子,大概有一个月左右,我在每一堂课上都受挫,连吃饭的时候都唉声叹气,后来我发现唉声叹气也得继续,连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很快适应了沮丧,也从沮丧中努力振作。我想,年龄的增长实际上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很多事情都看淡了,心脏也强硬了一些。因为知道别无他法,只有坦然面对。2018年的后半段,我成了一个稀奇古怪的人。比如,半夜写完作业涂了大红嘴巴再然后双手放平,安然睡过去。那时候,觉得睡过去的时光也是活着的。虽然常常是死了一般地睡过去。早上醒来的时候不小心看到自己的脸吓一跳。
大约是我总麻烦西西莉亚额外讲一些别人都很明白的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对我多加照顾起来。在博物馆上课的时候,偶尔她会告诉我哪里有很好的关于现代艺术的图书馆可以去一下———但是我一次也还没有去过,因为根本没有时间。
我最后一次艺术品分析写了意大利艺术家LucioFontana,他是20世纪欧洲NewRealism的代表人物。这个人常常用刀子在一张单色画布上画出切口。有一天我站在他的画前面,想象了关于他作画的动态细节。那是我第一次想象自己是一个艺术家,进入另外一个人的世界,尝试着感受他的感受。
我不觉得这是一种误打误撞,我把它理解为自然而然。一整个学期,西西莉亚给我营造的,就是去尝试理解。理解艺术,理解世界,理解人。实际上,在我看来,艺术和文学的存在,就是人的存在。我们都只是在做一件事———寻找理解与被理解。
最后一场笔试,三个小时内我做了一堆题目,写了一个小论文,交卷的时候我非常感谢西西莉亚。那是一种奇异的感觉,她让我觉得自己有了价值。我第一次对理解20世纪的艺术有了信心,是她让我发现人的潜力真的巨大,尤其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作用力在这样的人身上,是十分惊人的。
交了考卷之后才去拿最后一次的文章,西西莉亚这次给了我28分。她说,想象Fontana作画这里,真是很美好的画面啊,我真的太喜欢。
我还没有来得及把她的评语读完,就听到她叫我:Lin,你来一下。
我走到她的身边,她说,你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里来,有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会有这样好的结果。———那时候她还没有看我最后的答卷。那里面我写了很多乱七八糟的语言,但是我很享受她的夸奖,一路上我跌跌撞撞,她从未夸奖,一直鞭策,在最后的几分钟,我终于得到了我想要的。而我发现,我得到的其实比我想要的多很多。
我們所得到的帮助,往往会好得超出我们的意想之外。
我常常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我在旅行中,看了大量的现代艺术,每看到一次,我就会想到西西莉亚。我的手机里有一张她的照片,她坐在美第奇别墅咖啡馆里给我们上课,她的身后是一扇打开的窗户,窗外是罗马的景致。那里有教堂,有宫殿,有城市的车水马龙。是一个古老又现代的世界。偶尔,我在某个瞬间会丧失“现实感”。但也正因为这样,却拥有了比“正常的”人们更深切的现实感。
在罗马的每一天,对我而言都是幸运,是想要留住的时光。我知道我将在此生深深怀念它,不因为我最终做了自己想要做的事,而因为我遇到了许多我想要珍藏在记忆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