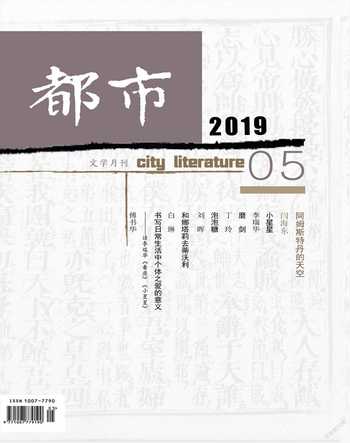泡泡糖
刘晖
我只见过蔡晓武一次。那年我六岁,蔡晓武八岁。在此后的二十八年里,我一直没有忘记他,有时会幻觉我在人群中见到他,同时知道我一定认不出他。蔡晓武的声音常常从我记忆的深湖中迅速浮起并水花四溅:
“我回家给小莉拿一个泡泡糖!”
小莉就是我,崔小莉。这是蔡晓武在我听力范围内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就跑开了,用我到现在都认为是极其敏捷潇洒的姿势。蔡晓武没有回来,没有给我拿来泡泡糖或其他任何东西。我至今仍然记得他,是因为他是我们华兴县里出现过的最白净最漂亮的男孩,因为他说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因为他右手臂上有骨折后留下的突起,更因为他说要拿给我却一直没有拿来的泡泡糖。那一天,蔡晓武随父母从新疆到华兴县来看他的爷爷,当天就离开华兴去了省城。
华兴县是一座偏僻的小县城。以前我在这里生活得还算平静,但是从我上小学之前的那个暑假开始,我发现自己不喜欢这座小县城,也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七月初的一天,我从午睡中醒来,看到父亲坐在八仙桌旁看书,母亲坐在八仙桌的另一边慢慢摇着扇子。我突然觉得母亲的姿势里透出十足的无聊,而看书的父亲比母亲更让人难以忍受,因为我看见他的一缕神魂从蒙着绿纱的窗子飞出去了,像一阵烟一样,斜斜地飞向巷子西边的王玲妹家。六岁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只发现自己不属于这个家,不属于我称为爸爸妈妈的这两个人。我从这一刻起陷入了没着没落的飘游和惶惑之中。我没有故乡,没有亲人,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谁掌管我的生命和灵魂。我成了一个沉默忧郁的孩子。
一个忧郁的孩子是比较麻烦的,因为没有人懂他们的忧郁。大人们对孩子的忧郁要么表现得十分不耐烦,要么就认为孩子根本不会忧郁。其实大人们才不会忧郁,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忧郁是什么,尽管他们整天都在操心,想东想西,担惊受怕,从来没有轻松快乐的时候。
我以忧郁为家,对自己的生活几乎没有感觉和想法,从来不对什么东西产生向往和盼望,直到我在县里唯一的百货商店看到泡泡糖。
百货商店是红旗大街上一座两层楼的建筑,离我们家所在的棉花巷不远。上世纪七十年代,华兴县城里楼房很少,居民们都直接叫它“大楼”。暮春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天气暖洋洋的,让人犯晕。母亲对我说:“你以后要帮我做点事了。洗碗洗菜你已经会了,买东西还不会。今天我给你两毛钱,你去大楼给我买一斤盐。我不和你一起进去,在外面看着你。”
我手里捏着母亲给我的那张绿色的二角钱票子,独自走进大楼。以前母亲带我来过几次,在一楼的食品柜台前买盐、萝卜干、大头菜等,有时也买几颗水果硬糖。她还带我到二楼买过布料和花露水,那比买食品有意思一些。售货员转身从架子上抽出竖在货架上的布匹,放在宽宽的玻璃柜台上展开。布匹内部的木芯在滚动中发出沉闷的声音。綠色的花露水盛在大人手臂那么粗的玻璃管内,挂在架子上。售货员接过我们带去的旧花露水瓶,将连接着粗玻璃管的针头插进瓶口,花露水便缓缓地、无声地注入瓶中。那个区域整个夏天都弥漫着冷冷的香味。
今天我独自走向食品柜台时有点心慌,觉得大楼好像比往常更大,柜台也比往常更高更长。柜台上八只装糖果的玻璃罐晶莹剔透,让我眼睛发花。那个我见过很多次的白白胖胖的女售货员像往常一样穿着蓝布工作服,戴着黑色袖套。她奇怪地看看我身后,发现我身边没有人跟着,便笑得露出一排白得发亮的牙齿,说:“你妈妈没来吗?”以前我母亲来买东西时,她总会主动和我母亲说话。她以前是我母亲的学生,母亲叫她小戴。上次我母亲买了海带和大头菜回到家里,对我父亲说:“小戴越来越胖了,身上圆滚滚的都是肉。你们男人是不是喜欢女人身上有这么多肉?”我父亲说:“你说什么呢?当着小莉的面。”现在我看到小戴对我笑,心里突然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她又软又暖的样子让我觉得舒服,同时我知道自己不应该享受这种舒服,甚至不应该觉得舒服。如果我不是这么紧张,应该能看到她胸腔里有一只彩色的大蝴蝶不停地扑着翅膀,腾起一阵阵粉红色的烟雾。
在等我回答的时候,小戴的嘴在不停地动,在咀嚼什么东西,但又没有咽下去的意思。我说我母亲没来。小戴问我要买什么,我说买一斤盐。她转身,拿起一只白铁大勺,弯下腰,从放在地上的大陶缸里挖出盐来,装进左手拿着的报纸糊成的纸袋里。她的背影像一只梨,阔大柔软,似乎有一股温热之气传过来。我已经平静一些了,所以看到她身上有粉红色的烟雾弥漫出来。纸袋装到一半之后,小戴转过身来,将纸袋放在台秤上,用空出来的左手轻轻拨动横杆上的秤砣,然后将右手举起,将大勺里的盐慢慢往纸袋里加。台秤平衡之后,她把大勺放回地上的陶缸里,回过身来一边折袋口,一边说:“你刚才看到我不断往袋子里加盐,是不是觉得我给了你很多盐?”我红着脸,放胆说:“是的。我知道你是跟陈秉贵学的。”陈秉贵是全国劳模,售货员的典范,他的一个突出事迹是卖糖果的时候先少装一点,然后不断地往袋子里加,让顾客感觉自己买到的糖果特别多。他的理论是如果先装很多糖果,然后不断地往外面拿,顾客会觉得自己买的东西在减少。
小戴吃惊地看着我,说:“哟,你还知道陈秉贵啊?你还没上小学吧,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我说,我是从我母亲备课时跟我父亲的交谈中知道的。我没告诉小戴,其实当时我已经能看懂《人民日报》和《新华日报》了。小戴说:“你妈老说你古怪,我倒觉得你挺聪明的。”她忽然开心起来,弯腰从柜台下面拿出一样东西,递到我面前。这是一个扁扁的长条形的东西,红白两色的包装纸两端像普通糖果的包装纸一样扭绞着。我能看得出这东西散发着甜味,类似于牙膏的味道,但比牙膏更甜、更香。小戴说:“看,这是什么?”我看清包装纸上面的字,说:“这是泡泡糖。”小戴说:“我现在嘴里就有一个泡泡糖。泡泡糖真的可以吹泡泡。你看———”她的舌头顶着嘴唇往外面努,然后带着吓人的白色伸出来,吹出一个鸡蛋那么大的泡泡。泡泡很快破裂了。她努动嘴唇,把破裂的泡泡收入口中,得意地说:“好玩吧?”我看得呆了。这是我沉闷生活中难得的新异景象。小戴说:“我们刚从上海进的货,五分钱一个。我正准备上柜呢。我刚才找给你七分钱,你要不要买一个泡泡糖?”我突然想起我母亲还在大楼外面等我,同时知道没有母亲的允许我不能买任何东西,所以有点慌乱地说:“不,我不买。”说完就转身往大楼外面走。小戴在我身后叫道:“你的盐,不要啦?”我再转身,脸上像烧起来一样,从柜台上拿起装盐的纸袋。
泡泡糖就这样以一种让人不安的方式进入了我的生活。后来我想,如果我所接触的第一个泡泡糖是母亲给我的,我会觉得新奇,然后高兴地享受它,它就成为我童年记忆里的一个光斑,甜蜜,明亮,单调,像快乐一样虚幻,却把心情熨得妥贴。但是,泡泡糖最先由小戴向我展示,就让我有了比较复杂的感觉———它有趣,不甚高雅,在粉红色烟雾的烘托之下散发着年轻女子暖烘烘的口腔气味,让我又向往又迷惑,还有一种说不清的紧张感和莫名其妙的羞耻感。我想要一个泡泡糖,但又觉得它离我很远,不相信自己能得到它。我到现在都认为,我的父亲母亲从来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他们不但不能给我想要的东西,相反会千方百计阻挠我得到自己真正想要、而且也能得到的东西。这么说来,他们既然能阻挠我的得到,恰恰证明他们知道我想要什么,而他们的行为也就更加不可理喻。
从小戴向我推荐泡泡糖那天起,泡泡糖就带着特殊的粘性附着在我的意念之中。也许是因为小戴吹泡泡的样子让我感受到异样的刺激,但我只是一个六岁的孩子,我只会关注泡泡糖,而不会玩味一个丰满漂亮的女售货员的姿态和表情。半个月之后,又有一个人向我展示泡泡糖,这人就是蔡晓武,华兴县医院蔡院长的孙子。
七月中旬的一天,棉花巷东头的蔡院长家来了客人。我母亲说,蔡院长的儿子媳妇带着孙子从新疆来看他。蔡院长的儿子高中毕业后支边到新疆,在那里结婚,生了四个儿子,其中第三胎是双胞胎,大的叫蔡晓文,小的叫蔡晓武。蔡院长家和我家隔着两户人家,平常静悄悄的,今天却人语喧哗。一个小时后,一群人从蔡家出来。我正好到巷子里的水井边提水,先听到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那样纯正的普通话,然后看到和我们不一样的人———男人女人都比我们这里的人高大漂亮,风度翩翩。那个男孩说话声音最响,皮肤最白。实际上,我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个和我差不多高的、有点胖的男孩。蔡院长带着那几个人走进隔壁人家。
我母亲说:“蔡院长的儿子做了官,礼数周全,看来要挨家挨户拜访呢。”我父亲紧张起来,说:“有这个必要吗?也不事先打声招呼,我们什么都没准备,怎么接待客人呢?”我父亲生性孤僻,平常如非必要基本上不与人交往,似乎世上任何人都对他怀有敌意,让他感到紧张。我母亲说:“人家也就是礼节性地转一转就走,你紧张什么?”我父亲还在唠叨:“你看你看,柜子上都是灰,多难看哪,早知道就打扫一下了。”
我父亲正说着,蔡院长他们已经到我家门口了。那个白胖男孩最先跳进屋内。我母亲依次说出我们家人的名字,蔡院长也一一介绍他的家人。那个穿着灰色丝绸短袖衫的中年男人面带笑容正对着我们,但我一直看不出他的目光落在哪里。男人低声对男孩說:“晓武,不要调皮。”那个男孩,我已经知道他叫蔡晓武,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叫蔡晓文。蔡晓武带着自来熟的派头走近我,端起右胳膊让我看那个突起的地方,告诉我他曾经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手臂,骨头长好之后就成了这个样子。我觉得那个突起很丑陋,但他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反而觉得它很值得夸耀。我悄悄看他的脸。我看到了一只白色的大狗,胖胖的,活泼的,笑嘻嘻的。我的掌心里有松软、干爽、暖融融的感觉,仿佛捋过一只生性快乐的大狗的脊背。
灰绸衫身边穿白底碎花连衣裙的女人显然是蔡晓武的妈妈。她从人造革手提包里拿出几样东西,放在我家八仙桌上。这时候,我也觉得我家的八仙桌太油腻,并为此感到难堪。蔡晓武从自己的卡其色西装短裤里掏出一件东西,递到我面前。这是一个泡泡糖。我太熟悉那红白两色的包装纸了,还有那像牙膏又比牙膏更香甜的味道。我看着他手里的泡泡糖,还没做出反应(实际上我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反应),我母亲这位光荣的人民教师,此时拘谨得像大户人家的婢女,说:“小莉,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连衣裙女子说:“晓武,这是爷爷给你的泡泡糖,你不能随便送人,否则爷爷会不高兴的。我们也带了泡泡糖,在包里,你要送小莉的话,自己去拿一个吧。”蔡晓武高声说:“那我回家给小莉拿一个泡泡糖!”他一边说,一边跑出我家。
说一口纯正普通话的来自新疆的男孩蔡晓武说要给我拿泡泡糖,我就等着。一直到晚上,蔡晓武还没有来。我知道他不会来了,但我的等待是个痴心盲目的孩子,依然等着他和他的泡泡糖。我越等越伤心,于是就伤心地等着。我在伤心的同时又有一种奇怪的安心,因为知道这伤心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父亲母亲对我的状况一无所知,我也不指望他们知道。他们不知道还更好一些。从那天起,我特别想得到一个泡泡糖。
开学后,我上小学一年级了。自从我第一次独自买盐之后,我母亲就经常让我买东西。我有时会扣下一分钱。三四个月之后,我有五分钱了。就是说,我可以买一个泡泡糖了。这时候班级里已经有几个同学在课间吃泡泡糖。他们吹出白色的泡泡,嘴唇显出奇怪的形状。我有很多次捏着偷偷攒下的五分钱来到大楼柜台前,看着玻璃罐里的泡泡糖。那红白相间的颜色,那细长苗条的样子,十分好看诱人。如果是小戴当班,她会热络地跟我说话,问我要不要买一个泡泡糖。我有钱,但我摇摇头。小戴说:“你没有钱,是不是?我可以送你一个。我看得出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我喜欢聪明的孩子。”她脸上有讨好的表情,胸腔里粉红色的大蝴蝶振翅欲飞。我摇头的幅度更大了。如果小戴不当班,我觉得那些泡泡糖并不十分吸引人,但却会在装泡泡糖的玻璃罐前呆更长的时间。
我上小学之后获得了自信,因为我成绩很好。我父亲说,我一年级时认的字比大部分五年级的学生还要多。其实我天生就认得字。我来自另一个地方,原本不属于这里,不是这个年纪和相貌,和我的父亲母亲没有什么关系,当然也不叫崔小莉这个名字。我经常梦到自己是一个三十二岁的男人,身材高而匀称,面容清瘦,拥有知识和才华,性格温文尔雅,穿着白色的确良长袖衬衫走在街上,含笑和迎面而来的人打招呼……
这样的梦一再重复。醒来后,我强烈地感觉自己和这个闭塞的华兴县没有关系,和我的父亲母亲没有关系,和这个名叫崔小莉的沉默的女孩也没有关系。我一头扎进书里,对我身处的世界充满怀疑和抗拒。
我的父亲母亲经常吵架。我母亲炒豆子般的言词中不时地迸出“小戴”两个字。他们吵架时的片言只语,对于八岁的我来说并不像他们以为的那样隐讳,我听出我父亲和百货大楼售货员小戴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戴向我展示泡泡糖的样子:她饱满的面颊,她努起的嘴唇,她咀嚼的样子,她口中吐出的泡泡……我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多么想得到一个泡泡糖,因为我觉得自己想得到一样东西就一定得不到它,于是什么都不想,越是喜欢的东西就越不敢想。我六岁时和新疆男孩蔡晓武一见如故,觉得自己和他有更多共同之处,但他一个落空的许诺像一把刀拿在他手上,将我慢慢凌迟。对我的凌迟一直在进行,至今没有完成,也不会有完成的时日。每当我看见泡泡糖,我就被那把刀猛刺一下。
我母亲越来越看不惯我,因为我看书太多。我上三年级以后做很多家务,买菜、洗菜、做饭、洗碗、生煤炉、购物,除了拆洗被子等实在做不动的家务之外,几乎什么事都做,但我母亲还是认为我看书耽误了做家务。我生活在这个家里,就像一棵树长在阴暗的墙角,不快乐,但没有办法移动,只能一天一天过下去。
我上五年级时,为了逃离让我苦闷的家,放开胆子放学后往郊外走。我想找到那个真正属于我的地方———在那里,我是一个三十二岁的男子,饱读诗书,温润如玉。
六月初,郊外一片金黄。迎面吹来的风携带着成熟麦子的香气。麦香扑到我脸上,我觉得自己也是香的,全身都香。我们家永远有萝卜干的味道,八仙桌的四条腿在黄梅天长满霉菌。麦田又美又香,让我欢喜得不敢相信。于是我没有在麦田旁边呆很久,决定留一段精彩章节明天再读。
第二天中午我再次来到麦田。吹过麦田的风更香,那是麦子折断之后身体里面的香———麦田里有一半麦子已经被收割,戴着草帽的农人坐在田埂上用很大的白色搪瓷茶杯喝水。有人抬起头,对我招手,說:“喂,小姑娘,你来做什么呀?”旁边的人说:“多文静的小姑娘啊。”七八个人全都看着我,对我笑,让我过去。他们的眼睛有的像马的眼睛一样漂亮,有的像牛的眼睛一样忧郁,也有的像猪的眼睛一样幽暗。我站着不动。我不怕他们,我的胆子比一般十二岁的小女孩大得多,因为我体内住着一个三十二岁的有知识有才华的男人———这样一个男人有什么东西是他害怕的呢?我想没有什么东西是他害怕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我害怕的。
眼睛像马眼的农人说:“小姑娘你过来,我给你一样东西。”他不说话的时候嘴一直在动,和小戴吃泡泡糖时一样。我走过去。这个面庞方正的马眼农人从身边抓起一把东西递给我。是一小把麦粒。和我想象中干燥如沙子般的麦粒不太一样,因为它们居然有弹性。马眼农人说:“这是新麦,很好吃,还可以吹泡泡。你吃吃看。”
我将手里的麦粒放入口中,慢慢咀嚼。一种亲切的涩味。淡淡的面粉的香。新鲜阳光的甜味。唾液越来越多。我咽下去一些东西。有些东西留在口腔内,粘粘的。我用舌头拨动它,它就和我嬉戏。我用舌头和上腭将它压成扁平的小饼,用舌尖轻轻顶住小饼中央,让它像小帽子一样罩住舌头,将气息从舌面上轻轻送过去。小饼破裂了。我再试,还是吹不成一个泡泡。马眼农人看着我,说:“这是我们的泡泡糖。当然,你们文化人叫它面筋。”
我嚼着已经发苦的生麦面筋,离开麦田和农人。我走向华兴县城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的崔小莉了,因为我已经尝到了生活的味道———生活就是一把生麦,它有着天然与人接近的气质,对人进行平顺的滋养,但永远吹不出理想的泡泡。
我的丈夫叫蔡晓文。我已经说过,我六岁那年想为我拿一个泡泡糖但又没拿的那个男孩子叫蔡晓武,蔡晓武有个双胞胎哥哥叫蔡晓文。我的丈夫蔡晓文一开始就是以他的名字吸引我注意的。当时,蔡晓文吸引我的还有他跳舞时口中咀嚼的泡泡糖。那应该是口香糖了,红白包装的长条形的泡泡糖那时已经很少见,多的是绿色包装的口香糖,比原来的泡泡糖更短、更宽、更扁。
八年前的春天,我下班回家时,看到小区布告栏上贴着一张醒目的海报,海报上最醒目的是“蔡晓文”这个名字:
前歌舞团著名舞蹈演员蔡晓文将于今晚六点半光临我小区篮球场指导交谊舞,敬请各位交谊舞爱好者到场,并相互转告。
当时我身边有两个中年妇女也在看这张海报。她们中的一个说:“原来是前歌舞团演员啊,我还以为是前线歌舞团演员呢。”我的注意点和她们不一样,我看到的只是“蔡晓文”三个字。那个白净的、有点胖的、说一口纯正普通话的八岁男孩蔡晓武就在我面前,说要回家“给小莉拿一个泡泡糖”。对我来说,世间没有话是随便说的,蔡晓武说要给我拿泡泡糖,就一定会拿,虽然让我等了整个童年加上半个青春。为实践一句诺言,为证明一句真话,再长的等待都是值得的,也是应该的。现在,蔡晓武让他的双胞胎哥哥来找我了。我一定要见蔡晓文。
我看到蔡晓文的名字时那样激动,就表明我其实知道他和我见过的蔡晓武没有关系。如果没有盼望时的激动来增加心理能量,我怎么能够积聚起即将在等待中消耗的大量精力,怎么能够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再疯狂的人也有他特定的逻辑,再荒诞的生活也有它内在的平衡。
那天晚上六点半,我来到小区北面的篮球场时,居委会的几个人已经将灯光和音响准备停当。在场地边缘的人群中,我觉得自己的四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僵硬。随着人群中的一阵欢呼,我看到一个穿着亮片燕尾服的男人走过来。居委会那个姓姚的女干事迎向他时挡住了我的视线。姚干事挽着燕尾服的胳膊,转过身来激动地告知众人:这位就是著名舞蹈演员蔡晓文。姚干事激动的样子十分贱相,让我瞬间变得心情恶劣。我僵硬地站在场地边,在《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的歌曲声中看透了我自己:姚干事没有惹我,我心情恶劣是因为燕尾服显然和我见过的蔡晓武没有关系,他不会给我带来泡泡糖以及任何东西,我仍然被亏欠着,仍然被欺骗着。
我潜意识中的自虐念头要怎样狂热,才会让我不离开篮球场?我不会跳舞。我上中专的时候从来不去舞会,现在也不想学跳舞,但我没有走开。燕尾服在灯光下闪烁,像从云端飘过来似的,令人眩惑。大约十分钟之后,燕尾服走向我,拉起我的手,把我带到场地中间。他衣服上的亮片做工粗糙,他脸上的胭脂近看有点吓人,他不停咀嚼口香糖显得粗俗,但我却在他面前激动万分,几乎不敢呼吸。当舞蹈大师蔡晓文轻轻托起我的右手时,我觉得自己正和他一起演出隆重的戏剧,而我入戏太深、人戏合一,成了一个我不敢设想、但愿意付出一切变成的那个人,那个女王,那个发光的存在,那个刺穿所有忧郁日子的光源。我像女王一样尊贵、自如、大胆,相信自己能够得到想要的任何东西———不,不是去找那些东西,而是像接受臣民的贡品一样,降尊纡贵地、优雅高傲地接过那件东西。
当时我不会想到,我像女王般认定属于我的那件东西,竟然是退职舞蹈演员蔡晓文的求婚。事实是,蔡晓文在见到我一个月之后就向我求婚了。
那夜小区篮球场上的露天舞会是我有生以来经历过的最浪漫的场景,它像节日灯饰一样漂亮,不属于日常生活。那时,人群众星捧月般围着蔡晓文,他的燕尾服在灯下闪亮,匀称柔韧的身材比衣服上的亮片更加炫目。他的姿态优雅高贵,每一个动作都协调优美。我被他迷住了。那夜的眩惑以及此后的回忆让我肉体蠢动而头脑简单。我答应了蔡晓文的求婚。蔡晓文随即搬进我的单人宿舍。
我心里住着的三十二岁的男人睡着了,我只是一个二十一岁的中专毕业生,工作安稳,收入不错。我忽然想到,二十一岁,正是华兴县百货大楼售货员小戴当年的年纪。小戴现在过得好吗?十几年过去了,她更胖了吧?她和我父亲还在交往吗?她和我父亲交往这件事并不让我反感,因为我觉得任何女人和男人在一起都好过我母亲和我父亲在一起。当然这只是设想。我还想,我虽然读过中专,有一份稳定清闲的工作,但我对工作肯定不像小戴那样投入———她当年向劳模陈秉贵学习零售技巧,我就没有那样钻研的劲头。事实上,我的直接领导不喜欢我,因为我把她的每一句话都当真。比如,领导要我们好好干,过完年带我们到桂林旅游,于是我就等着。但是直到第二年夏天,“桂林”两个字也没有从她口中出现过,好像中国根本没有桂林这个地方似的。她还说,以后每一个节日她都会送我们一份礼品,我又等着。结果,除了三八节的一条粗糙俗艳的化纤丝巾外,我没有在节日里收到她的任何礼物,而且那条丝巾还不是我们部门领导送的,是单位工会发给所有女员工的。以我这样的性格,我的生活不会很轻松很快乐,不会像小戴那样充满热情。我想,我和蔡晓文订婚之后,生活应该会有点不一样吧?尽管蔡晓文在教女人们跳舞的时候过分热心,尽管他不记得我的生日,尽管他从来没有热烈的语言和动作,但我相信这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结婚以后一定会不一样的。
但是,和我同居的未婚夫蔡晓文一直不提结婚的事。我二十三岁那年,在第二次为蔡晓文做了人工流产手术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对他说:“你到底什么时候和我结婚呢?我已經跟了你两年了……当然我还不老,可以等,但是如果下次再怀孕呢?我不想去做人流了,我想把孩子生下来。”
蔡晓文说:“你知道,我从歌舞团退养后在电影院工作,电影院现在很不景气,我收入不高,整天还要到大单位去找工会主席软磨硬泡,让他们给职工买电影票作为福利。小莉,我要给你幸福,但我现在没有条件给你幸福。你再等等好吗?”
蔡晓文三十八岁了。他还是很帅,身体还是很柔韧,经过表演训练的眼神富有感染力。当他用罗密欧式的眼神看着我的时候,我的心立刻融化了,不会去想世上根本没有三十八岁的罗密欧。他又说:“我知道我让你受苦了。我会疼你的。”
我忽然想到,我的身体是因为他而倍受伤害,他欠我很多,我是他的债主,但我却如此依附他,把自己和他紧紧捆绑在一起,从未想过要离开他。我心里那个三十二岁的男人慢慢醒来,睁开眼睛,看到我的处境如此荒唐和悲凉。可是,我面前三十八岁的罗密欧更漂亮、更无耻,因此他赢了;那个三十二岁的、左手拿着理性、右手拿着直觉的男人,那个又聪明又纯洁的男人,再次沉睡。他生气了,离我而去。有多少守护天使因为人的愚顽而离去?天空中布满翅膀,如云掠过。
我是在二十五岁那年和蔡晓文结婚的。那是一个美好的暮春的黄昏,他像往常一样在我做好晚饭时回家,时间掐得真准。吃饭时,我对他说了居委会姚主任告诉我的关于他的传闻:他从歌舞团退养不是因为像他说的那样个子太高找不到舞伴,也不是练功太辛苦导致右腿韧带拉伤,而是他和团长的老婆睡觉。我并没有兴师问罪,相反我说得很轻松,甚至有点开玩笑的意思,因为这个传闻太庸俗、太没有想象力了,我根本不相信。蔡晓文笑笑,没说什么。他已经四十岁了,笑起来还是那样迷人。他那种脸型和五官真不显老。在一个恍惚的瞬间,我看到他的脸和八岁男孩蔡晓武的脸重叠在一起,又突兀又协调。我吃了一惊,但又奇怪地感到心安。
那天晚上,蔡晓文在床上的表现比平常弱一些。匆匆完事之后,他说:“小莉,我们结婚吧。”
我忽然问出了我以为自己永远不会问的问题:“喜欢你的女人很多,你会对我忠诚吗?”
蔡晓文不假思索地说:“我当然会对你忠诚。你是我的唯一。”
我又问:“我过生日的时候你会送我礼物吗?”相处四年来,他没有给过我一件礼物。
他说:“会的。”
我追问:“你打算送我什么礼物呢?”
他看着屋顶,说:“我要专门为你编一个舞,跳给你一个人看。”
我开心极了。六岁以后,我从没想过自己还能如此开心。
几年来我对婚姻有过种种幻想,但是真正到来的完全不是我预想中的婚姻。事实上,婚礼那天我完全没有笑容,花了很大力气才克制住想要对蔡晓文发火的冲动。不错,我有一个漂亮的丈夫,但整个家里也只有丈夫漂亮罢了———这些年他给我的钱加起来不超过五千块,新房装修、家具、电器都由我负担,我的结婚礼服和几身新衣服都是自己买的。我还给他买了一套燕尾服,只是不带亮片。他穿燕尾服的样子实在令人赏心悦目,我认为熹城所有男人都应该知趣地终生不穿燕尾服。
我在六岁那年夏天遇见一个面颊饱满鲜润、有着明朗笑容的男孩,从此念念不忘。蔡晓文面容清瘦,轮廓分明,和八岁时的蔡晓武完全不一样。蔡晓文当然是漂亮的,可是漂亮对于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来说实在算不上优点。广场上的交谊舞已经不流行了,但蔡晓文仍然有用武之地,他被文化宫的承包人聘请去教拉丁舞。他得意地对我说,文化宫为他专门开辟了拉丁舞教室,他是文化宫招徕舞客的头块牌子。他每天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出门,回家后精神饱满。我不知道他挣多少钱,他从来不给我家用,我也不向他要。他在服饰上越发讲究,一身名牌,头发整齐油亮,看来收入颇丰。
结婚八年,蔡晓文一直没有提起过当初答应为我编排的舞蹈。我一直记得他的承诺,觉得这个承诺本身就很浪漫。我认为心中的浪漫才是真正的浪漫,所以它能否变成现实并不是很重要。这个承诺是一个美丽的泡泡,它的形状、弧度、色彩和光泽都让我不忍放弃,也不敢接近。
买房需要蔡晓文的身份证,他正在文化宫上班。我给他打电话。手机通了,但他没接,也许他正在上拉丁舞课。下午两点,我到文化宫找他。电梯门在三楼打开时,《卡门序曲》扑面而来,带着浓烈的异域风情。走廊昏暗。从下午两点的阳光下走进这样昏暗的地方,我一向脆弱的眼睛根本来不及调节,头晕得厉害。我拉开拉丁舞培训室那扇包着棕黄色人造革的沉重大门。
里面更暗。在暗处,我的丈夫蔡晓文依然闪闪发光———他和一个腰身丰满柔软的女人搂在一起,脸对着脸,表现出拉丁民族的全部激情———他们不是在跳舞,他们甚至没有听到音乐,他们就是搂在一起,像一个立体的却又呆板得骇人的太极图。舞蹈室里没有其他人。没有正经人会在下午两点把自己放在如此阴暗的地方。
一男一女感觉到我,同时向我偏过头来。我认出那个丰满女人是十多年前居委会的姚干事,后来的姚主任,现在的姚董事长。
我如释重负。我上初中时解代数题就是这种感觉———我不喜欢那些题目,但我需要答案,所以不惜付出时间和心血去找出那答案。过程很痛苦,过后也得不到什么,但题目解开了,我就放心了。一直藏在我生活中的答案就是:蔡晓文说要对我忠诚,但我不相信他的忠诚;我盼望一些美好的东西,但我肯定得不到。生活一再向我证明我是对的。
生活是一团生麦,永远吹不出理想的泡泡。我的婚姻是泡泡糖———虚假的甜蜜和饱满在空中破裂,没有被遵守的诺言在风中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