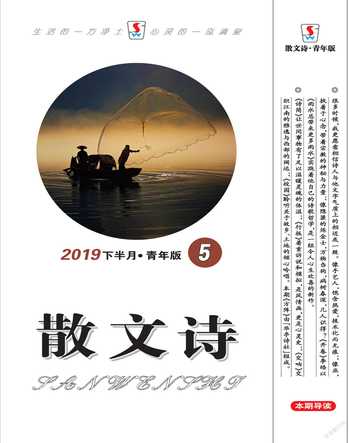灵魂麦
赵利勤
“小满十八天,不熟也风干。”意思是说,小满节气后大约十八天,麦子就是没长熟也不长了,必须要收割了。可这句话是对于水浇地来说的,我们家除了水浇地,还有坡岭上的旱地,因為不能浇水,麦子成熟得更早,可以说,每年小满刚过,父亲就开始磨镰割麦了。
坡岭地在村子的北面,离村有五六里路,还要上一个高坡,走过大路还要走小路,因为地形所限,小路也就成了羊肠小道,起伏曲折,不能拉架子车,走上十分钟才到。麦地就在小路的旁边,一层层,一弯弯,梯田似的,依高岗处是荆棘,临边是用小石块堆起的坎儿,麦田就在那里,或平躺,或微倾,反正不能浇,只要能种上麦,靠天收。风调雨顺就多收一些,干旱少雨就少收一些。天旱得久了,颗粒无收也是正常,好在还有坡下的水浇地。我记事的时候,生活虽算不上富裕,但家家差不多已经能吃饱饭了,所以,人们并不单纯指望着坡上的麦子丰收,只不过是不闲着地罢了。可是,父亲却不这样,虽然不能浇,但他依然把地拾掇得平平坦坦,这样,有雨的时候,可以多留存一些水,麦子相对长得好些。为了这一点点的平坦,父亲每年播种前都要用耙子在地里多耙上两天,每耙到石子,哪怕只有枣大,他也要弯腰把它拾起来。
那时,母亲就劝他说种地不用那么细心,谁家地里没有石子?再说又不是水浇地,你还靠它过日子?父亲却说,不管贫地肥地,旱地良田,都好比是庄稼汉自己的孩子,哪有嫌弃孩子不争气就不好好管教的?越是有缺点的孩子,越要好好教育啊!当时,父亲还年轻,像大山一样,有的是力气,母亲也就任他去了。可是,麦子却并不遂人愿,常常因为天旱,长得只有一拃高,稀得能数清棵数。
后来,人们的生活条件渐渐好了,很多人家外出打工或在本地工厂干活,他们感到种地出力多,收入少,连能浇的良田都不想种了,更别说离村远、收获少、种着费劲的坡地了,所以,高岗上的麦地荒得越来越多了。我们家虽说父亲年过六十,不能出去打工,但我们都有工作,也很想让父亲把地租给别人种,至于高岗上的旱地,更是没种的必要了。可每年,趁种地的时候,和父亲一合计,他依然还要坚持种,并说,旱地种上去就不用管了,只等收割就行了,种着省事,荒着可惜了!
其实,旱地只是没办法浇,平时除草打药父亲没少过一次,特别是到割麦的时候,平地割麦有收割机,而旱地还得用镰刀割,然后打成捆,顺着山路,曲曲弯弯,背到大路上停着的架子车上,上坡下坡地拉回来,还要晾晒、捶打、趁风去皮……又麻烦又累人。零零散散六块地,还不到一亩,父亲为此忙上十来天,收获的还不及别人做一天工挣的钱多,可父亲却说:“有收成就好!看见地荒着,我闷得心慌!”
那些天里,父亲天一亮就拉着架子车,当然,有时是母亲或者我和他一块儿去。可割麦不到半个小时,我腰就疼得直不起来,父亲就让我坐到树阴里等他,直到把架子车装满,我们才一起拉着回家。我坐在地头的石头上,感觉吹过脸庞的风也是热的,坐在树阴里也汗流不断。看着父亲黄铜色的脊梁在烈日下渗出滴滴汗水,渐渐汇成小溪一样在身上流淌着:听着父亲闪亮的镰刀在低矮的麦丛中嚓嚓慢响,迟缓得像快死的鱼一样在麦浪里挣扎着;望着麦子只有筷子高的麦秸、花生大的麦穗,稀疏得像做操的小孩子一样在地里站立着,再加上周围别人家荒芜的土地,不远处层层叠叠的秃岭,辽阔的天空和渺小的父亲,我终于忍不住流出了眼泪,而且和着汗水,越流越多……
劝父亲是没用的,因为地是父亲的灵魂,直到他因病卧床不起,直到他躺进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