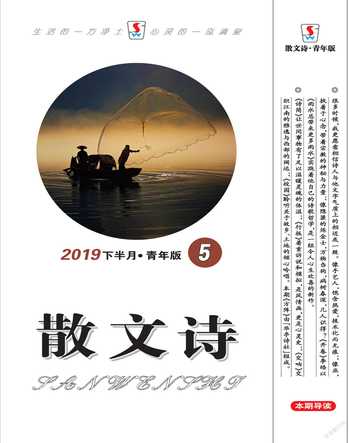短租
2019-09-10 15:55:56徐凤叶
散文诗(青年版) 2019年5期
徐凤叶
上海的冬天,铅灰色的云块,又厚又脏,总也擦拭不净,连雪都下得节制。隔壁又换了人家,窗台上放着布娃娃。
东安路270号四围,陷落在城市边缘的族群,和那些漂在北上广的人一样,来来去去。街角,一个穿灯芯绒裤子的男人,繃直被岁月磨白的膝盖,点燃一支烟,抽空自己。暮色压过来,他抖落肩胛的青灰,决然转身。街灯疲惫,挤出了几声迟疑的咳嗽。
我和树梢的风一样丧失了方向。夜潜伏在胸口,月色的鞭梢抽打着影子,湿滑又清亮。腊梅的香气刺穿冰冷,正像长长的针头穿刺在我的脊椎。
月亮圆睁,在眼眶里,打转。
春天时,隔壁住着的姑娘,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却爱了她一辈子。
猜你喜欢
金卡生活(2021年9期)2021-09-13 11:16:30
牡丹(2021年17期)2021-09-11 23:28:38
小小说月刊(2019年19期)2019-11-14 03:19:38
小小说月刊(2019年10期)2019-10-21 05:56:33
作文周刊·小学一年级版(2019年28期)2019-09-07 03:42:03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2019年1期)2019-03-01 05:41:12
小资CHIC!ELEGANCE(2018年22期)2018-07-06 08:46:44
永善文学(2017年1期)2017-07-18 22:44:52
中国房地产业(2016年9期)2016-03-01 01:26:28
中国工程咨询(2014年1期)2014-02-16 06:2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