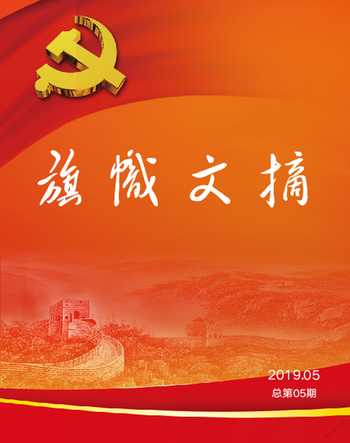令人警醒的历史反思与人性考量(评论)
李掖平
中篇小说《遗忘》的作者尤凤伟,是1980年代即蜚声文坛的“文学鲁军”中一位实力派作家,从1977年发表作品至今已有四十余年。在这近半个世纪的风云流转中,其创作一直秉持鲁迅先生倡导的直面人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现实主义立场, 沿着历史重述和現实关照两条主线展开。历史重述类小说,注重在纵向性时空坐标中解剖特定年代的历史现象,通过还原重大场景重要事件,重塑身处社会转型风雷激荡大节点处的人物群像,还原其芜杂微妙的心灵图像,对过往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寻根溯源的深刻反思。代表作有《石门夜话》 《鬼子来了》《中国一九五七》等。现实关照类小说,则注重在横向性时空格局里向社会日常生活内部深辟,扣住矛盾冲突和人的心灵创伤及精神痼疾,聚焦时代症候、关注民生热点、書写底层苦难、考量人性沉浮,代表作有《泥鳅》《中山装》 《金山寺》《命悬一丝》《水墨》等。
《遗忘》以冷峻的反思意识和沉厚的悲悯情怀,将历史与现实相勾连,由一个五十年前的刑事案件引入了对当下官场现状以及贪污腐败问题的描写揭示。通过寻访打捞这桩历史命案的种种蛛丝马迹,在既是旧案嫌疑人又是当下贪腐高官初永新的生活历程中,剥离出一个个令人震惊的历史和现实秘密。不仅展示了纠结于历史/现实、忠诚/背叛、正义/邪恶、真相/假面、惊恐/沉痛等巨大漩涡里的隐秘复杂的心灵暗影与人性脉动,进而寻根索源其历史、政治、哲学、经济和民族心理等多元传统基因,标示出一种清晰可见的现实主义高度与深度。
小说的故事情节在一个过去与现在的时空并置框架中展开和推进:刑警范强受命组队侦破“无名白骨案”,几经走访调查,锁定了这是一起发生在五十年前“文革”时期的历史旧案,犯罪嫌疑人初永新也露出水面。但这个初永新却是一名以常务副市长身份退休多年的高官,范强数次问询查证都被他以年代太过久远记不清了予以抵赖,案情调查一时受困。受富有侦破经验的老干警点拨,范强转而调查初永新的现实经济犯罪案,经过数次精彩紧张的心理对峙和情感博弈之后,最终迫使初永新承认了自己五十年前犯下的罪孽,命案水落石出。刑警范强破案立功之过程,既是探寻人性罪恶之源、体制漏洞之殇的过程,亦是警醒读者对抗习以为常的可怖性遗忘,复苏小到个人大到民族国家必须留存的历史记忆的过程。
小说的叙事空间在历史与现实的回环对照中不停转换,“文革”初期初永新以非法手段绑架常宗宝企图夺权之时,漫天的落霞已然见证了他盛满罪恶的潘多拉魔盒的开启。而经过五十年的兜转后,他起高楼,宴宾客,不断放纵贪婪的欲望,于贪腐道路上愈走愈远。这背后利欲熏心的人性之恶不禁让人唏嘘,理想信念的抛弃与崇高信仰的缺失引人沉思。由此看来,小说的命名确实别有一番深意。作者将这桩刑事案发生的时段设置在五十年前的“文革”背景之下,并且围绕被害人常宗宝设置了犯罪嫌疑人、“文革”时代和现今时代的三重“遗忘”。不仅时空背景得以有效延伸,文本内涵也更加丰富深邃,一个蕴含着双重警醒之意的巨大时代隐喻浮出水面:一是初永新对常宗宝的杀害,隐喻着当年的文革悲剧,隐喻着在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下人性良知与理性的扭曲破碎;二是初永新连环套式的系列“遗忘”,拧成了一条清晰的因果链,隐喻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一富含哲理性的精神命题。在过去与现在的时空穿梭中,初永新可憎面目有源可溯,当下的贪污腐败、为官不正的作为,正是其“文革”时不惜杀人争权这一狂妄行为的再次上演。由五十年前对自己非法绑人行为的遗忘,到后来对“文革”历史之痛的遗忘,再到对人民干部应有的初心与良知的遗忘,小罪终于积成大恶。由此,尤凤伟以过人的胆识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文革”背景下发生的不论有意或无意的伤害,遗忘固然不行,但今天的我们又该怎样从历史劫难中吸取教训,如何将深刻的反思精神融汇于民族的血液中?
《遗忘》的叙事形式亦可圈可点。从结构上看,情节的铺衍并非捋着一条反腐线索贯穿到底,而是将范强受命破案、日常工作、生活情感三条线索拧在一起有主有次交叉推进,情节生动丰富但绝不散漫,叙述节奏缓急相间张弛有度,人物性格得以多侧面多角度丰满。与此同时,刑侦、悬疑、反腐、官场、爱情等多种元素杂糅一体,满足了读者的多种阅读需求。案情侦破过程一波三折而又环环相扣,针对破案遇到的难题逐个击破,无论是刑警现场勘查还是多方调查走访,无论是警察内部人员的逻辑推理还是外部人事因素的干预,抑或是让人疑窦丛生的各个环节安排以及缜密精细的细节设置,都显现出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小说以初永新承认五十年前的过失致人死亡案作为结局,但文本依然留白出一个巨大的可言说空间,由“范强的心不由得劲跳了一下”这句话作为收束,意味深长,让人突然察觉其实事情也许并非如此简单,也许比我们了解的更加不堪。仿佛逐渐缓慢下来的曲调突然高扬而后戛然而止,留下耐人寻味的余韵。真相与谎言的迷雾之中,事情的本质和真相究竟如何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引起了令人警醒的历史反思与人性考量。
责任编辑 师力斌
(:北京文学2019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