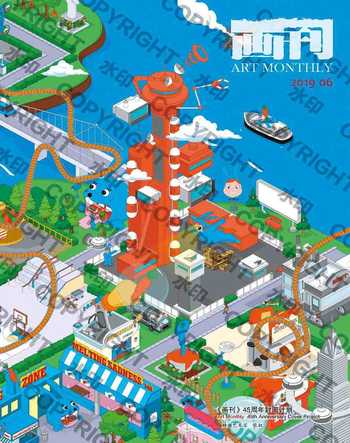山水之光
张春旸

想写一篇山水精神与山水之光有关的文章。就像孔子所讲的:智者爱山,仁者爱水。我理解这不完全是说智者去喜爱山水,而是山水能培养出人的品质。就像我特别喜欢王阳明的心学,人在不断格物、不断地致良知过程中,在自我的心性中强大,超越自我,这是人的伟大之处。如同人在宗教情感中所要焕发出的精神吧。就是在超越自我的过程中跳出自我的情绪感受,获得一种光芒的为人品格。从山水的品质里与心性的开阔里,寻找到了一些可贵之处。这是我在这批风景画里体悟到的收获,也是我画风景的内在需求。面对自己,如何用熟悉的油画形式,画出我个人不一样的理解。同时,我在大理的地理环境中体验到一种具体的金色的光,像人性里的一种光芒!绚烂、灿烂与温暖,对我是一种指引。如何将这种对光的向往指引内心,以一种更博大的情怀与之共存?与其说这批风景画是对自我的挑战、对更加完备自我的向往、对自我的修炼等等,不如更贴切地描述为:尝试不断地超越自己,超越现有的情感与人的状态。就像我以前是追着光芒跑,直到光芒驻足心里。在心中有饱满的光明的状态,这是我从山水中获取的品质:一个画家从自我的困惑与迷茫到与自我的和解,都是在寻找一种近乎宗教情感的品质。在获得这种情感之后,能够将它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地回到生活的原点。用这样一种更广泛的人类情感,包容了以往的曾经的所有。这种宽容的感受就像水一样,具有无限包容性;而山的笃定、雄壮与坚韧,可能是在绘画中培育出来的或者提炼出来的,焕发个性中最坚韧的一面。乐山与乐水,遂山与水的品质连同阳光炙热地照射进我内心。感叹天地间同一个太阳,这接近赤道带的阳光曾经给予艺术大师们的慰藉,在我的这批作品中也能找到。

我曾把中国的古典山水画和西方的印象派之后的绘画建立了一个比较关系,通过比较中国绘画的章法与西方印象派之后的绘画语言,如何以绘画元素来构成绘画的共通关系。比如,线条作为一种绘画元素而存在,色彩凸显出来成为更加纯粹的色彩。色彩和线条构造一种对空间意识的理解,绘画语言的内在逻辑像中国绘画的章法构成。这种知觉心理的感受从属既定的范式,比如开合、疏密、曲直等许多相对的元素来构成空间关系。那么我理解到的印象派之后的西方绘画,就是线条与色彩都相对突出出来,空间关系也区别于以往西方油画光线的理解。把人的因素融入进来,人在绘画中游走穿行。在一个更为广袤的空间里,人是很小的,在与天地相契合的大道中,人的情感是低微的。如何在山水画中追求开阔的大山大水的视觉精神?中国山水画中产生了一种纯粹的水墨,其实黑白就是一种光,应该被更贴切地描述为一种心性的光明。不是寻求外在的光影的变化,而是引申到人的心理层面去导引出光的存在。中国绘画里一直在讲人的修养,如石涛的“一画论”,一笔就能画出人的修养。这里面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所理解的绘画里生成的智慧就像光芒一样,把光引入心里,然后这个光从内心中不断地散发出来,我以一种比较抽象的方式来解释中国古典绘画对光的理解。就像一个人的自我修养,自我不断地提升,不断地修为,不断地像圣人一样去引导自己的心性。这些修为其实都是对光的精神内化,人格中的光芒才从绘画中被带出来。一个人绘画里存在的这种绘画语言关系,其实和他的个性与一生的经历有关,画里的光是个人人性光芒的延伸。比较中西画中对空间关系的理解,如何在人心的光芒里表达对空间关系的独到的理解。


就我个人的绘画来说,来到大理之后,结束了《马语》系列。马其实是我对宗教情感的追求,对自身不具备的心理上的向往,而后我迫切希望回到现实生活中。居住在大理,喜爱亲近自然,常常爬山,每每站在苍山上眺望洱海,如同攀登与攀越就是我的修行。所以近一年半,都在画风景里的光,画上山的路,就像不斷地引导自己,走到那种光明中。于是我的绘画里出现了一些比较硬朗的一面,在山水与光明的描述中,可以说我重新塑造了自己,让我的品质与性格变得更加浓重与厚重,也更加简单了。这些绘画让我对光明的追求更加迫切,充满了希冀与向往。我感觉自己的生命热情也由此被点燃了,生命变得更饱满。就像王阳明说的人性的光明,我把光注入我的心里。其实我的绘画里的山水就是我的生活指引。我在画风景画时,常常想象塞尚晚年在画圣威克多山时候的情景,他通过简单的色彩,在晚年的绘画中营造出的那种光。我觉得人性的光芒与绘画中的外在的光是同质的。一个人的个性与绘画语言完全融为一体。绘画是对自我情绪的一种安抚,同时是对自我的指引。我在这些风景画中所追寻的,其实和这些大师所做的一样,我把我的心性通过山水画培育出来。我在绘画的过程中,修行与不断地度化自我,在山水画中我又超脱了自我,进入山水——自然——大道这一中国传统的山水精神的命题,由此遵循生命个体体悟的绘画语言应该不分中西。所以,我感觉山水之光是这批风景画所要表达的主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