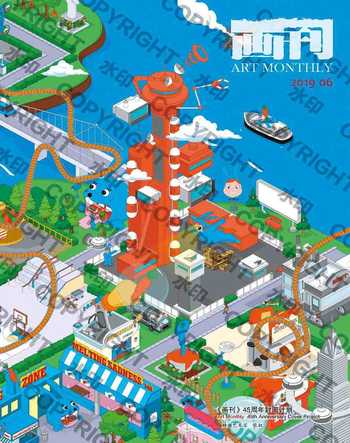一些被动物咬过的名字

秦三澍作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巴黎高师—法兰西公共学院“知识共和国”实验室博士研究员,从他的文章《一些被动物咬过的名字》中,你轻易就能嗅到在他的“007”中,洋溢着夹杂在各个语种中文学工作者的忙碌气息。当他为这篇文章匆忙安装完最后一个句号,便立即冲向巴黎机场。按照计划,6月15日下午2:30,他必须出现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主办的“诗歌来到美术馆”第五十七期“秦三澍诗歌朗读交流会”现场。他在“007”中向我们展现了命运中必然会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来路不明的痒,和他卓有成效的挠,然后是所有被挠过的地方通通变红。
——丁成
从这周第一天开始,我就发现胳膊上时不时浮现成片的小痘。很痒,挠了之后会变红。第二天就像被蚊子咬过。我以为是喝红酒过敏。我以为它们一般在晚上8点到8点半之间出现。这两个假设在一周之内被反复验证过。不过它们帮了我一些忙。每当我在人群里插不进嘴的时候,我就挠胳膊。需要低头,并且,不需要去看说话者的眼睛和嘴。彼此都轻松。
在阿爾勒国际文学翻译学院(CITL-Arles)驻留的最后一天,我很艰难地8点多起来,10点准时到楼下的图书馆开讨论会。为了合群,养成吃早饭的习惯,还要喝咖啡。一群年轻译者合伙把美国诗人Eleni Sikelianos翻译成法语。他们常常看起来同意了对方的意见,却在稿子里加塞完全不同的东西,一旦暴露就要彼此温柔地翻白眼了。在南部,鸟都懒得飞,只有猫整夜撕心裂肺地嚎叫,我也跟着天天犯困,唯独大家吵架时最清醒。我喜欢看别人吵自己却不吵,尽管这种吵法其实一点不费神。但今天连这样的好事也没有。来了几位协助我们定稿的“专家”,他们说话一般都很轻柔悠扬,显示某种权威。一上午我都在专心看身旁的黑发法国姑娘Ninon在译稿上画龙,《权力的游戏》里面那种,好像也混了一点中华血。她画得最好的是“龙鳍”,这是我四天后才想到的译法:我回到巴黎和齐悦翻译“Emmanuelle Sordet”的时候遇到一个词组“les crêtes de ton dragon”,显然不是指中国龙的两只角。Ninon带了小学生的简便水粉颜料,把这几天用来讨论的稿纸都当成了调色盘,又把每个选颜色的时刻都当成盛大的仪式。但我最惊讶的是她在认真上色的过程中还能头也不抬地发表对翻译的意见。关键是,还赢得了赞许。

这件事我确实做不到。而且作为这次工作坊唯一的非欧洲语言的母语者,我做不到的事儿还很多。下午分配好晚上朗诵会的任务,我一个人坐着练习,有点怯场。我自选的法文译本里有一个长词的连续辅音让我发得很惆怅,我真心觉得中国舌头不适合读法语,但偶尔,我也怀疑这跟牙齿的位置关系很大。我的同行们去楼上卧室休息前,都要从我身边走过,略微停一停:如果你需要我陪你练习,不要犹豫哦!我回答得都一样:那行,请坐,陪我练吧。我觉得跟法国人相处的一个原则,就是他们既然要帮助你,那你就接受好了。到了晚上,Eleni每读一首英文诗,我们就挨个读相应的法文译本。她读到重音时朝前扭动的右肩依旧具有侵略性,而且相对于上周五在高师的那场,她在聚光灯下更有存在感。轮到我,我还是囫囵吞枣地读错好几个词,而且错的地方都是练习的时候没错过的。紧接着就是我译成中文的诗。我故意调整了速度,把三行本来断开的句子连成一气,我自己也惊叹竟然可以读得这么流畅。现场有几个观众很配合我,惊呼般地吸气。从气息的强度我能听出来,是一些老年观众。

果然,晚上冷餐会的时候,几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来找我握手,说,太棒了,你的中文翻译,美妙啊。他们用浑浊但坚韧的眼神暗示我,只是表达一下赞美,没什么别的想说。可能他们也怕我反客为主地提问:您倒是说说怎么个美妙法。我的译者同事Johana插嘴,我听懂了“分钟”!她有一点汉语底子。我说,你都听懂了“分钟”,难道就没听懂“分钟”前面那个“一”吗?她拿新买的有徕卡镜头的华为手机给大家拍照,炫耀拍出的照片多么有大片感。这是中国牌子,叫Uawei(哇为)。她扭头示意我也发表发表意见。我说,对,中国的,准确的发音是Huawei,我觉得不太好用。但法国友人很信赖她的免费广告,排着队央求她拍大片。其中一个科西嘉来的胖胖的姑娘一直不满意照片里她的下巴,反反复复换了好几个仰角,结果轮到我时,天都完全黑了。Johana觉得我既是最后一个客户,又是客户里唯一的中国人,必须好好感受一下“哇为”,耐心把我头发拨到右边,又拨到左边,总觉得不太合适。我都替她犯愁。然后,你手扶着露台的栏杆,对,但手别太紧,微微弯曲手指就行。哎,对。右腿向后抵住墙,脚抬高,对对。很好,头抬高一点。我已经抬了啊。而且,我脸型不太适合仰头吧。不不,很适合,这样才能大片。



晚上大家玩累了去睡觉。胳膊又痒起来,我几乎要归咎于晚睡了。有几个打算一大早离开的译者过来道别,说了很多温柔的话。大部分人都对我暑假不留在巴黎感到遗憾,又说,9月份再见倒也不赖。我回房间,计划明天按照翻译学院赠送的地图去把阿尔勒的历史文化遗产都逛一下,但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没了兴致。露台上晾着的浴巾越来越少,我知道一半人已经离开,一半的一半并没有回巴黎,而是继续南下了。回巴黎的高铁上,我接着看已经看了三次都没看完的电影《末代皇帝》,溥仪和婉容的激情戏本身不激情,而且溥仪满脸的唇印让我觉得很恐怖,想起蒙巴纳斯公墓那块最著名的石碑。我身边的金发小男孩一直在偷瞄。对不住,只能退出全屏。我礼貌性地也回瞄了他的屏幕,他正在看油腻的当代家庭伦理剧,还不如我呢。傍晚出去觅食时,在T3a电车上见到了家骏、他老婆和他们的三条小狗。我在巴黎经常毫无准备地碰见家骏。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刚才不是还给我朋友圈的照片点赞吗?而且你不是在阿尔勒吗?怎么回事?我说,我还刚想说,原来这几只狗就是照片上那几只啊。显然狗们走累了,扒着我的腿要抱,但我不敢。没抱过,怕它们不舒服。

被狗狗一阵猛舔之后,我觉得胳膊又开始红了。我终于去了Place Monge那家被亚洲游客挤爆的网红药店。你最近住宾馆了?还真是。但我没必要说CITL不是严格意义的宾馆。光头药师严肃地说,你好像被L*****咬了。那是啥?啊,没什么,我是说,你被一种动物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