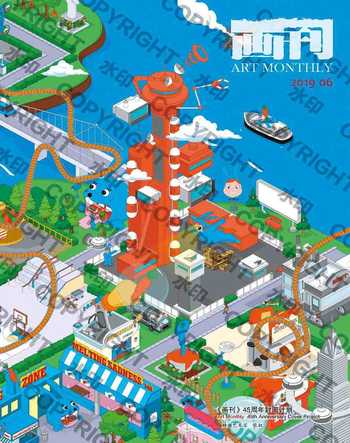我每天都在死亡
一旦处于极度的悲伤中,人也许瞬间就会变成另外一个物种,曹久忆就是个鲜明的例子。命运的黑手,能够让好端端的人生,在不该停的地方停,在不该转的地方转。本期特稿,把曹久忆的文章放到第一个推出,是想表明,人生在很多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得从结束的地方开始。曹久忆是音乐人,本来要么和一堆乐器搅和在排练房,要么和形形色色的观众狭路相逢在音乐现场。然而最近的一个“007”,他却不得不浸泡在丧父之痛的情绪中,披麻戴孝地安守于父亲的葬礼,因此他的文章《我每天都在死亡》,既可以看到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单向告别,又可以看到一个音乐人对死亡和生活的双向思考,甚至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宏大的等待和仪式结束之后的空虚和疲惫”。
——丁成

我每天都在死亡,有时候是6%有时候是60%有时候是31%或是99%。只要没有100%死亡,我就必须重启,每天都在重启。有时候是因为头顶的日光,有时候是手中的茶,一个好心人善意的举动,一次美妙的心动。只要没有100%死亡,我就必须重启。今天我又活了,hallo,你看到了一个随机的我。
我从没养过宠物,然而工作室有一只苍蝇,可能是天气的缘故,它的行动十分迟缓,时常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一整天。有时候我以为它已经“圆寂”了,伸出手去,它又悻悻然飞走了。不似我晚睡晚起作息有常,它起居完全没有规律。
当我醒来时它会出现在床单上、茶几上、杯沿、我的拖鞋上、落了灰的琴弦上、灯上、将死的绿植上。有一回它贴在窗玻璃上张望半天,我想你这小畜生也会渴望自由吗?行吧,念在你有此觉悟,我便发发慈悲,开窗度你。然开关十来回合,这厮竟纹丝不动,完全不领情。一个掉头粘在天花板上,开启上帝视角俯视着我,像看傻逼一样看着我。
那一瞬间我真觉得丫是一只特立独行的苍蝇。莫非是我的同类,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有这样的想法让我十分苦恼,我当然承认自己是个loser,可我把它当成同类的时候并没有征得它的同意,说不定它在苍蝇界甚至昆虫界都混得风生水起呢,说不定它是一只成功的苍蝇,有过辉煌的一生。
我经常在它旁边躺下来观察它的行踪。我有很多疑问,比如,它靠什么生活?因为工作室没有厕所,我也不制造垃圾,除了噪音,我几乎没在工作室吃过东西,除了喝水。
这让我十分困惑,它究竟靠什么生活?莫非它是一只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苍蝇?视粪土为……粪土?爱听古典更爱摇滚乐?
像这样观察并思考着一只苍蝇的一生,忧虑着它的生计问题的时候,我躺着躺着就睡着了,醒来它已不在原地,我看见白得似雪的墙壁,没有任何杂质,纯粹的白,没有边界。我被这无止境的白色覆盖着,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好像我也不存在在这世上了。

昨夜我是打开的,有很多悲伤和希望,乘着夜风涌入身体里,梦见有一个急速旋转的内核,它看起来比想象得要结构复杂,天花板不停旋转,和有形态一些,散发荧荧光芒。早起洗漱,擦干自己蜷在沙发上,像一只受伤的鹤,陷入泥沼里,滑进一片芦苇坡,慢慢滑向了“忘记”,那里没有温暖的草甸,和牧人悠远的长笛。
“荒天为你领路,荒天为你领路。”然而在梦里,我始终走不出去啊,出不去!使我们相恋的,是共同的痛苦而不是片刻的欢愉。在这所有焦灼的渴望之中,我终于又一次失去了你。
因为太害怕寂寞,竟生吞一把安眠药。只是我又忘记在梦里该如何飞翔,那只受伤的鹤高悬在我的头顶,鸣声嘶哑,一直叫唤,一直叫唤,越来越大声。我始终逃不出去,在我的梦里。渡过这条浅水湾,就能到达理想栖息之地吧!然而并没有一条船为我摆渡,整个梦境下起了墨色暴雨。开始决堤。我双手抱头,缓缓下沉……没有人可以一点不羞愧地看待这个世界,我生怕一觉醒来,已经学会了如何宽恕自己。
(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逻辑自洽,人最难自洽。我跟自己没完。我发现人的记忆出现的偏差的原因在于,记得的版本都是按着自己希望的结局去的,而现实中的版本往往背道而驰。(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个人的一生要经历好多,又远又沉重!发现自己还没有变成大甲虫,没有变成(看不清),也没有掉进小人国,还他妈是一只大loser,这种感觉实在太操蛋了。
用愉快、虚幻,略显幼稚的笔触写在梦中的生活,时不时被带回现实生活。原因一:妈妈发来短信:你在上班吗?原因二:外婆喜欢看新闻联播,一派和谐气象。到底梦境和现实哪个是真、哪个假?我是否应该回去?背包客说他要浪迹天涯,要去真正的天堂香格里拉。我说没有天堂,去往地狱的路原本也是通向天堂的。这个夏天刚开始,一切似乎都没有变,然而却都不一样了——

杯·虚
从水仙花和夹竹桃熟睡的下午出走,
搁在案头的茶早已凉却,
一饮而尽。
它独自惆怅,空等下一位斟茶者。
将我注满吧!
当某些碎裂的念头,
蠢蠢欲动。
在未来某一时刻从我虚空的体内迸发,
默不作声。
顺着葛藤在房间四壁攀爬,
我知再无法因这无意义的牵挂而郁郁终日。

(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原來每个啤酒瓶盖的锯齿个数都是相同的,21个。
(我不知在干嘛)江南以北,船鸣是金色的,夕阳下的沙堆是呜咽的。我以为风只是风,河面却荡起波纹。我以为日落就是黄昏,当夜幕降临。我曾发现过一个小国,一片沙与一条消失的河,一个发黄的苹果。父亲,你看那消瘦的运河,你看那发黄的苹果,你说过的那些话都是对的,你说过的那些话都是错的。我们都是被带走的一粒沙,还要对抗什么?
(我不知道在干嘛)我明白,就是一场宏大的等待和仪式结束之后的空虚和疲惫!部分的真实,它俯身向我。你想渡过自我,是不可能的;你想一声不吭盗走她的心,是不可能的;
你想辱骂自己的父亲,是不可能的;你想弄清楚一个艺术家的意图,是不可能的;你想漫不经心地过完这一生,是不可能的;你想没有缘由地抱头痛哭,是不可能的;你乞求爱人伸出双臂,是不可能的……
每个理论总有站不住脚的时候,即便人生终将指向虚无,如同我们不曾停止生活,即便死亡必然来临。影子瘫在地上抽搐,我告别他,踽踽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