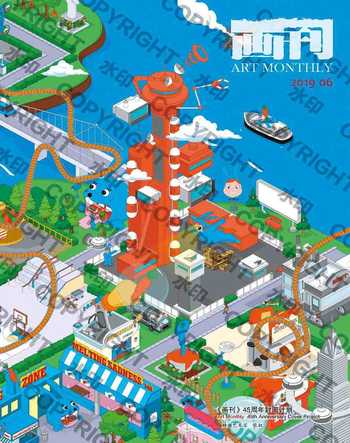关于绘画、生活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一切
黄立言

前一阵子我在东京画廊做了个展 “一人一兽一游仙”,名字是策展人王晓松博士起的。晓松在展览前言中说:“画中的人物,像是艺术家个人的自画像,脱不了读书人佯装世故、假意使坏的天真:处江湖之外仍放不下江湖上的事,有心跳出三界外,也只能做游荡在七环外无正式编制的游仙。”真是一针见血,感觉作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的最后那条遮羞布都被剥光了,尴尬的境地一览无余。
《画刊》孟尧兄约我从这次个展开谈,聊聊自己的创作观和我对艺术的理解。我其实不知道从何谈起,有些事情不说自己可能还貌似清晰、兴致勃勃,说出来之后,反而会变得糊里糊涂,怀疑自己做这个事情的意义。不过就算我胡扯几句,也并不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坏。


艺术来源于生活,且低于生活。这是我个人最深刻的创作体会。在马尔克斯和门多萨的谈话录《番石榴飘香》中,马尔克斯谈到他写作所需要具备的条件是“一个目睹的形象”,他说“我总是先得有一个形象”。《百年孤独》的激发点就是源于他小时候的经历——外祖父带着他去见识冰块。那时候,马戏团把冰块当做稀罕宝贝来展览,这成了他小说开篇的一句话:“多年之后,面对枪决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我创作也是一样,要有个切入点,某个人物形象或某个场景,然后再从这一点展开。我画画从来不画草稿,有个大概的想法直接就在画布上画了,边画边根据画面调整、修改,甚至有时候最后的画面和最初的想法完全是两回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画面是会自动生成的,这也是我不画草稿的原因。


我总是觉得,相对于现实,所谓的超现实简直太乏味了!尤其是中国当下的这个大环境,对文艺创作者来说简直是“黄金时代”,能够亲历这个伟大而怪诞的时代是一种幸运。现实生活中已包含所要表达的一切,哲理、诗意、荒诞、戏剧性等等,而不动声色的呈现往往比声嘶力竭的表达更有力量。“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所谓的原创其实并没有人们所想得那么重要,只要把你骨子里原本最真实的那一面展示出来就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往往就是因为这样你才成就了自己。甚至,我觉得艺术家不需要往作品里灌输太多的思想,那些更多是偏见,只要本人更开放一些,不带任何成见和价值判断地去拥抱和感受现实,就足够了。用不着刻意去追求个性,那样真的挺幼稚可笑的。
对技法和材質,我不是太敏感,也不是很看重,反倒是现实中事物本身及其背后传达出来的信息让我更感兴趣。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艺术创造力,而是对生活的感受力,说得矫情一点,有没有一颗柔软的心,去感受和捕捉那些隐秘而动人的事物。我觉得任何事物都带有某种情绪,都有叙事性,就算是一块色斑,一个不经意间的动作,都可以给人不尽的遐想。我自己做的事就是对现实生活进行某种摘取、剪辑、重构与呈现。有人说:作为一个诗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面对一双破皮鞋也会痛哭流涕感慨万千。艺术家应该也是一样。

有时候,我会想,艺术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自己从事这一行当的初衷是什么?也许最吸引我的不过是一种无所事事、自由散漫的生活状态。自由是艺术对我最大的回报。我不愿跟这个社会有太多的牵扯,不想被一些东西绑架,更偏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感受和观察这一切。像我这种人对这个世界没什么作用,不过也没什么害处,这样挺好,我不想和它纠缠不清。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建造一个王国,只要你明白并能够接受——你能掌控的东西不多——就好了,艺术恰好给我提供了一个被抽离出来的、相对独立的时间与空间,通过作品去感知和平衡自己与世间事物、自己与自我的关系。对我来说,保持这种生活状态,保持不断创作的欲望,比创作一幅所谓的好作品更重要。
凡·高曾经说过:“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达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初春的北方景色如此令人迷恋和兴奋,再也没有比看到一棵看似枯死的树枝上冒出一两枝新芽更令人感动的事情了。也许,死亡是上帝给予人类最好的礼物,但在这之前,活着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