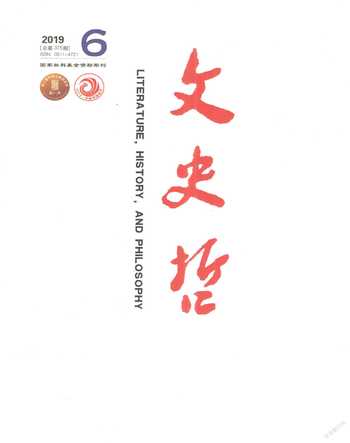“责任心”及其美德论限度
一
美德伦理学自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学界复兴以来,日益成为现代伦理学谱系中的一支强势力量。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它对康德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反叛有多“时尚”,也不是因为它向亚里士多德主义或休谟主义的复归有多“特别”,而是因为——它用以观察、理解和反思道德问题的美德论视角,在很多方面更加切近人类伦理生活的真实状态,从而能够更加精细地将这种状态所蕴涵的特质与限度揭示出来。
为了准确把握美德伦理学,我在《美德伦理学与道德多样性》一书中曾经提出,我们至少需要引入三个比较的维度,即:古代美德伦理学与现代美德伦理学之间的比较,现代美德伦理学与现代规则伦理学之间的比较,以及美德伦理学的中西方案之间的比较。我相信,只有通过这三个维度的互鉴,我们才能较全面地理解美德伦理学【李义天:《美德伦理学与道德多样性》,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43页。】。其中,第三个维度,对中国伦理学的研究者来说尤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借助美德伦理学的视角,我们不仅可以重新审视中国伦理学的若干重要概念或问题,同时,还可以由此反思并确认“美德伦理学”本身作为一种伦理学类型的基本内涵与核心特征。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有在中国伦理学的充分参与之后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这项任务只有依靠中国伦理学的研究者的努力才可能完成。就此而言,安靖如教授的这篇文章正是在此维度上的一次有益探索。
安靖如教授的问题意识很明确。他通过梳理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关于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的论述,试图澄清两个问题:第一,孔子、孟子和荀子并没有忽视“责任心”在伦理行动中的实际作用。第二,即便如此,“责任心”也依然存在明显的缺失和局限,它无法像“美德”那样真正有助于成就儒家圣贤的理想人格。因此,安靖如教授虽然花费诸多笔墨,详细考察《论语》《孟子》《荀子》等文本中有关“责任心”的讨论,但他的目的却并不是要否定儒家伦理通常展现的美德伦理形象,而是要直面“责任心”在儒家伦理中的位置及其与“美德”之间的差别,从而再度确认儒家伦理作为一种美德伦理资源或范式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根据安靖如教授的定义,“责任心”意味著“一个人自觉地去确保自己做某事(履行职责)的意识”。因此,一个尽责之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并且“能够强迫自己服从自己的职责”。在孔子那里,出于“责任心”而行动的人,正是那些能够让自己遵从外在礼法、合乎社会规范的行为者。这样的人尽管真实存在,而且他们的行为方式似乎还构成了培育和发展美德的一条必经之路,但他们却时刻面临“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危险。同样地,孟子也注意到尽责之人的存在。然而,在孟子眼中,这些人不过是在“行仁义”,而非“由仁义行”;他们“只谈责任而不谈其他的习惯……无法为个人或社会带来真正的道德进步”。与孔孟相比,荀子对尽责之人的态度则更为宽厚。在他看来,出于“责任心”的行动者虽心存私欲而不能安于为公,但他们毕竟能够通过后天努力,让自己保持克制从而趋善远恶。因此,尽管不能成为具有充分美德的“圣人”,但他们却因为勉力前行而有资格堪称“劲士”或“君子”。荀子并没有过多地贬低那些尽责之人,这显然与他的人性理论和修身学说密切相关。
二
安靖如教授对先秦儒家的上述分析及其最终得出的结论——“《论语》《孟子》《荀子》都表现出了美德伦理的形态,而不是义务论的或独特的同时基于规则和基于美德的伦理”——基本是可信的。因为,他的分析建立在美德伦理学关于道德心理问题的一个关键区分的基础上,即,“责任心或义务感”不同于“内在的美德品质”。前者不仅不能适用于所有的伦理情境,而且会因为其内在的律法气质和普遍主义诉求而扭曲甚至阉割了伦理生活的丰富性。因此,美德伦理学之所以会发生现代复兴,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现代伦理生活已无法满足于来自“责任心或义务感”的单调解释,无法满足于该解释所蕴涵的那种关于人类道德心理的“对抗性/冲突性”说明。美德伦理学相信(并且已经通过理论努力而表明),我们完全可以在人类伦理生活的具体实践中、在数千年来的伦理思想资源中发现某种伦理反应——它并非出于对抗、强迫、克制的具体动机,而是基于平和、自然、从心所欲的整体倾向。
对伦理反应的这两种心理基础的区分以及优劣判别,不仅可以像安靖如教授这样在东方古典学术的文本中发现证据,同样也可以在西方古典学术的文本中获取资源。亚里士多德关于“自制”(continent)与“节制”(temperate)的区分,就构成了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说明。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谓“自制”和“节制”,都是行为者在处理与肉欲相关的实践事务中所展现的不同方式。亚里士多德指出,自制者虽然在追求肉体欲望方面没有表现得过度,但他仍然存在“强烈的、坏的肉欲”【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1146a9.】,始终受到这种不良欲望的影响或威胁。因此,尽管自制者可以形成正确的判断,坚持正确的抉择并最终把持住自己,但他的“坚持”本质上却是一种“抵抗”,即对坏的情感与肉欲的抵抗【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1151b9.】。因此,自制者虽然可以因为服从理性的指令而有意克制,坚守职责,但他在本质上依然处于一种纠结和忍耐的不适状态。这种状态或许谈不上十足“痛苦”,但也绝对无法堪称“快乐”。
而“节制”则不同。“节制”是一种美德,是行为者在处理与肉体欲望相关的实践事务中所展示的那种“合乎中道”的品质。与自制者相比,节制者根本“没有过分的或坏的欲望”【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1146a11.】。因此,节制者不会像自制者那样感受到肉欲的诱惑和压力。所以,他无需对欲望加以专门的约束或特别的克制。自然地,他也就不会体验到自制者的那份纠结和痛苦。当他展开实践推理并实施正确行为时,他感受到的只是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轻松和愉悦。
因此,根据亚里士多德,自制者虽然“可以算是比较正派,但并非圣贤,他们的习惯化没有将理性向往和欲望、情感完全协调起来”【C. D. C. Reeve, “Aristotle on the Virtues of Thought,” in The Blackwell Guide to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edited by Richard Kraut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6), 210.】。毕竟,能够用来解释其行为的“是她的自制而非她的美德,是她的自制导致了自制的行动,而非合乎美德的行动”【Paula Gottlieb, “The Practical Syllogism,” in The Blackwell Guide to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 239.】。相反,一个真正具有节制美德的行为者在理性与欲望之间并不会出现严重的对抗,因此他既不可能也不需要“自制”。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自制”不仅不是美德,反而是一个人缺乏美德的标记【“古典美德伦理学的一个特征就在于,把毫无对立倾向地做正确之事当作有美德之人的标志,使之不同于那些仅能自制之人。……美德作为一个品质问题,要求出于正确的理由并且没有严重的内在对立地做正确之事。”参见Julia Annas, “Virtue Ethic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thical Theory, edited by David Cop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517。】。
三
无论是借助东方的思想资源,还是诉诸西方的古典文本,最终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发现,承认“责任心”与“美德”的区分并对后者予以倡导,构成了美德伦理学的核心特征之一。因此,不论如何解释“责任心”或“美德”的含义,也不论我们在现代语境中如何定义“美德伦理学”,强调一种更加发自肺腑的善意和优良品质,势必成为美德伦理学在现代建构过程中的一个不可让渡的方面。它意味着,与其他伦理学类型相比,美德伦理学不但强调行为者的内心状态,而且强调行为者应当具有如此这般的内心状态:不是克制和纠结的,而是从心所欲和顺其自然的。在这个意义上,安靖如教授的文章,显然是从中国伦理学的角度和资源出发,为这项工作增添了一个注脚。
然而,在区分的基础上,仍需进一步追问和推进的,至少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当我们希望以自然、轻松、愉悦的心理状态,出于一种被称作“美德”的心理反应而行动时,这里的“美德”究竟指什么?如果它是指一种特定的实践推理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可以被构造或还原为怎样的实践三段论?如果它是指一种特定的情感反馈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又依赖于哪些主客观的构成要素或环节?诚然,在特征与功能上,将“美德”与“责任心”区分开来是容易的,但是,要想描述和论证“美德”的具体心理进程,却是不容易的。
第二个也许更棘手的问题是:尽管我们试图做出上述区分,但这个区分终究成立吗?或者说,美德伦理学是否完全不能容纳“责任心”?一旦行为者出于“责任心”而行动,那么他将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有美德的”了?答案似乎要比想象的复杂。因为,一方面,人们完全可以接受康德主义的美德概念,将“责任心”从一开始就理解为最基本的美德;另一方面,即便依然坚持美德伦理学的立场,也应该意识到,“责任心”与“美德”之间的心理状态差异只是浅层的表象,真正深刻的问题在于,“责任心”意味着行为者只需对行为的规则及其普遍必然性负责,而“美德”却还需要行为者继续追问规则之善,追问善的总体性,追问这些善与他本人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在道德心理层面上,“美德”虽与“责任心”明显不同,但“美德”并非与“责任心”格格不入。如果一位行为者既能洞察总体的善又能理解规则之善,从而在遵从规则时虽然因为敬重规则而依然保有明确的“责任心”,但却并未因此感到这份“责任”所施加的巨大强迫或压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能说他缺乏“美德”而仅仅出于“责任心”吗?
以上两个问题,不一定是安靖如教授这篇文章所需处理的,但它们却是我们借助美德伦理学的框架展开分析时不可忽视的问题,更是我们进一步理解和建构现代美德理论时不可回避的问题。无论我们是面对先秦儒家,还是诉诸古希腊的思想资源,皆是如此。
【责任编辑 刘京希 邹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