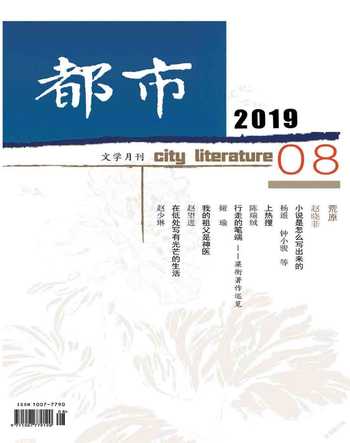短评:佛与刀
弟弟带刀出门?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弟弟可能会遭遇某种困境,他需要刀子,至少需要刀来削弱恐惧。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弟弟安全返回,还带着两样东西:“佛”和“刀”。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想象,这必是一个典型的弃恶从善的故事。可自古佛、刀不两立,弟弟怎么就成了“个别”:卖佛,也卖刀呢?其中是否有写作者不愿坦白的动机?如果有,那是什么?
直到“正常”的生活被打破,意外出现———我是说弟弟英雄般的壮举,他救下了白衣女孩。弟弟收获了爱情,更准确地说,是爱情的幻觉。很快,他就不得不尝幻觉破灭的苦果:他心里那尊“雪白的慈观音”和白牡丹一起“碎裂”。
佛还在,但“佛缘”尽失。或许是这篇小说一个显在的主题。但如果我们停留于此,就无法理解弟弟接下来的“疯狂”:他近乎偏执地寻找着白牡丹,尽管每次都无功而返。我认为,弟弟正是在这一“无意义”的行动中认领了自己的力量,他要在遍布褶皱的世界上掘开一道缝隙,让生命重新袒露它诚实的底色。所以,即便那个被佛和刀占据的店铺已然夷为废墟,弟弟还是要在精神上将它彻底删除,连同废墟本身。
至此,弟弟以一场庄严的仪式完成了自我意识的重塑,也完成了对世界的想象性再造:重建屋子。但有一个细节十分可疑。就是弟弟屋子建成的那天,奶奶庙也同时竣工。这座“庞大”建筑里供奉的究竟是何方神佛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动用村集体资金修建的,而这笔款项得自于田地荒芜和村民欲望的双重“献祭”。也就是说,它因“信仰”而建,却是最“无信”的。或者说,在“信仰”佛一样的笑容下,藏着一把刀,一把锋利的刀,这刀的持有者不是任何人,而是人丧失了人的基本品格的物性。正是在這个“笑里藏刀”的隐喻里,佛和刀重归于好。
问题来了,既然奶奶庙是“无信”的,是一片意义的废墟,又怎么会与寄托着弟弟全部“信”的新屋同处于共时性的空间内呢?只有一种解释,即,写作者对个体意识的觉醒依然充满警惕。是的,弟弟的“新生”不容置疑,但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铁的现实:个体的志向从来就不是万能的,它必有自己的边界。
小说家杨遥看到了这个边界,但他坚信,“白”,这种纯然之色,会为世界重获美好负起责任。
作者简介:
王朝军,笔名忆然、正石。1980年生于山西晋城。青年文学评论人,山西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第七届全委会委员。曾任《名作欣赏》副主编,现供职于北岳文艺出版社。在《文艺报》《文学报》《长江文艺评论》《黄河》《山西文学》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及散文百余篇。出版有评论专著《又一种声音》。鲁迅文学院第36期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