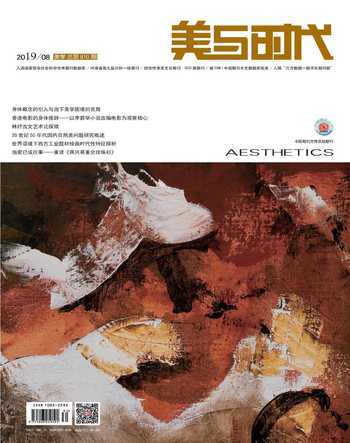香港电影的身体修辞
摘 要:目前,对于香港电影的研究较多关注的是香港电影的历史流变,较少从身体面向进入。李碧华作为香港极为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其作品中充斥了大量的身体意象,这当中的身体符号与香港的历史脉络、政治文化有着紧密的勾连。同时,李碧华的文学创作与香港电影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多部作品都曾被改编为电影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透过李碧华的小说改编电影,如《青蛇》《潘金莲的前世今生》《胭脂扣》《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等,深入探讨身体意象之于香港电影有着怎样的特殊意涵。现代消费社会女性身体时常处于被“观看”的地位。因此,不管是李碧华的原著作品,还是被改编的几部电影,都能看到其中充斥了大量女性情欲的展演,这其中一方面是为了迎合商业需求,另一方面也试图以此翻转男性视点。同时也可以看到,此时的女性身体已经不再是“不洁”与“淫荡”的代名词,而更多地是一种身体的展示,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身体炫耀,这其中也包含了强烈的女性自我身份的建构。同时在情欲面向之外,也包含了特殊历史时期港人集体的迷茫不定,身体/身份与时代政治产生了复杂而紧密的勾连。
关键词:香港电影;身体;李碧华
香港电影寄托了独有的港式情怀和文化想象,在两岸三地乃至海外华语圈都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在香港电影中,身体修辞成为了特有景观,从武侠电影的英雄身体到警匪片中的“香港警察”形象,再到王家卫、关锦鹏、许鞍华后现代电影中的身体情欲意象,身体成为了香港电影的重要修辞意象,并具有了多重复杂的意涵。对此,本文将选取香港作家李碧华的作品《胭脂扣》(1987)、《潘金莲的前世今生》(1989)、《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1990)、《青蛇》(1993)几部被改编为电影的文本展开讨论,进而思考女性身体在这几部影片中的特殊意涵。
本文之所以选取李碧华的作品为讨论核心,是因为李碧华作为香港极为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其作品中充斥了大量的身体意象,这当中的身体符号与香港的历史脉络、政治文化有着紧密的勾连。同时,李碧华的文学创作与香港电影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多部作品都曾被改编为电影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一方面与电影中的商业元素有关,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城市,很早就进入了资本消费社会,而在消费时代底下女性身体时常处于被“观看”的状态,因此,在这几部电影中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女体情欲镜头,包括张曼玉、梅艳芳、王祖贤等知名女星的出演也为影片带来了十足的商业噱头。另一方面,身体情欲展演的背后也包含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透过影片可以看到此时的女性身体已经不再是“不洁”与“淫荡”,更多地是一种身体的展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身体的炫耀,包含了强烈的女性自我身份的建构。同时,在情欲面向之外,也包含了特殊历史时期港人集体的迷茫不定,《胭脂扣》中穿着不合时宜的复古旗袍穿梭于现代都市的如花正是如此,全片都笼罩在深刻的怀旧情怀之中,此时身体与时代政治也产生了复杂的纠葛,对此下文将展开论述。
一、身体情欲的展演
德勒兹将电影分为“躯体电影”和“大脑电影”。“躯体电影”的主体是欲望,“大脑电影”更多是思考和精神[1]。而由李碧华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多为躯体电影,这与她的书写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碧华的小说向来以大胆的情欲书写著称,在改编的几部电影中可以看到大量的身体情欲镜头,由徐克导演、李碧华参与编剧的电影《青蛇》可谓当中的代表作。小说《青蛇》是对中国古典名著《白蛇传》的重写,相较原著的白蛇故事,小说《青蛇》作为古典新编融入了现代思维,正如戴锦华指出:“任何一部经典之作之常新,不在于‘永恒’的审美价值,而在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语境下的重读,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非神话讲述的年代。”[2]因此,相较李碧华小说《青蛇》对《白蛇传》的“背离式创作”,徐克导演下的《青蛇》则更为大胆,借由电影这样一种直观的视觉媒介,将其中的身体隐喻进行了更加淋漓尽致的展现。徐克作为香港“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电影风格融入了西方现代主义电影技巧。在电影《青蛇》中,除了徐克最为擅长的武打场面外,他还融入了更为复杂的现代电影语言,正如台湾影评人闻天祥所认为的,徐克的电影是“一步步往更古老的时代里走,又一面尋来新的手法刺激电影幻觉,无论是在古、新或中、西的互用,绝对有其划时代的意义”[3]。因此,在重新解读电影《青蛇》时,不可只将其视为简单的武侠片或是古装片,而应该深入探讨其背后更深层面的社会历史脉络。
电影在情节上保留了传统《白蛇传》的几个关键段落,包括白蛇恋上书生许仙,并通过借伞、换伞使两人的恋情逐渐加深,直到端午节误饮雄黄酒现形将许仙吓死,白蛇冒着生命危险盗取仙草营救许仙性命,导致出现了后来与法海斗法水漫金山寺,在斗法过程中白蛇产下小孩最终大败而亡。不过电影的结局进行了改编,选取了青蛇将许仙杀死陪葬白蛇作为结束,并将故事聚焦在了南宋时期而没有进入现代中国革命史当中。电影《青蛇》最大突破仍在于将青蛇拔高到了主角地位,成为主角的小青,将原有的主仆关系彻底调转,并且具有了相当的独立人格,对于许仙和法海的大胆挑逗也彰显了现代女性主义精神。青蛇的情欲展演作为电影的核心,也是女性欲望的大胆呈现以及对男权机制的否定与戏谑。影片一开头就以法海的形象切入,并以近景的方式将法海的样貌占满整个画面,此时高高在上的法海审视着在尘世/地狱打滚的庸人。不过,徐克很快就对法海这一历史上刚正不阿的男性形象进行了颠覆,电影中法海由形象俊俏的赵文卓扮演,这与人们传统上认知的老僧法海有着较大的出入。同时,正如一开场法海在降服一只修炼两百年的蜘蛛精时所说:“惭愧,我的修龄只有二十多年。”或许是修行未够的缘故,法海在后来无意中看到一名赤身裸体的村妇产子时竟动了色心,情欲的勾引也成为了法海最大的“魔障”。直到后来在与青蛇的对决/修炼中,情欲再次占据上风,让法海有了正常男性的生理反应,最终一败涂地并进而恼羞成怒。可以看到电影中法海的形象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得道高僧,而是一边口说“戒色”,却始终无法抵制性诱惑的寻常男性。如果说《白蛇传》中的法海代表正统,是一个去欲望化的身体展现,感性存在的身体被理性所压制。那么到了电影《青蛇》中的法海,则展现了强烈的身体欲望①,这也是身体的一次阹魅过程。《青蛇》作为一部香港商业电影,当中夹杂了强烈的消费时代的欲望,这也使得法海这个历史上代表正统的形象被彻底解构,“新的欲望美学和消费主义一道将抽象身体的经验的形态湮灭了”[4]。
此时,身体欲望也变成了欲望身体,这在青蛇的身上有了更为突出的體现。青蛇的第一次出场就极具性意味,由张曼玉饰演的青蛇与王祖贤饰演的白蛇,在屋顶伴随着印度舞相互扭捏贴合,随后青蛇更与印度女舞者进行了充满情欲的共舞。这样一种女女眷恋的场景不但颠覆了传统的青蛇与白蛇形象,当中也包含了对于女同性恋的想象,这也是李碧华和徐克对于性别议题的关注。除了同性恋的想象外,影片更着力于呈现异性恋和多角恋,并试图以此重构女性形象。不管是青蛇还是白蛇,都可以看到此时的女性不再是处于被动的“观看”地位,从影片开头的扭腰摆臀的学步,到后来白蛇追求许仙、青蛇色诱法海,都可以看到此时的女性更多占据的是主动/支配角色,借由自身的欲望身体展演,从而诱发男性的性欲,而当中男性形象却多是软弱不堪一击的,不管是多情的许仙,还是无法抵抗诱惑的法海,都折射了男性的虚伪与脆弱。这也与徐克电影对女性的推崇有关,正如香港影评家石琪所说:“徐克片一向崇拜女性,由《蝶变》、《第一类型危险》、《新蜀山剑侠》、《上海之夜》而至《刀马旦》,都表示中国女人的美丽、灵敏、多情和坚毅,比中国男人可取,他监制的《东方不败》特别嘲讽了中国男人丑态百出,不如去做女人!”[5]因此,由徐克导演、李碧华编剧的《青蛇》故事主体也是女性,并且女性的主体意识也伴随着身体情欲的复苏被不断召唤出来。
这也是女性透过身体欲望促进了自主意识的觉醒,这在电影《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王祖贤饰演的潘金莲尽管不断处于被男权机制压抑的命运,但仍然爆发出了强大的身体原欲。客观地说,《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都不是一部经典作品,不过李碧华巧妙地选取了《水浒传》与《金瓶梅》片段,构造了一个被时代命运玩弄的女性。然而,在这当中却也看到了女性强大的生命力。历史上的潘金莲时常被“淫妇”等负面词汇笼罩,《金瓶梅》更是充斥了以男性为主体对女性的猎艳视角,正如林少雄对身处男性书写历史中的女性所说的:“她们要么成为男性征服并用以达成政治军事或生理目的的工具与对象,要么成为同流合污或助纣为虐的恶魔,甚或成为男人由于懦弱或暴戾的天性所决策失误的替罪羊……至于女性作为历史事实的参与者、亲历者、体验者与创造者的角色被彻底忽视,女性作为历史叙述的主动书写者的资格被彻底剥夺,只能被动地等待男性的被书写。”[6]李碧华正是有意透过大胆的身体展演以此扭转女性的被动地位,透过塑造了一个穿梭于前世今生敢爱敢恨的潘金莲/单玉莲,展现了对命运的不妥协。“情欲”也成为了当中的关键因素,作为一种源自内心的一股力量,是对女人生命的一种肯定。而一旦拥有了情欲的启蒙,女人就会变得不愿意顺从命运,并重新开始关注自身的命运。
影片中的单玉莲与历史上的潘金莲层层重叠,两人的命运极其相似,例如单玉莲的失身与潘金莲也是类似的,作为舞蹈演员的单玉莲被图谋不轨的章院长强暴,却反过来被诬陷,导致被舞蹈学院开除,流落到工厂。然而,单玉莲并没有放弃对爱情的憧憬,并喜欢上了年轻帅气的武龙。影片在处理单玉莲这段革命时期的爱情时采用了极具情欲的手法。单玉莲与武龙的第一次相遇,唤起了单玉莲的前世记忆,此时影片采取了特写镜头,尤其凸显了武龙健壮流满汗水的肌肉,并配以较为暧昧的背景音乐,而单玉莲此时也陷入了意乱情迷之中。随后观看武龙打球,同样是具有青春活力的男性身体对单玉莲的诱惑。单玉莲通过给武龙赠鞋的方式表达爱意,不过这样的行为很快就被人发现举报,这在特殊的革命时期是被禁止的,因此单玉莲马上成为众人批斗的目标,被人冠以“破鞋”的称呼,再次与历史上的潘金莲遥相呼应。为了划定立场,胆小的武龙也加入了批斗单玉莲的队伍之中,再次凸显了男性的软弱无力。心灰意冷的单玉莲选择自我流放到了广东惠州,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被香港富商武汝大看上从而远嫁香港。由曾志伟饰演的武汝大对应历史中的武大郎,身材短小其貌不扬,并且在性方面几乎无能,与他的兄弟武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单玉莲对于武龙仍然持有感情,在被武龙拒绝后伤心欲绝的单玉莲前往酒吧消愁,此时的镜头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伴随着单玉莲的视角,可以看到当中充斥着大量的裸露情欲身体。作为拥有正常欲望的女性,单玉莲最后被SIMON对应于历史中的西门庆所引诱,从而发生了一夜情。影片在此采用了交叉蒙太奇的方式,将现代与古代两人寻欢作乐的场景进行了同时呈现,也再次昭示了单玉莲与潘金莲之间的联系。
影片多处将单玉莲作“淫”妇设计,一再凸显单玉莲与潘金莲当中女性身体欲望的展现,正如简·盖洛普指出:“挺立的阴茎和具有象征意味的菲勒斯不一样的是,它不代表一再庞大而具有整体意义的权力,而只是一种欲望,需要通过另一个身体来求得满足。”[7]女性只有将男性体验作为身体(阴茎)而不是超验的符号(菲勒斯),才可以确立女性自身的欲望和权威性,从而消解男性建立在菲勒斯基础上的权威性。因此,单玉莲(潘金莲)作为男权制度下的受害者,在与SIMON(西门庆)的性交中获得的快感,SIMON(西门庆)对她而言是阴茎而不是菲勒斯,两人的属性是“身体—快感”,男性在此时反而成为了女性欲望的消费品。也正是在这一次次的情欲召唤中,单玉莲的自我主体意识最终彻底觉醒,最后以撞车自杀殉情的方式与一生所爱的武龙共同走向自我毁灭。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自我毁灭中才最终成就了两人的爱情。李碧华也正是以此重新为历史中被人斥之为“淫妇”的潘金莲重新翻案②,展现了女性在大时代背景下的“身”不由己,以边缘的女性身体展演来抗衡主流大历史,进而彰显女性的自觉意识。
二、身体/身份与政治的纠葛
李碧华作品在进行身体情欲展演的同时,当中的身体意象与时代政治也产生了紧密的勾连。正如香港学者陈国球评价李碧华作品时所说:“一方面它们包括一切畅销小说的元素:浅白、媚俗、不求思想一致,但求局部趣味。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社会意识非常强烈的作家,她的作品紧贴社会脉搏,诸如国家身份、历史、政治、命运、性别等学术界非常感兴趣的话题。”[8]李碧华作品中对于香港历史文化中的“边缘性”“混杂性”,尤其对于九七香港回归祖国前集体性的迷茫也有着多面向的深刻思考,这在《胭脂扣》中得到了最突出的体现。原著小说《胭脂扣》在1987年由关锦鹏拍摄为电影,在当时香港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成为当年最大的黑马,分别斩获了香港金像奖、台湾金马奖等多项奖项。《胭脂扣》所引起的共鸣与当时的香港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许子东所说:“九七回归带来的压力,也让港人产生怀旧感而遁入旧时的历史记忆中找寻未来自我的定位……八十年代后期的电影《胭脂扣》表露的怀旧感,除了受到八十年代前期的世界潮流影响,加上香港历史环境的特殊因素,对九七回归的不安感,于是怀旧从‘西式复古风’转变为‘中国式’,甚至进而‘香港在地化’的怀旧。”[9]香港从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伴随着世界复古风而掀起了一阵怀旧潮。随着殖民地统治时期即将结束,回归祖国的时间日益临近,这对于向来缺乏政治历史感的香港人而言是陌生而新鲜的体验,“我们这一辈对香港历史的认识近乎于零,但当殖民地历史走向终结时,我们忽然觉得自己脑袋空白,急于追认自己的身份。‘身份’是一种流动而非静止的观念,如何看待往事,如何置身其中,都是表述身份的重要方式。”[10]《胭脂扣》正是以香港历史的断裂处为切入点,借女鬼如花之口重述了“我城”过往的点滴,这当中也包含了强烈的自我身份追寻的意味。
《胭脂扣》当中流露的强烈怀旧感成为了香港人最大的共鳴,这与香港的时代命运有着密切的联系,怀旧来源于香港人对九七回归的时间焦虑。现代人早已被现代性中的“线性时间观”内化,一旦出现“时间裂缝”(time-gap),就会给现代人带来巨大的历史虚无感,而1997年对于香港人来说正是如此。当习以为常的时间“连续性”被打破,出现了“时间裂缝”以后,人们对于自身命运的困惑,“时间裂缝在我们对于时间流逝的意识中产生了迷一样的空白。这种时间错觉同样应被视为一种可扰因素,它使得我们难以把握当下”[11]。由于当时香港并未真正回归到祖国的怀抱,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强烈的躁动不安,人们对于前景与未来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而此时怀旧则成为了缓解社会震荡、抚平心灵创伤的途径,因此,在电影中可以看到,变成鬼魂的如花来到现世所谈论的都是过往失落的香港记忆:“我看的是大戏,太平戏院开演名班,我们一群姐妹于大堂中座。共占十张贵妃床,每张床四个座位,票价最高十二元,那时演的是《背解红罗》、《牡丹亭》、《陈世美》。”在如花的讲述中被拆除的太平戏院以及关于香港的过往此刻又复活了过来,并且在小说的基础上借由电影语言,透过交叉叙事结构、色彩、音乐、华丽的影像,重新构筑了逝去的香港景象,更大程度地增强了怀旧的氛围,并进而带动当时整个香港社会的文化怀旧潮流。这种怀旧也反映了现代人对往昔纯真爱情的渴望。现代人生活的快节奏,让人们对单纯美好的事物进行缅怀,同时集体式怀旧也充满着香港人对于自身命运的疑虑,喻示了香港世代交替的失落与文化传承的危机,正如周蕾所说:“怀旧往往被看作是一种时光倒流:过力发生的事情、时光流逝、我们在今天回顾过去、我们感觉旧日更加美好,但却已无法返回从前;在这种对旧日的怀旧里,我们变得怀旧。”[12]59当处于迷茫不定的当下之时,人们会不自觉地回到过去,试图在历史中重新自我定位。人们透过美化过往的记忆和生活样式,来回避、思考当下的现实处境,即使过往的生活很艰苦,在人们的记忆中也变成了黄金岁月。此外,人们正是透过对自我历史与身份的追寻,试图在混乱的现实中理到一丝头绪,在迷茫的状态中找到某种确定的存在。然而,这种集体式怀旧最后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虚无,正如影片中的如花穿梭于阴阳之间,无处安放的身体也隐喻了香港人回归前夕无根的情景,正如永定的女朋友楚娟对如花所说:“好听一点是怀旧,说得难听一点就真的像鬼。”其中的怀旧最终指向的是充满鬼魅之气的历史虚空,正如福柯所说的“是以过去来取代无法承受的现在”,它寻求的是一种“病态的出路”,表面上得到纾解的焦虑其实蕴含了更深层的困境。
正如《胭脂扣》结尾如花与十二少在片场相遇,此时片场的导演要求演员不但要有鬼气同时还要兼具侠气,这也让演员彻底混乱,无法明白鬼气和侠气这二者截然不同之物如何兼容,这也隐喻了夹杂在中西文化之间的香港的尴尬处境。正如论者所说:“香港意识也正是处于这样尴尬的境地:它悬置在历史和文化中,悬置在历史传统与当下经验中,携带着破碎的历史经验在两极或多极文化之间摇摆不定。香港在历史文化身份上的悬置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焦虑,正是《胭脂扣》所包含的内在阴影。”[13]如果说《胭脂扣》中不管是被夹在阴阳之间、迷茫不知去处的如花,还是最后亦鬼亦侠的女演员隐喻了香港的处境,那么到了电影《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1990)中,以女性身体来对香港处境进行隐喻的冲动则更为强烈。川岛芳子及其身体包含了香港作为殖民地的寓言,身为中国人的川岛芳子被日本义父强奸,并且在强奸的时候日本义父说着极具日本军国主义的话语:“芳子,你是皇族,我是勇者。结合我们的血,所生的孩子定是人中之龙,勇者无惧,是最伟大的人类,大同世界的统治者,最高统帅,是真命天子。”这也正是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国力衰弱,导致香港被割让出去,而香港作为殖民地的悲哀之处,被殖民地对于殖民者而言,如同一个享乐、发泄的女性身体。正如刘登翰所说:“在西方的后殖民论述里,性是一种象征。西方/男性/殖民者和东方/女性/被殖民,是一组对应结构。女性的被动是被殖民的象征,而男性的雄风却是殖民者权威的体现。”[14]萨义德早在《东方学》中就曾指出,西方对东方国家的想象无不包含着性与欲望,因此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处境就正如川岛芳子一般,为了在乱世中苟活于世,只能出卖身体供殖民者蹂躏。这也正是香港作为被放逐的他者,身上所具有的强烈的“边缘性”。
然而较之于《胭脂扣》中的身份迷茫,《川岛芳子》中的身份认同则更为清晰,川岛芳子作为末代清朝的十三格格,在被送往日本之初抱持着强烈的反抗,并高呼着“我是中国人”,此处也隐喻了被强制割让出去、离开祖国怀抱的香港人的心声,从中也可看出李碧华潜意识中对祖国的认同。香港由于曾被英国长期殖民与祖国分离,因此使得香港文化具有了强烈的“杂糅性”,如同一个具有中西文化的混血儿。然而透过李碧华作品所改编电影来看,当中的身份/身体迷茫最后还是回归到了对于中国的认同,不管是幼年十三格格铿锵有力的“我是中国人”的呐喊,还是《潘金莲的前世今生》《青蛇》《胭脂扣》等电影的取材,无一不是来源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可以说李碧华内心潜藏的香港意识与传统中国是深刻交织的,而香港电影中对历史/身份的追寻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中华文化当中,因为香港的根与祖国是紧密相连的,这样一种“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是无法割裂的,只有真正回归到祖国这个母体,才能安放香港人迷茫无措的身体/身份迷思。
三、结语
本文透过“身体情欲的展演”“身体/身份与政治的纠葛”两个面向,探讨了李碧华作品改编为电影中的身体意象,《青蛇》《潘金莲的前世今生》中的女性身体也在进行自我翻转,从身体欲望到欲望身体,从被动的地位变成了主动的身体展演,而男性此时反而成为了被玩弄之物,展示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李碧华电影也借由身体意象隐喻了香港的特殊处境,不管是《胭脂扣》中的如花,还是《川岛芳子》中的十三格格,这些处于社会时代边缘的妓女、满清遗民也象征了香港的“边缘性”。正如周蕾认为电影《青蛇》中将青蛇拔高到主角地位,暗含了作者对自我身份追寻的困惑:“李碧华用一些被社会鄙视、从事被社会鄙视的行业的人物,来创造一段既具魅力又琐碎不堪、既惊天动地又一文不值的历史。而青蛇地位的崛起,从一个平淡无奇的情节剧中的毫无个性的丫环(女侍)一跃成为洞悉一切、举足轻重的主人公,其戏分的增多本身就隐含了香港地位的攀升和作者主体的期待视野,同时也暗示了在这过程中身份找寻的焦虑。”[12]51这也正是临近一九九七回归祖国前香港社会的集体焦虑,面对这样的身体/身份的迷茫状态,李碧华最终选择了回到中华文化中寻找自我存在的根,只有回归到祖国这个母体,才能真正寻求到安身立命之所。
注释:
①电影开篇就展现了法海被情欲勾引的情景。被躶体村妇产子扰乱了心智的法海在寺庙内对抗心魔,然而修行极高的法海在此时面对所谓的“妖孽”却明显力不从心,而妖孽的形状也极为怪诞形似男性精子,并使用了俯视镜头从法海胯下显示这些妖孽其实就出自于法海身上,这当中充满了性暗示,而方寸大乱的法海和巨大的佛像面部出现裂缝,都显示了在这场自我情欲斗争中,出家人法海最终还是败给了心魔。
②这样一种对女性的翻案在李碧华作品改编的电影中并不鲜见,包括后文将展开讨论的电影《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中的川岛芳子同样如此,在历史中的川岛芳子是出名的“汉奸”,可是在电影中却将川岛芳子刻画为被时代命运尤其是男性玩弄的女人,许多的行为都是无奈之举。
参考文献:
[1]德勒兹.时间——影像[M].谢强,等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323.
[2]戴锦华.文学和电影指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
[3]闻天祥.徐克的险与偏[N].联合晚报,1993-10-31(10).
[4]张颐武.超越启蒙论与娱乐论——中国电影想象的再生[J].当代电影,2004(6):18-22.
[5]石琪.香港电影新浪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76.
[6]林少雄.镜中红颜:话语电影的性别体认[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132.
[7]盖洛普.通过身体思考[M].杨莉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5.
[8]陈燕遐.流行的悖论——文化评论中的李碧华现象[C]//陈国球.文学香港与李碧华.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144.
[9]许子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小说与“香港意识”[J].清华大学学报,2001(6):36-41.
[10]陈丽芬.普及文化与历史想象——李碧华的联想[C]//陈国球.文学香港与李碧华.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149.
[11]李道新.“后九七”香港电影的时间体验与历史观念[J].当代电影,2007(3):34-38.
[12]周蕾.写在家国以外——当代文化研究的干涉策略[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13]毛尖.香港時态——也谈《胭脂扣》[M]//永远和三秒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24.
[14]刘登翰.道不尽的香港(序)[C]//施叔青.她名叫蝴蝶.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1.
作者简介:杨森,台湾中正大学中文系博士,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两岸电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