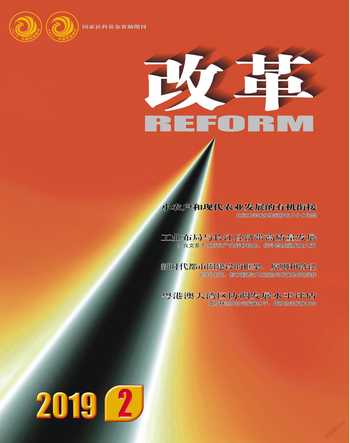贫困地区农户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的增收效应
胡伦 陆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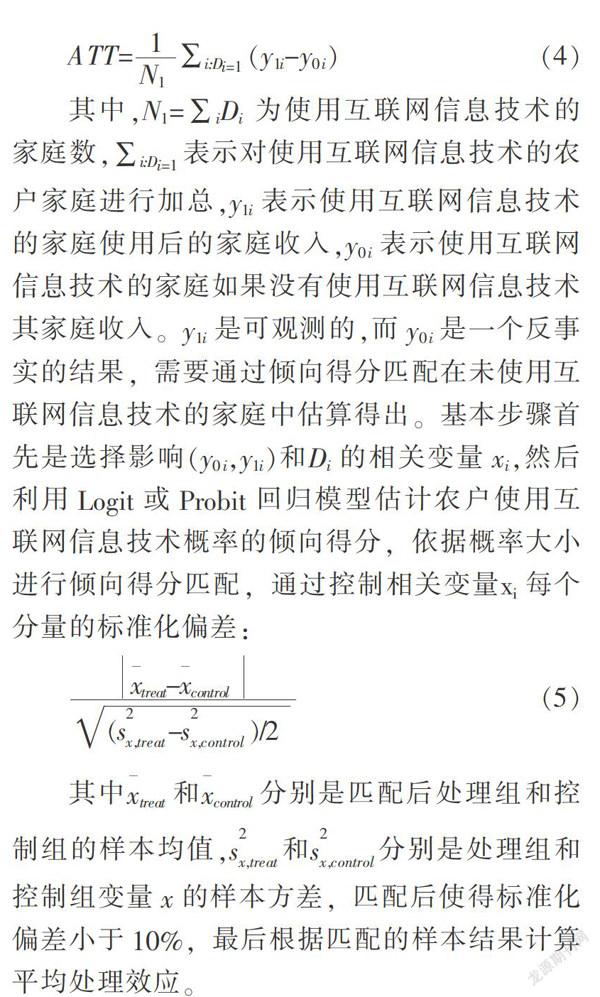



内容提要:运用贫困地区793份农户调查数据,考察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异质性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增收效果比较明显。在消除农户个体选择偏误后,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总收入、人均纯收入、非农总收入和农业总收入效应分别为25.7%、20.O%、23.5%、29.6%;采用OLS回归和Heckman回归估计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不同来源构成的收入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增收效应在不同教育水平和年龄阶段具有显著个体异质性;作用机制显示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会降低农户信息搜寻成本、形成较强价格效应、拓展市场参与范围、提升人力资本,进而达到增收效果。
关键词:互联网信息技术;农户增收;精准脱贫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 (2019)02-0074-13
我国正处于快速的信息化时期,以手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农村日益普及。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8%,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2.09亿,占比27.0%。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宽带网络覆盖90%以上贫困村的目标要提前完成。为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各级政府投入极大热情,推进农村现代信息技术建设,填补城乡“数字鸿沟”。国家先后组织实施了“互联网”示范工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化应用能力培训、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等活动,以此提升农民信息化能力。
那么,手机和互联网使用是否能够显著提高贫困地区农户收入?对此问题的回答,理论界尚未形成一致性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信息技术具有信息传输的便捷性、覆盖广和渗透性强的特性,能够减弱和消除市场信息在时空方面的障碍,节约交易成本,分享市场扩张成果,实现农民增收。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能够促进个体额外工资收入增加25%~30%[1],积极促进个体找到合适工作[2],增加非农就业概率[3]和创业机会[4],能够提高农业信息传播速度和改善农户收入结构,提升农民工福利水平[5]。但也有学者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发达地区与农村贫困地区之间、沿袭传统农业生产的小农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城乡之间形成了一道更加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且由于农村信息技术设施可接触的机会欠缺和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能力不足导致大多数生产者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的农户未能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分享到数字红利以及促进其收入增加。Bon-fadelli研究发现,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不利于弱势群体贫困户增收[6]。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手机和互联网使用的增收效应引起广泛讨论,但以往文献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方法上都有进一步优化的余地。一是一些研究使用宏观数据研究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运用微观数据资料估计分析的尚不多见,专门针对贫困地区农村的实证研究就更加缺乏;二是在使用微观数据考察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研究中,没有考虑个体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的异质性,无法体现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的增收效应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性;三是以往文献主要集中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的影响,缺乏对农户总收入、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和农业收入构成的影响;四是关于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增收效应的研究方法多数采用传统线性回归模型,忽略了样本选择存在差异性,可能存在高估或低估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的增收效应。
基于此,本文利用2016年陕西省贫困县793份农户微观数据,采用OLS回归方法、Heckman两阶段回归及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讨论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总收入、人均纯收入、非农总收入和农业总收入的影響,并深入分析不同教育背景、年龄下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不同收入结构增长群组的差异性,进而分析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的作用机制。
一、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分析
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增收的影响机制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能够直接降低农户信息搜寻成本。在传统的中间商交易方式下,农产品收购、售卖等交易环节众多,另外中间收购商利用信息垄断优势压制农产品收购价格,提升销售价格,从而获取高额利润,损害农户利益。而互联网信息技术通过提供透明化的农产品信息,直接匹配买卖双方,排斥中间商利润价格差的盘剥,尤其是对农户来说,互联网信息化工具的使用对打破其低水平均衡、改善信息困境、提高信息获取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是克服信息壁垒、促进农户收入增加的有效手段。一方面,与没有手机或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户相比,使用手机或互联网可显著增加农户在产品销售和农资采购等方面的信息可得性,即信息化意味着农户可获得更为有利的信息,获得最优的产品价格和经营利润[7]。另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能突破卖家和买家的时空限制,形成虚拟交易平台,交易的信息和过往记录能够形成大数据,降低买家和卖家交易农产品的信息搜寻成本。
第二,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具有较强的价格效应。现代通信工具使用能够显著影响农产品价格。Goyal指出,印度在互联网上提供价格信息和质量测试项目,该项目的推出导致当地大豆价格的上涨[8]。Jensen发现手机覆盖提高了渔民的销售价格并规避了渔民损失[9]。也有学者实证研究得出,手机覆盖的推出降低了农场的价格波动程度[10]。在某种程度上,互联网信息技术能够影响农户产品价格进而提升农户收入。
第三,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有利于拓展市场参与范围。与传统信息技术相比,手机或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对农户降低信息成本、克服信息壁垒具有明显成效[11-12],对农户拓展市场参与范围的影响更加显著。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作为一种特定的新型媒体,信息技术的扩散功能有助于改变农产品在产业链中的劣势地位。农户个体处在生产制造链的最低端,其通过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营销和售后的内部化,促进农产品由生产低端地位向高端营销服务地位的延伸,改变农产品产业内部链条利润分布不均衡状态,增加了参与营销服务环节的机会。另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能够促进农产品由省内向省外、国内向国际市场拓展,是连接不同市场的有利工具。互联网使用连接到的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农户连接到其他市场的机会也越来越多。销售渠道拓展和市场范围扩大为农户提供了更多盈利机会。
第四,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能有效提升人力资本。在信息经济时代,以互联网和手机为载体的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由此出现了互联网和手机偏向型技术进步态势。若把互联网和手机获取信息资源以提升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改进劳动生产率的技能,则意味着拥有更多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主要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资源渠道代表个体“技能”水平更高。而现实中,农户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能够加强自身学习能力和技术水平,有利于提升农户技能型人力资本。此外,农户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搜索相关的健康知识,使农户更加注重锻炼和保健,有利于保健型人力资本积累。无论哪种人力资本提升,都能提高农户收入水平。
二、数据来源、描述性统计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课题组于2016年8月组织15名研究生,专项调查陕西省集中连片区陕南片区旬阳县、丹凤县和商南县3个县。样本区贫困发生率为6.3%,贫困程度深,扶贫任务繁重,此地区具有比较典型的代表性。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基本情况、农户是否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及其不同收入支出构成等情况。调研采取随机抽样方法,对7个镇27个村的800农户进了问卷调查,剔除异常值和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793份,问卷有效率为99.13%。
(二)描述性统计
在变量选择上,本文使用调研前一年农户总收入、人均年纯收入、非农总收入和农业总收入作为结果变量,以是否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处理变量,选择农户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作为协变量,具体变量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下页)。
(三)模型说明
为了分析农户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对总收入、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较多研究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收入方程如下:
本文同时分析农户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对家庭非农收入、农业收入的影响。贫困地区农户不同的生计策略选择及差异化的兼业行为导致农户既有农业收入又有非农收入,而农户获得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行为可视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农户选择参与或不参与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即参与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的决策过程;第二个过程是选择参与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的农户进一步获得的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即参与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的收入。可见,只有在观测到农户选择参与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时,才能进一步观测到此部分农户获得的农业总收入、非农总收入的金额。因此,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在本文中是存在的。为了解决这种选择偏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来分析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农业总收入、非农总收入的影响。
Heckman两阶段模型涉及两个方程.即选择方程和结果方程,选择方程采用Logit模型来估计农户家庭是否参与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通过选择方程计算逆米尔斯比和是否参与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及其他控制变量作为自变量,而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为因变量,通过OLS模型估计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农业总收入和非农总收入的影响,具体公式如下:
贫困地区农户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不是一个随机行为,也不是随机分配的结果,而是农户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作出的选择,是自选择的结果。农户是否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不是外生变量,而是虚拟变量。因此,采用OLS来估计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家庭总收入、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会产生白选择导致的偏差问题。此外,农户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可能是由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决定,而这些特征同时也会对农业总收入和非农总收入产生影响,这就导致在估计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业总收入和非农总收入产生的影响时存在内生性问题,即农户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行为与农业总收入和非農总收入相关,也与误差项相关。
因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来解决这种自选择导致的偏差问题。Rosenbaum&Rubin于1983年提出通过构建反事实框架将非随机数据近似随机化[13],即由于数据缺失在无法观察到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农户如果没有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家庭收入,只能观测到使用信息技术后的家庭收入,由此提出采用倾向得分作为农户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概率。一般采用Logit模型根据影响农户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特征计算每个家庭的倾向得分,就能在没有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家庭中找到与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家庭相似的对照组,构建一个近似随机化的数据。根据Rosenbaum等的定义,处理者的平均效应为:
倾向得分匹配的匹配方法有多种,大部分不存在适用的绝对好方法,尤其在实证过程中,采用不同的匹配方法比较其匹配结果,如果得到匹配结果相似,说明结论是稳健的。而在本文中主要采用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局部线性回归匹配来进行具体匹配。
三、实证分析
(一)OLS回归模型与Heckman两阶段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本文分别采用OLS与Heckman两阶段回归模型估计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收入效应的影响,结果如表2(下页)所示。不难发现,OLS回归结果的P值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Heckman回归模型中的逆米尔斯比均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可见,本文采用OLS与Heckman两阶段回归模型是合适的。
基于OLS模型估计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总收入和人均纯收入的收入效应,结果发现,农户是否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对其总收入和人均纯收入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产生正向显著影响,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农户比未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总收入和人均纯收入分别高出23.4%、20.6%。同时,户主年龄、户主性别、是否有村干部、抚养系数比对农户人均纯收入产生显著影响;每年通信总费用、通信技术使用便捷程度、村庄自然灾害对农户总收入产生显著影响。基于Heckman两阶段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在矫正农户家庭参与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选择性偏差后,相比未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农户,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农户的非农总收入和农业总收入分别高22.3%和32%,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此外,户主年龄、户主教育程度、户主职业、村庄类型是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的共同因素,而户主性别、户主职业显著影响农户非农收入,户主性别、村庄类型、村庄地理特征显著影响农户农业收入。
(二)倾向得分匹配法的估计结果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第一步是估计倾向得分,选择匹配是关键,选择变量必须同时影响农户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以及家庭收入,同时选择变量也不会因为农户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而受到影响,因此本文选择户主年龄、户主教育程度、户主性别、户主职业、是否有村干部、抚养系数比、男性劳动人数、家庭耕地面积、通信总费用、村庄类型、村庄地理特征、村庄自然灾害作为匹配变量。本文使用Stata15.0软件运行模型,方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表3显著模型P值在1%水平上显著,模型拟合度较好。
从表3可以看出,本文选组的协变量对农户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行为有显著影响,其中户主年龄、抚养系数比、村庄自然灾害显著负向影响农户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户主教育程度、男性劳动力人数显著正向影响农户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户主性别、户主职业、是否有村干部、家庭耕地面积、通信总费用、村庄类型和村庄地理特征对农户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不显著。
(三)农户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对收入的影响
表4(下页)给出了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收入的处理效应估计结果。就农户总收入而言,使用邻近匹配法得到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TT)为0.26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使用半径匹配法、核匹配法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法得到ATT分别是0.262、0.244、0.261,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四种匹配方法结果相似,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匹配结果的稳定性,同时说明在消除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家庭以及未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家庭可观测异质性导致的显性偏差后,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家庭总收入比其如果未使用通信技术的家庭总收入高25.7%。相比OLS估计结果,收入效应增加了2.3%,说明传统线性回归模型没有考虑选择性偏差,低估了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总收入的处理效应。就人均纯收入而言,使用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局部线性回归匹配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分别是0.197、0.196、0.206、0.201,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四种匹配方法的平均处理效应值和显著性水平都类似,说明估计结果比较稳定,同时表明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农户比其如果未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农户人均纯收入高20%左右,比OLS回归模型估计结果低0.6%。就非农总收入而言,使用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局部线性回归匹配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分别是0.245、0.233、0.231、0.230,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四种匹配方法的平均处理效应值和显著性水平都类似,说明估计结果比较稳定,同时表明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农户比其如果未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时农户非农总收入高23.5%.比Heckman回归模型估计结果高1.2%。就农业总收入而言,使用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局部线性回归匹配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分别是0.314、0.295、0.291、0.284.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四种匹配方法的平均处理效应值和显著性水平都类似.说明估计结果比较稳定,同时表明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农户比其如果未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农户农业总收入高29.6%。
(四)不同方法估计出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差异分析
从表5可以看出,OLS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农户比其如果未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农户总收入、人均纯收入高23.4%、20.6%.相比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OLS估计回归结果总收入增收效应低估2.3%;平均纯收入增收效应高估0.6%。
Heckman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农户比其如果未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农户非农总收入和农业总收入高22.3%、32.0%。虽然使用Heckman方法修正了不同选择性偏差,估计的收入效应也不相同,严格意义上結果不具有可比性,但使用Heckman方法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结果表明在修正了选择性偏差后,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对农户家庭非农总收入和农业总收入有较高的显著正向效应。相比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Heckman回归结果得到的非农总收入增收效应低估1.2%;农业总收入增收效应高估2.4%。
(五)匹配的平衡性检验
为了保证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质量,需要对四种匹配方法作出平衡性检验,以检验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农户之间解释变量是否存在系统差别,结果如表6(下页)所示。四种方法匹配后,Pseudo R2的值都几乎为零,LR ch12似然比检验匹配前在1%水平上显著被拒绝,而匹配后都未被拒绝,标准偏差均值(Mean Bias)和标准偏差中位数(MedBias)都大幅下降,并且四种匹配方法匹配后的B值均小于25%。由此可以推断,经过倾向得分匹配最大限度降低了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可观测变量显性偏差,通过了平衡性检验,表明倾向得分估计和样本匹配是成功的。
四、拓展性研究
(一)分群估计
上文已经考察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不同收入构成的影响,并得到了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有助于提升农户收入的结论。但上述结论只是全样本层面的平均效应,并没有考虑不同农户群体教育程度、年龄之间的差异。为此,此部分考察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年龄阶段农户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对其收入影响的异质性,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
分教育样本来看,教育年限大于6年的样本使用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核匹配法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法,得到农户总收入效应分别是0.338、0.351、0.360、0.366,分别1%、1%、1%、5%的水平上显著。同理,农户人均纯收入效应分别是0.250、0.234、0.260、0.252,分别在1%、1%、1%和5%的水平上显著;农户非农总收入效应分别是0.329、0.301、0.315、0.288,分别在1%、1%、1%、5%的水平上显著;农户农业总收入效应分别是0.372、0.344、0.352、0.366,分别在1%、1%、1%、5%的水平上显著。教育年限小于6年的样本使用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核匹配法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法得到农户总收入ATT不显著。教育年限大于6年的样本农户总收入、人均纯收入、非农总收入和农业总收入的收入效应均大于教育年限小于6年的样本农户收入效应,说明相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户而言,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带来的收入效应更为明显,可能的解释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获取和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资源的能力较强,且拥有的信息资源的质量也较高,因此能够获得更高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的收入回报。
分年龄样本来看,年龄小于50岁的样本使用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核匹配法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法得到农户总收入效应显著为正,分别为0.346、0.490、0.419、0.464,而相比年龄大于50岁的样本,农户总收入效应不显著,说明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带来的总收入效应对年龄小的农户更加显著。但年龄大于50岁的样本使用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核匹配法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法得到农户人均纯收入、非农总收入、农业总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均值分别为0.280、0.323、0.354,均高于年龄小于50岁样本农户的收入效应,说明农户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带来的人均纯收入、非农总收入、农业总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对年龄大于50岁的样本农户更加显著。分年龄段的差异分析显示: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年龄较小农户的总收入促进效应显著高于年龄较大者,但其带来的人均纯收入、非农总收入、农业总收入的正向效应对年龄较大者作用比较明显,不论如何,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不同年龄农户收入构成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作用机制分析
实证检验发现,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不同收入构成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那么促进农户增收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呢?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可能从四方面影响农户收入:一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能够丰富信息获取渠道.帮助农户及时把握市场动态,增加收入所需的各种技能并且降低交易成本;二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通过提供市场消费的路径、促进农产品价格提升,从而促进农户积极获取不同收入;三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能够维持和提升人力资本,增强农户体魄;四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能够拓展市场范围,进而增加农户收入。
本文用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对信息搜寻的容易度”“对农产品价格的讨价还价能力”“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程度的知晓度”“对买卖双方交易的满意程度”作为交易成本指标,用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价格效应用“您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对获取农产品市场价格信息的容易程度”表征,“非常不容易”取值为1.“不容易”取值为2.“一般”取值为3.“容易”取值为4.“非常容易”取值为5;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对获取健康知识的容易程度作为家庭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用农产品销售市场范围作为市场范围的代理变量,“省内市场”取值为0,“省外市场”取值为1。
表8(下页)显示了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信息搜寻成本、较强的价格效应、拓展市场参与范围、提升人力资本的影响。从表8第1列可以看出,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确实降低了农户交易成本;从表8第2列可以看出,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通信技术使用能正向影响农产品价格;从表8第3列可以看出,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能够增加农户人力资本存量;从表8第4列可以看出,通信技术使用能增加市场范围,可能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能够提供较多的市场信息资源,降低市场进入壁垒,从而拓展市场范围。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16年陕西省贫困县793份农户微观数据,采用OLS回归方法、Heckman两阶段回归及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分析了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总收入、人均纯收入、非农总收入和农业总收入的影响效应及群体异质性和作用机制。
第一,运用传统的线性回归方法、Heckman两阶段回归及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的实证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对农户收入来源构成有显著促进作用,主要对总收入和农业收入的贡献较大,而对人均纯收入、非农总收入的影响有限。其中,户主年龄、抚养系数比、村庄自然灾害显著负向影响农户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户主教育程度、男性劳动力人数显著正向影响农户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
第二,OLS回归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农户总收入和人均纯收入比未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分别高出 23.4%、20.6%。Heckman两阶段回归模型在矫正农户家庭参与非农业劳动和农业劳动选择性偏差后,表明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农户的非农业总收入和农业收入比未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农户分别高出22.3%和32%。倾向得分匹配考虑农户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异质性的情形,估计出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农户比如果未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农户的总收入、人均纯收入、非农总收入和农业收入效应分别高25.7%、20.0%、23.5%、29.6%。与倾向得分匹配估计方法比较可知,运用OLS回归低估了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总收入增收效应的2.3%,而高估了人均纯收入增收效应的0.6%;运用Heckman模型则低估了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非农总收入增收效应的1.2%,但高估了農业总收入增收效应的2.4%。
第三,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收入增长效应不会是同质、等量状态,因农户资本禀赋存在差异性,农户内部必然出现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增收效应的差异。受教育程度在6年以上的农户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的增收效应大于受教育程度在6年以下的农户;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仅对年龄为50岁以下的农户的总收入更为显著,但其对年龄在50岁以上的农户的人均纯收入、非农总收入、农业总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更为显著。
第四,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形成较强的价格效应、拓展市场参与范围和提升人力资本等四种机制促进农户增收。
通过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快农村贫困地区通信技术设施建设,拓宽增收渠道。鉴于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收入增加具有正向效应,政府需要增加农村互联网信息技术设施投资,消除农村贫困地区因数字鸿沟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割”“贫富分化”等问题;努力提升互联网信息技术供给能力,降低以手机、互联网为代表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费率,提升上网速度,尤其要加快农村贫困地区光纤宽带网络、光纤到户和无线基站建设,与此同时要为农村贫困地区提供快捷、网络性能更稳定及优质低价的网络传输存储服务[14],以改善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要大力推广“互联网+农业”计划.促进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与农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更加先进、方便、实惠的经营体系和网络销售平台,以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第二,实施差异化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培训.提升农户信息获取能力。我国农户接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且年龄较大,导致其在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等实际操作中有效接受和辨识信息的能力较弱。因此,针对不同年龄和教育水平的农户,应实施差异化的互联网信息技术推广与应用措施。一方面,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教育分层中,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学历在小学以上的农户的收入带动作用更大,因此要将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瞄准具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农户,针对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农户,积极引导并培养其获取优质信息的意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更大程度地提升此类农户收入。另一方面,要重视低文化素质农户,普及此类农户九年义务教育,同时政府对此类农户要实施多样化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培训模式,并鼓励具有血缘、地缘关系的农户之间进行互联网信息技术交流,以提升此类农户的信息获取能力。增加互联网信息技术资源收入回报率。同时,不同年龄段农户互联网信息技术增收效果具有显著差异性。针对不同年龄群体,要实现多方合力支持互联网信息技术推广,以缩小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数字红利差距。一方面,针对年龄较大且信息接收能力较弱的农户有必要进行“一对一”专人辅导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的知识和实际操作步骤,提升其互联网信息技术基本知识及相关的基本技术技能,防止老龄化带来的收入下降问题。另一方面,年龄较小且信息接收能力较强的农户可以通过网络慕课学习等方式积极主动地学习金融基础知识[15],了解市场销售渠道信息。
第三,充分挖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能动效用机制。为促使农户有效使用互联网,有必要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及其配套设施,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充分发挥互联网信息技术对降低农户市场信息搜寻成本的作用,提升互联网信息技术“点对点”“面对面”信息平台的共享程度。农户应积极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通过线上线下农产品商品交易、进行支付结算及社会往来等形式融人数字社会[16],积累自身的互联网无形信用资产,降低农户潜在交易成本。鼓励农户利用市场公共信息资源,充分发挥微信等新媒体运营商信息终端普及率高的优势,积极拓展农产品交易市场参与范围,提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覆盖率和使用的回收率。与此同时,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为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提供的提升人力资本的健康知识,打造农村互联网健康生态信息平台。
参考文献
[1] FELDMAN D C,KLA AS B S.Internet job hunt-ing: a field study of applicant experience withon-line recruiting[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02, 41(2): 175-192.
[2]马俊龙,宁光杰.互联网与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J].财经科学,2017(7):50-63.
[3]周洋,华语音.互联网与农村家庭创业: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7(5):111-119.
[4]黄昊,舒何军.新媒体、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工作搜寻——基于长三角四市的调查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1):161-162.
[5]BONFADELLI H.The internet and knowledgegaps: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European Joumal of Communication,2002,17(1): 65-84。
[6]侯建昀,霍学喜.信息化能促进农户的市场参与吗?——来自中国苹果主产区的微观证据[J].财经研究,2017(1):134-144.
[7]APARAJITA G.Information, direct access tofarmers, and rural market performance incentral India[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Applied Economics, 2010, 2(3): 22-45.
[8]ROBERT, J. The digital provide: information(technology), market performance and welfarein the south India fisheries sector[J]. The Quar-terly Joumal of Economics, 2007, 122 (3):879-924.
[9]KYEONG H L, BELLEMARE M F. Lookwho's talking: the impacts of the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 of mobile phones on agricul-tural prices [J]. Joum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13, 49(5): 624-640.
[10]jOHN, J, CHARLES M, EMILY O. Transactioncosts and smallholder farmers' participationin banana market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of Burundi, Rwanda and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J]. Africa Joum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0, 6(1): 302-317.
[11]PAMPHILE K D. Transaction costs in thetrading system of cashew nuts in the northof Benin: a field study[J]. American Journal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2012, 71 (2):277-297.
[12]馬奔,温亚利.生态旅游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研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 (10):152-160.
[13]ROSENBAUM P R,RUBIN D B.The central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Jl. Biometrika, 1983,70(1): 41-55.
[14]杜振华.“互联网+”背景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愿景[J].改革,2015 (10):113-120.
[15]胡金焱,李建文.“双创”背景的新型金融模式:解构P2P网络借贷[J].改革,2018 (3):74-89.
[16]来有为,王开前.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形态、障碍性因素及其下一步[J].改革,2014(5):6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