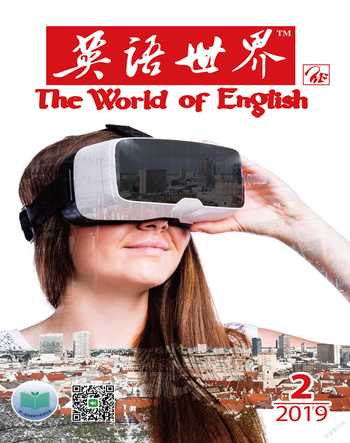从余光中的译论译品谈文学翻译的创作空间(一)
金圣华
【小引】
2018年10月13日,笔者应高雄中山大学之邀,于余光中教授九秩冥诞之际,出席参加“余光中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专题演讲,题目为《从余光中的译论译品谈文学翻译的创作空间》。
余光中先生毕生的文学事业,涉及四维空间,翻译乃其中之一,换言之,余先生创造的文学殿堂有四根大柱,翻译是四柱之一,支撑着这座巍巍巨厦,其重要地位不可或缺。
由于余光中先生的译论,早在一个甲子之前已经陆续发表,开风气之先,而目前学界时常引用的翻译理论在当时尚未成形,故本文不欲将余先生的译论跟后来者做一比较。本文着重聚焦在余光中本身的译论,以期寻根究底,理其脉络;此外,余光中的译品浩如烟海,本文也只能选其具有代表性的文本,略择一二,以为例子。
由于论文较长,故从本期起,将在本栏分期刊登,以飨读者。
(一)
常言道,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就好比戴着镣铐起舞,不但如此,还得在斗室起舞,尽管身负重荷、空间有限,舞者也必须举重若轻、挥洒自如,跳出翩翩舞姿——这就是行内对译家的期望,也是对出色译作的要求。
然而,翻译毕竟不同于创作,创作时可以天马行空、恣意尽情;翻译时因有原文在侧,译者无论多么才情横溢、创意勃发,亦不能在过程中率性而为、自由发挥,而必须依照原文亦步亦趋、循规蹈矩。有说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然而这创作的空间究竟有多大,却成为历来学者探讨无尽的主题、争论不休的重点。
其实,镣铐之下,斗室之中,舞者虽受种种牵制,仍要舞出百态千姿,并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种能耐,端赖其功力之深厚、用心之所在,换言之,翻译之中创作空间的大小,实在与译者自身在文学上的修养、造诣与匠心息息相关。
本文旨在以文学巨擘余光中的译论为根据,译品为实例,对文学翻译的创作空间此一议题,作一实事求是、寻根究底的探讨,从而剖析历来坊间各种名著尽管译者众多、译作如林、一书多译、各师各法,然种种译品中创作空间的宽窄与大小,却何以高下立判、瑜瑕分明的缘由。由于余教授的译论内容丰富,译品数量众多,本文只能择其要者,以为例证。
(二)
如所周知,余光中毕生的文学事业占有四度空间,即诗、散文、评论、翻译。历来论者对余光中的诗歌与散文钻研极多,对其翻译的评述却相对较少。余光中曾经为翻译作不平之鸣,认为希腊神话中有专司灵感的九位女神,遍及艺术、诗歌、音乐、舞蹈、戏剧、历史、天文等范畴,却偏偏独缺极其重要的翻译,因此,提倡把翻译尊奉为“第十位缪思”,不仅如此,诗人毕生在创作之余,也的的确确曾跟“第十位缪思”展开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永恒之恋1。
余光中早在学生时代已崭露头角,开始文学创作。1952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出版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当时已经开始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名著《老人与大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的翻译,以连载方式在《大华晚报》发表;同年以第一名考入“联勤海陆空军编译人员训练班”;次年,加入“国防部”联络官室服役,出任少尉编译官。从这段早年的经历,可以得见余光中的创作与翻译,是并蒂莲开、同步发韧的;尽管诗人日后自谦“翻译乃别业”,但是以最初的从业实况来说,反倒像是“以翻译为正业,以创作为别业”。不管如何,无论是正业或别业,翻译在余光中的文学生涯中,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则无可置疑。以下试将余光中与翻译千丝万缕的关系,逐一审视,以显其经纬与脉络。
(三)
要讨论余光中有关翻译的真知灼见,首先应从他对翻译的认知和看法着手。余先生身为蜚声国际的著名诗人、执教大学的文学教授,却对翻译情有独钟,认为“翻译乃大道”,绝对不是为人轻忽的小技。“我这一生对翻译的态度,是认真追求,而非逢场作戏”2,他在文章里慎而重之地宣称。
由于这种认真的态度,促使他对翻译的本质上下求索、反复思量。身为创作不断的文学家、努力不懈的翻译者,他在1969年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创作与翻译》,剖析了两者之间微妙的关联和异同。诗人说:“流行观念的错误,在于视翻译为创作的反义词。事实上,创作的反义词是模仿,甚至抄袭,而不是翻译。”在他心目中,文学性质的翻译,“尤其是诗的翻译,不折不扣是一门艺术”3。要知道这时候,余光中不但早已翻译出版了《老人与大海》和《梵谷传》,连《英美现代诗选》亦已于1968年问世,因此,作者所述的并非人云亦云的泛泛之词,而是现身说法的过来人语。“真有灵感的译文,像投胎重生的灵魂一般,令人觉得是一种‘再创造’。直译,甚至硬译、死译,充其量只能成为剥制的标本:一根羽毛也不少,可惜是一只死鸟,徒有形貌,没有飞翔。”4由此看来,余光中的译论,从一开始,就非常着重于译文如何再现原著神髓、原作风格的问题。毕竟,在他心目中,翻译是一种艺术,而艺术的创造,往往是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在这篇文章之中,余光中致力阐明自己既不认同上述的“直译”,也不赞成“假李白之名,抒庞德之情”那种“意译”,而坊间有关“意译” 与“直译”的高下争论不休,译者下笔时到底该何去何从?余光中明确指出,翻译之为艺术,是无可避免包含“创作”的成分的,他认为翻译与创作都是心智活动,两者相似之处,在于彼此于操作过程中都无法忽略匠心与抉择。翻译时“例如原文之中出现了一个含义暧昧但暗示性极强的字和词,一位有修养的译者,沉吟之际,常会想到两种或更多的可能译法,其中的一种以音调胜,另一种以意象胜,而偏偏第三种译法似乎在意义上更接近原文,可惜音调太低沉”。这时候,译者就必须斟前酌后、顾左盼右、煞费思量了!这种情形,余光中认为“已经颇接近创作者的处境了”5。此外,翻译时,不但用字遣词要选择,字句次序的排列也得注意6,英文与中文,毕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相异之处,涉及内在与外在的因素,“内在的属于思想, 属于文化背景; 外在的属于语言文字”7。因此,余光中对一个称得上优秀认真的译者,要求甚严:“成就一位称职的译者, 该有三个条件。首先当然是对于‘施语’(source language)的体贴入微,还包括了解施语所属的文化与社会。同样必要的,是对于‘受语’(target language)的运用自如,还得包括各种文体的掌握。这第一个条件近于学者,而第二个条件便近于作家了。至于第三个条件,则是在一般常识之外,对于‘施语’原文所涉的学问,要有相当的熟悉,至少不能外行。这就更近于学者了。”8余光中本身就是这样一位“三者合一”的翻译家。尽管如此,在长年累月的创作生涯与翻译实践中,他深深体会到要做到译作和原文无论在形、在神方面,都等量齐观、铢两悉称,又谈何容易!因此,提出了“翻译如婚姻,是一种两相妥协的艺术”的看法。他认为原文和译文之间,必须慢慢磨合,相互妥协,以求“两全之计”,“至于妥协到什么程度, 以及哪一方应该多让一步,神而明之,变通之道,就要看每一位译者自己的修养了”9。在同一篇文章之中,他还提到译者与巫师的比喻,这个比喻,他在1991年为香港翻译学会撰写的书签中,说得特别清楚:“如果原作者是神灵,则译者就是巫师,任务是把神谕传给凡人。译者介于神人之间,既要通天意,又得说人话,真是‘左右为巫难’。”10此处值得注意的是“通天意,说人话”,巫师倘若深谙天意,却向凡间重述得语无伦次、含混累赘,则完全失去了传达的意义,翻译亦然。然而这种功夫,毕竟很难,否则,也就不必大费笔墨去阐述了。因此,余光中认为翻译是一种“十分高明的仲裁艺术,颇有鲁仲连之风,排难解纷的结果,最好當然是两全其美,所谓‘双赢’,至少也得合理妥协,不落‘双输’”11。他觉得“译文是旗,原文是风,旗随风而舞,是应该的,但不能被风吹去。这就要靠旗杆的定位了。旗杆,正是译文所属语文的常态底限,如果逾越过甚,势必杆摧旗扬”12。翻译在余光中心目中,因而是妥协,是仲裁,是一种兼顾两语双方的中庸之道。
——黄忠廉教授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