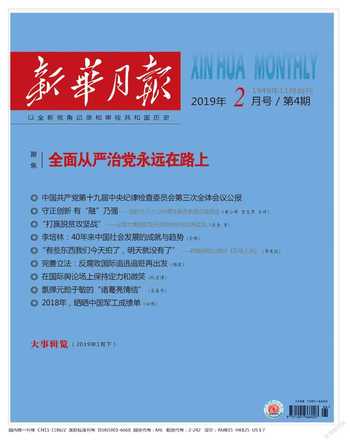战争哲思的当代共鸣
胡欣
经过几千年的演进,人类文明创造了空前的物质繁荣,但关于争斗的本质却似乎没有改变过。
20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战争与和平始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深刻命题。“一战”前,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极度尖锐,而在那个地球村初显雏形、工业文明突飞猛进的“进步时代”,进步带来自信,自信催生盲目,积极备战的各国几乎都相信战争的正义盾牌和制胜长矛掌握在自己手中。
当时,有人单纯地以为,战争已是无利可图的暴政,新世纪的繁荣与和平乃人心所向(这种心态与当今世界那些过度迷信全球化的人有相似之处),如英国媒体称,“所有的君主、政治家和国民都知道……战争将是一场无可估量的大灾难”。遗憾的是,理性从来都不是国家的全部,理性的立场从来也都是千差万别的。萨拉热窝枪声响起后,一切寄托于文明进步的信心与愿望迅速崩盘,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驱动下的战争机器轰响了八月的炮火。
从“一战”废墟中幸存下来的人渴望不再有如此惨烈的杀戮。尽管和平主义的愿望十分真切,却依然挡不住20多年后另一场浩劫的发生。
追究“一战”爆发的原因,有说是帝国主义的争夺,有说是均势的破产,还有说是“修昔底德”式的宿命,而战争的后果更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对欧洲,大战的结束不仅酝酿出“二十年危机”进而走向新的大战,更拉开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体系的衰退,西翼的英法等老牌帝国元气大伤,东侧新的洲际大国苏联渐渐兴起,隐现的裂痕昭示了未来的伤口。
对美国来说,“一战”让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的角力成为对外政策中日渐凸显的矛盾,并开始逐渐赋予美国自认为天命所归的全球领导责任。对弱国,这是一场混杂了怯懦的胜利者、弱小的无助者复杂心态的国家记忆。当时,如中国这般在国际上处于权力等级底层的国家,即便战后侥幸领到一张胜利盛宴邀请函,也不过是从上一个列强的盘中餐变为新列强的盘中餐而已,这也促成了近现代中国一个强烈的认识,即弱国无外交,时至今日依然是影响中国行为的重要观念之一。
纪念是为了不忘却痛苦的起源。世界大战清晰地警告世人,大国既可以是国际安全最重要的稳定轴,也可以是最危险的破坏者。尤其当强国站在军事金字塔的上端,膨胀的决策层、被煽动的民意、军事冒险主义的盛行和自以为是的战争正义,都会成为国际安全的重大威胁。那场大战后,国际社会曾试图建立一种既尊重权力现实、也维护和平理想的诸边制度。尽管先天不足的国际联盟很快就堕向失败,但也开创了建立全球性国际安全组织的先河,为“二战”后建立联合国提供了重要借鉴。
即便如此,现实主义的魔咒似乎从没有解除过,新兴大国与现有霸权之间的竞争似乎仍在延续,只是换了剧场和演员。在纪念“一战”结束100周年同时,也有人抱着旧思维寻找下一场大战的原罪之国,并把中俄这样的新兴大国视为新的威胁来源。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基辛格在把美中关系类比为“一战”前的英德关系,进而提出两国可能发生冲突的警告,质问“冲突将把我们带向何方”。
历史毕竟不会简单复制。中国不是帝国抑或“修正主义”国家,相反,而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安全机制的倡导者、受益者和遵守者。今天的中国更关注如何实现和谐治理的愿景。中国想为世界提供的,是在同一片天空下共享繁荣的机遇。中国还一直努力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开创某种既竞争又共处且能互惠的关系模式。
近来美国国内对华论调的集体转向虽然预示了未来两国关系必将面对更严峻的挑战,不过,大国间竞争依然存在可预见性和可控性,塑造新时期的戰略稳定也并非遥不可及。
从历史经验看,稳定的关键在于拥有相互敬畏的战略力量、避免军事冲突的共识,以及合作共赢的利益空间。当然,塑造这样的关系,过程必然是动态的,也存在被不可控变量改变进程的风险。正因为如此,更加需要大国间能正确地界定核心利益,做到相互尊重、避免冲突。
还顾望来路,所思在远道。缅怀逝者的伤痛是不区分种族和意识形态的,渴求和平的愿望真正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反思“一战”教训,最终目标不是要彰显胜利者的荣耀,而是要让世人更清醒地记住,战争从来不是游戏,而是国之大事,事关生死存亡。轻易信奉炮舰主义的国家,往往难逃被反噬的命运。
(摘自《世界知识》2018年第23期。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