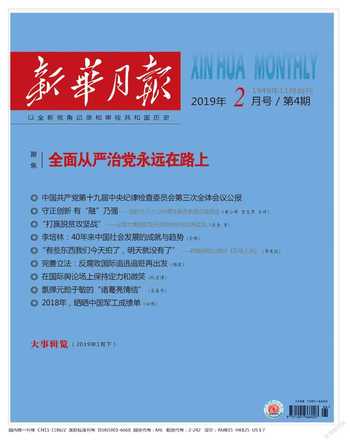警惕全球冲突极端年代可能重现
什洛莫·本·阿米
已故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把20世纪描述为“极端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国家社会主义导致出现古拉格集中营;自由资本主义导致出现周期性萧条;民族主义则引发两次世界大战。霍布斯鲍姆后来预言,未来会成为过去和现在的延续,其特点是“暴力的政治和暴力的政治变革”,以及“社会分配,而不是增长”。
民族主义撕裂社会
历史经常前后呼应。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名言是“根本没有社会这回事”,只有“独立的个体”。当今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政客制造分裂的世界观和自私自利的行为,就应和了撒切尔夫人的言论。
如今,就像20世纪一样,民族主义正在撕裂社会,分裂昔日的盟友,方式是煽动对“他者”的敌意,为有形的和法律上的保护主义壁垒辩护。大国在很大程度上重新采取冷战时期的姿态,在心理上——甚至可能是在军事上——为公开冲突做好准备。
正如霍布斯鲍姆预测的那样,急剧增长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成为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增多的主要原因,甚至导致一些国家转向威权主义。欧洲十年来一直坚守紧缩政策,削弱了福利国家的基础,促使数百万选民投入民粹主义者的怀抱。这证明糟糕的经济状况与政治极端主义之间存在联系,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强调了这一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今的政治越来越像20世纪的事态发展,一大原因是人们担心重蹈“大萧条”的覆辙——这种担忧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因为这场金融危机令人想起1929年的股市崩盘。
但紧缩政策走得太远,使得反体制的政客们能够利用经济上的困难(以及仇外心理和厌女心理)来赢得支持。许多主流政党为了在选举中具有竞争力,都偏离了中间路线,导致整个政治领域变得越来越两极分化。
政治走向趋于极端
这种趋势出现在美国,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共和党基本上已经没有温和派。在英国也一样,在杰里米·科尔宾领导下,更加激进的工党面对着被脱欧极端分子绑架的保守党。
在意大利,主流政治力量在选举中失败后,民粹主义的五星运动和民族主义的联盟党团结在一起,组成摇摇欲坠的执政联盟。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对弗拉基米尔·普京说,俄罗斯是意大利的“战略伙伴”。很显然,作为欧盟和北约核心成员的意大利已经成为可能破坏稳定的国家。
在西班牙,人民党在强硬派巴勃罗·卡萨多的领导下已经毫不掩饰其民族主义倾向。首相佩德罗·桑切斯领导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与人民党一模一样。为了与极左的民粹主义“我们能”党竞争,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抛弃了费利佩·冈萨雷斯留下的中间路线遗产。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的一批批选民抛弃了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中右翼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其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绿党获得了较为温和的社会民主党的选票,而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赢得大量选票。由于中间派力量遭到削弱,德国继续充当统一欧洲支柱的能力岌岌可危。就连德国有朝一日可能再度由激进的领导人统治的想法都不再像以前人们认为的那样牵强。
随着多个民主国家放弃温和的态度,滥用权力的现象正在增加,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在美国,特朗普经常妖魔化反对者,非人化边缘群体;在他执政的第一年,出于政治动机的谋杀案数量增加了一倍,这些谋杀案主要是由狂热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制造的。
和平体系不堪压力
这些事态发展构成的风险并不局限于有关国家。维护相对的世界和平——或至少避免国家之间的大型战争——取决于牢固的联盟,还有领导人是否认识到他们手中的武器可能造成多大破坏。但是,随着短视、激进和缺乏经验的人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这两个防止战争的支柱被削弱了。
事实上,世界和平的体系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在俄罗斯与北约国家的边境附近出现了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
更糟糕的是,特朗普让美国退出了《中程导弹条约》,打破了世界几十年来在核军备控制方面取得的进展。特朗普似乎希望通过威胁“发展核武器”,来迫使俄罗斯(以及中国)与其达成新协议,但他不太可能成功。当年与罗纳德·里根谈判的是具有改革思想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而特朗普将面对的是渴望权力的普京。
全球挑戰多样难控
世界所面临的风险还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监管的新技术而加剧。网络战已经成为日常可见的现实;事实上,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针对北约国家的网络攻击,一旦出现将触发北约的共同防御保障机制。同样,由于没能压服反对意见,联合国到目前为止还未出台针对基于人工智能的致命性自主武器的监管法规。
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加剧,暴力冲突的风险还会继续增加。除常见问题外,中东和非洲的大规模荒漠化将带来饥荒,其规模将远超20世纪发生过的饥荒。人类迁移的数量激增,争夺资源的斗争将加剧。
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对于20世纪的人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但基本的政治发展态势却是人们非常熟悉的。现在我们应该评估这些态势预示着什么,并严肃对待历史的教训。
(摘自2018年11月28日《参考消息》,原载于2018年11月20日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作者为以色列前外交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