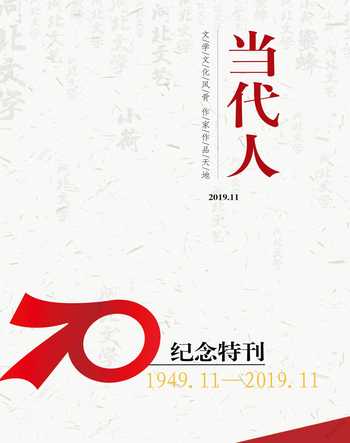一把泥
下午上班后,接待室里清闲下来,甄德志来到程振洋办公室,不知怎么就议论起了农村建房。“‘齐不齐,一把泥’,还真是这么个讲究。”程振洋说。
在邢台西部这一带农村,从前盖的都是石头房子,青石或者红石,红石居多。盖房时,垒墙的石头,分表石和里石,表石大而整齐,里石就差一些了,往往凹凸不平、坑坑洼洼。里石外边要糊上泥,一来是为了堵住缝隙,二来找平了墙体,经泥瓦匠一抹,墙变得平实光洁。这就是俗语说的“齐不齐,一把泥”。
正说话间,从外边走进来一个老乡。
这老乡胡子拉碴,头发花白,已到花甲之年。都是三里五乡的,程振洋认识,他是西坡村的。
他站在那里,犹犹豫豫不说话。
程振洋问:“咋了老乡?我也叫不上来你名字,你有事?”
他苦笑一下说:“我叫李大海,来反映个事。”
程振洋指指桌前的长板凳说:“来,坐下慢慢说。”
李大海边朝长板凳走边说:“吴三军把我房子点着了。”
程振洋一听,从椅子上呼地一下站了起来,皱起眉头问:“他是故意纵火吗?”
“不不不……不是。”李大海赶忙解释,他摇着右手说,“他是不操心,才把房子弄着了的。”
李大海把事情来龙去脉简单说了一遍。2014年底,吴小庆翻盖房屋,将相邻表哥吴三军的旧房拆了,吴三军没地方占,吴小庆找到李大海说,看能不能让表哥在东垴你旧房里住。李大海答应了。吴三军就一直住在那里。到去年二月份,不知道咋搞的,房子着火了,烧得不成样子。吴三军是个光棍,心眼儿也不全。李大海找吴小庆交涉,吴小庆不说长短,村干部也管不了。
程振洋打开手机,看看时间,才下午三点多点儿。他用商量的口气问甄德志:“要不,咱跟李大海去西坡村,察看察看现场?”
甄德志是浆水镇里的信访办主任,兼浆水法庭陪审员。程振洋是镇前任书记要过来的信访办一名临时工,浆水法庭一成立,他也当上了陪审员。
浆水法庭在镇里有间办公室,庭长在法院里办案,平时根本顾不上来,全凭程振洋盯摊儿。别看程振洋是名临时工,可全镇一些难掰扯的信访案件、纠纷,要靠他去化解。也就是说,程振洋是镇里解决信访纠纷的主力。几年来,化解了不少老大难,去掉了镇书记、镇长心里的疼痛,他可是镇里的一个宝贝。
甄德志对程振洋差不多是言听计从,知道他是个急脾气,再说,看完现场,顺便就可以回家了。便说:“行,咱这就去。”
李大海是骑三马车来的,还骑着三马车回去。程振洋和甄德志各骑自个儿的摩托车。
西坡村距浆水镇六公里远,出浆水村一直朝西。去年,沿浆水川河道,修了一条“苹果路”,宽敞、直溜,骑摩托车只用十几分钟。
西坡村,顾名思义,整个村建在西坡上,西高东低,东边是一条从北至南的河流。穿过一座小桥,上坡,经过南口村南,就到了西坡村东。程振洋和甄德志跟在李大海后边,他们朝南一拐,在胡同拐了两个弯,停在了一片废墟前。
这是一溜红石头西房,南边两间被火烧得落了架,梁檩椽横七竖八,裸露着残余的焦黑,从房顶上落下的石板,歪三扭四,有的摔成了几瓣。北边那房屋,靠南边梁檩椽都被烧成了黑炭,其中一根檩强撑着,岌岌可危,说不定啥时就会塌落下来。
程振洋让李大海把村干部找来。一会儿来了一位管民调的村委委员。他们从镇里来时,就带着皮尺。甄德志和村委委员拉尺子,程振洋在纸上画了个草图,标上尺寸。完全损坏的房屋宽5.26米、长7.3米;损坏严重的房屋长1.2米。
李大海背靠一棵梧桐树蹲着,不吭不响地瞅着他们丈量,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临走时,程振洋让李大海明天上午九点到法庭调解,让村委委员通知吴三军和吴小庆。
第二天上午,李大海提前来了,那两个人也按时到庭。
程振洋瞅瞅三人,说:“都说说吧!”稍停,他瞅着吴三军说:“三军先说吧。”
吴三军是个大个子,长胳膊长腿,五官长得憨实,目光呆滞。他说:“不知道咋回事,早上我往地里走时还好好的,回来就着没了,邻居都在那儿救火。”
程振洋点名说:“小庆,咋弄?”
吴小庆仰头瞅一眼屋顶,也不看程振洋,也不看李大海,又盯着对面的墙,说:“我介绍他去那里占,也没让他着火。”
程振洋又点名问:“李大海,你说咋弄?”
只见李大海犹豫了一下,之后他站起来,把程振洋叫到院子里,小声把自个儿的意见给程振洋说了。“要是好好叨叨说,都是乡里乡亲,就算了。要是不好理好道,原来是啥样,还弄成啥样。”
程振洋心里说,这个意见还私下说啥,有啥不能当面说的?于是就说:“咱还是进屋说吧!”
回到屋里,都坐下。程振洋说:“我知道,调也不一定一下调成。想想这事,人家好心好意让你住下,没签合同,一分钱也没要,这会儿弄成这。”说到这里,程振洋瞅着吴三军说,“看你夯哩!俗话说,薅毛的拣有毛的薅,三军啥也没……”
吴三军轻轻哼两声,说道:“你算说对了,俺啥也没了,锅碗瓢勺和被褥,着的着砸的砸,本来俺就是个光棍儿,这下真是光的连锅碗瓢勺也没了。”
程振洋瞅着吴小庆说:“这事你得好好想想,是你介绍住进去的,现在弄成这,粘也粘住你了。”
吳小庆小声嘟囔道:“我没钱!”
程振洋笑着说:“三军没毛薅,你还力量点,就是没钱也能顶起来。”
吴小庆不吭声,盯着对面的墙,一个劲地眨眼。
程振洋说:“小庆,都说做人要顶天立地,敢作敢当,这事跟你有关系没?”
吴小庆支支吾吾地说:“也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三军没地方住了,是我找的大海,三军住进去,房子毁了。”
吴三军打了一辈子光棍儿,没媳妇没孩子,人也半傻不俏的,别说赔李大海的钱,自个连一套被褥也没了。房屋着了火,还是一个亲戚可怜他,给了点钱,才置了一套锅碗瓢勺,一床被褥,暂时住在大哥三间旧房里。
吴小庆和吴三军临走时,程振洋让吴小庆回家考虑考虑。吴小庆说,那让我想想吧!
过了十来天,程振洋给西坡村管民调的村委委员打电话,让他通知三方来法庭调解。这中间通知过两次,推三阻四的,都没来成。所以,这次程振洋特意嘱咐村委委员,不行你带他们来。为了保险起见,他还亲自打了电话,吴三军没手机,程振洋让吴小庆通知他。
等到第二天早起,西坡村村委委员打来电话说,小庆要去邯郸,去不成了。中间通知两次,都是吴小庆来不了。程振洋一听火气就上来了,他大声对村委委员说:“不行,他就是去北京开会也不行,这次必须来,有多大的事!才这点事就不敢面对?”
那边说,行行,我通知他们去。
放下电话,程振洋有些后悔,觉得不该对人家村委委员着急,好像村委委员犯了错,训村委委员一样。
不管怎么,吴小庆还是来了。李大海和吴小庆是一前一后来的,吴三军没来。可吴小庆走进程振洋办公室,还没站稳就急着说去邯郸。
程振洋急了。“你不能去,坐这儿!”
吴小庆心里一颤,忙坐下。
程振洋口气有所缓和,说:“前边有个拦路的,后边撵来个债主,你还有心思干啥?”
吴小庆一脸尴尬,坐在那里不吭声。
程振洋说:“你甭去邯郸了,去了也干不成事。”
吴小庆被说得脸有些涨红,他不自然地笑笑说:“让你说对了,在邯郸谈了笔买卖,眼看火炎炎地成了,可就是定不下来,好像你会算卦,让你说准了,嗯!今儿不去了。”
程振洋问:“为啥不让吴三军来?”
吴小庆回答:“他是我表哥,他穷,赔不了钱,给他说也不懂,也说不通。我安排他去那儿住的,我也有责任。”
吴小庆总算认识到自个儿有责任了。程振洋让吴小庆先回避一下,他单独先征求李大海的意见。李大海的意见是,给个钱也行,重建也行,反正都是老熟人,老兄你看着整吧!
李大海出去,程振洋把吴小庆叫了来。吴小庆问:“给五六千行不行?”
程振洋说:“你拍拍自个儿的心,看看行不行?”
吴小庆听那口气,肯定是不行。他说:“不行了,我给他修修。为修铁路,水门村拆了不少房子,有石头、石板、旧木料,我可以买了,重新整整,也花不了多少钱。”
程振洋说:“行,修旧如旧,也行。”
吴小庆有些犹豫,他嘟囔道:“重建,就是时间长些,摊的工多,要是自个儿一个人建,时间太长,修得好了赖了,说不清,要是利索,多给他个钱。”
程振洋问多给多少。
吴小庆反问:“你说给多少?”
程振洋说:“你自个儿说给多少,能打住人家心火就行。”
吴小庆犹豫不决。给多了,自个儿心里舍不得,给少了,人家不同意,真是不好说。程振洋让他在这里想想,他出去给李大海谈谈。
李大海在院东边一个门台上坐着,他见程振洋朝这边走来,仍坐那儿没动。程振洋到他跟前,蹲下去。
“你到底要多少钱?”
“说不清,也算不准。要多了,他不掏,少了我不干……不好说。”
程振洋站起来,说:“你跟我进来。”
二人进屋坐定。程振洋总结了一下,有三个标准:第一,按铁路征地补偿标准补偿,房子已经有了尺寸;第二,小庆你给建,工夫不打账,我算了算,做房架、拉网板、上梁、抹苫、上石板、摔里皮泥、修屋地、抹麻刀,别看两间半房,不省事,东西不值钱,工儿值钱,以前都是乡里乡亲互相帮个忙,现在,都忙啦啦的,叫谁去都要给工钱。搂了搂工,得一百八几十个,均拉一个工一百五,下来就是两万七,再说质量好了赖了,合适不合适,光缠缠了;第三,就是给个钱,一个村的,低头不见抬头见,都得讲人情,好多事不是钱能买来的,粗算了一下,就是一万五到两万五之间。
不料,就在这时候,吴小庆说了一句,让屋里的三个人都没了话。他说:“就是说成,我也没钱,咋办?”
屋里的人沉默了,就连程振洋一时也不知道说啥好。李大海从兜里抽出一根烟,又掏出打火机,“啪,啪,啪”,捏了三次才打着火。他把烟卷对在火苗上,重重地吸了一口,然后就攥着打火机,阴着脸,吧嗒吧嗒地狠劲抽。
正好到了中午,镇里开饭了。程振洋让他俩都别走,中午到外边吃点饭,下午继续。
下午两点,俩人都来了。
程振洋让吴小庆出去一下,吴小庆知道他要和李大海单独谈,不吭不响地走了出去。
“你愿意多要点,这理解,要三万他没有也没法儿,少要点他还能想想法。如果你要起诉他,打官司,那关系就彻底闹掰了。甭光听算账,要到手里才是东西,咱说的再好,他真没,咋办?看来这事你就得背屈,你考虑考虑。”
李大海始终不吭声,一根烟抽完了,再接一根。程振洋让他在外面等会儿,把吴小庆叫进来。李大海啥也没说,出去了。吴小庆走了进来。
“你想咋办?”
“这——这——咋办?”
“咋办?给钱!”
“给多少钱?”
“两万五。”
吴小庆一听笑了,是皱着眉头笑的。“我真没,我能屙钱啊!那我借你的吧!”
这不是明显要耍赖吗?程振洋管这事,哪有借管事人钱的道理?程振洋硬着头皮,说:“我也不怕你借。话说回来,没啥多与少,还是老百姓说的那句话,‘齐不齐,一把泥’,只要这把泥糊上去,能抹平就行,不管多和少,沾光背屈说到明处。”
吴小庆咂咂嘴巴,小心地试探着说:“你跟人家商量商量,看一万八行不行?”
程振洋一听此话,心里不由得笑了。这下有门了,离调解成功不远了!但他表面上仍不动声色, 只是说,去跟他商量商量。
到院里,給李大海一说,李大海头也不抬,说:“没法弄,这样我赔得太多!”
程振洋说:“你自个儿翻盖新房,赔个人情呗!”
李大海咂巴咂巴嘴,像是下不了决心。他说:“哪怕他出个两万二三,叫我少赔点。”
程振洋又一听,心里有谱了。他笑着说:“你是不是让我摸一下底儿?痛快点,两万沾不沾?”
李大海长出一口气,笑了,“就那吧!”
回屋,见了吴小庆,程振洋伸出两个指头,说:“两万。”
吴小庆没打磕绊,也说:“就那吧!”
双方说好钱五天内交清。天色已晚,就不立协议了,等吴小庆交了钱,再立协议不迟。程振洋把他俩送到门外,瞅着他们离去。
这时候,近处的山峦在夕阳的映照下,涂上了一层瑰丽的颜色,显得山坡更加生动了。蓝蓝的天空,似明净的天湖,湖中还飘着几片零星水草。太阳已到了西边遥远的群山山顶,变得柔和了,像一个红彤彤的光盘。过了一会儿,太阳亲着西山的山头,圆脸也被笑红了。紧接着,太阳悄悄一跳,藏到了西山的背后。
以后的几天里,程振洋边忙别的事边想,可别再节外生枝,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但愿吴小庆能如数按期交款。
不想,第三天下午一上班,程振洋正在办公室草拟一份调解书,接到吴小庆的电话,吴小庆说:“我弄清啦!钱给了他。”
程振洋问:“你给大海钱了?”
那头说:“我把钱给他了。”
程振洋说:“清不清你说了不算,得让李大海说。”
过了一个多小时,李大海来了。李大海说吴小庆给了他两万,吴小庆恐怕立协议,嫌败兴,就提前把钱给了李大海。
程振洋嗤嗤笑了,他想起了自个儿给吴小庆说过的话。这时候甄德志从外边走了进来。见程振洋高兴的样子,便笑着说:“咋,一把泥抹齐了?”
程振洋说:“只要这把泥能把事儿抹平就行!”
李大海也嘿嘿笑了。“你们说得还挺形象哩!”
(王金平,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邢台市作协副主席、郑州小小说传媒有限公司签约作家。曾获第十一届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选三等奖、中国当代小说奖等。出版个人文学作品集5部。)
编辑:安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