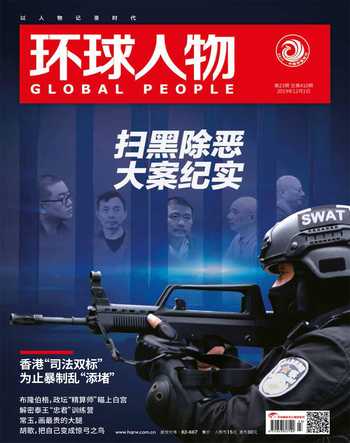90岁的管管,19岁的童心

徐学
两岸交流之初,在内地搞到一本台版书很难,见台湾作家更难,能近距离观察台湾作家更是难上加难。40年后的信息时代,天涯若比邻,台湾文友的样貌笑容和新出炉的创作,一下子就被推送到眼前。岛内80岁以上玩微信的作家并不多,从前是洛夫,我的手机里至今还有他生前的微信语音;现在是管管,我经常在朋友圈看到他的新鲜事。这不,最近他又出了一本幽默诗集《烫一首诗送嘴,趁热》,诗集的扉页上写着“九十岁的人生,十九岁的青春”。
我曾多次和创世纪诗社的同仁相聚论诗。白天会上的焦点是洛夫、痖弦,晚上酒酣耳热,正是管管大显身手之时。只见他一头白发扎成一个小辫儿,一身牛仔服时髦得褴褛穿洞,或朗诵创世纪诗群的名诗,如痖弦的《盐》,或朗诵他自己的诗。
这个老顽童用地道的京剧腔朗诵:“大清早,妻就拿着菜篮子捡拾蝉声,一会工夫/就捡拾了满满一篮子蝉声回来/小孩子们却以为家里有了树林/他们正在树底下睡觉呢(他即兴把“在树底下睡觉呢”改成“在树底下打秋千呢”)妻却把蝉声放进洗菜盆里洗洗/用塑胶袋装起来放进冰窖了……”众人听得入神,他却忽然停下,举起手说:“报告老师,我忘词了。”一片笑骂中,他念出最后两句:“听说/他们压根儿/也没吃过蝉声这种东西。”话音未落他又说:“还好吧,这首诗?好,大家鼓掌!”
遇上这样有趣的人,我一定不会放弃与他结交的机会,赶忙近前请教:“您叫管管,我怎么觉得您好像是从来没被什么人管理过似的,天不管地不管……”管管听后仰面笑得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而后说,自己的笔名本来是管弦,但痖弦说小小台湾诗坛已有纪弦和他两根弦了,就不要再多一根弦了。管管说:“姓管很好取名,我给孩子取名‘管领风’,字‘骚之’。我本来还想叫他‘管领风骚’的,管领风骚五百年嘛,哈哈!”而后他又滔滔不绝说起和纪弦的交往。
台湾诗人的朗诵,以余光中和管管最具特色,余光中一口江南口音,音色圆润,每每都是他领读再让听众跟读。“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从早潮到晚潮。”“梦”,他向台下一挥手,众人便齐声道:“也听见”。他又接着念“醒”,下面又和:“也听见”。余光中的节奏较为适中,自缓板到快板不等,而管管的节奏常在快板和急板之间。如果余光中的朗诵是羽扇纶巾地说,管管则是淋漓尽致地唱,常常摆脱诵的框架,禁不住为生命的可爱可敬发出一番浩叹吟咏!余光中温文雅致,一派学人风范,管管插科打诨,犹如闯荡江湖的艺人。刚刚从“战天斗地”的文学走出的我,在管管身上发现了嬉戏兴味,也从他的诗歌表演中悟出了“只有人完全是人时他才游戏,只有他充分享受游戏时他才是个完整的人”这句话的美学意义。
多年后,我還记得管管站在台上,表情恣肆,吐字清晰,动作细腻,依稀老派影星的风范。后来我才知道,他演过30多部影视作品,角色有老僧、匪首和嫖客等。所以,两岸文坛友人都这样说,管管不是诵诗而是演诗。

管管在台北大直的书房。

管管在台北大直的书房。管管水墨作品《秋这浪子》(上)和《影子》。

管管(右)与本文作者合影。
管管是大家族里的独子,母亲32岁才生下他,宠爱非常,穿百家衣(向各家讨布来拼凑成),吃千家奶(找村里哺乳期的女子讨奶吃,一直吃到8岁)。沉溺于宠爱的他还没完全长大,却被抓了壮丁。他永远记得生离死别的一幕,母亲踉跄着小脚跑了20多里来到军营,他安慰母亲说只是去帮军人挑个东西就回家,母亲给了他一个小手帕,里面紧紧包着一块“袁大头”。“这银元我家一共就两个,她心想我可以拿这钱买路回家。”管管说。袁大头早不见了,母亲的形象却不可磨灭,他写了好多首思念父母的诗,感动了音乐家,被谱成歌曲传唱一时。
“故乡是俺心中的坟,里面住着父亲母亲,天天过着寒食、清明,冷雨纷纷。”40年后回到山东老家,亲人对管管说,每逢大年三十全家吃饺子,他娘总要把大门打开,敲着碗,叫着他的小名。管管到台湾后,寄过一封信,这封信家人有没有收到,他不知道,不敢多想,也不愿呼天抢地,只能安慰自己道:“关于家乡,已经是很老很老的古董了!”管管的《荷》被收入台湾中学国文课本,写的正是人世间的沧海桑田之叹。“那里曾经是一湖一湖的泥土。你是指这一地一地的荷花。现在又是一间一间的沼泽了。”一问一答间藏着管管至深的痛。他当兵多年,在海南岛和金门都见到过血与火。他深知历史常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不恭维汉唐盛世,而想活在最古老的年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2011年,我策划了一场海峡两岸跨界诗歌研讨会,会后结集出版了一本《台湾跨界诗歌选》,其中就收入管管的6首画配诗。他交来这样的简介:“管运龙,山东人,青岛人,台北人,1929年生,写诗50岁年,写散文40岁年,画画40岁年,演戏20岁年,诗集散文8本,画展联展6次,演电影20多部。有子女各一,爱吃花生米、鱼、水果、酒,喜欢素食,爱小孩、女人、月亮、春天、山水、树、花草自然,爱稀奇古怪事物,爱京剧、国乐笛琴琵琶;嫉恶如仇,天生善良。出生时有异香是菩萨转世,不太相信,但有慧根。”这简介一如他的诗,色香味俱全;一如他的人,活泼天真。
他的童心一直到90 岁也未消减。他说“把自己写成诗”比写诗更好。他总是纯真美好一如少年,对这世界永远怀有童稚初见的感觉。
大家都说管管的童年比别人长,19岁离家之前都是童年,我觉得他的童心一直到90岁也未消减。他说“把自己写成诗”比写诗更好。他总是纯真美好一如少年,对这世界永远怀有童稚初见的感觉。他说夜是提着小灯笼出来的,说小草有咯吱人的辫梢,说蝴蝶是无根的花……他笔下的春天,有嘴有脸,有手有脚,能飞能看。他说:“春天是坐着花轿来,四个轿夫抬着的大花轿。可以听到鸟们在山林里的唱歌的嘴,看到沾满春雨的翅膀。”
管管能玩出款式不同的成就或者花样;喜欢在一切艺术中把平凡事搞得石破天惊,他像是江湖狂徒,却又能在电影里塑造出一个心如古井的禅师;说他禅心向佛,却又七十生子,每日欢欢喜喜地趴在地上让孩子当马骑;说他是前辈诗家,他又穿起唐装去办童心洋溢的画展;说他是画家,他又有板有眼地唱起《平贵别窑》,那一声“三娘”叫的撕心裂肺;说他是演员,他得的却是金马奖最佳编剧奖……
去年到台湾开诗歌研讨会,我找管管喝酒,年近九十的他,穿着黑色上装水蓝牛仔裤,背不駝腰不弯,细腻而粗犷,心志活泼。餐桌上,他声音最高酒量最大,仰起脖子把53度金门高粱酒一口喝下。我打趣问他:“为什么你说唱戏35年看女人却47年7个月。”他说:“女人难懂,一笑一哭一闹像庐山烟雨浙江潮,所以耐看。儒家总体很棒,缺点就是欺负女性,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我问这句话怎么解释?他说:“女孩子太聪明,心很细,就不大好对付,说她难养,要折腾人,这不对。她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为了她的爱,她当然要多个心眼,她抓着一个男生,就怕这个男生跑,她当然要采取一些手段嘛。”这些地方可以看出管管的细腻。我问他最喜欢哪个女子,他说:“章子怡,那部《我的父亲母亲》真的好,清纯! ”
总忘不了多年前的一幕,我和管管与众多诗人在一起,他朗读自己的诗:“这六十年的岁月么/就换来这一本烂账/嗨!说热闹又他娘的荒唐/说是荒唐,又他妈的辉煌。”洛夫笑着用浓重的衡阳乡音评点:“异数,这就是异数。”管管却笑了:“我就是调皮捣蛋呀!”大家都笑了,在那一刻我没笑,想到他身经战乱,却深爱魏晋那种战乱灌溉出来的奇花;想起他的诗歌《蝶》:“你开在小孩子脸上,你是一朵漂泊的花吗?” 我心中默默祈祷:“管老,愿你生命之花年年盛开永不败!”
原名管运龙,1929年生于山东,诗人、画家、演员。曾任台湾创世纪诗社社长、好时年出版社总编、民众日报出版部总编。著有《管管世纪诗选》《茶禅诗画》等,多次举办画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