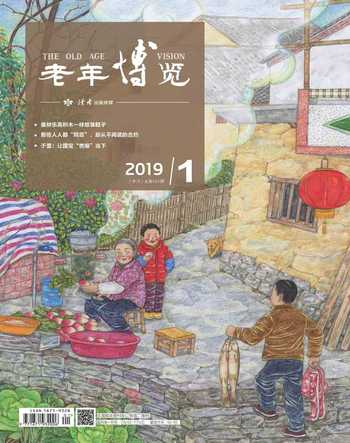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林鸣
高莉
2018年10月24日的伶仃洋上,从太平洋灌入人工岛的海风,吹不散建设者的自豪和喜悦。被英国《卫报》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正式全线贯通。
55公里跨海大桥加6.7公里海底隧道,从动工到通车,总工程师林鸣带领着4000人的铁血军团“9年磨一剑”,终于将这份杰作摆到了世人面前。
今年61岁的林鸣是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在他整整40年的职业生涯中,第一个作品是珠海大桥,第二个是珠海的淇澳大桥,加上这次的港珠澳大桥,他已经“三下珠海”。
虽然建桥林鸣是专家,但隧道工程之前他从未涉足过,可以说是十足的菜鸟,而港珠澳大桥项目中他负责的恰恰是最具挑战性的岛隧项目。
项目一开始,林鸣就把家从北京搬到了珠海,因为工程的建设难度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深埋沉管隧道,由33节沉管对接而成,每节沉管重达8万吨,相当于一艘航空母舰。沉管在海底深处对接,误差只允許有几厘米。
在港珠澳大桥之前,我国的沉管工程加在一起长度不到4公里。当时我们的海底隧道技术,在不少外国专家眼里,“就相当于小学生的水平”。
技不如人,只能四处取经。当时世界上只有两条超过3公里的海底隧道,一个是欧洲的厄勒海峡隧道,还有一个是韩国釜山的巨加跨海大桥。
2006年,林鸣前往韩国釜山,希望学习类似工程的建设经验。然而在林鸣向接待方诚恳地提出能不能到附近去看一看他们的设备时,却被一口回绝。最终,他们只是乘交通船在工程数百米外转了转就悻悻而归。
接下来,林鸣找到了当时世界上海底隧道技术最尖端的一家荷兰公司希望合作,结果人家抛出了天价:1.5亿欧元!当时约合15亿元人民币。谈判过程异常艰难,最后一次谈判时,林鸣提出妥协方案,希望花3亿元人民币换取一个项目框架。
但是荷兰人戏谑地笑说:“我给你们唱首歌,唱首祈祷歌!”一句话,将林鸣团队的尊严碾压殆尽。
跟荷兰方面谈崩了之后,林鸣和他的团队只剩下最后一条路可走:自己攻关!
林鸣坚信:只有走自主研发之路,才能掌握核心技术,攻克这一世界级难题。可在几乎空白的基础上自主研发,林鸣和他的团队面对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外国人都在看:中国工程师到底行不行?当然行!2013年5月1日,历经96小时的连续鏖战,海底隧道的第一节沉管成功安装。没日没夜的论证、成百上千次的试验、一项项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林鸣就这样率领团队“摸着石头过河”,开启了铸就超级跨海通衢的逐梦之路。
组成隧道的3 3节沉管,林鸣给它们一一标上了序号。从E1到E33,每一节都有自己的故事。在林鸣眼里,它们就像他的一个个孩子一样。

沉管的安装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工程。要把这些重达8万吨的大家伙从工厂用船运到施工地点,再精准地沉放到指定位置,并与前面的沉管对接,每一次都需要几百人一起上阵。严苛的外海环境和地质条件,使得施工风险不可预知。每一次安装前离开房间的时候,林鸣都会回头看看,因为每一次出发,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2013年底,在筹备第8个“孩子”—E8沉管安装的关键时刻,林鸣因劳累过度鼻腔大出血,4天内实施了两次全麻手术。醒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沉管安装的准备情况。未等身体恢复,他就又匆匆回到工地,昼夜监控施工全过程。等沉管顺利沉放对接后,林鸣才下船复查。
“工程建设就像走钢丝,每一步都是第一步,每一节都是第一节。”这句话一直深深地烙在林鸣心中。
死神对林鸣的第15个“孩子”—E15—发出了通告。在第15节沉管安装的时候,他们碰到了极其恶劣的海况,珠江口的海浪有1米多高,工人们都被海浪推倒在沉管顶上。
尽管如此,工人们还是护送沉管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坞内。当时起重班长说:“回家了,回家了,终于回家了!”“命”是捡回来了,E15的安装计划却就此搁浅。第二次安装是在2015年大年初六,为了准备这次安装,几百人的团队春节期间一天也没有休息。但是当大家再一次出发时,现场又出现回淤,船队只能再一次撤回。将沉管拖回之后,许多人都哭了。
第三次,团队申请到有关部门的支持,珠江口的采砂企业全部停工,终于顺利完成了安装。
从2013年5月的第一节到2016年10月的最后一节,3年时间,林鸣总算顺利安置好了每一个“孩子”。
10年来,几乎每到关键和危险的时刻,林鸣都会像钉子一样,几小时、十几个小时、几十个小时地“钉”在工地上。体型的变化透露了一切:他瘦了整整40斤。
2017年5月2日日出时分,世界上最大的沉管隧道—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顺利合龙。中国乃至世界的各大媒体都在为这项超级工程的完美落幕欢呼,此时的林鸣却在焦急地等待着最后的偏差测量结果。
偏差16厘米!这对水密工程而言算是成功的。中国的设计师、工程师,以及瑞士、荷兰的顾问,大都认为没问题。
但林鸣说:“不行,重来!”
茫茫大海,暗流汹涌,要把一个已经固定在深海基槽内、重达8万多吨的大家伙重新吊起、重新对接,一旦出现差错,后果不堪设想。“算了吧!”“还是算了吧!”几乎所有人都想说服林鸣罢手。
但林鸣内心有一个声音:如果不调整的话,这会是自己职业生涯和人生中一个永远的缺憾。他把已经买了机票准备回家的外方工程师又“抓”了回来。经过42小时的重调,偏差从16厘米降到了不到2.5毫米。
那一夜,他睡了10多年来的第一个安稳觉。
清晨5时许,林鸣又开始了自己风雨无阻的长跑。从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营地出发,途经淇澳大桥,最后到达伶仃洋上的淇澳岛,来回10多公里。
读大学前,林鸣当过3年农民、4年工人。他曾经在工厂做学徒,拿着锉刀、锯条等练习锉、锯、凿、刨等基本功,学当铆工和起重工,后来才到西安交通大学接受了为期半年的技术培训。
在同行看来,他的动手能力极强。在工地上,他是拿着榔头、扳手等工具给数以千计的工人一个个讲原理、讲方法的。
10多年的时间,林鸣走完了港珠澳大桥这座世界上最长、难度最大的“钢丝”。在他看来,高品质的工程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越是普通人看不到的地方,越要做好。
2017年,团队施工时赶上了超强台风“天鸽”,岛隧桥处在台风的中心位置,却安然无恙,这让大家对桥梁的抗风险能力信心倍增。如今,大桥不仅外表壮美,而且“秀外慧中”。为了避免施工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他们在前期规划的时候,就注意到了附近海域中华白海豚的存在。团队在水上作业的过程中,在白海豚身上也花了很多心思。2010年,这个区域的白海豚大约有1200只,到了2016年竟然翻了一倍。
如今桥通了,林鸣的头发也白了。林鸣觉得,自己最亏欠的是家人。全年无休的工作节奏,让他与家人长期分隔两地,妻子只好在退休后放弃北京的生活,到珠海给他做后盾。
在一次采访中,林鸣曾愧疚地表示,这么多年来一次都没有给儿子开过家长会。好在儿子长大后也加入了他的工程团队。有家人在身边支持,也成了他坚持下来的最大动力。
港珠澳大桥究竟创下多少“世界之最”也许很难说清楚,但有一点可以确信:每一项突破都标志着中国自主创新的远大抱负。林鸣曾说:“从47岁干到61岁,这么一个百年工程能够亲自参与并将它完成,我的一生就值得了。”
(摘自微信公众号“经济之声笑傲江湖”,田龙华荐)